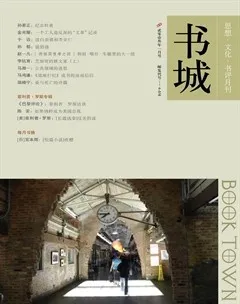昆曲传承与文化创新
2024-01-03郑培凯
郑培凯
昆曲传承与文化创新,说到底,其实是关乎审美情趣、审美境界在表演艺术上的展现,究竟和文化传承与创新有什么关系,又和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有什么关系。这是个大题目,涉及当代中国如何提升审美品位与文化修养,如何利用传统审美资源开创文化复兴之道,不只是限于狭义的“昆曲”表演艺术研究。探讨昆曲的“四功五法”、“原汁原味”、口传心授、雅俗共赏,在在都与非物质文化传承有关,与如何继承与转化传统,以求持续创新与发展有关。
长期以来,我们谈中国文化,往往是从子曰、诗云开始,继之以深入经史子集的探讨,主要都是文献层面的探索与思考。进入二十一世纪,由于科技的发展,与文化阐释的多元化,改变了我们文化研究的思考方向,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考古发现提供的文物实证,二是非物质文化传承展示的审美意识。我们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早期文化的形塑过程,都不是古代文献所提供的史料能够解释清楚的,而近代考古文物的发现,则打开了一片新天地,让我们可以观察到司马迁看不到的材料,重新思考过去文献忽略的上古生活实况。今天家喻户晓的良渚文化、红山文化、三星堆文化,以及学术界高度重视的大汶口文化、陶寺文化、石家河文化、石峁文化、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焦家遗址,等等,完全刷新了我们对中华文明肇始进程的认识,再也不能拘泥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一脉相承的历史观。
更重要的是,近百年来摄影与视像技术的发明与发展,生动记录了人们的生活细节与表演艺术的呈现,使得非物质文化传承成为可以深入探索的研究资料。如何从研究当前非物质文化传承的材料,掌握其发展的历史轨迹,甚至上溯文化传承的进程,则需要在方法学上进行深化,建设可行的理论架构。以昆曲为例,如何理解昆曲的现代舞台表演,在什么程度上可以上溯到乾隆时期的“姑苏风范”,又如何体会与阐释当前的昆曲艺术,与明代万历年间肇始的昆腔水磨调及汤显祖剧作,有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这是文化研究的新领域与新挑战。通过视像记录以及现代影视场记的方式,再由老艺术家现身说法,阐述他们一生学艺的经验与体会,我们希望尽量理解传统表演艺术的传承细节,探视古人追求审美境界的苦心孤诣,以汲取传统审美艺境的资源,作为现代转化与创新的借鉴。戏曲行内人总是念叨“原汁原味”,还流传许多口诀,以师徒手把手口传心授的方式,点传了艺术想象世界的人生体悟,这是我们学术界(也就是行外人)研究昆曲文化必须探究的方向,也必须由此提炼出适当的理论框架。
自古以来,民间文娱形式都通过口传心授,由师傅传授给徒弟,一代一代得以赓续。然而,没有系统化的传承规划,传授方法因人而异,更或许缺乏适当传人,而出现断裂灭绝的情况。有些表演形式虽然精彩万分,博得文人学者的赞扬,撰写诗文记载,但所记多为欣赏角度的印象与感想,对整体技艺的传述比较零碎,同时掺杂了个人的文学想象,无法成为艺术传承的规范性教案,只能留给后人无限的怅惘。以杜甫写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为例,他描绘公孙大娘的剑器舞:“㸌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在安史乱后又看到公孙大娘弟子的表演,虽然觉得传承有序,感慨万分,同时也意识到这门绝技病危,感到“乐极哀来”。他的文化危机感不幸成真,公孙大娘的剑器舞与浑脱舞,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缘,在历史的硝烟中永远消失了。
昆曲演出持续四五百年,口传心授有其严格的规范,又有文化精英从明清以来长期参与昆曲雅化过程,因此传承有序,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可以从中探究传统审美境界追求的历程。有了近代影视记录的丰富材料作为支撑,学术研究更能深入探索,综合中外审美意境,进行创造性转化。
“原汁原味”的昆曲传承计划
这几十年来我做的文化教育工作,最主要是推广对中国文化的认识,通过介绍传统审美的各个领域,引导青年人体会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美好的精华。推展昆曲审美境界就是一大重点,一方面是因为昆曲在表演艺术展现上,达到了中国戏曲艺术的巅峰,展示了高雅的审美情趣;另一方面则因为五四精英批判文化传统的糟粕,采取“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一篙子打翻一船人,铲除传统文化艺术不遗余力,受害最深的便是昆曲,以致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昆曲列入人类口传非物质文化传承时,好几代的中国人连“昆曲”是什么都不知道。推展昆曲在现代学校教育中有重大意义,它促使现在的年轻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昆曲表演艺术上有如此优雅的展现,追求如此美好的审美情境,以去除他们年轻心灵中以为中国传统文化低劣庸俗、难以企及西方艺术的误解。昆曲与各种地方戏不同的特色是,剧本有明清文化精英、文人雅士的参与,文辞十分优美,和《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同属精英文学系统。因此,在大学里教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审美,昆曲也是很好的材料。
进行昆曲教学推广之时,我设计并执行了一个昆曲艺术传承计划。“戏以人传”,戏曲演员的一生就是非物质文化传承的见证。昆曲在舞台上怎样展现,具体的传承,往往集中体现在一些昆曲表演艺术家身上,需要研究者發掘、记录与分析,才能把传承的脉络清楚展现出来。所以,我们申请了各方资金,做了许多的调查研究。调查包括两种,我在《昆曲传承与文化创新》一书中也提到具体执行的方法。一种是邀请资深的昆曲表演艺术家到香港,以优厚礼遇的方式,请他们到大学做客座教授和专门研究员,有了大学教职的名义,他们可以到香港正式工作,而他们的工作就是展现自己的艺术生涯与心得。我们请几位助理给他们做影像和口述记录,还让他们进行示范演出,把主要的昆曲剧目一个个从艺术呈现角度阐释清楚。过去也有不少记录昆曲艺术家的书籍,主要是呈现他们一生的经历,属于传统传记的形式。我们的艺术传承计划,则是记录昆曲传承的轨迹,展示昆曲“四功五法”,在每一出戏的演出中,是如何具体得到艺术阐释的。而这种阐释的传承,又是如何经过“口传心授”,一代一代成为非物质文化传承的。
我们请的这些表演艺术家,当时的平均年龄是七十岁左右,比如江苏省昆的张继青与姚继坤,北昆的侯少奎,浙昆的汪世瑜,以及一大批上海昆剧团昆大班的艺术家,还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一代,前后总有三四十位。我们记录的要点是,他们当年从自己老师那里怎么学艺,一招一式当年老师怎么教的,个人又是怎么体会一出戏的,怎么演的,等等。戏曲表演虽然有程式可寻,但是每个人天生的禀赋都不一样,一个好的艺术家在舞台上要尽其所能发挥自己所长,就不可能与老师一模一样。这里就牵涉到戏曲传承的关键所在,所谓“原汁原味”究竟是什么意思,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称作“原汁原味”,把昆曲艺术传承下来?所以,我一开始就和老一辈的昆曲艺术家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原汁原味是精神上的原汁原味,是艺术展现境界上的原汁原味,不必刻板地一招一式学样。资深的昆曲艺术家在舞台演出五六十年,从翩翩年少唱到古稀之年,其间的唱腔与身段中有没有细微的变化?中国这五六十年社会经过很大的变动,艺术政策的变化会不会影响昆曲在舞台展现上的调整?他们都经过了“文革”改唱样板戏的阶段,这是否影响了昆曲表演的范式?近代电影电视,以及各种舞台剧、音乐剧,成为中国民众普遍接受的文娱形式,是否也影响了戏曲表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是否也被吸收进昆曲表演艺术?这些历史变化其实跟传承发展是有关系的,吸收了之后怎么体会,体会了之后如何去表演,每个人的吸收与体会不同,进而影响个人演出的艺术风格,甚至形成一个个流派。
一般的说法是京戏有流派,而昆曲没有。比如说,老生有谭派,有余派,有马派,旦角有梅派、程派、尚派、荀派,这种现象在昆曲传统中不曾出现。其实,强调流派的出现,只是为了突出某位演员的表演艺术特质,不能说这个流派是某个艺术家独自创立的,与演剧传统无关。京剧这种流派现象的出现,相当程度上是戏迷粉丝追捧偶像所致,是京戏成为流行文化的过程中由粉丝吹捧而成的。所有戏曲艺术表演不可能没有师承,就算没有单独的师承,也是从整个演戏传统中吸收艺术传承,优秀演员会按照自身的禀赋发展出独特的风格,就成了戏迷口口相传的流派。昆曲不是流行文化,昆曲迷一般也不会制造偶像跟风的风潮,只追捧演员甲而吐槽其他演员,赋予自己心仪的演艺风格为艺术流派。其实,昆曲老艺术家们也都各自有其风格,演戏演了一辈子,当然会有自己独到的体会,对艺术的舞台展现有其独特的展演方式。假如我们真要学京剧迷的流派观念,应用到昆曲表演,以个人风格划分昆曲流派的话,则张继青是张派,华文漪是华派,梁谷音是梁派,侯少奎是侯派,汪世瑜是汪派,计镇华是计派,蔡正仁是蔡派,岳美缇是岳派,石小梅是石派,刘异龙是刘派,张世铮是张派……不一而足。说明了什么?其实只是说,老艺术家们都有其自己的演艺风格,流派不流派,是观众粉丝群追捧偶像的话语。
重要的是,我们研究昆曲传承,不要被昆曲有没有流派所惑,而要清楚记录下每一位艺术家独特的表演风格与艺术传承的关系,如何从传承血脉中锻炼出感动观众的表演艺术。资深的艺术家到了一个年纪,回顾自己的演艺生涯,会有自己成长发展的艺术体会,这种体会要传给下一代。我们要记录的是,他教给学生的艺术体会和当年他从老师那里学的有什么不同,什么是原汁原味的传统,什么是他自己独特的阐释,这就是昆曲艺术传承,是真实具体的传承,也是“原汁原味”的真正精神,这样才不会让昆曲抱残守缺。否则完全按照老师怎么动一下,你就跟着动一下,明明知道这个动作不是最适合你个人的,非要削足适履,如此传个几代,完全只是形体与声音的模仿,则昆曲就会“画虎不成反類犬”,成为死的样板传承,那么文化不可能有所创新,也无法好好继承。
我们计划之中,还包括了广泛的调研,是香港大学资助委员会(UGC)提供资金,支持我们去调研国内每一个昆曲团。当时有六大昆班,温州永嘉剧团才刚起步。我们去调查的时候发现,各大昆班所收集的材料和累积的往往只是剪报,而且是以名角为主,也就是注意演出的社会反应与效果,以观众接受为主要考量,而不是从剧团发展、整个戏怎么演入手来储存资料。一出戏的制作,从剧本形成到如何演出的讨论过程,演员如何调配,一次次排演的调整过程,这些资料,无论是文字或影像,基本没有留存,而这些材料其实是很关键的研究资料。现在所有的昆曲演出,在舞台上呈现的版本,都与明清原来剧本的安排不同,都经过了改编调整,演出制作的过程跟排演电影很类似。排演电影的时候有场记,所有的发展过程一步一步,都有很清楚的记录。这与过去戏曲演出的排演方式很不同,过去演出基本不怎么排练,表演者似乎各自为政,但却心有灵犀,上场之前互相交流一下,上场就可以表演,这就导致上一代人过去以后,假如没有留下清楚的记录,后来的研究者不知道怎么下手。
研究昆曲、发展昆曲和表演昆曲,是一项文化的事业,不是一个单纯的娱乐事情,不能从票房的经济观点来看待,这是一个长远而重大的中国文化创新和复兴的事情。它需要不同人共同参与,只要你有心关怀中国文化的复兴,演员、研究者、观众,都有责任担负起时代的使命:演员是内行,科班出身,他们在舞台上天天练功,然后把艺术展现出来;研究者从文献入手,做调查研究,阐释艺术的历史审美的过程,展示昆曲是人类追求美好的艺术想象;观众也很重要,他们能够欣赏昆曲,了解昆曲艺术是中华文明的精粹展现,是中国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会赞扬西方有歌剧与芭蕾的艺术传承,甚至推崇其为西方文明的优秀典范,我们也称颂日本的能剧与歌舞伎,认为日本人善于保护传统。那么,我们怎么可以漠视昆曲传承,不去了解自身优秀的精华传承呢?
我在香港推广昆曲二十多年,深有感触国人对自己文化的隔阂,其中不乏一种“现代化无知的傲慢”,认为昆曲是过时的戏剧演出,又慢又无聊,故事也不接地气。许多人质疑,昆曲太老了,教学生干吗,学生词句都看不懂,我们在香港,又不是在内地,让内地的学者去做就好了。但我们还是做了,有了一些大体上的成绩,另外我个人也花了一些功夫,做了一些昆曲历史文化传承的整个历程的梳理,这次出版的《昆曲传承与文化创新》(文汇出版社2023年),就展示了我推广与研究昆曲的心路历程。
文辞雅化与昆曲水磨调
中国戏曲发生得比较晚,相对来说欧洲的古希腊戏剧发生得很早。古希腊戏剧最辉煌的时候是公元前四五世纪。古希腊演剧是和祭神活动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演的故事都是与神相关的故事,展现的人类处境,反映了在神的操纵之下的一些遭遇。有意思的是,希腊悲剧展现的人生处境,许多都呈现了人有自我意志,不肯听神的话,而那些高居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也不见得都是好的。当神的安排让人进入困境,身处其中的人怎么面对困厄,就显示出宗教性的悲剧反思,因为人再坚强也无法战胜神的操弄。希腊演剧往往都和祭神庆典有关,类似的现象在中国上古的酬神戏中也有,但中国的酬神戏没有人神对抗的故事。中国的神和古希腊以人性为主的神不一样,中国的神一开始是许多自然神,再来有一个模糊的天帝,这个模糊的天帝是会听人的话的,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基本是先民对自然宇宙的崇拜。再来就是我们的祖先认为,祖宗过世也会变成神,它的魂灵会上天,侍奉天帝左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代中国的祭祀都很隆重庄严,不会有人间处境的人神冲突,这和古希腊戏剧的悲剧不太一样。
中国探讨人间处境的戏曲,主要展现的是人伦关系与社会冲突,完整的形式出现得比较晚,要到宋金之后,也就是元朝时风行的北杂剧以及稍晚的南戏文。南戏文受北杂剧的影响,两者一短一长:南戏文很长,可以有四十至六十出,慢慢演绎一种故事;北杂剧是四折,最多加楔子,一个转变。从剧情铺展的情况来看,北杂剧像电影,南戏文像电视剧。我们现在所继承的中国传统戏曲则是南北曲的融合,结构上以南戏文为主。四大南戏(《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文辞比较本色,在文士眼里稍显粗鄙,在明朝时期成为地方戏发展的基础。
到了明朝,南戏的发展出现了两个比较大的分支:一个就是比较民众化的、到处散布的弋阳腔,后来发展成不同地区的不同的腔调、唱法;另外就是海盐腔和昆腔的出现,它们的发展和明朝文人雅士的参与有关,这种雅化的过程就成为昆曲发展的基础。从元末明初的《琵琶记》,到明朝中叶的《浣纱记》和晚明的《牡丹亭》,再到清初的《长生殿》《桃花扇》,剧本的文辞逐渐雅化,再加上音乐的美化,形成现在昆曲舞台上最精彩的演出典范。
我们现在从高明《琵琶记》中,还是可以寻见文辞非常本色的东西,也就是民间戏曲文辞的痕迹,有些唱词虽然情感充沛,却并不文雅,不像文绉绉的雅士写的。《琵琶记》的情节,源自宋元期间广为流传的赵五娘和蔡伯喈的民间故事。故事的原型是:赵五娘的丈夫蔡伯喈进京赶考,中了状元,而妻子赵五娘还在家乡承受灾荒的苦难,一直到公婆都饿死了,蔡伯喈也没回来。民间传说是,蔡伯喈抛弃糟糠之妻,在京城独享荣华富贵,赵五娘背着琵琶进京去找蔡伯喈。蔡伯喈在马路上见到了也不相认,还当场马踏赵五娘,最后惹得老天震怒,雷轰劈死了蔡伯喈。
有意思的是,文人听到这种批判贪享荣华富贵、不顾父母妻子死活之人的故事,心里很不舒服,所以就有许多改编本,一直到高明改编出《琵琶记》,就出现了“全忠全孝蔡伯喈”,因为牛宰相硬要把女儿嫁给他,种种波折使得他不能回家,不是他抛弃糟糠。最后是让社会精英满意的大团圆结局:赵五娘和牛小姐,都跟他一起过上好生活。好像赵五娘吃糠、他的爹娘饿死,都无损于“全忠全孝”。高明改写的《琵琶记》第二十出《五娘吃糠》中的唱段:
[孝顺歌]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嗄住。糠!你遭砻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
从《琵琶记》中的情节与意识形态的冲突,可以看到民间故事戏曲的发展,有其曲折的脉络,最后会变成一个新的故事传统,但转变的痕迹却往往失散了。
昆曲水磨调出现以后,大量文人雅士参与戏曲创作,以配合昆曲美妙的新调。由魏良辅等音乐家发展起来的水磨调,综合了南北曲,打磨出了比海盐腔更为精致婉转的昆曲音乐,成为文人撰写戏曲的唱腔新基础。水磨调风行一时,独占南戏传统的鳌头,由苏州传布到江南各地,再由江南散布到全国,备受上层精英赞誉喜爱。魏良辅创制昆曲水磨调,不是一人之功,而是汇聚了一批音乐家的心血,融合南北曲而成。魏良辅作为昆曲音乐的创新代表,其文化意义绝不亚于欧洲歌剧的莫扎特与威尔第。
晚明文人撰写戏曲剧本,以昆腔水磨调作为演唱模式,是很重要的舞台表演转折。梁辰鱼创作的《浣纱记》,是第一部利用魏良辅新腔的作品,把水磨调的优雅,通过戏剧情节的展现,发挥得淋漓尽致。除了水磨调音乐的优美动听之外,《浣纱记》的文辞隽美,以高雅的文学性配合戏剧人生的生活性,把昆曲推上了中国戏曲舞台的巅峰,成为演艺艺术的模范。
我经常强调,昆曲艺术之所以传承不朽,在于“三结合”的绝对优势。
一是昆曲水磨调是中国戏曲音乐发展的巅峰,它以最精致婉转的调式,展现细腻情感,达到抒情的极致。
二是劇本呈现出的高雅的文学性。文人雅士参与剧本创作,有许多本来不完全是使用昆腔水磨调的作品,也都在长期演艺的实践中,融入了昆曲系统。如大家熟悉的汤显祖,他的剧本原来并非为昆曲所写,而是以南戏系统的海盐腔变种宜黄腔为底,但是南戏基本都是一脉的,所以汤显祖的戏很容易就融入了昆曲系统,以昆曲的方式优美展现。
三是舞台表演(唱曲、身段)经历代演员精工打磨,从舞台演艺的角度呈现了音乐与文化的审美境界。
三者综合,呈现了昆曲丰沛的艺术感染力。
必须澄清的一个概念是,昆曲是百戏之模,不是百戏之祖,也不是百戏之母。上面讲过,昆曲的发展是南戏衍生发展出来的,南戏是祖宗,昆曲不可能变成祖宗的祖,这是一。第二,什么叫“百戏”,中国文化中百戏是有清楚定义的,汉朝壁画汉像砖上,百戏就是各种文娱的表演,吐火、玩球、爬杆、鱼龙曼衍等,这些是“百戏”,自从春秋战国就十分活跃,所以不要混淆,昆曲怎么也不可能变成春秋战国的百戏之母。有的人说,“百戏”是指现在的地方戏,昆曲是现在的百戏之母。我觉得还是不要故意混淆。现在福建流行的梨园戏、高甲戏,是直接从南戏传承过来,和昆曲没有直接关系,也属于地方戏,昆曲凭什么做人家的母亲?我们还是老实点,说昆曲是百戏的模范,大家都可以参考吸收。
从《浣纱记》《牡丹亭》
到《长生殿》《桃花扇》
梁辰鱼的《浣纱记》、汤显祖的《牡丹亭》,到洪昇的《长生殿》及孔尚任的《桃花扇》,都继续发挥文学、音乐与表演艺术结合的艺术追求。其中有文学家、音乐家、舞台表演艺人的合作,才造就昆曲开创艺术新天地的范例,为今天戏曲复兴,以及舞台艺术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梁辰鱼(约1521-1594)《浣纱记》,它是第一部长篇的、以昆曲水磨调为基础、在舞台上演出的戏曲。昆曲的建立和这个剧本有一定关系,梁辰鱼以昆腔创作戏曲,确定了昆曲在戏曲流传中的地位,让昆腔成为舞台表演的主流。
梁辰鱼是一个很好的文学家,《浣纱记》的戏词有许多是非常优美的。比如《浣纱记·寄子》中伍子胥的唱段:
[胜如花](外)清秋路黄叶飞,(同)为甚登山涉水,(贴)只因他义属君臣,(外)反教人分开父子。(贴)又未知何日欢会,(外)料团圆今生已稀,(贴)要重逢他年怎期,(外)浪打东西,似浮萍无蒂。(贴)禁不住数行珠泪,(外:儿吓)羡双双旅雁南归。
这段曲词写得富有诗意。在舞台上怎么用最优美的曲调和动作,表现生离死别的场景,让戏剧情节停顿下来,以诗化的音乐曲词唱出内心深层的情愫,是最能感动人心的。西方歌剧的咏叹调为什么吸引人,在情节进行时突然停顿高歌,使观众感到缠绵惋恻,也是这个道理。
关键是看戏到底是看什么,是看故事,还是看表演?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你假如连戏的故事情节都不知道,这么可能看懂戏曲表演的奥妙?看戏是去看表演的,不单看昆曲如此,看其他戏剧也是如此。《寄子》这一折戏,舞台空静,只有父子俩,演出生离死别,相对凄然,勾起了观众必定要经历的人生历练,感染的强弱就全在表演展示的艺术境界,演员的好坏,也就高下立见。演员唱做俱佳,就带动整个剧场的气场,产生一种很特殊的气氛,让观众一下子就进入他的内心状态,而曲文唱的是他内心的深层感受,文辞美妙才能比较深刻地展现这种感受。
再看《牡丹亭·惊梦》中最有名的一段[皂罗袍]: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杜丽娘小姐游园,丫鬟春香跟着,两人载歌载舞,犹如芭蕾的双人舞(Pas de deux),是有其传承的舞蹈程式,其中的优美舞姿展示了几百年来累积的审美情趣与境界。十六岁的小姐第一次进入大花园,看到断井颓垣之中,满园绽放姹紫嫣红,有一种青春绽放的感觉,同时又感到时光无情、芳华易逝的威胁,展示了春光短暂,生命无常,引发人们生命的感喟。我常以毛笔书法抄写这段曲文,因为它让我想到青春的灿烂与生命的无常,由诗文唱曲激发了写字的灵感,笔下的字迹也比平常写得隽美,这是中国传统审美不同领域的相通之处。
欣赏昆曲是有门槛的,没有入门的人,希望他们可以入门,因为昆曲是很美的东西,年轻人没有机会接触,真是很可惜。有人说,欣赏昆曲很难,很费事,划不来,不如去听流行音乐会。我总是劝告年轻人,世界上一切最精粹、最优美的艺术,都是艺术家呕心沥血的创作,不费点力气,怎么能获得最高级、最美好的人生经验?《诗经》《楚辞》不难吗?莎士比亚不难吗?乔伊斯、艾略特不难吗?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难吗?贝多芬、马勒、肖斯塔科维奇不难吗?你读过索尔·贝娄、大江健三郎、约恩·福瑟吗?看得懂梵高与黄宾虹吗?太难,不好懂,并不是爱好文化的人的借口,还是得花点时间精神,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然,我们推广昆曲,也要想方设法普及,让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到美好的艺术。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崭新的制作,把传统的昆曲表演变得让年轻人容易接受。这是属于艺术接受的范畴,我们研究艺术学、文学批评学,在推广昆曲上,也经常参考文艺接受理论的看法,因为艺术的受众也很重要。
《牡丹亭》是明朝万历年间写的,离明朝覆灭、清朝建立约四十年,反映了晚明文化的开放与蓬勃。清朝康雍乾三代开疆拓土,军事、政治都很强势,却在文学艺术与思想的自由开放方面有所限制,文字狱不说,整理《四库全书》,不但禁毁了政治不正确的书籍,连所有违碍字句都要除掉。然而,文学艺术发展与影响,和政治变化并非同步的,所以一旦有了一个风气传统,就会延续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到康熙的时候,一直到十八世纪乾隆时期还会有很好的作品出现,像洪昇《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曹雪芹的《红楼梦》。所以这个风气是文化的延续,并不会因为政治上大的变动马上停止,可是之后就会慢慢衰微,而《红楼梦》就是晚明开放风气的“天鹅之歌”。
《红楼梦》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你仔细看看红楼梦里面对人生与情欲的探讨,包括二十三回林黛玉听到《牡丹亭》唱词时的那种感动,以及脂砚斋的批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汤显祖对曹雪芹的直接影响。到了乾隆时期,舞台的昆曲演出,逐渐定型,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姑苏风韵,实际是乾隆时期大体上定下来的,这个我们从当時的唱词与舞台演出本(如《缀白裘》)可以窥知消息。
清朝初年,剧本写得好,曲词与曲牌配合得最好的是《长生殿》,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但这不只是一个爱情故事,它还包含着家国危亡、生离死别以及个人遭际之凄凉。一切皆因安禄山造反而天翻地覆,虽然唐朝没有马上灭亡,但整个唐朝跟早先的盛唐是不一样了。这个国破家亡的意思,洪昇借着安史之乱写进去了,《桃花扇》则更直接写了明朝的覆灭。洪昇跟孔尚任都是明亡之后的第二代遗民,是明遗民的后人,从小就见证了明朝的覆灭,对大环境的变化内心有着深刻的触动。所以《长生殿》与《桃花扇》,都着意描绘了家国之变,大时代的沧桑变化,造成男女爱眷的生离死别。《桃花扇》的结尾很突兀,都入道出家去了,个人超脱了世尘,世上的乌七八糟都不管了。我始终觉得这个结尾不是一个好的结尾,可它也和大多数明遗民的现实境遇一样,除了出家与隐居,没有其他更好的结尾。《长生殿》比较不同,《长生殿》的后半部分都是在忏悔,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唐明皇的忏悔,他觉得自己辜负了生死与共的誓言,对不起杨贵妃;第二个是杨贵妃的忏悔,她对不起唐代的江山百姓,因为杨家的奢靡贪腐,完全不管民间疾苦,导致最后安禄山造反,这是杨贵妃一个很深刻的忏悔。可是我们在舞台演出时,一般不太展现《长生殿》的后半部分,只强调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与生离死别。或许是因为原剧太长也太复杂,这两条线索很难编成顺当的故事情节。我希望将来的改编剧本,可以像大家逐渐接受《牡丹亭》后半部分情节一样,想个方式呈现《长生殿》关于忏情与救赎的部分。
《长生殿》舞台演出最感人的有两段,一段是唐明皇唱他自己对不起杨贵妃的悔恨。马嵬兵变之时,御林军不杀杨贵妃就不肯保驾,逼得唐明皇放弃了杨贵妃,让一代倾国倾城的美人死在佛堂。唐明皇说了当时兵荒马乱的情况:
[叨叨令]不催他车儿马儿,一谜家延延挨挨的望;硬执着言儿语儿,一会里喧喧腾腾的谤;更排些戈儿戟儿,不哄中重重叠叠的上;生逼个身儿命儿,一霎时惊惊惶惶的丧。[哭科]兀的不痛杀人也么哥,兀的不痛杀人也么哥!闪的我形儿影儿,这一个孤孤凄凄的样。
这段唱词很有意思,它有民间说唱的意味,但又不是简单的民间文学,倒有模拟元曲文辞的意味,叫李渔来评论,就是典型的“本色”了。唐明皇事后忏悔,觉得是自己懦弱,没有承担起作为丈夫的责任,违背了与杨贵妃当年向天盟誓的永不分离的诺言:
[叹科]咳,想起我妃子呵,
[正宫端正好]是寡人昧了他誓盟深,负了他恩情广,生拆开比翼鸾凰。说甚么生生世世无抛漾,早不道半路里遭魔障。(《长生殿·哭像》)
《长生殿》另外一段《弹词》,像是故事情节中插进去的楔子,由李龟年来总结大唐盛世衰落的整个过程,从杨贵妃入宫,两人如何恩爱,到安禄山造反,贵妃死后的凄凉,写出了帝国的衰败,也道出他晚年流亡江南的凄凉:
不堤防余年值乱离,逼拶得歧路遭穷败。受奔波风尘颜面黑,叹衰残霜雪鬓须白。今日个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揣羞脸上长街,又过短街。那里是高渐离击筑悲歌,倒做了伍子胥吹箫也那乞丐。(《长生殿·弹词》)
由昆曲艺术家计镇华以老生的宽亮声调开唱,一人连唱九转,从娘娘入宫的奢华与唐明皇柔情蜜意的爱怜,唱到安禄山造反,马嵬兵变的仓皇纷乱,到贵妃死得凄凉,整个舞台完全被他抑扬顿挫的气势所笼罩,可以看到昆曲表演艺术的极致。
《弹词》这段来源是杜甫的诗《江南逢李龟年》,写他流落江南(今湖南),碰到了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开元天宝当年是多么辉煌,现在呢?“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不知道历史背景,你以为在江南欣赏好美的风景,其实写的是安禄山事变之后,长安沦落,大唐崩溃。杜甫亲历安史之乱,唐明皇逃到蜀地,杜甫的人生开始沦落,最后流亡到湖南,见到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李龟年,不久杜甫就死在了這里。读诗可以有各种各样解释,诗无达诂,了解历史后再读这首诗,杜甫写这首诗的真实处境,与洪昇转用这段故实的寓意,会让你更深体会洪昇意喻国破家亡的感受。
从“花雅有别”到昆曲复兴
乾隆时,戏曲有花雅两部之别。雅部指昆曲;花部则指昆曲以外之曲,例如京腔、秦腔等。《燕兰小谱》(乾隆五十年刊)之例言解之曰:“元时院本,凡旦色之涂抹科诨取妍者为花,不傅粉而工歌唱者为正,即唐雅乐部之意也。今以弋腔、梆子等,曰花部;昆腔曰雅部。使彼此擅长,各不相掩。”(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第四篇)这里引出的消息是,花部与雅部同时并存,“各不相掩”,即使是“相争”,也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的现象。
学者常讲近世有“花雅之争”。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下)中提到:康熙末至乾隆中叶(1700-1774),乱弹勃兴。乾隆末至道光末(1775-1850),花雅争胜,乱弹取得绝对优势,地方戏繁荣。乱弹时期,“梆子、皮黄两大声腔剧种在戏曲舞台上取代了昆山腔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从而使戏曲艺术更加群众化,更加丰富多彩”。这是早期的《中国戏曲通史》,写得很不恰当,资料有限、观念有限,我不太赞成它的说法。
我认为,花雅有别,并不是说在历史进程中,花部要打倒雅部,取得胜利。乾隆至道光末地方戏繁荣,昆曲也还很蓬勃,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不同社会阶层各有所好,两者并不冲突,也不能简单归结为一方起来,另一方必然没落。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有这样的叙述:“乾隆末年,昆剧在南方虽仍占优势,但在北方却不得不让位给后来兴起的声腔剧种。”同书还说:“嘉庆末年,北京已无纯昆腔的戏班。”认为乾隆之后昆曲没落,当皮黄戏曲在舞台上取代昆山腔以后,戏曲艺术就群众化了。表演艺术的发展,群众化就是好吗?艺术不是这样讲的,多元才是好,没有说群众普及了,高雅消失了才是好,这种艺术一刀切的观点是不太恰当的。
朱家溍以故宫的升平署档案,归纳出清宫演戏的具体情况,并从演出材料中看到昆曲、弋腔与乱弹(以京戏为主)的互动、消长与演变的关系。他写过《清代内廷演戏情况杂谈》《升平署时代昆腔弋腔乱弹的盛衰考》《清代乱弹戏在宫中发展的史料》《升平署的最后一次承应戏》《〈万寿图〉中的戏曲表演写实》等文章,提出了确凿的证据,驳斥了过去以为昆曲在乾隆以后就没落的说法。
朱家溍根据升平署的档案资料,明确展示:“同治二年至五年,由升平署批准成立,在北京演唱的戏班共有十七个,其中有八个纯昆腔班、两个昆弋班、两个秦腔班、两个琴腔班(其中包括四喜班)、三个未注明某种腔的班(其中包括三庆班)。各领班人所具甘结都完整存在。说明到同治年间,昆腔班仍占多数。光绪三年,各班领班人所具甘结也都存在。当时北京共有十三个戏班,其中有五个纯昆腔班,比同治年减少一些,但占总数三分之一强。”
所以真正昆曲、弋腔出现大的变化,要到清末民初。光绪的时候昆腔在北京还是主要的。光绪之后,宫廷喜欢京戏,昆曲逐渐没落。民国以来特别在五四之后,是中国传统戏曲整体走向没落的时刻,新式精英是鄙视传统戏曲的。只在民间还保留一些地方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文娱还以戏曲为主,但是昆曲丧失了新式文化精英的支持,逐渐式微。这种状况持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昆曲开始纳入国家系统,一些戏班建立了,戏曲学校成立了,历经沧桑的昆曲艺人才活了下来。
改革开放以后,昆曲舞台演出令港台惊艳,可是改革开放对于戏曲团体刺激也很大,社会变化太大,许多演员离开了经济条件不好的戏班。
迈入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的复兴带来了昆曲的振兴。二○○一年五月十八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正式宣布十九项“人类口传非实物文化传承”,把昆曲列在第一项。这件事我印象很深,当时我在香港教书,推展昆曲,报社总编打电话来问昆曲是什么,可不可以写整篇介绍,可见当时社会对昆曲几乎完全不认识,连报社总编都不知道如何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大决定。还好自此之后,全世界对于非物质文化传承分外重视维护,包括中国的昆曲、古琴等,这个风气从二十一世纪初一直延续到今天,倒也令人宽慰。二○○四年,由白先勇策划和制作了青春版《牡丹亭》,我有幸和二十几位朋友参与制作过程,在短时间内演出近百场,迄今已演了两百多场,大获成功,掀起了一股“昆曲热”。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我认为,昆曲能发展到今天真的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奇迹,它是舞台艺术死里逃生的特例,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传承的绝佳范例。
昆曲活下来了,并获得重视,是中国文化复兴的见证,也展示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中华古文明得以延续,文化传统历劫重生,再度崛起,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突出的现象。昆曲作为传统文化审美的典范,是值得珍惜的。
审美境界是文明追求的极致。在上古文明中,古希腊、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都基本没有了,印度还有一些东西,其他都很难。所以我觉得审美境界和昆曲的关系这是一件大事,有助于中华文明的创新。我们能尽多少力,应该就多做一些。
本文系作者在新华·知本读书会第九十二期所做演讲,刊发前经作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