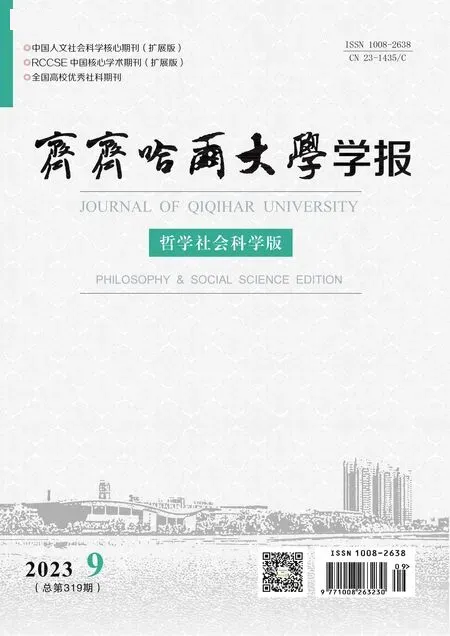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可接受性及其提升
2024-01-03林建辉
林建辉
(闽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就是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语言表达。话语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无论是以理服人还是以情感人,都离不开话语的内在影响力。“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同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可能因为不同的话语表达而产生截然不同的说服教育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通过恰当的话语来实现说服教育目标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习近平强调:“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1]思想政治教育者要讲好道理,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和实效性,必须高度重视并着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可接受性。
一、话语对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具有直接影响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必须通过一定的话语沟通来实现信息传递和思想交流,其中,教育者的话语处于主导地位。教育者的话语能力和话语状况对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具有直接影响。若没有恰当的话语表达,再有说服力的思想或道理也会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有些教育者的理论水平并不低,但不善于或不愿意根据教育对象和具体场景,对思想政治教育文本中大量的理论话语、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等进行必要的阐释性转换和创造性表达,存在着话语晦涩难懂、刻板老套、虚浮空洞、言不及义等问题,容易导致有理说不清、说了没人听,或者受教育者听了不理解、听了不相信等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在群众思想政治工作中,也有些领导干部话语能力不足,与不同群体的人们说话时,存在着说不上去、说不下去、说不进去、给顶了回去等种种尴尬现象。对此,习近平曾经指出:“很多场合,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失语状态,怎么能使群众信服呢?”[2]419除了口头话语,书面话语也有不少问题。有学者指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报刊、网络上,不少文章充斥着大话、套话、空话、废话,表态式、口号式、堆砌式的话语屡见不鲜,缺少有思想深度的解读和深入浅出的阐释。[3]231-232当然,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诸多话语问题,既与部分教育者的话语能力不足有关,也与党内外存在的某些学风文风不正现象有关。
对思想政治教育者来说,话语能力是其主体说服力的重要来源。亚里士多德指出,演说者仅仅掌握演说内容是不够的,还必须懂得如何更好将演说内容表述出来,以便“使得演说显示出某种性质的特点”。[4]161如果教育者话语能力欠缺、话语水平不高、话语方式失当,势必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有学者指出,“部分教育者将教育内容变成‘假大空’的‘套话’和‘官话’”,这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缺乏足够说服力的重要原因。[5]因此,看似寻常的话语表达绝非无足轻重的小事情,而是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乃至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大问题。
在当今新媒体时代,多样化的信息和个性化的表达层出不穷,人们的话语习惯和接受特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思想政治教育中某些陈旧刻板的话语方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由此带来的话语不适应和沟通低成效问题亟待破解。教育者应当创新话语理念、优化话语表达,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可接受性,让受教育者愿意听、喜欢听、听得懂、听得进,这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的必要条件。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可接受性的基本要求
话语是人们沟通交流的基本手段,不同的话语主体、话语目标和话语情境会产生不同的话语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从本质上讲是面向大众的一种公共性话语、价值性话语和说服性话语。与单纯作为信息传播手段的一般性话语或工具性话语相比,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对可接受性的要求更为突出。早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毛泽东就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教授法,其中第4条到第7条分别是“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6]104这四大方法都直接涉及话语表达,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可接受性的一贯重视。
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而言,话语的可接受性就是教育者的语言表达在内容、方式、风格等方面具有易于被受教育者理解、认同和接受的内在属性。具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可接受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话语要言之有物。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旨在影响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它不同于一般的交际性话语、工具性话语,必须表达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主导意识形态。换句话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必须包含科学的、先进的、丰富的思想内容,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时代性、主导性,切忌空话套话、言之无物。否则,不但无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而且容易损害思想政治教育声誉。毛泽东在著名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就将“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和“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列为党八股“八大罪状”的头两条,主张“禁绝一切空话”,并强调共产党是靠真理、实事求是和科学吃饭的。[7]833-836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无论写文章、作报告还是授课、演说等,都要做到言之有物,力戒空洞无物。当然,言之有物同时也必然要求言之有理,即话语要符合认知规律和语言逻辑,能够科学地阐明或揭示蕴含着规律性认识的道理学理哲理,从而给受教育者以深刻的思想启迪和有效的价值引领。
第二,话语要平易近人。教育者说话的态度、语气等往往给受教育者留下第一印象,并影响后续对话效果。教育者的权威性固然是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的必要条件,但这并不等于教育者要板着面孔、说着狠话来显示自己的威严。思想政治教育讲究以说服教育为原则方法让受教育者信服,这恰恰需要教育者有鼓舞人心、温暖人心的话语亲和力,而不是要让人敬而远之。温和、真诚、朴实的话语能够让人感到亲切可信,减少沟通障碍。有调查显示,“态度和蔼、平易近人”是最受大学生欢迎的高校教师品质之一,仅次于“知识渊博、治学严谨”。[8]53-57教育者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能够增添其人格魅力,从而产生“亲其师、信其道”的亲和力和说服力。话语的平易近人,往往体现着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尊重和关爱,这也可以为双方的和谐沟通奠定基础,从而有助于达成思想共识。
第三,话语要通俗易懂。话语通俗易懂,受教育者才能听得明白、易于理解,这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的充分实现。列宁曾经提出一个简明的等式——“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9]468以此强调通俗化表达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大意义。从文本形态来讲,各种马克思主义典籍浩如烟海,许多还是晦涩难啃的大部头,但从理论内涵来讲,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则是融会贯通、一脉相承的,可以通过恰当的概括和阐释变成通俗易懂的原理、道理。比如,毛泽东用“造反有理”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用“实事求是”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就是采用中国式语言通俗而又精辟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者就应当深入浅出地做好这种概括和阐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简单质朴的语言讲清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白”,[10]让科学理论能够从浩瀚典籍中“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广大民众充分理解、掌握和运用的强大思想武器。当然,对不同受教育者来说,通俗易懂的标准并不一样。对文化程度或认知水平不高的人,要多讲一些朴素直白的生活话语,对文化程度或认知水平较高的人,可以多讲一些深刻隽永的理论话语。
第四,话语要准确可信。话语是思想内容的语言呈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准确性、可信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真理性、真实性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者应有的实事求是精神和科学严谨态度的重要体现。教育者在阐释基本理论、剖析思想观点、解读方针政策、援引论据资料等各个方面,都要力求语言表达的准确性,杜绝言不及义、言过其实、含糊其词的话语。特别是在涉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或关键信息,比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断、法律规章及方针政策的具体条文、重要人物事件及相关数据信息时,语言表述一定要真实准确,使之符合原意和事实(对某些次要信息可以适当淡化或回避,但决不能故意歪曲、改变或忽略重要信息),否则会引起受教育者的误解或质疑。如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经常出现差错或漏洞,必将削弱教育者和教育内容的说服力。
第五,话语要形象生动。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话语(也包括内容)枯燥乏味是最常见的弊病之一,某些教育者的讲课或报告也因此被听众戏称为“催眠曲”。形象生动的话语有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和感染力,也有助于受教育者更好地理解和记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和实效性。教育者要善于结合历史典故、现实事例、名言佳句等资料,并吸收借鉴人民群众以及其他学科的话语智慧和话语经验,增强话语的形象性、生动性。比如,讲故事就是很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一种话语方式。习近平指出:“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传承革命精神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要把先辈们的英雄故事讲给大家听,讲给青年一代听”。[11]当然,形象生动不等于戏说搞笑或粗陋庸俗,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政治性、学理性、规范性等鲜明特征,追求话语的形象生动不能以偏离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属性和目标要求为代价。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可接受性的提升之道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可接受性,必须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规律和受教育者话语接受特点,坚持理论与话语相促进、语言与非语言相配合,从不同层面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创造性表达。
第一,要坚持对思想政治教育核心话语体系的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事业最鲜亮的底色。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内涵丰富,其中最根本的核心话语体系,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核心话语体系。与其他话语体系和话语形式相比,马克思主义核心话语体系具有本源性和稳定性,体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本质属性和战略方向。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定的规律和逻辑,对待马克思主义核心话语体系,应当坚持守正和创新的辩证统一。一方面,“老祖宗不能丢”。比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理想,以及人民立场、实践观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核心话语及其理念,要经常讲反复讲,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不能轻易改变或放弃,否则,我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变色、变质。另一方面,要讲出新话语。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当社会生活发生变化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及其话语表达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核心话语体系的说服力和生命力,就在于“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2]121从根本上说,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13]并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互动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核心话语体系。比如,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创新性话语,就充分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和发展,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既是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核心话语体系守正创新的现实需要。
第二,要善于对各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式进行合理转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具体形式丰富多彩。从话语场域来看,有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宣传话语、教学话语、生活话语等;从话语载体来看,有文件话语、教材话语、网络话语等;从话语来源来看,有官方话语、民间话语或大众话语等;从话语主题来看,有革命话语、斗争话语、改革话语、发展话语等;从话语功能来看,有说理话语、叙事话语、对话话语、协商话语、抒情话语等。各种话语形式各具特色,并在不同场合或条件下发挥独特作用。当然,它们之间也存在交叠,并且相互影响和融通。在多数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需要综合运用不同的话语形式,以增强话语效能。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运用方面仍然存在着两个极端。一是过度照搬政治话语、文件话语、宣传话语等,导致整体话语风格比较单调乏味,现实性、生动性、趣味性不足,话语的可接受性不高;二是过度采用生活话语、网络话语、民间话语等,导致整体话语风格比较主观随意,政治性、权威性、严肃性不足,话语的思想政治教育属性不强。其中,第一个问题相对普遍和突出,需要重点解决,第二个问题也不能忽视。总体而言,教育者要在学深悟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借鉴各种话语资源,尤其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少生搬硬套,多活学活用,不断提高话语感悟、话语表达、话语转化和话语创新能力;要善于根据不同的对象、场合和情境,灵活运用不同话语形式,比如用适当的生活话语、大众话语、学术话语、网络话语、叙事话语等来转化或对接政治话语、官方话语、文件话语、教材话语、说理话语等,让整体话语(并非每一句话语)兼具政治性、规范性、学理性、现实性、生动性、趣味性等,便于受教育者理解和接受,从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说服力的通达和实现程度。当然,话语转化只是话语创新的途径之一,从根本上讲,各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式也都需要不断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实际上,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善于运用各种话语资源进行话语创新,都有很多既深刻有力又生动活泼的话语表达,这也给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话语创新提供了典型示范。
第三,要注重语言与思想、情感、作风等其他因素的有效配合。完整意义上的话语是语言和思想、情感、作风等其他人格化因素的结合体。重视语言表达,并不等于可以忽视其他因素。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是辩论赛,更不是脱口秀,如果没有深刻的思想、真挚的情感、优良的作风、恰当的方法等,单靠雄辩或生动的语言只能产生一时的、表面的吸引力,并不能产生持久的、强大的说服力。正如卢梭所言:“如果你不能使我信服,即使把我说得哑口无言,又有什么用呢?我的自发的情感始终要驳斥你”。[14]449因此,教育者要提高话语说服力,除了学习和掌握一定的语言表达技巧之外,更要注意加强理论学习和道德修养,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只有理论功底扎实、知识积累厚实,语言表达才能言之有物、深入浅出;只有坚持以德立身、以身作则,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话、写文章人们才愿意听、愿意看、愿意信。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经常给延安各个院校的学员们讲课、作报告,即便是常人感到抽象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也能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大受学员们欢迎并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学员们反映:“毛主席的话,讲到我们心窝里去了”;“他的语言、思想、风采,像阳光沐浴着我们”;“听毛泽东讲课是一种精神享受”。[15]毛泽东的精彩语言和强大说服力的背后,是他对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深刻理解以及自身的超凡人格魅力。比如,为了给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前后花了几个月时间专门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后来成为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主要内容;为了准备某个专题的讲课,他往往先用一段时间认真搜集材料、研读著作、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然后集中几天几夜时间写成提纲(讲义)。正因为毛泽东有深入研究和精心准备,讲课时才能够得心应手,充分展现出理论和语言的魅力,进而产生强大的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
第四,要重视讲好中国故事。讲故事是思想文化传播中最生动有效的话语方式之一。相对于抽象的理论、概念和道理,人们更容易被鲜活的事例和语言所吸引。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大多数人也从小就喜欢听故事。好的故事既形象生动,又蕴含道理,能够有效地吸引受众、启迪思想。在中外思想文化史上,讲故事是深受重视的传播策略和教育方法之一。从我国的先秦诸子到毛泽东、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到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再到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桑德尔,无不善于通过讲故事来阐明道理、推动工作。正如英国学者卡拉瑟斯所言,“历史上最有说服力的人物都是讲故事的高手”。[16]9我国5000多年灿烂辉煌的文明史、180多年跌宕起伏的近现代史、70多年翻天覆地的新中国史、40多年高歌猛进的改革开放史,以及最近10年来伟大变革的新时代,构成了中华民族延绵不绝的历史坐标,也孕育了不胜枚举的中国故事。当前,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讲好中国故事不仅具有丰厚的实践基础和素材资源,更成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使命。[17]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也强调:“会讲故事、讲好故事十分重要,思政课就要讲好中华民族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改革开放的故事,特别是要讲好新时代的故事。”[18]31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要重视教育与叙事的有机结合,通过精心筛选、组织和讲述,把真实、具体、精彩、凝练的中国故事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这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的重要途径。以中国故事为媒介构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互传互动的话语平台,可以促进话语内容的具象化、话语方式的感性化、话语主体的交互化,激发受教育者的思想共鸣,增强受教育者对所学理论的兴趣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