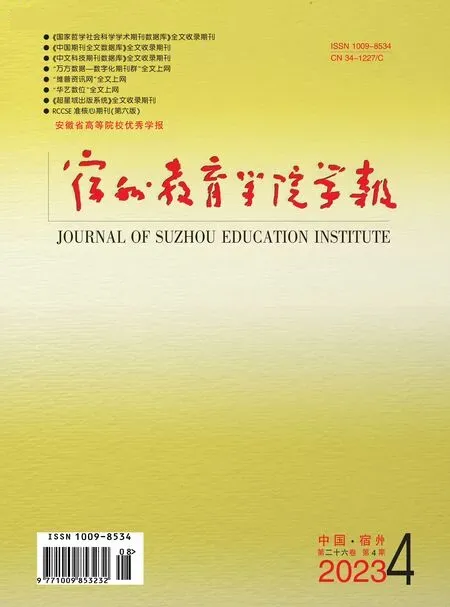试论汉代民间信仰的实用性特点
2024-01-02李承柳
李承柳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长春 130000)
有汉一代, 社会弥漫着浓厚的神祇崇拜之风,受等级观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等限制,阶层间的信仰也各有不同。 民间信仰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现了当时乡村民众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变化,表现出独有的特点。 早在先秦,受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双重威胁的民众便产生了对神灵的信仰和崇拜,此时的神灵还具有明显的原始特征。 伴随着生活领域的扩大和接触事物的增多,基于个体小农特性的两汉民众在传承先秦民间信仰的基础上也逐渐形成了多神崇拜。 民众对各方神灵报以精神上的崇信,无非是希望借助其神力以祈福禳灾、趋利避害,从而解决现实中所遇到的困境和问题,民众对神灵的崇信主要是从自身或与其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性出发。 而随时代发展,民众与神灵间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在对神灵的崇信祭拜中,人的意义及其功利目的不断凸显,使民间信仰表现出实用性的特点。
一、从虔诚崇拜到制而用之
我国民间信仰的发源甚早,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其表现出的形式和内涵也有所差异。 相较于处在民间信仰萌芽阶段的人们,两汉民众的认知和生产水平均有了质的发展,其对各方神灵信仰的特点也产生了从恐惧、依赖到理解、利用的实用性转向。
在史前时代,生产力低下,生存环境恶劣,人们受自身赖以生存又变化多端的大自然影响很深。 大自然丰富的资源给人们提供各种必需的生活资料,如“今夫山,一拳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 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1];同时其莫测突发的灾祸也会对民众的生存造成威胁,出现“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2]等情况。 民众面对大自然“恩赐者”和“压迫者”的双重身份,便产生了对其依赖和恐惧的心理。 无法抵御的自然灾害及无从理解的自然现象也令时人对这些神秘的异己力量萌生出歪曲幻想和敬畏之情,由此产生了“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
人们把与自身生存密切相关的日月、 山川、雷电、水火等自然现象都当作信奉崇拜的对象,认为其背后皆有神灵主宰, 且他们的形象具象而简单,原始特征明显。 人们见天则拜天,遇山则叩山,采用直接祭拜自然物或自然现象本身的方式以表达对其虔诚的崇拜。 他们会因山川之中的资源而充满感激;会因雷电之后的巨响而产生恐惧;会因鱼蛙自身的繁衍能力而报以向往……受到认知能力的限制和朴素思维的影响,此时自然界的价值远高于民众的自我价值。 人们臣服于自然的权威之下,虔敬地祈求能够持续得到各方神灵的恩赐来满足自身生存的基本所需,且永远免遭灾难,还未产生对崇信对象进行实际利用以讲求信仰实用性的期待。
史前时代的自然崇拜和神灵观念到汉代依然存在,然而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民众对其所信奉神灵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 人们摒弃盲目崇拜而运用理性思考,逐渐意识到大自然的运行规律。 一些神灵的自然属性不断减弱,社会属性却持续增强, 其原始神秘的外衣随之褪去,开始有人提出神依靠人而存在的观念:“夫民,神之主也”[3]。 加之民众多元细致化的需求,他们的崇拜对象不再专一,各方神灵被制而用之,以满足其实际要求和愿望,多神崇拜现象随即产生,民间信仰的实用主义色彩也愈加显著。
二、信仰对象的实用性
(一)民众对信仰对象的选择
汉代民间信仰的神祇众多,且功能不一。 与主要关注统治者及国家前途命运的官方祭拜不同的是,民间信仰并不以“礼”为特点,而更加注重信仰的实用性,在乎的是较为个人化的利益。 其信仰的对象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产物,都是像门神、灶神、行神等与其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众“小神”。 《白虎通·五祀》写道:“人之所处出入,所饮食,故为神而祭之”。 人们信奉神灵的目的也从不同方面体现出实用性的要求,皆是围绕自己而产生的对健康长寿、福佑子孙、驱病避灾、尊荣富贵等渴望。
随着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世袭制的瓦解以及生产力等方面的发展进步,各种神灵的地位和职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尽管统治者仍把持着对名山大川、日月星辰等一些重大神祇体系的祭祀权,但普通民众的神灵信仰范围和祭祀权也在逐渐扩大。 加上“祭不越望”以及“神不歆非类”而不可淫祀等要求,久之,百姓对离其日常生活遥远的各方神灵实则也并不关心。
百姓实际生活中所信奉的神祇鬼怪们,要么能威胁其生活与生存,是其畏惧的对象;要么能为他们禳灾祈福,对他们有实用价值。 如人们祭祀门神的目的是“禳除凶灾,御止疫鬼,勿使复入”[4],主要是为了驱鬼避灾与迎福纳祥。 所以 《淮南子·时则训》有云:“孟秋之月……其祀门,祭先肝。 ”[5]119在当时可称为“仙灵之最”的异域神西王母,也成为两汉民众崇奉的吉神,人们为了满足自己长寿和升仙的欲望而虔诚拜祭,期冀能得到传说中其掌管的不死之药。 汉代铜镜铭文中便经常提及西王母,并将其与长寿、福佑子孙等相联系。 如:“尚方作竟,明如日月不已。 寿如东王公、西王母、长宜子孙,位至三公,君宜高官。 (《古镜图录》卷中)”[6]另外,具有司察人过职能的灶神更是常驻各家,监视着每个家庭,并定期归天向上陈禀入住之家的善恶功过。 《太平御览》引《淮南万毕术》称“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上天以此作为予以福祸灾祥的具体判断标准, 决定着每个家庭的命运。 因此灶神是不能得罪的,当时的百姓对其敬畏有加, 乞求其对上天多言好事而降福于人。 如《论语·八佾》言:“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 ’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7]也可见得民间对灶神信奉的普遍性。
由上可知,汉代的普通民众在其信仰受到当时的等级、阶层、祭拜传统等限制之后,需要考虑和关心的,不过是目光所及的实际生活,所以人们对其信仰对象的选择上目的明确,功利性强,一切讲究实用。
(二)民众对信仰对象的创造和取舍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以及民众自我意识的增强, 人们的需求和欲望也在不断地扩张,加之每个神灵的职能范围有限,原有的神灵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各方面要求,所以人们又依需创造出了许多新神,并在多个角度对其提出了实用和功利的要求。
受等级等因素的影响,百姓与那些主管江山社稷、 国家命运的高地位神灵间的联系逐渐减少,只是着眼于日常生活,对其信仰对象进行选择,只要其能发挥灵验效用以满足人们现实中的愿望,就可能成为人们祭拜的对象。 无论何方神圣,灵验就有人叩头;不管神祇大小,实用便有人烧香。 如《风俗通义·怪神》有载鲍君神之事:“汝南鮦阳,有于田得麏者,其主未敢取也。 商车十馀乘,经泽中行,望见此麏著绳,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鲍鱼置其处。 有顷其主往,不见所得麏,反见鲍鱼,泽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为神。 转相告语。 治病求福,多有效验。因为起祀舍,众巫数十,帷帐钟鼓。方数百里,皆来祷祀,号鲍君神。 ”[8]403由此,一只普通鲍鱼便也阴差阳错的被供奉为一方神灵,尤其在有人祭拜确得福报后,便更使人趋之若鹜。 可见当时的人们会站在一个功利的角度将所信仰的客体神灵化,主观上认为这些客体具备着超过常人的神力,并能利用这些力量给人以好运。
与此同时,人们的信仰对象随着时代发展其世俗化、人格化特征也不断加强。 各方神灵不再只是高居于神坛之上, 他们同样具备了不少世俗人性,反而更像是百姓的邻里朋友,逐渐成为人们实际生活中的一部分。 人们对于神也不再是单向的绝对崇拜,在二者的交互中拿到了一些主动权,进而对神提出了诸多要求以及评判准则。 东汉术士费长房“能医疗众病,鞭笞百鬼,及驱使社公”[9]4037,可见在此时,一度“不能得罪”的社神也成了可为人所调遣的对象。 一些神灵若犯错或未能起到令人满意的作用,甚至有可能受到惩罚。 如对于当时主管降雨的神灵龙王,人们平日会通过设置土龙以及各种舞龙仪式希望能将其感动, 以达到降雨消除旱灾的目的,然而一旦祈雨无效,人们便会采取暴龙的惨烈方式以示惩罚。 而且祈雨所用的土龙只在祭祀过程中才持有神物身份,仪式结束后不过只是待弃的泥土草芥。 《淮南子·齐俗训》载:“刍狗土龙之始成,文以青黄,绢以绮绣,缠以朱丝,尸祝袀袨,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后,则壤土草芥而已。”[5]205形象地反映出时人实用主义的祭神观念,同时也可见人神间关系的逐步变化。
而那些灵验不再或已失去实用价值的神灵,更是会遭到唾弃并逐步被人们所淘汰。 如《风神通义·怪神》中的李君神:“汝南南顿张助,于田中种禾,见李核,意欲持去。 顾见空桑中有土,因植种,以馀浆灌溉。 后人见桑中反复生李,转相告语。 有病目痛者,息阴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谢以一豚。 目痛小疾,亦行自愈。 众犬吠声。 因盲者得视,远近翕赫其下,车骑常数千百,酒肉滂沱。 间一岁馀,张助远出来还, 见之惊云:‘此有何神, 乃我所种耳’。 因就斫之。 ”[8]405在李君神的真实面目被揭穿之后,民众对其态度迅速转变,其神灵特性也随之消散。
可见,时代的不断前进引起人们需求的日益增长,同样推动着其信仰的持续变迁,对于生活在帝国统治下受到各种约束限制的民间百姓,他们一方面会根据自己的实际要求,创造出职司该领域的新神祇,以期解决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同时也会淘汰一些对他们用途不大的神灵,由对神灵的绝对仰视转变为与之对等交易。 而这一切皆是从个人功利性目的出发, 以神祇的实用性作为核心的判断原则。
三、祭祀中的实用主义
随着人们崇拜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活跃在民间的神灵也愈发增多, 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对所信仰的各方神灵进行合理有效的祭祀也是民众生活不可缺少的活动。 同时,人神关系的微妙变化也使得祭祀活动逐渐趋于实用化、功利化和娱乐化。
(一)宗族内部祭祀
两汉社会浸润在儒家统治思想之下,家族的地位在社会组织结构中得以凸显,人们的宗族意识不断增强,宗亲关系持续拉近。 除了一些人们普遍信仰和个体依需所独奉的神灵之外,以孝为核心的祖先神祭祀成为民众信仰的重要内容。 所谓“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 依据《四民月令》的记载,宗族内一年中会有很多次的正式祭祖活动,如“二月,祠太社之日,荐韭卵于祖祢……厥明于冢上荐之。 ”[10]25“八月,荐黍豚于祖祢。 厥明祀冢,如荐麦鱼。 ”[10]84“十二月,腊日,荐稻雁……遂腊先祖,五祀。 ”[10]87人们借此以示对先祖的敬重与感恩。 同时其更重要的目的, 便是希望祖先的神灵能荫护子孙,在他方世界为现世的后代们纳福禳灾,以保证家族的世代传系和兴旺发达,正如应劭谈到的“俗说:凡祭祀先祖,所以求福”,反映出时人信仰的实用性特点。 此外还有一些非定期的祭祖活动。 频繁的祭祀以及祀后的宴饮等活动也是促进家族成员间交流聚集的绝佳平台。 由《四民月令》“正月之旦,是谓正日。 躬率妻孥,洁祀祖祢……及祀日,进酒降神。 毕,乃家室尊卑,无大无小,依次列坐于先祖之前;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10]1观之, 可见族人在祀后宴会时温馨欢乐的氛围。
祖先崇拜是汉朝维系族人关系和宗法关系的重要纽带,民间各家族也借助这种与先祖间伦理情感交融的特殊方式,使家族成员树立以祖先神为中心的共同信仰和观念, 从而维护家族的和谐与团结,加强内部凝聚力,能够“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11],这也是人们期冀借助其信仰发挥实效性功能以解决现实问题的又一体现。
(二)社会集体祭祀
除了宗族内的祭祀,民间还有以乡里为单位的大型祭祀活动,百姓们借此以表达集体性的虔诚和公共的愿望, 其主要目的是为自身所处的乡里祈福。 社祭是对土地神的祭祀活动。 持续发展的小农经济造成人口增加迅猛,加之各种自然灾害等未知因素加大了人们对土地和粮食的需求。 据《白虎通·社稷》载:“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 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 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 ”[12]可知“社”之由来和功用。 两汉民众继承先民对土地的这种神化, 并在每年的春秋二季分别举行社祭活动。《援神契》曰:“仲春祈谷,仲秋获禾,报社祭稷。”全体居民向他们共同尊奉的社神祈福与报功,希望能禳除灾害以求五谷丰登。 随着两汉社会发展,乡里之社的政治性色彩减弱而娱乐节庆色彩增强,逐渐脱离官方的控制发展成一种民间组织,民众掌握了更多的祭祀主动权,而这对一直处于闭塞乡里环境中百姓的生活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影响。 人们将公共性的社祭活动视为属于自己的节日和休闲娱乐活动而广泛参与,如《礼记·郊特牲》载:“唯为社事,单出里”[4]1499。 民众通过共同的祭祀与娱乐活动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协调关系、解决问题、放松身体、调适心理等。 对于社祭活动的盛况,《盐铁论·散不足》有载:“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 ”[13]显然,此时的社祭已不再只是为了祈福报功、驱邪禳灾而“娱神”,更是一种为了满足乡里百姓的各种要求从而日益节庆化发展以 “娱人”的活动,这甚至成了主要目的。 人自身的重要性在其信仰中不断凸显,尽管各方神灵仍会得到人们的虔诚信奉,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其终究只是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精神工具,一切皆讲究实用。 同时,自我意识的不断高涨使民众把更多的关注聚焦于同类和自身,逐渐把人也尊为神灵,将自己和神抬到同样的高度,进一步拉近人神间的关系,以望其能更加方便地去理解和满足自己的要求。 对循吏良能的祠祀活动即为人们这种实用性目的最直接的体现。
在中央集权统治下的闾阎百姓是否安居乐业,与地方官员的吏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以,对此深有体会的民众会通过立祠祭祀、修庙树碑等活动以表达对那些政绩斐然、造福一方、施惠于百姓的循吏良牧的爱戴之情。 如西汉时期, 齐相石庆,“不治而齐国大治”[14]2197,后卒,当内地民众为其立石相祠。 景帝末期的蜀郡太守文翁,于任期大力提倡文化事业,蜀地“由是大化”[14]2626。“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 岁时祭祀不绝”[14]2627。 昭帝时胡建为谓城令,“治甚有声”[14]2911,后卒,“谓城立其祠”[14]2912,对其祭拜至东汉亦未绝。 东汉时期,周嘉于零陵任职太守七年而广受爱戴,死后“零陵颂其遗爱,吏民为立祠焉”[9]3941。 岑彭为益州木,“首破荆门,长驱武阳,恃军整齐,秋毫无犯……谥曰壮侯。 蜀人怜之,为立庙武阳,岁时祠焉”[9]2183。
除了为已卒的地方官吏立祠祭祀之外,两汉民众甚至为在世的良吏树庙立祠。 如九真太守任延,“令铸作田器, 教之垦辟, 田畴岁岁开广, 百姓充给。 ”又为制定嫁娶礼法,使当地“谷稼丰衍”,百姓“始知种姓”。“九真吏人生为立祠”[9]3327。东汉时王堂治蜀有绩,“巴、庸清静,吏民生为立祠”[9]1981。
从以上例子来看,两汉民众会利用民间信仰的方式对曾经或正在施惠于民、造福一方的循吏良牧进行立祠祭祀,建庙树碑。 之所以这样做,除了真切地表达颂扬与感恩之情外,同时也表现出对继任者和其他官吏的期盼与鞭策,反向激励他们向一众榜样学习,给地方和百姓带来更多的好处。 更是希望通过祭祀的方式以沟通神人, 期望得到其庇护保佑。
社祭活动频次的愈发走高和内容的娱乐休闲化,反映出民众对各方神祇要求的增多以及对自我娱乐的期待和欲望。 为官立祠、尊同类为神的广泛性表达出人们对自身价值的肯定,以期用现实人物而非臆想客体去解决实际问题。 这体现出民众信仰的实用功利主义色彩更加强烈,其对诸神灵虔诚付出的终极目的是索取回报。 同时也体现出人神关系的变化,从绝对依附到平起平坐,神的实用工具属性不断凸显,而整个祭祀活动从目的、主体到具体过程等逐渐皆以人为中心展开。
结 语
汉代处于神祇崇拜的转型时期, 相较于前世,两汉民众在继承和吸收的过程中又进行不断改造与创新,使民间信仰有了更为实用的变化和丰富的发展。 他们会选择那些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神灵进行祭拜;也会依据现实所需对其信仰的对象进行创新与要求、改造与淘汰;还会将自身的意愿融入于各大祭祀活动中, 更加突出人本身的实际意义。因此这一时期民众的信仰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实用主义,皆暗含着一种人神之间的新式关系,人们不再甘于匍匐在神的脚下, 而是注重和提升自身价值,去与神进行平等交易。 民众的信仰以趋利避害、祈福禳灾为现实目的,各神祇在人们看来不过就是可资利用的工具,可以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为迷茫和无助的民众提供情感的支持与慰藉,使其获得精神寄托并调适心理。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为的是免灾逃祸。 我们的祭祀很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 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鬼神在我们面前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15]这对于汉代民间信仰所渗透出的实用主义特点也可谓是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