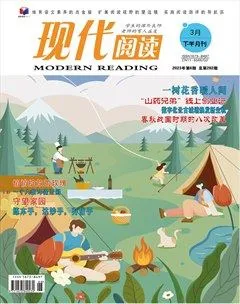大湖印象
2023-12-29沈念

夜色入冬,薄雾拂卷,阒寂覆盖。
穿过村庄,翻上长堤,洞庭湖咫尺之间。冬天湖水退去,广袤的湖洲湿地一片苍茫,草苇疯长,坑洼与水沟交错,牛蹄踩出一个个坚硬的脚印,小路上泥辙结冻,像伸向湖心的轨道。
没有人会相信这就是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洞庭湖,太瘦了,如同几条分岔的干涸的河流。有据可查的档案记录里,湖一年年做着“瘦身”运动。《水经·湘水注》中是“广圆五百里,日月出没其中”,唐宋诗文中频繁出现的是“八百里”“天下水”,也是“横无际涯”“水尽南天不见云”。它已经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大湖了,但到了明代嘉靖、隆庆年间还在长大,原因是长江北岸分江穴口基本堵塞,水沙分泄,湖面扩张,往西、南延展出了后来的西洞庭和南洞庭。清道光年间《洞庭湖志》中,它全盛时期面积约6000平方千米,差不多是现在的3倍。明嘉靖年间那张传播印刻的《广舆图》,描绘的是湖的全盛期和最大值,此后步步走向湖的衰落。
水去了哪里?水又是从何处而来?似乎每个此刻站在此地的人,都会问这两个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问题。
有来水才有去水。洞庭湖的南北两大来水,早已在郦道元记载的“同注洞庭,北会长江”和范仲淹吟诵的“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中予以印证。北水是城陵矶以上的长江来水,主要是长江荆江段,其实“衔远山,吞长江”中一个“吞”字已道出了江与湖的亲密关系;南水是长江支流的湘、资、沅、澧四水,它们都是先入洞庭湖再去往长江的。洞庭湖于是就变成了一个大口袋般的调蓄湖。但水是不分先来后到的,有时络绎不绝,有时蜂拥而至,加上雨水充沛,如同汪洋大海的湖面会变得格外好看,但“好看”的背后,是每到汛期湖区老百姓的胆战心惊。
在北斗卫星地图上,湖像一片蓝色的大地血液,在看似巨大实则狭长的动脉血管中流动。再定睛细看,流动的却是一个毫无规则的多边形,轮廓线豁牙硌齿。20世纪20年代开始,热情参与围湖造田的人们,像蚕一般细细密密地啃噬着洞庭湖这片巨大的桑叶。千里湖洲,百里沃野,顺水而来的开荒者,赤膊挑胯,或者一担箩筐挑着儿女和全部家当,跟着春天一起到来。插根扁担在金子般的泥地里,3天就能“发芽”,这是当地人对开荒年代的形象比喻。
入湖泥沙淤积量大于湖盆构造下沉量,泥沙淤积,平衡状态打破,湖泊变洲滩,洲滩变垸土和湖田,人进水退,人与水争地,插秧插到水中央,大湖萎缩加速,滨湖堤垸如鳞,弥望无际。水所能打开的想象被不知不觉地划块分割,向往的终点是叹息声起处。自然与人之间的矛盾,在物欲“满血”的年代,没谁能一下把紧紧缠绕的结解开。这个结包裹着形形色色的利益,还有各式各样的桎梏、伤害、遗忘与抛弃。湖所承载的那些气象万千的美好,通江达海的往昔,伴随候鸟的漂泊、流浪、冒险而变得破碎与脆弱。
阅读思考
1.对于洞庭湖,作者从哪两个维度进行了怎样的描述?
2.为什么文章用“豁牙硌齿”来形容轮廓线?这样写有什么意义?
3.纵览全文,你有怎样的“大湖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