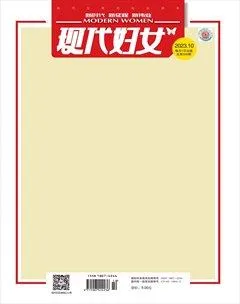独坐风月里
2023-12-29黄雪芳
在古画里,常看见一人独坐的情形:或坐卧于一棵老松下,悠闲舒展,仰头凝思;或席坐于瀑泉之侧,听耳边流水淙淙,取水煮茗;又或盘坐于山崖之巅,手挥七弦,泠泠音声中,游心太玄。
这样的画面,既令人神往,也极具治愈性——光是看见,已自觉褪去一身燥气,获得心灵的宁静与超脱。
古人尤爱独坐。王维在《竹里馆》里写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此时的诗人隐居蓝田,在抛开所有的俗尘杂事之后,他在月下独坐,弹琴长啸。但此时的王维并不孤独,因为自有明月来相照,所有的心事在月色下一一被洗净,不留块垒在胸中。
古人独坐,或是郁郁不得志之后的疏散怀抱,或是归隐田园之后的自我慰藉,又或是基于“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文人修养。对于今人而言,身处忙碌且浮躁的现代社会,更需要寻一方静地来独坐。这就像是一个给心灵充电的过程,让耗散在外的能量回归,再次元气满满;也像是让波动的水面重新安静下来的过程,在定静中让内心澄明,不至于在纷繁的俗世中迷失,并能辨清,此生真正追寻的不过是内在的宁静与平和。
独坐是一门技艺。毕竟,心不定的人是没有办法坐得住的。法国思想家蒙田曾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事,G/im4IDsES/iY743xKg+7sDW2axksl4wBaGN2+b0+oo=是一个人懂得如何作自己的主人。”无论是平抚心灵,抑或默默用功,一个懂得适时抽身回到自己世界的人,自带专注、自立的美感。在独坐的无边寂静中,不依恋,也不惧怕,坚定地站在自己这一头,去沉淀,或是去创造。
独坐,置身一处,也是置心一处。心不散乱,才能看见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独坐风月里,去看一朵花慢慢开放,去发现曾经忽略的美好。不迟疑,也不慌张,全心投入生命中的每一刻,积淀出岁月的厚重质感。
(摘自《广州日报》,本刊有删节)(责任编辑 王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