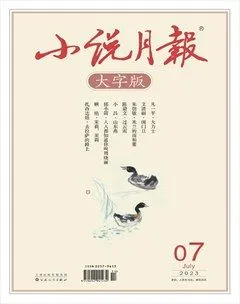大力士 Hercules
2023-12-29凡一平
他肩上扛着煤气罐子,另一只手还提着一罐,从一楼上十八楼,走的是楼梯。楼道空寂、阴冷,像一个废弃的矿洞。他一步一步往上,像背负矿石一样小心求稳。楼道的灯是感应的,他的脚踏上哪一层楼,那层楼的灯便亮了。楼层的灯递次闪亮,像水花弥漫。柔和的光明指引他上行,还造出影子。黑乎乎的滚圆的影子,像一只拽着猎物的熊,正兴冲冲地回窝。但1801不是他的窝,只是目的地。他肩扛手提两罐煤气送达1801,一趟便可得三十元报酬。只要他有能耐,往往复复,走多少趟都行。他今天走八趟了,现在是第九趟。如果房主不厌其烦,有耐心等,他打算走十趟,赚够三百元。房主应该是有那个耐心等的,她每次看到他出现在十八楼,脸上都会露出舒松、得意的神情,一次比一次释怀、满足,仿佛他越殷勤越受虐,她越感动越喜欢。他和房主两人,一个牟利,一个怡情,各得其所。
他又一次出现在十八楼。房主像是掐准了时间,恰好打开门。她穿着粉色的丝绸睡衣,趿着拖鞋,一手捧着瓜子,嘴里嗑着瓜子,慵懒而欢喜地迎接他。他在她跟前放下两个罐子,像是交差和等她验证。两个罐子都是充满了气的,连罐带气一共一百二十斤左右。一百二十斤两罐煤气,由同一个人肩扛手提上楼,而且是十八层楼,今天已经九趟了,人再年轻都实属不易。她看着他来不及擦的满脸满脖子的汗,怜惜又像挑衅地说:
“还能不能呀?”
他朴实地一笑,说:“我再来一趟。”
他提着两个罐子进电梯。从电梯下楼,这是允许的,主要是为了省时间,也省点力。考验人的关键是上,而不是下。现在是夜晚了,乘电梯往上的寥寥无几,往下的几乎没有。他和两个罐子在电梯里寂静地往下,电梯一次也没有暂停,直达一楼。
他从一楼楼梯重新步行上去。楼道的灯重新递次闪亮。
这第十趟,房主却没有开门迎接。他在房子的外边静候了一分钟,又静候了一分钟,不得不摁门铃。铃响过后,他听到里边传来声音:“进来吧,门没锁。”
他光脚进到房子里去,当然两个煤气罐也进去了。房主站在卫生间门口,满手的泡沫。她吩咐他将煤气罐放到厨房里。他从厨房出来,再经过卫生间时,看见房主在为澡盆里的一个小孩洗澡。小孩爽快地发着“汪汪”的叫声,他不禁定睛一看,发现洗澡的不是小孩,而是一条狗。房主看见他,让他到客厅去等她一会儿。
他在客厅等候,趁机观察房主的房屋。房屋宽大、典雅,目前看来仅住着房主和一条狗。房主精神空虚抑或心情烦躁是肯定的,不然她不会花钱使唤他、折腾他,在他身上发泄郁积的情绪,或者说是仇怨。她一定跟某个男人有仇,所以雇用他,把他当作与她有仇的男人,进行报复。他是供人发泄的真人偶,做这个行当有半年了,阅历让他的猜测八九不离十。这位今天折磨他的女人应该也不例外。他现在只知道她的微信名叫“爱上一个臭男人”。而她的闺密微信名则是“杀死一个白眼狼”。
“爱上一个臭男人”是在“杀死一个白眼狼”的家里遇到他的。
前天,他正在“杀死一个白眼狼”的家里,接受“杀死一个白眼狼”的辱骂,还有毒打。他扮演背叛她的男人,供她任意打骂,一个小时一百元。她骂得其实不狠,只是侮辱性强。打也不很带劲,只是手段阴毒,专攻他的下体。无论轻重、仁毒,他都必须接受、忍受。在打骂到第二个小时的时候,她的闺密来了。他看出她们两人是闺密,从细节看得出来。“杀死一个白眼狼”接过来访的她递过来的一包自制阿胶饼,居然不嫌弃,还如获至宝,显然关系非同一般。这都不关他什么事,主要是当时她看上了他,说他跟唐钟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像,要拿他去用,当唐钟用一用。“杀死一个白眼狼”说:“我还没打骂够呢,至少我还得再打骂一天,发泄完我心中的仇恨,再让给你。”于是他和她加了微信,约好了上门服务的大致时间。他今天如约上门,为“爱上一个臭男人”服务,服务的内容是运送煤气罐。煤气罐是早就备好的,两罐。罐子够重,里面煤气充足,像没有使用过。而罐子外壳斑驳,有些年头了。
“爱上一个臭男人”现身在了客厅,与狗一起来到他跟前。刚洗完澡的狗神清气爽,活蹦乱跳。它甩着没有彻底吹干的毛发,少许的水珠飞溅到他的脸和脖颈上,让他感到凉爽。他同时闻到一股好闻的味道,这好闻的味道闻所未闻,不知来自皮毛鲜亮的狗,还是来自优雅贵气的妇人。这位叫“爱上一个臭男人”的妇人看上去不会超过四十岁,皮肤光洁,眼睛明亮,保养得相当完美。她和她的狗都让他感到可爱可亲,何况她还给他递上了一杯水。
他喝着水,咕噜三口就喝完了一杯,显得很渴,但他拒绝了妇人为他续水的表示,起身告辞。妇人拦住他,将他扯回沙发坐下。她坐在他的身边,对他凝眸,脉脉含情,仿佛看着久违或失而复得的恋人。她不含一丝仇怨的目光让他感到奇怪。
“你和唐钟真的很像,太像了。”她忽然说,手不由自主地抬举,摸他的脸,为他擦拭尚存的汗。
他接受她的抚摸,这似乎是服务的内容,跟接受打骂是一样的,都是服务对象的宣泄。所不同的是,别人是把他当泄愤和泄恨对象,而她的举动,显然不是宣泄愤恨。让他扛煤气罐上楼,最多是一种惩罚,此刻的抚摸,是惩罚后的安慰。
她摸了他的脸后摸他的胸膛。他胸膛两块硕大、突出而坚硬的胸肌,在洇湿的白背心底下,像被薄雪覆盖的两座山峦。
“唐钟也有这么大和硬的胸肌。”她说。
“唐钟是谁?”他纳闷而好奇地问。
“一个臭男人。”她说,还轻轻捶了一下他的胸膛。
他轻轻哦了一声,估计只有他自己听见了。
“你这个臭男人,”她说,真把他当唐钟了,“当初追我的时候,就是通过给我家送煤气,每次都是两罐。还记得不?”
他点点头,把自己当成了臭男人或者唐钟,“你从哪里弄来的煤气罐?现在城里住宅都不用这个了呀。只有一些大排档还用。”他说。
“这就是你当年送到我家的煤气罐呀,我一直保留着。我住到这里的时候,搬过来的。”她边说边抚摸他的脑袋,像是提醒,“我怕我把你忘了。”
他有些莫名地感动,说:“还好,我今天跑了十趟。”
她以为他想要钱,转手拿过手机,边操弄边说:“我微信转给你了。”
他倏地脸红,说:“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今天很高兴,”她眉飞色舞地说,“我狠狠满足了自己一回对美好男人的幻想,真的。”
“我走了。”他说。
她送他到电梯口,看着他进电梯,然后挥挥手,说:“大力士,再见。”
“大力士”是他的微信名,高中毕业的时候起的,也可以说是进城打工的时候起的,因为他高中一毕业就进城打工了。他来到南宁,什么活儿最苦最累,他就干什么,因为他有的是力气。淘下水道、装卸货、送外卖,接二连三干了一年,挣了六万元钱,扣除吃喝拉撒,剩两万元。他觉得一年就剩两万元钱太少了,而他还有使不完的力气,无处可用。某天灵光乍泄,他想到了做真人偶,供人发泄。于是每天华灯初上的时候,他便到朝阳广场摆摊。身边立一块标牌,标牌上打印着“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价格面议、可上门服务”等字样,还有加微信及收费的二维码。摊摆出去没几天,生意便十分火爆,闻讯而来宣泄的人络绎不绝,午夜还有人在等。他任由人打骂,无论骂他祖宗八代、泼他脏水、拳打脚踢,他都不会反击,沉默以对,像一头任劳任怨的牛。纵使遍体鳞伤,他都不哼唷喊痛,甚至面不改色。即便被连续长时地击打到午夜,他依然屹立不倒,像傲立雪中的一棵树。他不愧是大力士,凭力气以及抵抗力挣了钱,半年下来,光是做真人偶这一项,便挣了七万元。这七万元是他出卖体力挣来的,当然同时出卖的还有尊严。每一个打骂他的人其实都是通过侮辱他来获得情绪的平复和情感的满足。但“爱上一个臭男人”似乎是个例外,她就是购买他的力气,或者说是购买男人求爱的样子。在“爱上一个臭男人”那里,他唯独不是仇怨的对象。
他回到租屋。五百元钱一个月租下的屋子逼仄、憋闷,像个微型集装箱。他当下不是没有条件换间大的、有窗的房子,只是舍不得。他在这里住了将近一年半了,习惯了,甚至有了感情,就像养猫狗的人对豢养多时的猫狗,无论它们如何顽皮或愚钝也舍不得离弃。
洗完澡上床,他才拿起手机,看到“爱上一个臭男人”通过微信转给他的钱,竟然是六百元,比他理应得的多出了三百元。他不敢接收,先给她信息:
你好,你给我的钱多了。
不一会儿,他收到她的回信:多的部分是加赏你的。
他复:这不好。这多的部分我不能收。
她回一个符号:?
他答:原来约定多少就是多少,我不能违反约定。
她复:哦。
紧接着,她加复了一个“好样的”的表情。
他先把三百元退给她,再接收了她的六百元。
他以为他和“爱上一个臭男人”的劳务关系就此了结了。
他继续摆摊、上门服务,被辱骂和殴打的活计应接不暇。之前找他宣泄的多数是女人,这段时间男人多过了女人——越来越多自认为被戴了绿帽子的男人,纷纷找上他,辱骂殴打一个比一个恶毒、凶狠,只差没有扒他的皮和阉割他。而他收费的价格基本不变,同工同酬,男女一致,虽然男人和女人宣泄的强度,差别是很大的。如果男人的宣泄是抡过来的大铁锤,那么女人至多是敲打的扫把。比起男人,女人真是温柔啊。而“爱上一个臭男人”又是女人中最温柔的,购买他的服务,不过就是让他出点力气罢了,或者说出一身汗而已。这段时间他不是没想过这个最温柔的女人,只是不曾想她还会找他。
深秋的这一天,她约他。约定晚七点、空腹,上她家,一小时一百元。服务项目或内容,她不说明。
他按时赴约。“爱上一个臭男人”的家里灯暗花红,弥漫着温馨和浪漫的气氛。他再愚钝,也明白他上门不是来挨骂和挨打,也不是来出苦力。她换了一套稍厚的睡衣,颜色也有了变化,紫色。那条狗身上穿着衣服,像个宠儿。它对不过一面之缘的他摇尾仰首,仿佛代表主人表示欢迎。饭桌那边飘来迷人的香味,比眼前性感美丽的妇人还要诱人。
“饿了吧,来。”她说着直接牵引他向饭桌走去。她安排他坐的地方,然后自己坐到了他的对面。她和他貌似保持了距离。
“今天请你来,不干别的,就陪我喝酒。”她说,指着桌上的两种酒,“喝白的还是红的?”
他摇摇头,说:“我喝不了酒,一喝就醉,醉了就没力气。”说完站起身,“对不起。”
她不让他走,说:“你看我喝。”然后抓过桌上一瓶白的,给自己面前的杯子倒酒。
他看她喝酒,尴尬而不知所措,忽然发现桌子上有几瓶水,说:“我陪你喝水吧。”
于是,她喝酒,他喝水。一小杯白酒对应的是一大杯水,她越喝越兴奋,他喝多了便觉得肚子胀,憋得慌。
她目不转睛看着他,仿佛要把他看完全、看透,这似乎是她坐到他对面的目的。
“唐钟也不能喝酒。”她又提及那个跟他相似的男人。
“唐钟是你……”他问。
“我丈夫。”
他看看她无疑没有丈夫的家,“那他……”
“死了,”她说,情绪忽然低落,“植物人,等于死了。”
“对不起。”他说,心里后悔他的提问。
“没什么,都十年了。”她说,“人现在在医院里,有专人专护,只要有钱,他就不会断气,也不会让他断气。我家有钱,他家更有钱。”
“有钱的人还用亲自扛煤气?”他又问了,因为他想不通。
“你恋爱了吗?”她说,端着杯子,只是把玩,不喝。
他摇摇头,说:“没有。”
“多大了?”
“二十。”
“唐钟也是二十岁的时候与我谈的恋爱,”她看着杯子里的酒说,“开始他家反对,我家也不同意。我们谈了六年,才结的婚。结婚才两个月,他就出事了。车祸。”
他脑子急转,算唐钟结婚的年龄和车祸的时间,算出她的年纪,不超过三十六岁,如果她与唐钟同龄的话。
“我们没有孩子,”她说,专注地看他,“我很想要个孩子,尤其是现在,我不小了。”
他惶惑,像不明白她为什么跟他说这话,也似乎懵懂。
“我想请你帮助我要个孩子,”她直截了当说了,“与我同居,直到我怀孕。”
他愕然。
“报酬按天计,”她说,闪了闪眼睛,“或者包干。”见他没反应,她放下杯子,用两手食指做了个十字,“十万,行不行?”
他依然定定的样子,像一口铜钟。
她忽地抓起酒杯,一口干了,再倒一杯,又干了。
他总算有了动作,抓起瓶子,想往杯子里倒水,一迟疑,索性对着瓶子,把水全部喝掉。空瓶子一搁,他的脸便出现了抽搐的表情,手不自禁地往下,去捂肚子。他觉得他的膀胱要炸了,起身往卫生间跑。
淋漓酣畅后,他并没有从卫生间出来,而是在看镜子。他看着镜中的自己,强壮、黧黑,像个铁塔。脸上的青春痘星星点点,像沙金闪烁。而镜子外边的他,松软并动摇,像栉风沐雨的树。他眼睛迷离,情绪错乱,心窍不受管控地打开,让灵欲放飞。他的魂儿飘回了上岭——那个山环水抱的村子,它是那般美丽,却百般穷苦。他六口之家,有三人卧病在床,一人残障,健康的二人一人留守,他则到外面闯荡。破败的家,像一个持久战的阵地,他的家人都在与苦难的命运搏斗。而他的职责和使命,便是给腥风血雨的阵地输送弹药,提供后勤保障,不能中断而且还必须足够。狗在卫生间外吠叫,他的魂儿回到身上。城市的富裕人家,连厕所都是香的。那个金贵的自动冲洗马桶,他忍不住又瞄了一会儿。
他从卫生间出来,看见狗上蹿下跳,迫不及待把他往餐桌那里领。只见“爱上一个臭男人”趴在了桌上,乱发包头,倾倒的瓶子在往外漏酒,洇着她的头发。他急忙过去,把酒瓶扶正,然后掀开她的头发,露出她的半边脸。看着她惨白的脸,他慌张不已。
犹豫思忖了片刻,他把她抱了起来,去往房间。她丰腴、奇香的身躯在他的怀抱里,像一条鲜鱼,也像一袋白面,考验着二十岁的饥渴青年。有狗在前面引领,轻易就能知道哪间房是她的卧室。他把她抱进卧室,将她正放在床上,脱掉她的拖鞋,给她盖上被子。
就在他转身离开的时候,忽然听到她的声音:
“你考虑好了吗?”
他停步,但是没有回答。
“如果J/RrPDqtJhtdO8OfDjiePQ==你考虑好了,愿意了,同意了,我们就签个合同。但是在签合同之前,你得去医院做个体检。体检报告证明你没有影响生育的男科问题,我们就可以签合同了。”
她听似酒醉说的胡话,却字字珠玑,也诛心。
几天之后,他拿来了体检报告。她拿出拟好的合同,要他签名。她事先已经知道他的名字了,叫韦亮。而他终于知道她的名字,是在合同上,黄红,甲方。
在客厅的茶几边,黄红把合同移动到韦亮跟前,把笔也移了过去。合同的各项条款是双方协商过的,清清楚楚,没有异议。
韦亮看着那支笔。黑色的圆珠笔静静地搁置在茶几上,在他的面前,像一根金条,又像一把刀子。他迟迟没有拿起它。
黄红说:“要不你再检查一遍合同,有什么要补充的,补上。或者有哪条不满意的,我们改。”
韦亮摇头。
“那就签吧。签了,我们就按合同来。”
韦亮伸出手去,触碰了那支笔,握住了那支笔。
但那支笔,迟迟没有被他提起来。它仿佛被粘住了,又仿佛很棘手。他凝视它的眼睛充斥着恐惧和厌恶。
一个大力士,最终提不起一支笔。
原刊责编 莫 南
【作者简介】凡一平,原名樊一平,男,壮族,1964年生,广西都安人。先后就读于河池师专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历任乡中学教师、文化局创作员、专业作家等职。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跪下》《老枪》,中短篇小说集《浑身是戏》,及诗歌、散文百余篇,据其小说或剧本拍摄的影视作品有《寻枪》《理发师》《跪下》《十月流星雨》《鲁镇》等。曾获广西青年文学独秀奖、铜鼓奖等奖项。《非常审问》获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现在广西民族大学影视创作中心工作,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