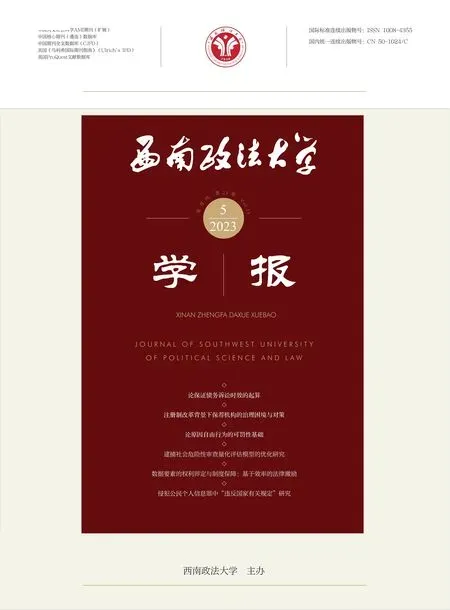论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基础
2023-12-28崔涵
崔 涵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78)
一、引言
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行为人通过饮酒、吸食毒品等方式致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的状态中,并在这种状态下实施犯罪行为后定罪处罚的问题。①参见陈兴良:《教义刑法学》(第3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221-222 页;张明楷:《刑法学(上)》(第6 版),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402 页。 如后文所述,本文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行为人在饮酒、吸食毒品之后依然是完全责任能力人,但为论述方便,本文将继续使用“原因自由行为”等表述指代醉酒的人、吸食毒品的人在表面上不具有责任能力的状态下实施犯罪行为的问题。这类情形在司法实践中并不鲜见,典型案例如下。
案例1(郑某故意杀人案):郑某吸食毒品后产生幻觉,认定妻子陈某出轨,欲与之离婚,其母范某某闻讯后对郑某加以斥责,郑某便用随身携带的刀具对其连捅数刀,随后,又捅刺瘫痪在床的父亲郑某某,导致父母二人死亡。①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2 年十大毒品(涉毒)犯罪典型案例。
案例2(龙某某故意杀人案):龙某某吸食毒品后产生幻觉,将其母李某英认作牛精,并用钝器击打李某英的头部与面部,导致其颅脑损伤死亡。 随后,龙某某又将死者的脑组织挖出,供奉于自家的神台之上。②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刑一终字第203 号刑事裁定书。
案例3(刘某某故意杀人案):刘某某饮酒后陷入精神障碍状态,将行人李某某拽倒后进行殴打,然后,又持砖头连续击打李某某的头部,导致其重度颅脑损伤当场死亡。③参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辽刑终83 号刑事裁定书。
在案例1 中,司法机关主张郑某是因吸食毒品致幻后实施的故意杀人。 在案例2 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认为,龙某某明知自己吸食毒品后会陷入精神障碍的状态,并进一步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却仍然自愿吸食毒品,且在吸毒后实施了杀人行为,属于原因自由行为。 因此,即便龙某某的杀人行为是在其无责任能力状态时实施的,也应当承担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 在案例3中,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出,刘某某虽被诊断为酒精所致精神障碍,但其事前的饮酒行为符合原因自由行为的行为模式,并非精神病理症状,从而认定刘某某成立故意杀人罪。
对于饮酒、吸食毒品等自陷责任障碍状态继而实施犯罪的情形,以上3 个案例揭示了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问题时形成的裁判规则:认定行为人实施的行为系原因自由行为,便可追究其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 但是,“原因自由行为=故意犯罪”的逻辑链条可能经不起推敲,以“龙某某故意杀人案”为例,纵然如裁判文书所言,龙某某在吸食毒品之前就已经认识到自己可能会陷入精神障碍的状态,也无法认定其在吸食毒品之前就具有杀害生母的故意。 在学理上,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也存在着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之分。 因此,不应不加检视地将此类情形直接认定为故意犯罪。④早先便有学者注意到了实务中这种无法令人满意的状况。 参见冯军:《刑事责任论》(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308-309 页。
此外,在学理上通常认为,原因自由行为中主要存在着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实行行为和责任能力同时存在原则与原因自由行为之间的龃龉? 二是如何界定原因自由行为中的实行行为?⑤参见陈兴良:《教义刑法学》(第3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222 页。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同时存在原则要求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必须具有责任能力,但醉酒的人、吸食毒品的人可能是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法益侵害行为的。 因此,如果将结果行为认定为实行行为,就无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显然,解决该理论问题是有难度的。 也正因为如此,施密特霍伊泽尔将原因自由行为问题称为“德国刑法学中的一道典型难题”⑥Eberhard Schmidhäuser, Die actio libera in causa: ein symptomatisches Problem der deutschen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1992.。 毋庸置疑的是,对原因自由行为中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区分、原因自由行为与同时存在原则之间的矛盾、实行行为的界定等问题的讨论,都需要回归到对可罚性依据这一基础性命题的追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虽未直接提及原因自由行为概念,但在第18 条第4款中对“醉酒的人”的刑事责任作了规定,强调“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一条款往往被视作原因自由行为在我国实定法中的体现。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这一规定与域外的立法模式不同,不仅没有采用“心智缺陷”“心神丧失”等表述①例如,《日本刑法典》第39 条规定:“心神丧失者的行为,不罚。 心神耗弱者的行为,减轻其刑。”日本刑法学界有关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讨论,都围绕着是否适用第39 条展开。,也没有将吸食毒品后实施犯罪的情形囊括在内。 在此背景下,确有必要结合《刑法》第18 条第4 款的规定对“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基础”展开研究,从而为吸食毒品后犯罪等情形中的可罚性问题确立理论根据。
然而,从国内的现有文献来看,不少研究仍止步于域外理论的推介②例如,张明楷:《外国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载《河北法学》1991 年第5 期,第14-17 页;于改之:《论外国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2 期,第109-114 页;王充:《日本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2 期,第115-121 页。,或是写就于刑法学研究的教义学转型之前③例如,陈兴良、王晨:《论醉酒人犯罪的刑事责任根据》,载《法学杂志》1992 年第1 期,第14-15 页;何庆仁:《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困境与诠释》,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 年第2 期,第25-33 页;陈家林:《也论原因自由行为——与齐文远、刘代华先生商榷》,载《法学家》2000 年第6 期,第73-76 页。,没有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或是未能实现与本国实定法规范的有效衔接。 同时,长期以来,《刑法》第18 条第4 款的性质究竟为注意规范还是法律拟制,学界一直未有讨论。 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本文首先对域外理论加以检视,考察其自身的合理性,以及与我国实定法规范之间的契合程度。 然后,再以《刑法》第18 条“特殊人员的刑事责任能力”为切入点,尝试挖掘责任能力的本质,为原因自由行为建构更为合理的归责根据。
二、既有理论之检讨
关于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绝大多数学者都持肯定态度,主要包含两种论证进路,即构成要件模式与例外模式。
(一)构成要件模式
构成要件模式主张,行为人具有责任能力时实施的原因行为是责任非难的重点,因而将饮酒、吸食毒品等行为界定为原因自由行为中的实行行为。 如此一来,对行为人进行定罪处刑,就不会有悖于同时存在原则。 其中,最典型的是“间接正犯类似说”,将间接正犯的法益侵害模式“移植”到原因自由行为领域:行为人将结果行为阶段陷入责任障碍状态的“自己”作为犯罪工具。④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 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 年版,第601-602 页;団藤重光『刑法綱要総論(第3 版)』(創文社,1990 年)161 頁以下参照。这种观点为原因自由行为找寻到了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其他概念与之联结,颇具创造性,但也存在着不少弊病。
第一,间接正犯类似说将饮酒、吸食毒品等行为视为着手,会不当扩张未遂犯的处罚范围。 我国《刑法》第23 条强调“已经着手实施犯罪”,要求未遂犯的成立须以客观危险的存在为必要。 然而,单就饮酒、吸食毒品等行为而言,很难认为这些行为具有侵害他人法益的客观危险性,也无法体现出行为实现不法构成要件结果的高度或然性。 此外,即便依据《刑法》第22 条的规定,主张行为人会因“准备工具、制造条件”所流露出的法敌对意思而具备可罚性⑤参见张志钢:《论未遂犯处罚根据的中国立场——以不能未遂的可罚性为中心》,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0 年第4 期,第44 页。,也缺乏足够的证据可以表明行为人在饮酒、吸食毒品之时就具有打破某条行为规范的主观恶性。
第二,间接正犯类似说将饮酒、吸食毒品等行为视为实行行为,会逾越不法构成要件的文义范围。 在行为人吸食毒品后杀人的案例中,很难将吸食毒品的行为与故意杀人行为画上等号,因为这种理解明显超越了刑法解释的界限。 同时,构成要件本应发挥区分此罪与彼罪的个别化机能,但饮酒、吸食毒品等行为无法体现出具体罪名“类型化”的危险。 此外,如果将饮酒等行为视为实行行为,就意味着可以向正在饮酒的行为人实施正当防卫,这也是无法接受的。①吉田敏雄「原因において自由な行為」北海学園大学学園論集167 号(2016 年)5 頁参照。事实上,构成要件模式所作的尝试,是将责任领域的问题纳入构成要件阶层来解决,因而其与既有的构成要件理论之间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冲突。
第三,间接正犯类似说实质上采用了“事后”的评价视角,缺乏合理性。 举一例以说明:甲想杀乙,但缺乏足够的勇气,于是,他通过饮酒为自己壮胆(第一行为),并在酒精的刺激下实施了杀人行为(第二行为),此时,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无疑是第二行为,而事前的饮酒行为只是不值得刑法评价的案外事实。 原因自由行为中的饮酒、吸食毒品等行为与之并没有本质差别,之所以会被构成要件模式确立为实行行为,其实是基于事后发觉行为人于结果行为当时责任能力减退后得出的结论。 不仅如此,饮酒等原因行为与行为人陷入的责任障碍状态之间虽有因果关系,但其和结果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却是无法证明的。 构成要件模式肯定了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显然是建立在事后视角之上。
第四,间接正犯类似说难以与有关间接正犯的构罪基础相契合。 根据罗克辛的“意思支配理论”,幕后操纵者对无责任能力者、限制责任能力者的利用,是通过“凭借错误认识的意志控制”或“凭借强制的意志控制”来实现的,前者强调幕后者“目的性”的操纵,后者则要求间接实行人施加的强制压力达到了足以使刑法免除幕前者责任的程度。②Vgl. Claus Roxin, Tä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10. Aufl., 2019, S. 260 ff.但是,饮酒、吸食毒品前的行为人可能不具有指向特定犯罪行为的故意。 此时,凭借错误认识的意志控制所强调的“目的性”便无从谈起,也无法认定行为人能对自己施加何种程度的强制压力。 间接正犯概念自萌芽之始便与不同的犯罪参与主体相关联,在概念形成与学说演变的过程中,始终居于“正犯与共犯”讨论的延长线上。 论者们往往要从自身对于犯罪参与体系、参与形态的理解出发,方能在间接正犯概念的必要性之争、与教唆犯的界限之争等问题上提出自己的主张。 可以说,不同人格主体是间接正犯相关问题的基石,但在原因自由行为的情形中,自始至终只具有单一人格,故而间接正犯类似说的“类似性”只是纸上空谈罢了。
综上,构成要件模式主张原因行为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实质上是以预期达到的刑事政策效果为导向进行的目的性建构③Vgl. Ulfrid Neumann, Die „actio libera in causa“ als Methodenproblem der Strafrechtsdogmatik,Kansai University review of law and politics,2006, Vol.27, p.49.,其基本主张与相关论据都存在着欠缺合理性的问题。
(二)例外模式
例外模式的基本立场是原因自由行为是同时存在原则的例外,饮酒、吸食毒品的行为不是构成要件行为,但会使行为人违反保持自我能力、不陷入责任障碍状态的义务(不真正义务)。 虽然行为人在实施结果行为时欠缺责任能力,但由于这种责任障碍状态是行为人自行招致的,因而可以通过“二阶归责”的模式,将结果归属于行为人。①Vgl. Joachim Hruschka,Probleme der actio libera in causa heute, JZ 1989, S. 311.诺依曼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良,主张由于行为人违反了不真正义务,所以他被剥夺了援引责任阻却事由的可能性。②Vgl. Ulfrid Neumann, Neue Entwicklungen im Bereich der Argumentationsmuster zur Begründung oder zum Ausschluß strafrechtlicher Verantwortlichkeit, ZStW 1987, S. 574 ff.因为责任的本质并非一种事实,而应借由“可非难性”这一规范性标准来诠释,所以不具有严格的时间结构,实施结果行为时的行为人可以被拟制为完全责任能力人。 这种见解拓展了例外模式的深度,因而为不少学者所赞同③例如,日本学者高桥则夫教授也持这一见解。 高橋則夫『刑法総論(第3 版)』(成文堂,2016 年)358-359 頁参照。 我国有学者以“评价性事实”“实在论事实”的表达方式进行论证,事实上也是借由规范性要素否定同时存在原则的根基。 参见王志远、杜磊:《评价性事实在刑事责任赋予中的意涵——以原因自由行为的犯罪构造难题为例》,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 年第2 期,第59-67页。,但同样存在着自身不合理、难以与我国《刑法》相契合等多种缺陷。
第一,例外模式并未解决原因自由行为中何以归责的合理性问题。 例外模式试图为公民创设一种“不得致使自己丧失责任能力”的衍生性义务。 虽然违反这种不真正义务并不会直接导向刑事制裁,只有在结果行为发生时才会要求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但这并不能完全消除它们的义务属性。④Vgl. Friedrich Dencker, § 323 a StGB - Tatbestand oder Schuldform? - Zugleich Besprechung von BGHSt 32, 48, JZ 1984, S. 454 f.而这种不真正义务的重大缺陷就在于于法无据。 立足于《刑法》第18 条第4 款的规定,只能推导出这样的规范诫命:禁止醉酒的人实施犯罪行为,但刑法从未向任何公民下达过“禁止饮酒”“禁止吸食毒品”的指令。 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形:甲意识到自己醉酒后会陷入心智缺陷的状态,可能会实施法益侵害行为,于是,他在饮酒前就将自己反锁在房中,杜绝出门伤人的可能,此时,不能认为甲违反了一种“不得致使自己丧失责任能力”的义务。 如果主张不真正义务并不包含任何实质内容,不能作为具体的行为指引⑤Vgl. Ulfrid Neumann, Zurechnung und „Vorverschulden“: Vorstudien zu einem dialogischen Modell strafrechtlicher Zurechnung, 1985,S. 279 f.,那么,这种义务就只能发挥抽象的解释性作用,在此基础上将违反不真正义务的行为人“拟制”为完全责任能力人,似乎更加缺乏根据。
有学者在例外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拟制条件:(1)客观标准,要求原因行为具有导致之后的结果行为、危害结果的抽象危险;(2)主观标准,要求行为人在自愿实施原因行为时,可以预见到这种抽象危险。⑥参见马天成:《刑法中原因自由行为的例外模式——基于中国实践的思考》,载《法学论坛》2023 年第1 期,第82 页。然而,抽象危险与预见可能性的引入,至多只能帮助增强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的关联性,限制排除适用责任阻却事由的范围,但排除事由本身的合理性仍然没有得到证实。 同时,抽象危险、预见可能性等概念属于以人的经验和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存在论范式,容易将不应归责的情形加以归责,因而在过失犯领域一直饱受争议,以致能否将其吸纳到原因自由行为的理论建构中来,也令人心生疑虑。
亦有部分例外模式的追随者指出,从禁止权利滥用理论着手,对于自陷责任障碍状态的行为人,追究其完全的刑事责任是必然的结论。⑦Otto, Der Vollrauschtatbestand (§ 323a StGB), Jura 1986, S. 431.然而,作为一个民法上的概念,权利滥用的含义是基于权利所为的“错事”,在外观表现上首先为权利的行使。⑧参见彭诚信:《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法律适用》,载《中国法学》2018 年第3 期,第252 页。责任阻却事由并未赋予行为人以任何种类的权利,只是起着减免刑事责任的功效,因而根本无法被滥用。 此外,“权利滥用”这一表述也过于抽象,于刑法中尚无印迹,若以此为论证根基,难谓妥洽。
第二,例外模式只能解决原因自由行为中是否归责的确定性问题,但在我国刑法语境之下,例外模式无法发挥此类实效。 由于《德国刑法典》中并不存在有关“醉酒的人犯罪”的规定,因而饮酒、吸食毒品之后犯罪的行为人,本可以援引《德国刑法典》第20 条、第21 条的规定免除刑事责任,或得以减轻其刑。 因此,例外模式所创设的“例外”,不仅针对的是同时存在原则,更是不适用第20条、第21 条意义上的“例外”。 因而不难理解,为何例外模式的提出者赫鲁斯卡会主张在《德国刑法典》第20 条之后作出另行规定,强调对无能力状态负有责任的行为人不适用第20 条①Vgl. Joachim Hruschka, Die actio libera in causa-speziell bei § 20 StGB mit zwei Vorschlägen für die Gesetzgebung, JZ 1996, S. 69.,以应对例外模式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批判。 然而,依据我国《刑法》第18 条第4 款的规定,是否归责的答案是明确的:醉酒的人犯罪,不能援引丧失责任能力这一责任阻却事由,“应当负刑事责任”。 事实上,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2003 年作出标志性裁判之后②BGH NJW 2003, 2394. 法庭在附言中主张,在自我造成醉酒的情形中,一般不允许适用责任能力大幅下降时可供选择的减刑规定(《德国刑法典》第21 条)。,学界越来越多的声音建议制定类似于原民主德国《刑法典》第15 条第3 款的规定,如果无责任能力是由行为人自我造成的醉酒导致的,那么,在犯罪行为时不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必须像完全责任能力人一样受到惩罚。③Vgl. Ulfrid Neumann, Die „actio libera in causa“ als Methodenproblem der Strafrechtsdogmatik, Kansai University review of law and politics, 2006, Vol. 27, p. 52.不难看出,这一规定与我国《刑法》的现有规定非常相似。 不过,这仅能说明,对原因自由行为进行本土化解读,不需要考虑如何在成文法之外创设例外,但不足以说明,可以从我国的实定法中直接推导出例外模式的合理性。
此外,亦有学者对我国实践中的一些判例进行了梳理,继而主张,排除适用责任阻却事由的逻辑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得到了体现,这也被视为采纳例外模式的理由之一。④参见马天成:《刑法中原因自由行为的例外模式——基于中国实践的思考》,载《法学论坛》2023 年第1 期,第79 页。然而,在本文看来,这也仅能说明,例外模式在德国刑法语境下希望解决是否归责的问题,在我国实务中几无疑问,但不足以说明,裁判者已将例外模式视作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基础。 退一步讲,即使例外模式更受裁判者的青睐,但这种青睐也不足以填补合理性论证上的不足。
三、可罚性基础的重塑:责任能力障碍之证否
在我国刑法语境之下讨论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应当将《刑法》第18 条第4 款的规定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 由于法条标题等都可以纳入解释时的考虑范畴⑤参见[德]托马斯·M. J. 默勒斯:《法学方法论》(第4 版),杜志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226 页。,而第18 条的标题是“特殊人员的刑事责任能力”,因此,条文中“不负刑事责任”“应当负刑事责任”是基于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作出的规定,而不是由其他阻却事由的有无决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我国《刑法》中并不存在有关责任能力的一般规定,而是直接规定了部分特殊人员的刑事责任,因而在我国刑法语境下,能否将行为人饮酒、吸食毒品之后短暂的言行举止失常视作丧失或部分丧失了责任能力,还有待商榷;另一方面,在规范责任论的体系中,违法性认识可能性、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等要素均以价值判断为中心,因而责任能力也不可能仅停留于混合生理与心理要素的事实判断,需要注入规范性内涵,否则便无法与不作为犯罪中作为义务、过失犯罪中注意义务的履行能力(构成要件层面具体的行为能力)相区分。
(一)理性选择能力作为责任能力本质之证成
当我们追问责任能力的本质时,不可避免地要面临3 个问题:(1)国民遵守刑法规范或违反刑法规范的动机是什么? (2)行为人具有什么样的能力? (3)在犯罪实践中,刑法规范与行为人的动机、能力之间具有何种联系? 这3 个问题直接决定了刑法规范如何筛选可以归责的行为人。 本文认为,将责任能力的本质定位为理性选择能力,可以合理回答这3 个问题。
1.理性选择能力的基本内涵与普遍性
理性选择理论在现代经济学中占据支配性地位,其基本内涵是:一个自利理性人首先会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何种后果,并据此进行利益的权衡,作出更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 该理论于20 世纪被引入到了犯罪学领域,论者主张,犯罪行为是具有目的的,犯罪人实施构成要件行为,是为了使自己受益;同时,潜在的罪犯又是理性的,即便无法获取绝对完全的信息,他们也会在了解犯罪成本与收益之后,以理性的方式选择是否实施犯罪行为。①See Derek B. Cornish & Ronald V. Clarke, The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in Wortley, R., & Townsley M. eds., Environmental Criminology and Crime Analysis, Routledge, 2016, p. 34.虽然在犯罪所得与刑罚后果之间权衡的见解于刑法领域并不陌生②参见[德]安塞尔姆·里特尔·冯·费尔巴哈:《德国刑法教科书》(第14 版),徐久生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 年版,第28 页。,但近几十年来,学者们通过理论建构与数据验证,不断证实了实施犯罪行为时理性选择过程的实在性。 相关研究表明,这种权衡利弊并作出理性选择的过程,共通于不同种类的犯罪,不仅存在于财产犯罪中,也出现在暴力犯罪与毒品犯罪的行为人身上,且不同群体也都会产生对犯罪成本与收益变化的理性反应。③See Loughran T.A. et al., Can rational choice be considered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Evidence from individual - level panel data,54 Criminology 86,107 (2016).这意味着,行为人普遍具有理性选择的能力,这不完全是理论上的一种假定,更是经由多次实验论证的科学结论。
2.理性能力:契合规范责任论的基本立场
目前,占据通说地位的规范责任论是一种非决定论的立场,以肯定自由意志的存在为前提。 刑法中的自由意志概念虽以哲学为基底,但早已完成了同一概念在不同研究领域间流转时发生的意义流变,发展出了独有意涵,主要包括两点:其一,在剥离了政治与伦理的原初背景之后,“自由”不再特指个人不受外部或内部决定因素影响的自由,而被赋予了另一重含义——在不同的行动方案之间作出决定的自由,基于此,期待可能性的讨论成为可能;其二,责任阶层接纳的自由意志,具有浓厚的法规范色彩,“按照自己的规范意识而行动的意识,才是真正的自由‘意识’”④[日]平野龙一:《刑法的基础》,黎宏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7 页。,这为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奠定了根基。 因此,自由意志不只是一种假定条件,更是贯通于规范责任论所有概念之下的基底性内核,对于责任能力的诠释,也应是围绕自由意志作出的推论。
在康德看来,意志活动本就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活动,而一切意志行为的根据都在于自由。 作为一个先验性的概念,自由意志虽然无法在思辨理性的运用过程中被证实,却可以凭借实践理性落实为人们影响外部世界的实际行为。①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5、15、129 页。如果行为人具备自由意志,那么,他就能够在实践活动中运用以经验性为条件的理性能力为自己设定目标,而后促使自己去行使与目标相符合的对象行为,这无疑就是个体的理性能力,代表着个体的自主性。 如此一来,即使依然无法回答对“人类是否具备自由意志”这一哲学命题的追问,但却可以作出对“某个人是否具备自由意志”这一具体问题的回答,关键就在于考察他是否具有理性能力。 如果行为人是能够自主决定、自由决策的理性个人,即具备自由意志,可以对其实施的不法行为加以谴责。
自由意志与理性选择能力可以将构成要件行为的刑事可罚性归属于行为实施者。 依据行为刑法的基本立场,刑事可罚性系于行为人所实施的构成要件行为之上,一个人不可能因为他是一个“这样的人”而成为法定责难的对象。 同理,也不应当仅因他是“那样的人”而得以减免刑事责任。责任能力障碍阻却刑事责任,并非完全是基于特殊预防的目的限制刑罚惩处对象的结果,更需要从行为人的个体特征与构成要件行为之间的普遍联系推导得出。 行为人通常具备理性选择能力,因而某个构成要件行为是经由其感知、理解、推理和行动等环节产生的,是自由意志的产物。 通过这种方式,原本吸附于行为之上的刑事可罚性被传导给了行为人,行为人不是为自己是“这样的人”负责,而是为自己选择实施的具体行为负责。 然而,对于少数无责任能力人来说,他们之所以不是责任承担者,不仅是因为缺乏预防必要性,更为关键的是,他们所实施的构成要件行为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行为与行为人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可罚性就无法通过理性选择过程归于他们。
3.利弊权衡:国民遵守或违反刑法规范的动机
其一,一方面,一般人会被规范背后的强力威胁驱使着遵从法规范的要求,在理解刑法中行为规范与刑罚后果的内容是什么后,潜在的罪犯会作出理性选择,放弃犯罪活动;另一方面,现实的犯罪活动是行为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只是在成本—回报关系的效用计算中,除了刑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之外,还有诸多因素在影响着行为人的选择,比如,被抓捕的几率、各类犯罪收益等。 对于不同的行为人来说,处于天平两端的不同因素可能占据着不同的比重,因而最终选择也有所差异,但理性选择过程依然是普遍存在的。 如前所述,这也是理性选择理论被引介入犯罪学领域时的基本构想,并通过实证研究得以证实与发展。
其二,国民的理性选择能力足以帮助他们理解刑法规范蕴含的法秩序价值,这也是国民遵循刑法规范的动机之一。 根据我国《刑法》第2 条的规定,刑法的任务是保护国民的各类利益,同时保卫从长远看有利于全体国民的超个人利益。 立足于普通国民的视角,他们会希望自己的生命、身体、财产等利益得到刑法的保护,因而就会期望刑法是切实有效的。 也就是说,刑法不仅应当被遵守与适用,更重要的是实际上被普遍地遵守和适用着。②参见[奥]汉斯·凯尔森:《纯粹法学说》(第2 版),雷磊译,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14 页。于是,抛开具体的刑罚后果不谈,摆在国民面前的两个选项分别是:(1)与其他国民一起遵守刑法确立的行为规范,放弃侵害他人的企图,面对来自他人的威胁时,可以寻求法规范的庇护,依靠国家提供的合法程序来定分止争;(2)不放弃实施私人暴力的可能,致使法规范丧失效力,在动荡的社会中力图保全自身。 由于国民是寻求自我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人,所以必然会选择维护而非破坏法秩序,使具有刑法规范就像运作中的机器那样发挥效用。
可以认为,刑法规范对国民的指引作用,正是建立在自利理性人的基础之上,考虑了国民可能放弃或实施犯罪活动的混合性动机。 如果仅从身体能力层面诠释责任能力,则无法诠释刑法规范规制国民行为的基本原理。
4.辨识能力、控制能力本质上就是理性选择能力
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剖析,可以以我国《刑法》第18 条前3 款中的精神病人为参照系。 一般认为,精神病人减免责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医学要件,行为人必须是“精神病人”;二是法学要件,行为人必须丧失或者部分丧失辨识能力或控制能力。①参见刘协和:《论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标准的制定》,载《中国司法鉴定》2008 年第6 期,第23 页。刑法研究的焦点通常集中于后者,但围绕着辨识能力与控制能力的争论从未消弭。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2016 年发布的《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指南》(以下简称《评定指南》)规定,辨识能力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在刑法上的意义、性质、作用、后果的分辨、认识能力,也就是行为人对其行为的是非、是否触犯刑法、危害社会的分辨、认识能力。 而控制能力则是指“行为人具备选择自己实施或不实施为刑法所禁止、所制裁的行为的能力,即具备决定自己是否以行为触犯刑法的能力”。 如果将二者统合于“责任能力”的概念之下,其应有之义是:行为人可以感知、理解刑法规范的内容,并通过推理来决定自己是否实施违反刑法规范的行为。由此可见,《评定指南》同样将犯罪行为解读为行为人作出的理性选择。 因此,一个人能否作为归责的主体,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具有辨识行为与控制身体的能力,而在于他本身是否是具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个体,能否在作出违反刑法规范的决定之前,就明白自己的决定意味着什么,将面临何种刑罚后果,并据此实现自我支配,实施犯罪活动。
(二)精神病人责任阻却的机理不适用于醉酒的人
如前所述,我国《刑法》中并不存在有关责任能力的一般规定,因此,在明晰了责任能力的内核是理性选择能力之后,应当以第18 条中的精神病人为研究对象,以理性选择能力为推论基础,剖析我国语境之下责任能力阙如阻却刑事责任的内在机理。
规范与理论的建构,都不能违背先于法律而客观存在的事物自身结构。②参见[德]汉斯·韦尔策尔:《目的行为论导论——刑法理论的新图景》(增补第4 版),陈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前言第4 页。正如拉兹所说:“我们必须要发现事物是如何运作的,才能决定我们应当做什么。”③[英]约瑟夫·拉兹:《实践理性与规范》,朱学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年版,第6 页。晚近以来,脑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大脑中存在一个认知与控制的神经网络,能够完成一些独有的执行程序,比如,设定目标、制定计划、检测行为结果等,当其进入决策模式时,人们便得以评估潜在行为结果的价值,计划更远的未来。 简言之,这些执行过程的主要作用就是确保人们基于自由意志所选择的行为对自己来说是最有利的。④See Hirstein. W, Neuroscience and Normativity: How Knowledge of the Brain Offer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Moral and Legal Responsibility,16 Criminal Law and Philosophy 327,334(2022).这主要包括3 种能力:(1)形成指向相关目标的准确意图;(2)形成有效的联想过程,认识到计划和意图的关联因素;(3)正确行使推理过程,对意图、行为与结果之间可能产生的联系具有准确认识。①See Robert F. Schopp, Automatism, Insanity and The Psychology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89.一般行为人作为可归责对象的基本条件就是具备这种相匹配的生理机能。 因为国民大多都具有这些帮助作出理性选择的能力,因而同样的规则几乎可以适用于所有人。
不过,对于少部分患有精神障碍的人(《刑法》第18 条第1 款中的“精神病人”)来说,由于其自主神经系统的关键部分无法发挥作用,因而上述3 种能力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受到损害。 立足于刑法规范的视角,精神疾病会破坏行为人对法规范的认知能力,且波及意志因素,使其无法依据规范指导自己的行为。 换言之,对于精神病人来说,他们不能准确认识自己的行为是否触犯刑法,将会面临何种刑罚后果,以及行为破坏的法秩序价值,也不具有权衡利益并作出理性选择的能力,因而他们实施的侵害行为并不是自由意志的产物。 刑法不会期待他们遵从刑法确立的行为规范,更不会对他们实施的行为加以谴责,这是刑事责任得以减免的关键所在。 这同时也注定了这种机理只能适用于个别群体,例如,精神病人、大脑尚未完全发育的未成年人等。 因此,以责任能力阙如作为责任阻却事由只能是一种例外,对于醉酒的人、吸食毒品的人来说,这种责任阻却机理无法适用。
不可否认的是,当行为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一定数值之后,辨识能力与控制能力就会大幅下降,其暂时性的言行举止与精神病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有学者将原因自由行为称为“自招性精神障碍”②竹川俊也「自招性精神障害の刑法的評価:『原因において自由な行為』論の再定位(1)」北大法学論集69 巻6 号(2019 年)参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醉酒的人就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根据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纂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酒精所致的精神病性障碍,必须达到单独可以认定为精神病人的标准③Se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ed),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2013, p. 502.,因而单纯的醉酒并不在医学上“精神障碍”概念的涵摄范围之内。 在不具备精神病人这一医学要件的前提下,无论行为人饮酒与否,是否丧失辨认行为、控制身体的能力,都不可能终局性地丧失驱使自己权衡利弊得失的理性选择能力,这与行为人系精神病人的情形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 在本文看来,之所以《刑法》第18 条第4 款并未像前3 款那样对行为人醉酒后的辨识能力与控制能力进行具体划分,甚至没有提及二者,原因便在于此。 在规范论的视野下,醉酒的人自始至终都是完全责任能力人,类似于前3 款中的“责任障碍状态”并不存在,对完全责任能力人加以惩处,也不具有可罚性上的疑窦。 这也意味着,《刑法》第18 条第4 款的规定本质上是一个注意规定,设立该条文的目的是提醒司法人员注意,醉酒的人无法等同于第1 款中的精神病人,不要将其误判为无责任能力人或限制责任能力人。
在行为人自愿摄入毒品的情形中,虽然不同种类的毒品都有可能导致行为人丧失或部分丧失身体层面的辨识能力与控制能力,但与醉酒的人一样,如果吸食毒品的人没有产生毒品相关障碍与精神障碍的共病,就不会陷入到类似于精神病人的责任障碍状态,仍要为自己实施的构成要件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指导性案例“彭某故意杀人案”的裁判理由也指出,行为人在实施杀人行为时虽然出现了精神障碍,但并非由于精神病的发作,因而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精神病人,也不需要作司法精神病鉴定。④参见《彭某故意杀人案[第431 号]——被告人吸食毒品后影响其控制、辨别能力而实施犯罪行为的,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编:《刑事审判参考》(总第55 集),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21 页。因而可以认为,司法者同样认为,不能将吸食毒品之后短暂言行举止失常的行为人与精神病人相等同,而唯有后者才能以丧失或部分丧失责任能力为由减免刑事责任。
以上解读可能面临的质疑是,将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根据重新落脚于精神病理学等经验性分析之上,有悖于规范论立场。 追本溯源,“自由”“责任”等概念自身是缺乏存在论基础的,也没有固定的含义,只是依据某些条件进行的归类,这些定义及其背后的评价性问题属于规范论的范畴,需要考虑的实质上是,行为人是否会被刑法期待遵从行为规范。①Vgl. Tatjana Hörnle, Kriminalstrafe ohne Schuldvorwurf: Ein Plädoyer für Änderungen in der strafrechtlichen Verbrechenslehre, 2013,S. 24.在本文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关涉两个层面:其一,由于责任能力的本质是理性选择能力,因而任何划分标准都应将其作为合理性内核;其二,如何以理性选择能力为出发点进一步筛选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个体,则属于本国实定法规范的权限,关乎合法性问题。 或者说,理性选择能力这一内核在不同的实定法规定中得以具体化。 《德国刑法典》第20 条、第21 条的规定表明,行为时是否具有实时的理性能力是衡量行为人是否具有责任能力的关键,而我国《刑法》第18 条前3 款虽然也强调行为时的理性能力,但为其框定了“精神病人”的医学前提,因而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障碍导致的理性选择能力阙如,才是我国语境之下刑事责任能力的边界。 责任能力概念所筛选的是规范接收者自身,而不是他们的实时状态,这是基于本国实定法作出的切实论断。 据此,纯粹饮酒、吸食毒品的行为,自然不会使行为人成为无责任能力人或限制责任能力人。
四、归责的具体化:注意义务之展开
由于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提出,原本就是为了解决醉酒的人、吸食毒品的人在表面上不具有责任能力的状态下实施犯罪行为的问题,所以,如何处理原因自由行为与同时存在原则可能存在的矛盾,是既有文献中的核心问题。 正因如此,前文花费了较长的篇幅来论证原因自由行为情形中的行为人具有实质意义上的责任能力,不能以责任能力障碍为由排除其刑事责任。 在完成了这一步骤之后,接下来需要检视的是司法实践中“原因自由行为=故意犯罪”的逻辑链条。
如果行为人故意地导致自己陷入近似于精神障碍的状态,且在实施原因行为之时就具有指向具体构成要件行为的故意,那么陷入醉酒状态只是其实现意图的环节之一,与“喝酒壮胆”的情形并无二致,应承担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 但在另一些情形中,行为人对饮酒、吸食毒品之后可能会实施某种犯罪行为毫无察觉,或者只能模糊地意识到存在这种可能性,但坚信结果不会发生,不具备故意要件中的“意欲”要素。 例如,在前述“龙某某故意杀人案”中,很难认为龙某某在吸食毒品前就具有杀害生母的意图。 学理中的释义难点便集中于此类过失的原因自由行为。②过失的原因自由行为主要包括两种情形,另一种是行为人于原因行为时点仅具有过失,但在结果行为时却具有故意。 参见[日]高桥则夫:《刑法总论》,李世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322 页。 不过,在本文看来,结果行为时点恐怕无法判断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与过失。由于过失犯罪的核心是注意义务的违反,因而在原因自由行为中考虑能否成立过失犯罪,也需要指明何为行为人的注意义务,并考察其是否具有履行这种义务的现实可能性。
(一)原因自由行为中的行为规范与注意义务
刑法会在犯罪发生之前对受法律约束的人的行为提出预期,虽然在过失犯领域中围绕着注意义务的本质与具体内容,存在着纷繁复杂的各类学说,但归根结底,注意义务的内核是刑法期待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或者放弃实施某种行为。 在挖掘注意义务的具体内容之前,确有必要探明原因自由行为中行为规范与注意义务之间的关联与界分。
第一,注意义务的设立,必须能够满足刑法所要求的避免法益侵害结果发生的目的。 如前所述,我国《刑法》第18 条第4 款是一项提示性规定,即使不设置或删除这一规定,司法工作人员也可以依据前3 款所包含基本的原理认定醉酒的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如果认为普通国民同样可以是提示注意的对象,那这一规定也必须附于各罪背后的行为规范之上,才能发挥一定的指引作用。 例如,将《刑法》第18 条第4 款与第232 条相结合,国民能获知的行为规范是“禁止在醉酒状态下杀人”,或是“禁止杀人,醉酒状态下也不例外”。 但提示性规定并不具有独立的规范目的,无法单独发出行为指令或设定注意义务的具体内容,不能将之与过失犯中科以注意义务的注意规范相混同。从这个角度来看,构成要件模式将“禁止陷入醉酒状态”视作注意义务的内容,显然缺乏合理性。
第二,注意义务的违反,并不等同于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 过失犯中注意义务的设定,常以前置性行政法规等为依托,最典型的无疑是交通肇事罪以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为前提,在此类案件中,注意义务的违反,可能发生于参与公共交通之前。 因此,单就发生时点而言,注意义务违反行为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可能具有时间差。 在归责理论的体系之下,注意义务的违反,相当于“创设或升高法所不允许的风险”,在原因自由行为的情形中,我们完全可以将结果行为视为行为人预先违反注意义务所创设之风险的实现过程。 这意味着,行为人对于注意义务的违反,可以早于具体的法益侵害行为,因而不必于结果行为时点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注意能力。
此外,德国刑法学界还存在一种极少数说——“扩张模式”,即通过扩张行为概念的方式将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连结在一起,追究整体的刑事责任。①Vgl. Franz Streng, „actio libera in causa“ und Vollrauschstrafbarkeit - rechtspolitische Perspektiven, JZ 2000, S. 22 ff.有英国学者持相近观点,See J. J. Child, Prior Fault: Blocking Defences or Constructing Crimes, in Alan Reed, Michael Bohlander eds., General Defences: Domestic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Routledge, 2014, p. 46.为了证明其可行性,论者选择从醉酒驾驶出发,主张行为人的义务可以扩及“不得使自己陷入不能安全的状态”。 诚然,可以认为《刑法》第133条之一确立了“不得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规范,但这种整体性规范的根据在于,刑法不可能设立单独的“不得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规范,因而必须与自陷于醉酒状态相结合。 但在原因自由行为的情形中,“禁止杀人”等行为规范已为各分则条文所确立,“禁止在醉酒状态下杀人”的核心仍然是“禁止杀人”,不应将“不得自陷入醉酒状态”也纳入行为规范的范围。
(二)注意义务的内容:采取积极的风险预防措施
如前所述,注意义务的内容应是依照法的期待,实施某种行为,或者放弃实施某种行为,以避免制造风险,或是排除、降低既存的风险。 过失犯相关的不同学说、不同领域实质上都是围绕着这一点为注意义务的具体化提出不同的方案。 原因自由行为情形的特殊之处在于,制造风险的危险源是行为人自己,而且这种风险会呈现出线性上升的趋势。 具体而言,法益侵害的风险肇始于行为人开始饮酒、吸食毒品之时,但此时的风险还只是一种远离规范保护目的的低限度风险,尚不具有为刑法所规制的价值。 但行为人摄入的酒精含量与实施攻击行为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正线性趋势,在持续饮酒的过程中,侵害他人法益的风险会逐渐升高,直至其最终丧失或者部分丧失辨识行为与控制身体的能力,继而实施法益侵害行为,此时,可以认为是行为人自己创设的风险最终实现了。
与此同时,在原因自由行为的情形中,行为人又居于监督保证人的地位,负有监督自己不对他人造成法益侵害的义务。①相近观点,Vgl. Susanne Beck, Neue Konstruktionsmöglichkeiten der actio libera in causa, ZIS 2018, S. 207 ff.这是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启动的危险的因果过程负责,确保危险不会转化为一种法益侵害结果。 也可以认为,只有行为人自己能够排除危险,依据排他性支配理论便可产生保证人义务。 因此,行为人必须思考的是,如何才能排除自己实施法益侵害行为的风险,或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对此,本文认为,可以拆解为如下两个步骤进行分析。
首先,行为人必须意识到这种风险的存在。 在本文看来,依据一般生活经验,就预见可能性而言,大致可以分出两种情形:一是根据自己的习癖与过往经验,行为人在饮酒、吸食毒品之前就能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在后续的过程中丧失辨识能力、控制能力,继而实施攻击他人的行为;二是在开始饮酒、吸食毒品之后,行为人发现自己正在逐渐失去辨识行为与控制身体的能力,甚至开始产生攻击他人的念头。
其次,需要追问的是,身处上述两种情形之中的行为人应当采取何种措施以排除或降低自己侵害他人的风险。 本文认为,在情形一中,行为人可以采取的积极性预防措施,是在饮酒或吸食毒品之前,将自己反锁在房中,或者预先拜托其他人帮忙看住自己,以此来杜绝自己之后伤人的可能性;在情形二中,在部分丧失辨识能力、控制能力之时,行为人应该凭借仅存的意识,示意身边人留意自己的状况,必要时限制自己的人身自由,或者马上停止饮酒、吸食毒品,并通过服用解酒药等方式使自己恢复辨识能力与控制能力,有效降低侵害他人的可能性。
概而言之,在原因自由行为的情形中,风险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因此,可以将结果行为与最终的法益侵害结果一并视作风险的实现过程,而注意义务的内容就是行为人必须采取积极的预防性措施排除或降低自己侵害他人的风险。 对于原因自由行为中的行为人来说,丧失辨识行为、控制身体的能力,并不等于注意义务的违反②部分学者认为注意义务的规范本质是能力维持规范,参见陈璇:《注意义务的规范本质与判断标准》,载《法学研究》2019 年第1期,第136 页以下。 本文认为,至少在原因自由行为的情形中,这种观点无法成立。,没有采取有效的预防性举措才意味着违反了注意义务。
(三)行为人履行注意义务的注意能力
在完成了“应注意而不注意”的判断之后,需要追问的是,行为人是否“能注意而不注意”。 原因自由行为情形的另一特殊之处在于,即使主张行为人自始至终具有责任能力,也无法否认其可能会在饮酒、吸食毒品之后失去辨识行为、控制身体的能力。 而根据“逾越能力则无义务”的原则,在超出行为能力的情况下,行为人也不会受到规范的约束。③参见[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论所谓“不被容许的”风险》,陈璇译,载《刑事法评论》2014 年第1 期,第224 页。因此,必须证明行为人在需要采取积极性的预防措施时具有足以履行注意义务的行为能力,一旦违反,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一方面,不同个体对酒精、毒品的耐受度差异很大,因而在饮酒、吸食毒品之后,不同行为人辨识行为、控制身体的能力的下降程度有所不同,侵害他人的可能性也因人而异。 基于此,在不同情形中,行为人须采取何种积极的预防性措施,应因时制宜、因人制宜。 换言之,注意义务的具体内容只能在个案中进行差异化形塑,形成特殊专属的判断标准。 或许可以将行为人大致分为3 类:(1)一个人在大量饮酒之后不会丧失辨识行为、控制身体的能力,确信不会实施任何法益侵害行为,他就可以不采取任何预防性举措;(2)一个人有一定的酒精耐受度,在开始饮酒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可以保有履行注意义务的行为能力,他也可以不采取事前的预防性举措,而选择在开始饮酒之后,密切关注自己的动向,必要时再采取排除或降低风险的措施;(3)一个人摄入少量酒精就会失去辨识行为、控制身体的能力,那他就应当在事前采取预防性措施。 因此,原因自由行为中注意义务的履行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不同的行为人对注意义务的违反,没有统一的发生时点,可能发生于开始饮酒、吸食毒品之前,也有可能发生于之后,但早于结果行为时点。 在此意义上说,原因自由行为中本就不应将实行行为限定为原因行为或结果行为。
在此可以类比忘却犯的情形。 在扳道工因疏忽未能履行职责导致火车相撞的情况下,注意义务的违反是以过失不作为的方式实施的。①参见陈兴良:《教义刑法学》(第3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89 页。刑法规范进行否定性评价的对象是扳道工没有履行扳道职责的不作为,对于扳道工来说,他在火车驶来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可以去履行这一职责。对于原因自由行为中的行为人来说同样如此,法规范给予否定性评价的不是他们应当在何时采取何种预防性措施,而是他们最终没有采取积极的风险预防措施,或者采取的措施不足以排除风险,导致由行为人创设并持续上升的风险最终实现了。
另一方面,虽然不具有量化判断标准,但因为行为人是自己的监督保证人,所以对自己可能制造的风险必然具有超越一般人的特殊认知。 比如,自己的饮酒限度处于什么水准,饮酒当时是否存在身体不适的状态,大概摄入多少酒精就会失去辨识行为、控制身体的能力,因而要求接受行为指令的行为人在个案中作出审慎判断,也并非难事。 个案中何时应采取何种具体的风险消除手段,完全可以交由行为人自行判断,只要具有理性能力的他们知悉一点:醉酒状态下也不可以实施法益侵害行为,而这正是《刑法》第18 条第4 款所宣示的。 另外,即便行为人之前没有接触过酒精、毒品,也能够在饮酒、吸食毒品之前意识到自己可能在后续的过程中丧失辨识行为、控制身体的能力,更应当采取事前周密的预防性措施,如提前恳请同行者关注自己饮酒、吸食毒品之后的言行举止,一旦流露出攻击倾向,应当加以制止。 如果行为人未能进行审慎判断,没有采取一定的风险预防举措,就可以评价为违反了注意义务。
综上,本文对原因自由行为中注意义务的研究可得出三点结论:第一,注意义务的内容是要求行为人采取积极的风险预防措施,排除或有效降低自己侵害他人的风险;第二,个案中应当采取何种具体的风险消除手段,必须根据行为人的身体状况等因素进行差异化形塑,可以交由行为人自行判断;第三,违反这种注意义务的表现是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风险预防措施,或者采取的措施不足以排除风险,导致侵害法益的风险逐渐升高并最终实现,法规范会对此进行否定性评价,因而成立过失不法。
(四)个案分析
在前述“郑某故意杀人案”“龙某某故意杀人案”中,郑某、龙某某二人均在吸食毒品之后产生幻觉,继而杀害自己的血亲。 如果采用逆向反推的思维,从避免结果发生的效果出发,就不难发现哪些行为对于行为人来说是可以期待的。 具体而言,毒品具有使中枢神经系统兴奋、抑制或者致幻的作用,导致吸食毒品的人可能产生被害妄想、幻视、幻听等症状,进而实施暴力性攻击行为,这一点经过国家、社会层面一系列的禁毒宣传活动,早已为人所共知。 在这种情况下,郑某、龙某某首先可以选择放弃吸食毒品,以确保自己不会在近似于精神障碍的状态下实施犯罪行为。 不过,虽然放弃吸食毒品可以从源头上避免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但《刑法》并没有设置具体的罪名以确立“禁止吸食毒品”的行为规范。 在缺乏禁止吸食规范的前提下,郑某、龙某某二人也可以通过在吸食毒品之前将自己反锁在房中,去远离人群的郊外独自吸食等方式,彻底排除自己伤人的可能性。 因为可供选择的风险预防措施具有多样性,而刑法只要求最终确定能防止结果的发生,因而郑某、龙某某原本可以自由选择采取何种具体的预防措施,刑法对他们的这种期待也不存在过度限制其行动自由的风险。 但他们最终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就应当认定他们违反了注意义务,最终的法益侵害结果可以归属于二人。 然而,由于郑某、龙某某杀害的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因而除非在案证据足以证明他们事先已经认识到自己会在吸食毒品之后实施杀害父母的行为,并具有实现这一结果的意图,否则不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而应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刘某某故意杀人案”则稍有不同。 如前所述,刘某某在饮酒之后无故殴打路过的行人李某某,导致李某某因重度颅脑损伤而当场死亡。 站在事后的立场不难看出,刘某某本可以采取不少能防止结果发生的预防措施,比如,在明知自己醉酒之后很可能实施暴力性攻击行为的前提下,他既可以严格控制自己摄入的酒精含量,也可以在察觉自己的言行逐渐开始失控时马上停止饮酒,采取一定的方式醒酒,还可以提前请求一起饮酒的同伴,在自己出现袭击他人的倾向时控制住自己。 事实上,刘某某持续饮酒的过程,也是他实施法益侵害行为的风险逐渐上升的过程。 如果在此期间,他可以认识到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会导致侵害结果的发生,却以放任或期待的心态任其发生,就应当承担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 反过来说,如果刘某某确实没有认识到源于自己身体的风险,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应当针对这种风险采取某种预防措施,或者虽然认识到这种风险,却认为即使不采取任何措施,风险也不会发生,那就认定其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
五、结 语
如何产出本土的教义学成果,是摆在所有研究者面前的棘手难题,可能的努力方向有二:一是搜寻产生于现实社会、独具中国特色的问题;二是认真对待本国的实定法规范。 《刑法》第18 条第4款是我国本土特色的规定,许多学者对该条款加以批判,认为其过于笼统粗疏,应当参考域外的立法范式加以修订。 在本文看来,我国没有采用域外“心神耗弱”“心神丧失”等表述,而是直接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相当于是省略了推理步骤,直接给出了参考答案。 而本文的写作意图正是通过逻辑演绎的方式证明这个答案。 关于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基础,构成要件与例外模式的解释进路都无法令人满意,二者不仅欠缺合理性,而且无法契合于我国的实定法规定。 本文主张,责任能力的本质是理性选择能力,根据《刑法》第18 条前3 款的规定,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障碍导致的理性选择能力阙如,才是我国语境之下刑事责任能力的边界。 在原因自由行为的情形中,醉酒的人、吸食毒品的人只会暂时性地失去辨识行为或控制身体的能力,但不可能失去责任能力,并非不值得刑法评价的无责任能力人,无法适用责任能力障碍这一责任阻却事由。 同时,虽然行为人于结果行为时点丧失了行为能力,但注意义务的内容是在丧失行为能力之前就采取积极的预防性措施,防止自己对他人造成法益侵害,因而不会有悖于“逾越能力则无义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