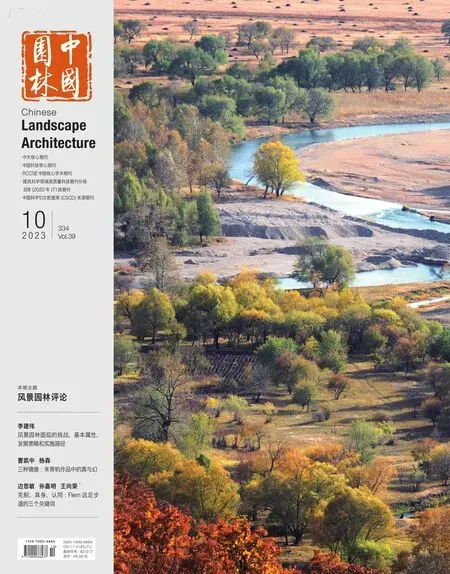解释学
——风景园林的一般方法论刍议
2023-12-27张振威肖涵岳毛颜康
张振威 肖涵岳 毛颜康
中国近40年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也孕育了具有现代实践性与学理特征的中国风景园林学[1]。毋庸置疑,中国风景园林无论市场规模(实践强度),还是设计师及学者群体规模,都可谓是全球前列。但是,相比之下,中国风景园林的理论贡献与知识生产还不足以匹配实践的强度、厚度与深度[2]。有一种现象值得反思,即作品非常多,但围绕作品的知识生产却很缺乏,甚至设计师关于自己作品的诠释也不充分。在理论上呈现为风景园林批评学的缺位[3]。与此相对的是,今天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理论,以规划设计师“如何作为第三人称,客观、正确地给出答案”为主,侧重一种理性、客观、功能、科学的自然科学方法或工具论,而愈发忽视景观本体意义、作品意涵及主体诠释作为一种基本设计方法的意义。
一般方法论是人们对世界存在和物质运动规律的解释,对日常概念思维和各门科学学科的思维有着较广泛的指导意义[4],“阐释的所有能指与所指都无法挣脱意义和方法2个层面的终极表达和表现”[5]。本文认为,解释学既是建构关于风景园林作品意义、含义、价值的本体论知识的方法,又是具有“元方法”意义的一般方法论,在风景园林方法论范畴中具有基础性地位。
1 作为一般方法论的解释学
解释学(hermeneutics,又译为释义学、诠释学等)是一种关于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解释学起源于古希腊哲学,早期主要针对《荷马史诗》(Homeric Epic)、《圣经》等典籍进行文义解释,也被称为解释技艺学,或称局部解释学。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1768—1834)将“理解”而非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有关正确理解和避免误解的普遍解释学理论,被称为一般解释学(hermeneutica generalis)[6]。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解释学,将解释学引入哲学范畴,将“理解”视为人类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或可称人文科学)的基石和方法论[7]。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完成了解释学向哲学的转身,关注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此在(Dasein)解释学”,“将方法论的解释学理论发展为一个基础的存在论问题”[8]。伽达默尔把意义的生成归结为主体与文本之间的“视域融合”[9],提出解释学循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哲学解释学体系。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和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的解释学仍关注“理解如何可能”,其深层解释学的内核是批判性反思。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等将解释学推进到后现代主义,核心关注文本间性及意义多样化问题。由此,解释学史共历经局部解释学、一般解释学、哲学解释学和后现代主义解释学4种阶段和形态[10]。
张汝伦认为,现在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定义来规定解释学的领域,但主要有6种规定:1)圣经诠释理论;2)一般的语言学方法论;3)一切语言理解的科学;4)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基础;5)存在和存在理解的现象学;6)各种解释系统[8]。意大利解释学家吉安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1936—)将解释学喻为“共同的话语”(Koine),哈贝马斯认为解释学具有方法论意义[11]。
方法论意义的论述十分重要,虽然被喻为人文科学方法论,但自然科学同样视理解为认知的核心概念——理解是科学的核心目标,试图实现核心的善(central good),其价值超出了知识的价值[12]。在自然科学中,解释是理解的一个必要性条件。因此,我们可以超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视解释为一种知识获取的普遍途径,解释学方法也成为一种可广泛适用的一般方法论。
风景园林理论与实践是解释学的天然对象。詹姆斯·科纳(James Corner)主张以解释学途径介入风景园林的理论中,或许可以提供一种根植于文化延续性的本体论[13]103。他在1991年率先以解释学理论中的“文本”来关照风景园林,提出了“诠释性景观”(hermeneutics landscape)概念,将景观视为“一个有待解释和嬗变的文本”,故而呼应了古典解释学含义。西蒙·斯沃菲尔德(Simon Swaffield)在《风景园林理论读本》一书中进一步将科纳的诠释性景观归结为解释性理论(interpretive theory),并认为解释性理论是区别于工具性理论(instrumental theory)和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的第三类理论,是一种独立的知识组织方式[14]前言。他将杰克逊(J.B.Jackson)式景观历史研究归类于解释性方法范畴。由此,斯沃菲尔德切既切中了解释学在风景园林中的核心地位,又点题了关于“存在”本体论的哲学解释学含义。
笔者认为,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15],解释学除为风景园林提供人文现象的综合理解与阐发之外,还应包含一种方法论能指。因此,风景园林解释学包含如下3个维度:1)关于风景园林作品的意义(meaning)和象征(significant)的解读;2)关于景观或场地作为一种存在的理解;3)通过将理解作为一种主体间性认知过程的设计方法。
2 知识论层面的作品解释
在整个解释学演变过程中,文本解释始终是解释学最核心的传统,正如施莱尔马赫提出“我们必须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作者”这一命题。
目前,关于作品解释最发达的理论成果集中于批评学领域。在艺术与设计类学科中,批评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学科地位。艺术评论家丹托(Arthur C.Danto)指出,围绕艺术作品的理论建构或艺术界(artworld)是由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和艺术史等做出的解释构成的[16]。文学批评认为批评离不开解释,差别只是在解释的对象、解释的方法及解释的程度[17]。郑时龄将建筑批评学(即元批评)视为建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8],并认为解释学属于基本学科——它涉及人类研究的特殊方法或人文科学,就方法论而言,建筑批评学与解释学有本质上的联系[19]。
解释学和批判不可分离。批评被视为一种动态过程和知识生产过程,同样涉及反思性的认识,进而涉及认识论和方法论[20]。批评学注重丰富关于作品的具体经验性知识,而解释学更注重研究“理解、解释”这一精神活动的目的、文体、对象、条件、性质、方法等[11,21]。换句话说,解释学是一个个批评经验的“理论化”过程,或者作为批评的方法论指引批评知识的生产。
本文借助并变通解释学家贝蒂(Emilio Betti,1890—1968)的四原则来阐述解释学区别于批评学的要义。
第一,诠释客体的自主性。贝蒂强调任何文本都有独立于作者和读者的“客观意义”。阐释者应排除自己的旨趣和任意解释,只是客观阐明含有意义的形式所含有的内容,从而达到客体化的建构。贝蒂实则强调对于作品本质的理解,这种理解可能是作者也未曾谋划的一种公认共识的存在。在风景园林作品解释中,我们可以将这种自主性理解为一种目的论,即在把握原作精神的基础上提出一种终极解释。这要求我们既不能无视或忽视设计师的原有意图,又要进行全面、整体的阐发。
第二,理解的整体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可视为自主性的方法,即要求把握作品的完整意义,“要求阐明一切参与构成含有意义的形式的因素”[22]。在风景园林作品的解释上,即采用制度解释、社会解释、历史解释、文脉解释、语言学、符号学、现象学等综合解释方法把握作品的多维含义,并能厘清其中的结构性关联。
第三,理解的现实性原则。现实性是指解释主体的存在与个体差异的现实性,但仍要以客观化的意义为依据,通过文本的语言系统和历史语境而开展能动的解释。首先,这里涉及主体能动性和客观性标准的问题。作为经验性学科,风景园林阐释者的智识和生命体验是解释的先决条件。作品传达的是设计师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以“经验”的形式表现出来。阐释者即通过语言系统来理解并通过移情这种心理活动来完成“心理重建”。其次,涉及理解风景园林的历史观问题。我们无法把历史当作纯客观的不以认识主体意志为转移的客体,而是要在我们与历史的对话中,在历史与现代的整体视界中,完成对历史的理解。这个过程即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和“视界整合”。我们在阐释作品时,首先要建立一种历史观——即不是只把历史当作一种考据的史实,而是结合古今来综合阐释其意义。
第四,解释意义的和谐原则。这里仍指的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虽然贝蒂反对解释循环,但实际上他论述的仍然是解释的发生与发展问题。解释是不断循环上升的,即柏拉图所说的“上升的辩证法”。解释学也并非是真理,而是不断通向真理之路。
此外,解释学自身的核心议题,诸如文本解释类型与分类(认识、创造与规范)、解释的标准(合法性、相应性、规范性、连贯性)、解释的原则(自主性、解释的循环与视域融合)、解释的能动性(客观性与主观性)、解释的本质(艺术领域观赏VS解释、自然科学说明VS解释、人文科学理解VS解释),都是评判和把握解释的重要理论源泉,应在风景园林的批评学和解释学中受到重视。
相比建筑、艺术等学科,风景园林批评和风景园林解释学的发展都较为滞后。胡玎等曾用谷歌搜索建筑评论和景观评论的条目,结果相差2个数量级[23]。王绍增早在2008年即呼吁《中国园林》应该带头开展风景园林批评并组织了专刊[24]。李景奇、宋本明、慕晓东等发展出风景园林批评学的框架[3,25-26]。虽然风景园林批评学和解释学都处在萌芽阶段,成果也不多见,但已经出现了面向风景园林的解释学萌芽。青锋用艺术批评理论路径解释了斯卡帕的布里昂墓园之“意义”(meaning),并提出作品的意义是建构风景园林评论学的一种经典路径[27]。实际上,青锋重申了从古典解释学到后现代解释学进程中一直作为解释学最正统、最基本的文本解释之传统,也回应了利科“回归文本”的重要性。以“意义”为旨趣是解释学应有之义,更为重要的应是如何理解意义的解释学方法。总体而言,从作品解释角度,风景园林的解释学建构还停留在“观照”层面。
3 本体论层面的本原解释
解释学经由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而转向哲学解释学,探讨历史、社会及人自身的理解,从围绕解释方法与技术的古典解释学转变为解释世界本原的哲学解释学,进入本体论范畴。哲学解释学具体应用到各种社会实践生活中,就形成了围绕核心对象历史、存在及意义的探讨。对于风景园林而言,作为风景园林最核心的“此在”莫过于景观(landscape)一词。
景观解释与风景园林设计作品解释有同源和同构性,作品的终极意义往往也是对景观本原的探究。但与作品不同的是,对景观本原的理解要更超脱于作品评论而指向关于景观的普遍化真理或公认理解。笔者认为,解释学从2个方面渗透到景观本质探源当中。一种是本体论层面,将景观作为一种存在形成了多样的解释。这一领域,连同景观的概念与定界,是风景园林学、地理学、设计学、艺术史、图像志等领域共同关注的话题,无论古今中外都有丰富而深刻的阐发,形成了诸多理论学派。将景观视为一种存在是风景园林学的一个元问题,这一问题的基础方法论便是解释学的。从科纳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概念、理论体系的套用,他都深受海德格尔哲学解释学的影响。在保持整体框架的前提下,他将作为本体论的历史转化为一种历史方法——哲学家视历史为一种文本来解读其规律与意义,而设计师将历史作为解读场地与景观文脉的一种结构要素。另外,景观解释一直呈现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评论模式,强调解释“视角”的多样性以抵达景观的多义性、可能性。曼宁(Warren H.Manning,1860—1938)用的10种棱镜说来解释景观[28],瓦尔德海姆(Charles Waldheim)主编《Is Landscape…?Essays on the Identity of Landscape》(中译本《何谓景观?景观本质探源》)一书从文学、绘画到生态、技术等14个视角透射景观的本质。
第二种是从认识方法层面,景观理论发展渗透着传统人文科学方法的理解与欣赏方法、自然科学中的理解和说明方法,以及社会科学中的批判解释方法。
其中,重要一支是从环境伦理学视野下的环境解释学,透射到景观作为一种环境介质或环境客体的景观解释学。随着《解读自然》(Interpreting Nature)的出版,环境解释学兴起,此书的序言中阐明了自然可以被解释的多种可能性。解释学提供了一种解释自然的方式。在理论层面,关注环境正义,致力于理解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在实践层面,以环境行动主义的形式,解决现实世界所面临的环境危机[29]。荷兰景观活动家威廉·范·图恩(Willem van Toon)提出了“可读性景观”(legible landscape)的概念,指出景观可以像有意义的文本一样被阅读。2004年,荷兰环境教育协会(IVN)基于图恩提出的“可读性景观”这一概念,提出“文化导览”活动,即由自然导游在社区中组织为期数小时的短途旅行,以教导当地居民“阅读景观”,从而能更深入地了解某一特定景观的特征、结构和意义。IVN区分了“阅读景观”的4种方式,包括垂直结构、水平结构、季节性构成和文化历史[30]。
景观解释的发达为景观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奠定基础。“景观”一词在欧洲成为一种显学。在英国景观研究(landscape studies)是与风景园林、建筑学、城市规划并行的学科专业方向。英国每个郡都有景观制图和景观地方志,其国家政策、法律和国家部委中有直接以“景观”命名者,并有像《欧洲风景公约》(European Landscape Convention)这样的国际法作为上位支撑。景观作为人地关系的一种媒介,不是止于科学家、设计师、哲学家的纸面探讨,而是实现了一种从学科到国家制度与社会意识的社会建构。作为学科基础的解释学功不可没。
回到理论层面的探讨。景观意义的探讨映射的是一部风景园林思想史。关于风景园林理论的判断,一派代表理性主义和理论批判,认为风景园林尚未建立正统的理论体系;另一派后现代主义观点认同景观理解应呈现多样化特征,用斯沃菲尔德的话说,非但不足,而是“盛宴”(feast than famine)[14]227。笔者认同第一种判断,风景园林学虽历经百年,但中西方学者都在不停地追问什么样的理论体系应该是风景园林所独有的,而不是一味借鉴与引用的体系[14]前言?
关于景观解释一直处于往复的解释循环当中,它从作为一切事物认知基础的理解出发,但却从来没有深刻地授受解释学的穿透。尽管处于一种萌芽状态,科纳和杨锐为解释学的发展建立了2种不同的进路,值得深入阐述。
科纳以解释学作批判并回应现代景观理论的3个流派,认为以一种批判的、阐释的态度来表达历史、文化、传统、自然和艺术过程,是一条适合风景园林学科的理论途径。科纳的观点具有高度的解释学指向。他较早关照了风景园林解释学的2个哲学问题。一是景观理解的条件问题。他将风景园林解释学的根基总结为:情境式阐释、知觉的先验性、传统的复现。但实质上,他是在用设计师式语言重述海德格尔“理解的前结构”(vorstruktur)中的3个先决条件——先有(verhabe)、先见(vorsicht)、先知(vorgriff),将哲学语言转化成专业语言。二是解释学的功能问题。他认为解释学不关心方法论层面的、普世的理论途径(范式),反而注重存在论意义上的、特定条件的理论类型[13]99。他赞同存在主义解释路径的同时,明确否定一般解释学的方法论功用。
杨锐基于汉语言及整体论思维提出“境其地”理论作为风景园林学的解释框架[31],这一范畴由“境道”“境德”“境理”“境术”“境用”“境制”“境象”“境意”8个基本范畴构成。与西方的棱镜说、多解说有着本质区别,“境其地”理论不是一个个视角的并置,而是一种关于景观本质、认知结构、形式要件、语言与语义的自主性理论。
4 从解释的方法到设计方法论
何卫平认为解释学在经历从局部解释学到一般解释学、从方法论解释学到存在论解释学之后,经历了由哈贝马斯和利科完成的第三次转向,即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相结合的解释学——注重批判性反思,同时注重经验分析的方法(empirical-analytic methods)和解释学方法的结合[20]。那么,解释学的转身是如何影响了设计方法及方法论的塑造?
笔者认为,大体有2条理论探索之路。第一条是风景园林学者沿着解释学路径的循环上升;第二条源于20世纪60年代一直持续的设计方法运动中潜化的解释学方法向各设计分支的渗透。
对于第一条道路,通常认为,规范性或者操作性方法是容易辨别并实施的,但设计师能动性的部分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因人而异的设计能力与默会知识,或将其归结为一种“心理移情”的心理学活动,最终陷入一种不可知论。莱瑟巴罗注意到此中的解释学要义。第一,场地解释与挖潜必须依靠设计师对解释的不断发展,理解对象的意义是依赖于理解者的,这是理解的条件问题;第二,通过批判和反思的不断循环,建立一种“客观化”的标准。他认为“除去面具”和“显露内在”的阐释学是以与场地对话的方式建立了设计的独特性[32]。我们经常用的地图术(mapping)和“刻画”(articulation)等技术性术语背后更底层的逻辑是阐释性和语义性。进而,可以说,关于设计师主体能动部分的设计方法,其本质是解释学式的,其基因建基于一种解释学传统。
另一种路径源于设计科学领域。1962年的英国设计方法会议标志着设计方法革命的开端。控制论、系统论、运筹学等科学理论深刻影响着设计工具与方法,此时设计方法的核心议题是如何通过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新工具破解作为复杂问题(wicked problem)的设计对象、过程及其规律。如我们熟知的卡尔·斯坦尼茨(Carl Steinitz)模型和方法即为建立在“三论”基础上的适用与创新。到了20世纪90年代,受认知心理学、结构语言学等学科影响,以尼格尔·克洛斯(Nigel Cross)为代表的设计思维学派认为存在一种类似于语言的先天思维结构,从而转向思维与认知研究,以期揭示设计师解决问题时的内部思维过程。他提出存在“设计师式认知方式”(designerly ways of knowing),设计思维的模式是与科学思维和人文思维的模式相并列的第三类智力范畴等核心议题[33]。
虽然这一范式影响广泛,其背后的认知学基础却很少有人论及。实际上,除去建模、图示等工具性、程序性方法,关于思维本质的把握仍离不开以“体验-理解-解释-再现-反思-重构”为核心内容的解释学方法。在关于设计理解的主体性(理解的有效性)、设计方法论(意义的建构)、设计思维过程(解释循环)等方面,解释学仍是探究设计与研究关系的基底性理论。在解释学的基础上高度融合设计师访谈、观察和案例研究、实验研究、模拟仿真(simulation)等研究方法及口语分析(protocol analysis)技术等经验分析的方法(empirical-analytic methods)[34],的确是设计方法运动的最新成果。它在解释精度和效度上提供了一种相对明晰、客观的评判依据和标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解释学的无限性和任意性缺陷。
此外,在设计方法层面,还存在借解释学之名的转译、隐喻等具体设计手法。如科纳评论哲学家德里达与建筑师艾森曼共同设计的拉维莱特公园投标方案,认为将7个“文本”缩放、叠加和移位“有利于不可复制的多重解读”[22]。与其说德里达借用了解释学最核心的“文本”概念来提供一种解释学设计路径,不如说是通过隐喻和转译的符号学设计手法用文本展现哲学家的空间理念。
5 结语
目前,解释学已经潜移默化地开始渗透到风景园林理论建构当中,闪现片段的光芒,但总体而言尚缺乏一种解释学视角的理论自觉与建构,需深入将解释学的原则、方法、关键概念与理论全方位照射风景园林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等理论内核。本文旨在发现解释学对风景园林学的形式功能,对现有风景园林解释学的闪光进行反思、批判的基础上,试图从传统解释学、哲学解释学、综合解释学3个向度探讨一种结构化理论,倡导一种基本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