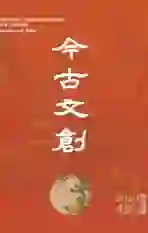从“诗可以怨” 观诗之“怨” 与“乐”的关系
2023-12-26赵书晗
【摘要】在中国传统文艺观念里,苦痛比快乐更能够产生好的诗歌。钱钟书先生《诗可以怨》指出,从古至今的中外文人学者普遍存在着重“怨”而轻“乐”的现象,但对于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以及诗中的“怨”与“乐”的关系,只是简单提及并一笔带过,在后继的文人学者的研究中也鲜少有涉及对这一问题的系统论述。如何理解“怨”?“诗可以怨”的作用是什么?以及为何“怨诗”比“乐诗”更受人重视?本文将就以上问题进行详细分析。
【關键词】《诗可以怨》;钱钟书;关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8-005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8.017
一、如何理解“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的相关论述最初见于《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何莫学夫诗”强调了“兴观群怨”对学诗者的作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则强调的是诗的功用性,即诗的社会教化作用。
何为“怨” ?郭绍虞将“怨”归为社会讽刺,强调了对消极情绪的宣泄,却偏离了学诗者这一主体,强调了诗的社会价值而非对学诗者自身完善和提升的价值。结合孔子“中庸”的思想并学诗者的角度看“怨”,“怨”更强调一种“怨而不怒”的状态,也就是说,诗能够让学诗者能够在学诗的过程中了解这个世界上的各种“酸甜苦辣”,在类似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虽然抱怨命运之捉弄,却不会偏激,以至于对自己的身心造成损伤。需要注意的是,孔子所谓的“诗可以怨”,并没有明确将“怨”归为一种消极情绪或对生活的否定态度。了解世界的酸甜苦辣,其中也包括“甜”这一积极方面。
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中,首先援引了《论语·阳货》中的上述语句,并直接采用了其中的“可以怨”作为自己文章的题目和主要论题,但很明显的是,钱钟书先生此处的“诗可以怨”与《论语·阳货》中的“可以怨”不尽相同。
内涵上,《论语·阳货》中的“可以怨”强调诗对学诗者的教化作用,学诗者可以从诗中获得情感、态度上的提高,用一种“怨而不怒”的态度对待生活中发生的种种;《诗可以怨》则并未谈及学诗者这一主体,而强调的是诗人作诗时的情感、态度,是以一种积极的心态看待生活还是以消极的态度看待生活。
外延上,又分为“诗”的外延和“怨”的外延。《论语·阳货》中的“诗”特指《诗经》;《诗可以怨》中的“诗”则泛指从古至今的各种句式整齐、具有韵律的诗。至于“怨”,《论语·阳货》中的“怨”既包括对生活的不满,也包括对生活的乐观,并无明显偏颇。《诗可以怨》中看似钱钟书先生虽然承认了欢愉之诗的存在,但明显存在着重愁怨轻欢愉的态度。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中的“诗可以怨”,是指作诗者主体在面对实际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时,能够通过作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态度、抒发自己的情感。本文的“诗”与钱钟书先生所谓的诗类似,均是广义上的诗;又因本文要论述诗之“怨”与“乐”的关系,故“怨”仅仅指的是诗的愁苦、怨愤情绪的一面;至于诗的欢愉、快乐一面,则被明确置于“乐”的范畴之中。
二、“怨”诗多于“乐”诗的原因
钱钟书先生在文章中指出,“怨”诗在质量上未必比“乐”诗要好,但好的“怨”诗在数量上确实比好的“乐诗”要来得多。“怨”诗本身的基数就远远高于“乐”诗,故好的“怨”诗多于好的“乐”诗也在情理之中,只是究竟为什么从古至今的诗中,多见“怨”诗而少见“乐”诗,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一)社会现实的打击
如果仅从字面上去理解诗的内涵,我们会发现,其实“乐”诗也并不在少数,在诗人描写对自然景观的赞美与对山水田园的向往时,表面上并不会表现出过多的“怨”的心态;但只从字面上理解诗意是浅薄的。
诗人对自然景观的赞美,往往不单纯是对风景的写实,不仅仅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而更多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描写自然景观,是为了表达诗人自身的情绪与状态;读诗者在品读诗文时,应该透过自然景观看到诗人作诗时的心态,这些心态是苦还是乐,又要具体分析。例如,对于归隐田园的诗人来说,他们创作田园诗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性本爱丘山”,本身就对山水田园心存向往;另一方面——往往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社会现实生活的打压。古代的文人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深远,如果不是受到社会现实的打压,诗人们往往也没有适当的导火索致使他们把归隐田园的想法付诸实践。
因此,读诗者在了解诗人的创作背景之后再去读诗,就会与初读时有不一样的体会,就能够理解“乐”诗背后时常蕴含着的浓浓的“怨”的意味了,因而表面上的“乐”诗在深层上还是一种“怨”诗。
(二)世人的普遍性格
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讲求“克己复礼”[1]等思想观念以及“食不言,寝不语”[1]等行为规范,强调世人在社会中的身份、行为和等级秩序。与尊崇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相比,儒家的各种礼教思想是对个体言行举止等各方面的约束,限制了人与生俱来的对自由的向往。当然,这里并不是要否定这种约束;相反,社会需要这种约束来维持秩序,以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同时,佛教中也有“众生皆苦”的观点,人生于世是为来世“修福”,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今生必须要对自己的言行进行约束。正因为这种偏向于内敛、收束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作用,从古至今,世人似乎就对社会生活抱有一种哀怨、愁苦的态度,形成了收敛、克制欲望的性格。因此,因“怨”而作的诗更能够引起人的共鸣,这种共鸣会使得“怨”诗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更容易流传于世,从而在后人的统计中,“怨”诗也就较“乐”诗更多一些,也就逐渐占据了上风,形成“怨”诗多于“乐”诗的现象。
此外,在人性观上,从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可以看出,人性里存在着对他人不幸遭遇感同身受的同情心,同时也存在着对他人欢愉幸事的嫉妒心。出于嫉妒,人们并不过多关注他人的愉悦,认为他人的愉悦与己无关;而出于同情心,人往往会对他人的不幸感到悲伤与不平,仿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一般。正因有这种同情心的存在,促生诗人因苦痛而作“怨”诗的动机;这种同情心的存在,也正是“怨”诗相较“乐”诗更能够流传于世的又一原因。
(三)“樂”本身的特性
“乐”本身趋向于发散,这在钱钟书先生的文章中也有表述:“乐的特征是发散和轻扬,而忧的特征是凝聚和滞重。欢乐‘发而无余’,要挽留它也留不住,忧愁‘转而不尽’,要消除它也除不掉。”[2]通俗来讲,人们在快乐的时候更乐于与他人分享或者通过一场狂欢把这份快乐发散出去。然而,人们往往在经历一场狂欢之陷入惆怅,因为狂欢时的激动、兴奋和狂欢结束后的平静、寂寥相差过于明显,让人不禁渴望回到狂欢时的状态,然而人又无法轻易地回到狂欢的状态中,因而在这种狂欢与寂寥的对比之下,人就容易陷入比往常更深的愁和怨之中,这也就是所谓的“乐极生悲”。因此,人本身就会因“怨”作诗,再加上因“乐极生悲”而作诗,这也导致了“怨”诗相对多于“乐”诗。
三、诗之“怨”与“乐”的辩证关系
尽管古人留给我们可供研究的诗中,“怨”诗远远多于“乐”诗,但是这并不代表“乐”诗不值得我们关注。“怨”与“乐”是一对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转化的矛盾。古人之诗多强调“怨”的方面,但如果不知道“乐”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无从怨了;正是因为有“乐”的存在,才能在对比之下反映出“怨”的不快与愁苦。
(一)“怨”与“乐”的相互转化
“怨”与“乐”是一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在前文已经提及有关“乐极生悲”,即“乐”转化为“怨”的问题;相应地,“怨”也能够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乐”。
钱钟书先生在阐述司马迁与钟嵘对“诗可以怨”理解的不同时,用“同一件东西,司马迁当作死人的防腐溶液,钟嵘却认为是活人的止痛药和安神剂”[2]来进行概括。这里所谓的“同一件东西”就是指诗。之所以将诗当作“死人的防腐溶液”,是因为司马迁认为诗人作诗的目的是避免“姓名磨灭”,着眼于诗在诗人身后所起到的作用,能够使诗人“死而不朽”,其思想和感情会在诗中得以保存和流传。而钟嵘却强调诗在诗人生时所起的作用,能够让诗人与艰辛冷落的生活相妥相安,一个人潦倒苦闷,全靠“诗可以怨”这一种“止痛药和安眠剂”来获得派遣、慰藉和补偿。不论是哪一种作诗目的,诗人都能够在作诗后得到精神上的补偿和慰藉,从而舒缓诗人内心的怨气和不平,消极情绪得以消解,实现了由“怨”向“乐”的转化。
另一方面,生活本不是一帆风顺,有些人会在就此沉沦、一蹶不振,而有的人会在悲戚中仍然心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在国之兴衰上,有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那种对改变社会风气、扭转百姓生活现状的大气磅礴的愿望。在细腻情感上,有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对团圆欢聚的向往;也有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细腻深沉的温情。在生命哲思上,有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对新旧更替、社会发展的期待和“暂凭杯酒长精神”的苦中作乐的乐观心态;陆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对生活阴暗的积极心态。李白更是一生留下诸多因“怨”生“乐”的诗篇:“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自信,“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情,“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高昂……都体现着一种在生活怨愤之中的乐观心态和对“乐”的向往,也体现着由“怨”向“乐”的转化。
(二)“怨”与“乐”的相互融合
矛盾双方的相互融合,体现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上。诗人在“乐”时,往往不能忘记“怨”的存在,就像钱钟书先生所说:要消除它也消除不尽。
相应地,人们的生活也有“怨”中有“乐”的情况发生,这里主要表现为古人的各种诗会活动,或者是聚会上人们一起创作的诗集。受儒家入世思想和佛教“来世今生”思想的影响,古人对生活持有悲观态度,养成了收束的性格,惯于从消极的方面思考。在这种消极悲观的大环境下,古人为调节心理,也时常会有“乐”的活动展开。例如,《红楼梦》中多有诗社活动,尽管《红楼梦》中的诗多有预示人物命运的作用,但在文章的语境里,作诗者由于当时所处的氛围是一种积极欢乐的氛围,所以作诗者尽管内心常含着愁怨,作出的诗也往往不再是诉“怨”而是表达对当下的“乐”的享受抑或是对生命的哲学思考。
儒家的礼教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世人悲观“怨”世的心态,但我们不能完全消极地看待儒学。尽管都是造成世人“怨”的性格的原因,认为世事皆苦,但儒家终究在目的上与佛教思想是相排斥的。佛教认为,今生的苦是为了来世的乐,因此今生必须要“享受”这种苦、与之共沉沦。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则正相反,他们并不否认生活中的苦,但我们更应从这种苦中寻找乐的存在。“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1]尽管生活条件十分艰辛,但并不是一点可乐的事都没有。“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1]人如果努力去学习、工作,尽力去寻找生活中的“乐”,人就能够“乐而忘忧”,暂时忘记生活中的不悦与愁怨,忘记衰老与死亡带给人们的恐惧与不安。往长远来看,孔子的所谓礼教是为了世人获得更好的社会生活、在这种苦乐交织的社会环境中尽力去享受、去寻找生活中的乐之所在。
以《论语》为代表的孔子思想看似是对个体自由的束缚,但实际上自由并非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了秩序和规律,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做的事,为了追求所谓自由而各自为营,其结果终究是谁都无法达成自己想要达成的自由的目的。而在社会规律的约束下去实现自己的自由,在不影响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去践行自己的自由,才是孔子所强调的礼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综上所述,孔子的礼教不是理所当然的悲观主义,其思想恰恰是充满希望的乐观主义,教导人们如何在绝望中点燃希望、在怨愤中寻找欢愉,而且孔子的这种乐观主义思想在后世的文人诗人中也有所继承。
前文提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这只是禅宗所想表达的对山水的第二层理解,最后一层则是“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山水田园、自然景观,它们始终是那个样子,并不因人的心情状态而发生改变。由这一思想生发出的对生活的冲淡以及对生命、宇宙的思考,在魏晋以来的文学创作中多有表现。陶渊明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3],《饮酒(其五)》全诗不提一个“怨”字,为读诗者描绘了一个远离世俗、归隐田园、与林鸟相伴的幽美景象。时代的兴衰更迭确实引发诗人对社会动荡的感慨,“怨”之一字潜藏在内心之中,而他归隐田园多年养成的沉著冷静的性格又令他对世事抱有泰然自若、苦中作乐的态度。王羲之作《兰亭集序》,整体呈现出“乐——怨——乐”一波三折的心路变化。初时体会宴会游玩之乐,在饮酒叙乐时,突然在怀抱自然之时兴发了对生死的思考与悲痛之情,“怨”从中来:欢愉之中的人们常会“不知老之将至”,短暂地忘记了衰老与死亡,但它们始终存在。但正因人生苦短、生命变动不居,人们更应对生活充满向往和热情,在短暂的生命中尽可能发光发热、享受生活之“乐”。衰老如何?那是我多年精彩的结果。正如曹操所作:“烈士暮年,壮心不已。”[4]老当益壮,是对生命的尊重、激情与热爱,是“怨”与“乐”相互融合的生动表现。
四、结语
古代的文艺研究者常过分关注诗人因“怨”而作的诗而忽视“乐”的重要性,司马迁认为诗“大抵圣人发愤之所为作也”,否认了“乐”诗的存在;韩愈论诗“欢愉之辞难好,穷苦之言易工”,因好的“怨”诗远远多于好的“乐”诗就认为只有“怨”才能作好诗……诸如此类,皆片面地看待了“怨”与“乐”的关系,存在着逻辑上的错误。后世的文艺研究者则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厘清诗之“怨”与“乐”关系后,我们发现,作“怨”诗和“乐”诗的并非两群人,此两类诗人往往是相互交叉和混合的,即既作“怨”诗,也作“乐”诗。
厘清诗“怨”与“乐”的关系,不仅对我们文艺研究者有着重要意义,同样地,对读诗者也会产生深刻影响。《论语·阳货》认为诗可以“兴观群怨”,读诗者能够从诗中品悟到各种哲思、不断进行中自我人格的发展与完善。了解诗之“怨”与“乐”的同等重要的地位,就能够更好地践行孔子所谓的“诗可以怨”了。换句话说,读诗者在领略各诗人的怨愤与欢愉的过程中,体悟生活之苦、同时不忘生活之乐,进而在现实生活中敢于拥抱社会生活带给自己的不公待遇、与愤懑不平和解,同时也始终对未来充满信心,有追求美好和欢愉的勇气和动力。这符合孔子“使人向善”的终极目的,也是对诗的作用的正确理解。
参考文献:
[1]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2]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3](晋)陶渊明.国学典藏 陶渊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4](宋)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 上、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
赵书晗,女,汉族,山西大同人,山西大同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