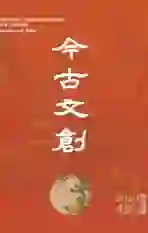被撕开的“面纱”
2023-12-26赵雅致
【摘要】在《面纱》当中,人物仿佛都生存在虚伪的“面纱”之下,冷峻犀利的毛姆将小说中的霍乱隐喻为一股强力,硬生生地撕开了人物用来掩饰真实自我的“面纱”。毛姆暴露出他们那看似正常的面孔下深深隐藏着的病态心理:霍乱暴露出的障碍心理、缺失驱使下的补偿心理、笑中带泪的压抑心理、死亡氛围下的冷漠心理以及无力反抗的宿命心理。这些心理的病态使小说中的人物一步步走向痛苦及自我折磨的深渊,但有着悲天悯人情怀的毛姆,又为我们展示了人对于强力的那无可奈何的顺应,揭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面纱》;毛姆;病态心理;隐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8-0029-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8.009
“卑鄙与伟大,恶毒与善良,仇恨与热爱,是可以互不排斥地并存在同一颗心里。”[1]人在很多时候是带着伪装的,在现实当中,我们往往只注意到了个体主动展示给他人的美好的一面,而在那美好“面具”的背后隐藏的那不为人知的丑恶一面往往被我们忽略。作为冷峻无偏袒的观察者,毛姆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总是乐于利用人无法抗拒的强力来揭开人性的“面纱”,犀利地解剖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病态。在《刀锋》中,毛姆以战争和死亡为强力逼迫主人公拉里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与自我存在的意义,在《人性的枷锁》中,他又以天生的残疾为强力来迫使菲利普不断地在痛苦迷惘与挫折当中探索。而在《面纱》当中,霍乱就担任了“强力”的角色,在霍乱那无法抗拒的死亡威胁下,毛姆揭开了人物虚伪的掩饰,将一个个病态的障碍心理揭示出来,透过那病态的人物,毛姆展示的又是人无力对抗强力的无可奈何。
一、霍乱暴露出的障碍心理
首先是偏执型障碍心理,在《面纱》当中,瓦尔特在众人面前是令人敬佩的舍生忘死的伟大防疫专家,但在其伟大人设背后,却是强烈的偏执。弗洛伊德认为,性压抑是一切心理扭曲的根源,而长期的自我压抑也正是导致瓦尔特偏执型障碍心理的主要因素。婚姻生活中自持且百般顺从的他对待妻子有着近乎仪式化的礼貌与尊重,但在进行夫妻生活时,瓦尔特却充满狂热与激情,且十分情绪化,“他的自我控制归结于羞涩或长久以来的习惯。”[2]那狂热的激情像是压抑后的反弹,更是自卑后的无所顾忌。偏执的他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婚姻被画上污点,因此在得知妻子有婚外情之后,瓦尔特立刻在悄无声息当中利用霍乱对凯蒂进行报复,在面对凯蒂的质问时,他直接用轻蔑的态度来嘲讽凯蒂的愚蠢:“我知道你愚蠢、轻佻、头脑空虚,然而我爱你。”[1]“世上再没有比对一个人又爱又鄙视更折磨人的事了。”[3]251瓦尔特对凯蒂那卑微又自恋的爱更彰显了他那自虐式的偏执,他去世前说的最后那句“死的却是狗”,正是充满了幽愤的控诉与执拗。小说中拥有偏执心理的还有凯蒂,现实境遇里的处境和心理幻想结果的巨大差异直接导致了她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幻象的偏执,霍乱撕碎了凯蒂对查尔斯的幻想,曾经令她神魂颠倒、无比信任的情人竟是如此的冷漠懦弱。但是在前往湄潭府的路上,尝试去憎恨查尔斯的凯蒂还在不断地回忆查尔斯与她相处的美好时光,以至于最后得出“她爱他,哪怕他曾经出卖了她,抛弃了她,哪怕他再对她冷漠无情”[1]的结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她偏执地固守着自己一点点可怜的自尊与幻想,遮掩着因卑微而带来的羞耻,而疫区的贞节牌坊却又不断地提醒着她自己的身份以及曾犯下的羞耻的过错,让她在自我幻想的偏执当中又承受了巨大的心灵痛苦。
其次是悖德型障碍心理。霍乱为凯蒂揭开了情人查尔斯·唐生道貌岸然的面纱,婚外情曝光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查尔斯亲手将凯蒂推往死亡禁地湄潭府,当凯蒂带着将要面对死亡的绝望离开时,身为昔日情人的他表现出来的不是悲伤与无措,而是轻松与解脱。霍乱迫使凯蒂撕开查尔斯虚伪的面纱,其暴露出的无道德感与无羞耻感,极端的自私自利、道貌岸然都是他悖德型障碍心理的体现。拥有如此病态心理的还有瓦尔特,他的悖德性体现在他的冷漠残忍与压抑扭曲上。在面对妻子的不忠时,瓦尔特想出的报复方法就是置凯蒂于死地。在被霍乱的暗黑魔爪所笼罩的湄潭府里,身为防疫专家的瓦尔特让仆人每天都给凯蒂吃蔬菜沙拉,以增大她感染的风险。毛姆曾说“疾病和古怪、隔离的生活奇怪地影响着他们,扭曲、强化并恶化了他们的性格。”[4]长期待在湄潭府的瓦尔特仿佛在这种可怕的环境当中强化了自己的障碍心理,他不仅对出轨的妻子冷血无情,还对自己刻薄残忍,漠视自己的生命。小说当中,身为细菌学家的瓦尔特为了研究霍乱,一直在拿自己的身体做实验,最终感染死亡。霍乱揭露并强化了瓦尔特的悖德型障碍心理,让他在冷酷无情的报复与自我实验当中葬送了生命。
二、缺失驱使下的补偿心理
补偿心理是指个体为了克服生理上的缺陷或心理上的自卑,发展自己的优势,赶上或超过他人的一种心理适应机制,个体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总有一些偏差,力求得到补偿,便产生了补偿心理。《面纱》中,毛姆展示了多个光鲜亮丽的中产阶级人物形象,他們自诩拥有社会地位,乐于交际,左右逢源,无时无刻不披着一层虚伪华丽的外衣,但长于讽刺的毛姆往往又会寻找契机来揭开他们的伪装,展现他们藏在心底的缺失与自卑,以及自卑内驱下的补偿心理。
凯蒂的情人,身为司部长的查尔斯在社交场上是幽默风趣且人人尊敬的政府长官,受众人的羡慕与追捧,但在面临名誉危机时,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将情人推往霍乱疫区,留自己明哲保身。毛姆用一场霍乱将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本性展露无遗。他在接受凯蒂质问时表现出来的怯懦以及对妻子多萝西的依赖正展现了他在家庭地位中的缺失。他那矫饰的礼服,拼命挺起的胸,健美的身材无一不是对其自卑内心的掩饰,在婚外情中,凯蒂对他那含有崇拜的爱也正好弥补了他在家庭中的地位缺失。毛姆对查尔斯自卑内驱下的病态补偿心理的展现也正揭示了20世纪现代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空洞虚伪、外强中干的病态特征。
在20世纪初期的西方社会,残酷的战争将人们的信仰冲击得破碎不堪,失望、怀疑情绪在人们心中普遍存在,陷入精神失落中的西方人总是在寻找新的心灵寄托来填补内心的空缺,参与过一战的毛姆常常让自己笔下的人物在异域中寻找新的信仰与生命的意义,在他的小说《刀锋》中,主人公拉里在经历了战争和战友的死亡后,就在印度走上了一条通往宗教的自我疗伤之路。《面纱》中的凯蒂也是如此,一场霍乱让她受到了情人的背叛,看清了丈夫的厌恶,于是将人生价值依托于婚姻的凯蒂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而湄潭府破败恐怖的环境又加剧了她的绝望,在绝望之余,一座中国的庙宇却给了她全新的感受,看到清晨的神奇虚渺的庙宇时,她受到了心灵的震撼,“她还从未有过如此神思飞扬的感受,她觉得她的身体此时只是一具空壳,而她的灵魂在荡涤之后变得纯净无瑕。”[1]她的心灵得到了暂时的平静,这也为凯蒂主动寻找人生的价值提供了一定的精神力量。凯蒂认为真正让她找到自身存在价值并且实现心灵自由的地方是修道院,在修道院中,仿佛有一种神秘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修女们在疫区奉献自己,而这种精神力量正是凯蒂所渴求的。在修道院中,她不再是委身于丈夫或情人身边的没有独立能力、只会社交迎合的弱女子,她发挥自己缝缀的才能,看管照顾可怜的孤儿,修女们的赞赏和孩子们对她的依赖带给了她极大的心理成就感,找到人生价值的凯蒂也因此不断地弥补了因情伤带来的自我怀疑的空虚。不难看出,凯蒂对自我价值的怀疑也正象征着战后现代西方社会人们的精神困境,毛姆通过凯蒂这一人物在中国找寻自我价值也正体现着毛姆想要在东方异域中寻找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的愿望。
三、笑中带泪的压抑心理
毛姆是人世间的挑剔者,具有洞察万象的能力,善于以犀利的眼光来审视人与社会,行医经历令他看到了原汁原味的生活,见识过赤裸裸的人性,他发现:“在人体解剖中,完全正常的情况才是罕见的。”[5]也正是这种独特的体验启发了他对人的理解:完全的正常只是人幻想的一种理想状态,而真实的人性其实混杂着“自私和厚道、理想主义和肉欲、虚荣、羞涩、公正勇气、懒惰、紧张、顽固”[5]等诸多性格特征。在《面纱》中,毛姆着重刻画了两个看似再正常不过的人物,一个是风趣幽默,热情智慧的沃定顿,一个是庄重善良,令人敬畏的修道院院长,他们二人对人生的看法带给了凯蒂巨大的启发,在凯蒂自我成长的道路上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毛姆依旧毫不客气地将审视的眼光放到二人身上,洞察他们人性中的不为人知的非正常部分,展示那笑中带泪的压抑心理。
谈笑风生的沃丁顿在众人眼中十分洒脱不羁,即使是恐怖的霍乱都能成为他笑谈的对象,但毛姆洞察并刻画出的,还有他那不为人知的孤独与压抑。封闭的疫区,死亡的氛围,这是沃丁顿长期的工作环境,面对初次到来的凯蒂夫妇,他与他们谈论的话题并不是死亡会随时光顾的疫区,而是英国和香港,“他的话题放到了戏院上。他清楚地知道此刻伦敦正在上演哪出剧目。”[1]毛姆在不经意的谈话中展现出来的是沃丁顿对外界的向往,是他无人诉说的孤独。而他却不能离开,不仅是因为他助理官员的身份,还有因为他的满洲妻子。他对满洲妻子的责任大过爱,“她为了我放弃了一切,她的家,家人,安定,还有自尊,”[1]他曾将妻子送回去过,也曾偷偷溜掉过,但他都无法彻底抛弃这个“离开他就会死”的女人,他向凯蒂表明:“等我退休了我会在北京买一处小房产,在那儿一直过到死。”[1]这时毛姆展现的是一个因社会责任而受压抑的内心,正如沈从文所说:“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滩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用微笑表现的。”[6]沃丁顿在笑声中诉说着这世界的诡异怪诞与荒唐,而这笑声也正是他反抗这压抑社会的仅有的窗口。
在充满恐慌与不安的疫区湄潭府,唯一给人安宁之处就是山顶的修道院,而院长那近乎苛刻的理智则是维持这一静谧和谐的支柱。但深谙人性的毛姆还是写出了院长极端理智下隐藏的压抑的内心。在死亡随时降临的环境当中,为了修道院有条不紊地正常运作,身为院长的她只能将自己人性当中脆弱的部分隐藏压抑起来,代以沉稳与权威的姿态来面对心怀热忱的修女们,带领她们对抗这残酷的现实世界。面对朝夕相处,共抗霍乱的修女姐妹的死亡,院长想要极力压抑自己的悲伤,但“源于人之本性的悲痛,与理智和信念激烈地交锋着,使她肃穆而美丽的面孔扭曲了。”[1]正如毛姆所说:“感情有理智所根本不能理解的理由。”[2]在毛姆笔下,具有圣人般肃穆与沉稳的院长也会有“铜铃般咯咯的笑”,也会“忍不住哭”,也会不觉地露出自己原本多变的性情。而面对无情霍乱和混乱的环境,身为大家长的她只得以理智来极力控制自己人性中的情感。在圣人般的悲怆背后,是被压抑的真实的内心。
四、死亡氛围下的冷漠心理
毛姆总是在冷峻犀利的笔锋中透露着自己悲天悯人的情怀,在揭示个体的病态心理时,又透露出博大而深切的人性关怀,表达着对于人的生存困境的巨大悲悯。
在《面纱》中,毛姆描写了在霍乱侵蚀下湄潭府人消极的冷漠心理。正如老舍所说:“愚蠢和残忍是这里的一些现象,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7]在疫区湄潭府,霍乱就像城堡里的毒气一般,不断暗示人们他们无处可逃的死亡宿命,这里的霍乱具有极高的致死率,“人们在以每天一百人的速度死去,一旦被感染上这种病,就别想有生还的希望,”[1]患病的人阵阵呻吟,大声哭喊,迎接将要到来的死亡;未患病的人死气沉沉,阴郁漠然,在瘟疫的掌控下苟延残喘;因病死去的人或被裹布送出,或横尸街头;防疫官员要么冒着感染的风险去埋葬尸体,要么就被枪毙。人们貌似生活在一个绝望的,没有出头之日的地狱当中,不断地被捉弄。在颓废暗淡的环境当中,人们无法逃离,便逐渐放弃了生的挣扎,以死的沉默与冷漠来等待着霍乱的降临。在病态压抑、沉默死寂的环境当中,人也逐渐形成了冷漠心理。
“冷漠”即冷淡、不关心、缺乏同情,是一种人际关系上的隔膜与孤独化,疫情的长期作祟已经让当地人已经麻木冷漠。毛姆特意通過底层人轿夫来展现这一现象。毛姆笔下的轿夫是艰难的苦役、沉默麻木的人,在路上遇到因霍乱而死之人的棺材时,他们会突然兴奋地彼此议论,然后又沉默不语,因为他们好奇今天死去的是谁,又惧怕明日死的是自己。在沉寂的背后隐藏的是他们对于自身悲苦处境的哀婉,但当他们面对同命相连的乞丐时,他们竟还会“大叫一声叫他滚开”[1],任由其做霍乱中的浮萍,横尸街头,无人问津,由此足以见其冷漠与麻木。并且在被死神扼住咽喉的湄潭府,渡船上的人们眼神古怪,脸如死灰;大街上冷冷清清宛如死城;“路上的行人多是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态,让人以为是撞见四处游荡的幽灵。”[1]人们对待死亡依旧恐惧,但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却从崇敬变为了漠然,这是人性的冷漠,更是对现实无力的顺应。正如毛姆自己所说的:“作家更关心的是了解人性,而不是判断人性。”[2]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毛姆不仅写出了人的冷漠心理,还写出了人在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通过消极的生命形态透露着自己对人的生存的巨大悲悯。
五、无力反抗的宿命心理
叔本华曾指出:“人生的悲剧性就在于人们常常处于幸福与痛苦的钟摆式的轮回中。”[8]毛姆创作的《面纱》就是这样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悲剧。尝试自我救赎的凯蒂不断地在满足与失落之间轮回,在这样无法逃脱的困境当中,毛姆揭露的是她那无力反抗的宿命心理。宿命心理“始于主体对当下处境的荒谬性的惊奇和诧异”[9],是对苦难经验无可究诸的思索之后的结果,具体指“人自觉到面临了一种超乎其自身力量的对象或一种他所无法解决的困境,使他因此感觉到自身的软弱和渺小,从而产生一种对于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的猜测”[9]。而这被猜测的神秘力量就是宿命。这种宿命心理通常会产生于自觉为弱者的人身上,尤其是现实中的受难者。
在《面纱》当中,凯蒂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不断地在满足与失落之间徘徊,而这种徘徊的困境让她陷入到了无可抗拒的宿命心理当中。在强势母亲的长期熏陶下,凯蒂以嫁得如意郎君作为自己最大的人生目标,她的人生价值来源于社交场上的左右逢源,来自于别人对她的看法。但丈夫瓦尔特的傲娇自持与细菌学家的身份又让凯蒂在社交场合屡屡受挫,在这样的境遇之下,凯蒂投入了司部长查尔斯的怀抱,查尔斯的阿谀奉承仿佛又让凯蒂找到了自我的价值与幸福。但在婚外情曝光后,通过与瓦尔特和查尔斯的对峙,凯蒂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自私冷漠的查尔斯并不爱她,从前对他百依百顺的瓦尔特如今对她也只剩憎恶。凯蒂瞬间感觉“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她是一刻也活不下去了。”[1]又一次陷入了自我价值的怀疑当中。但“人的自我主义使得他不愿去接受生命的无意义,当他不快地发现,他对自己一直以来促进的更高能力不能再给予信任,他就通过建构另一些特定价值来赋予生命意义。”[4]到达霍乱肆虐的湄潭府后,浑浑噩噩的凯蒂进入了修道院,她在修道院里帮助照顾病患,看护孤儿,孩子们对她的依赖仿佛又让凯蒂找到了自己生存的价值,让她的精神焕然一新,她貌似摆脱了因失去男人的爱慕而陷入的自我认同的焦虑,书中这样写道:“她现在再想起查尔斯,已经无所谓了,她已不再爱他。哦,她真的摆脱了,这真是一种解放啊!”[1]但她又总觉得与修道院“隔着一点距离”,在她每次离开修道院时,都会觉得“她不仅是被关在那所小修道院的门外,而且被关在了她孜孜追求的神秘精神花园的大门外。她忽然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1]127凯蒂这样的内心独白正暗示了她那认为自己注定没有精神安宁的宿命心理,正如她自己说的:“你看到了,我处在这样一个境地里——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灵魂找不到一个归宿之地。”[1]而让凯蒂真正绝望的那一刻,也就是她无意识地再次投入情人怀抱之后,清醒的那一刹那。在这个时候,凯蒂看清了自己,看清了人理性的有限性,也明白了過去的一切是如此荒谬。“她已经不是女人,她的精神融化了,身体里只留下了膨胀的欲望。”[1]她本以为自己找到了精神的解脱,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但是到头来还是成为了欲望的奴隶,那句“畜生”不仅是痛恨自己荒诞的行为,更是对她那注定得不到人生意义与自我价值的现实命运以及荒谬世界的控诉。最后,她还是依附于父亲,逃离到了那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去了。人类渴望理性与和谐,但是又处处受非理性因素的控制,通过凯蒂追求的失败,毛姆写出的是缺少精神支撑的人类的荒诞体验,是现代人面对荒诞现实的无力感,这也让我们窥见了人类生存于荒诞的必然性。
六、结语
综而观之,毛姆以霍乱作为强力揭开主人公虚伪的面纱,暴露出他们病态的心理与现实人生的困境。但他一方面以冷峻敏锐的眼光来洞察周围的世界,揭露残酷的现实,另一方面又以悲悯的眼光来关照那被现实折磨得千疮百孔的人性。我们像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样,总是乐于将我们美好的那面展示给人看,而将内心中那充满伤痕的非正常的部分竭力掩饰起来,仿佛它们从未存在,但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的奋力隐藏终归抵不过现实的强力。所以,毛姆为我们展示的并不单单是被霍乱揭开的病态心理,还有那现代人难以逃脱且无法战胜的人生无意义的困境。但又如前文所说,毛姆是悲悯的,他在自己的另一本书中仿佛给了我们继续生存的希望:“人生既已如此颠沛可怖,知道它没有意义反而使人鼓足勇气,大胆面对。”[3]
参考文献:
[1]威廉·萨默赛特·毛姆.月亮与六便士[M].傅惟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2]威廉·萨默赛特·毛姆.面纱[M].阮景林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20.
[3]威廉·萨默赛特·毛姆.人性的枷锁[M].张乐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
[4]威廉·萨默赛特·毛姆.毛姆文学课[M].孙戈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
[5]威廉·萨默赛特·毛姆.让灵魂舒服一点:毛姆自传[M].王敏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
[6]沈从文.沈从文全集·17·文论·2版[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7]老舍.骆驼祥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
[8]叔本华.叔本华人生哲学[M].李成铭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9]董江阳.论“命”观念的心理意义[J].求索,1994,
(02):69-72.
作者简介:
赵雅致,女,汉族,山东济宁人,聊城大学文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