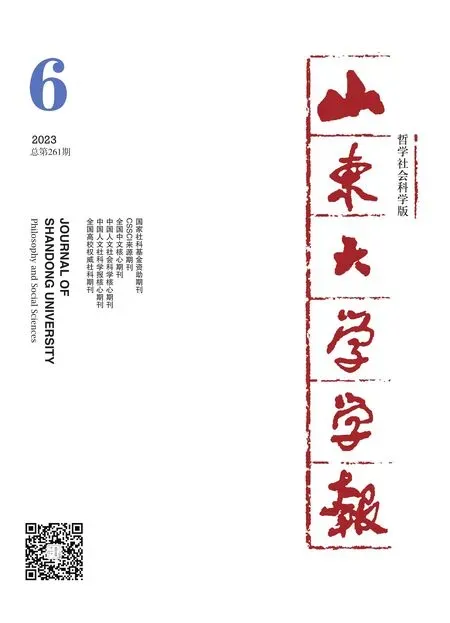利他救助的内涵界定与促进机制探析
2023-12-25周煜
周 煜
在危难关头向他人伸出援手是社会得以构建的重要道德基础。人类社会通过信任、互助和合作得以存续与发展。在不同种族和文化体系中,利他救助都是被褒扬与提倡的行为。不过,令人沮丧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利他救助并不容易发生。纵观近年来的公众事件,自南京“彭宇案”肇始,救助人被讹诈的事件屡见不鲜,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规定了利他救助的免责事由,但是仅仅通过免责条款无法抵消民众对损失风险的规避心理,前法典时代就一直存在的逻辑困顿并未消除。
涉及利他救助,仍有两个核心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其一,怎样精确地界定利他救助行为的内涵,将不属于此制度范畴的行为予以排除,这是正确调整利他救助行为的前提。其二,如何通过制度促进利他救助行为的发生,这是制度构建的目的。
“利他”与“利己”是相对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对种群行为和进化策略的研究。然而,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法学中并没有 “利他行为”和“利己行为”的概念划分,故无论将利他救助接入权利框架还是义务框架都无法对其法律属性进行完整界定。基于传统教义学理论,法律只能通过公平原则赋予救助人向受助人要求适当补偿的权利,这使得问题很难突破。故而,需要在法学城堡上“打开一扇窗户”①桑本谦:《法律简史:人类制度文明的深层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 年,第ⅷ页。,考察行为动机因素,构建行为促进机制,找寻法条背后的底层构架。
本文基于上述思路,在界定利他救助范畴和内涵的前提下,剖解行为人的动机构成因子,指出传统法律干预方式面临的难题,并尝试构建有效的行为助推机制,以学科融合视角重新审视制度运行的深层逻辑。
一、利他救助的范畴与内涵界定
(一)基于行为视角的广义界定
1.利他救助是人类利他行为集的子集。利他行为集是指对其他个体有利且没有明显自我获利的行为集合。利他行为先于人类的道德和立法出现,普遍存在于生物界中。在人类经历的“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粗略进化路线中①根据脑容量和颅骨形态判断,在直立人和智人之间可能还存在着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特人两个重要分支。Samantha B.,Diyened M.,Maxim K.B.,et al.,“The Earliest Denisovans and Their Cultural Adaptation”,Nature Ecology &Evolution,2022,6(1),pp.28-35.,皆能寻迹种群中利他行为存在的证据。利他行为是人类合作行为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维系着社会网络演化的动态平衡,但究其发生的动因仍为难题②韦倩、姜树广:《社会合作秩序何以可能: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经济研究》2013 第11 期;Aaina G.L.,“125 Questions:Exploration and Discovery”,https://www.science.org/do/10.1126/resource.2499249/full/sjtubooklet-1686067070670.pdf,访问日期:2022 年8 月20 日。。社会科学模型一般以利己主义为基础,并将利己设为人性的基础。利他主义所表现出的“无人性有德性”使得其在与利己主义的交锋中处于下风③刘清平:《利他主义“无人性有德性”的悖论解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1 期。。很多社会问题,如“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奥尔森困境”等,其核心皆是人类利己行为导致的社会失控。有些学者尝试从生物种群、环境和生态,乃至适合度(fittness)层面进行实证分析,构建利他主义的深层逻辑体系,但宏观与微观行为机制的二律背反仍难以消除。利他救助与助人为乐、自我牺牲、利他惩罚等行为同属于利他行为集。不过相较于其他的利他行为,利他救助发生的场景更为随机,留给当事人作出决策的时间更加短暂。
2.利他救助在客观表现上超越了亲缘和对价关系。乔治·威廉斯主张“基因”作为主导因素分别沿着两条路径决定着人类行为模式:在外部路径上,基因决定着哪种行为模式的个体能够生存并繁衍后代;在内部路径上,基因决定着亲缘关系,从而渐进性地演进出四种利他行为模式,分别是亲缘利他、互惠利他、纯粹利他和强互惠利他④亲缘利他,指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他人做出的牺牲。互惠利他是指没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了日后的回报而作出牺牲。纯粹利他即没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在不追求任何物质回报的情况下采取的利他行为。强互惠利他是一种特殊的行为,是指在目前和未来都不能期望得到收益的情况下支付成本来奖励公平和惩罚不公平的行为。Herbert G.,Joseph H.,Samuel B.,et al.,“Strong Reciprocity and the Roots of Human Morality”,Social Justice Research,2008,21(2),pp.241-253.。虽然达尔文、汉密尔顿和道金斯的理论框架对“己”与“他”的界定并不相同,但都没有超越社会关系紧密度模型的假设⑤Guo J.,Shi L.,Liu L.,“Node Degree and Neighborhood Tightness-based Link Prediction in Social Networks”,2019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ICIST),IEEE,2019,pp.135-140.。不同于动物界的“天择”过程,在高度文明的人类社会中,个体并不会直面生存抉择,利他个体也没有表现出生存适应度的明显升高⑥据史料,人类最后一次面临利他或者利己的选择能直接决定种群灭绝的是尼安德特人与智人之间的竞争,尼安德特人明显具有更加强壮的身躯和更大的脑容量平均值。关于最终智人成为现代人祖先的原因,一种可供考证的猜想是虽然智人的体型不占优势,但是胜在团结并且具有合作意识,种群内出现利他行为的频率更高,甚至出现了利他救助的萌芽,从而能够抵抗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斯万特·佩博通过基于尼安德特等古人类基因层面并还原其行为特征和灭绝原因的研究,获得了2022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Skov L.,Peyrégne S.,Popli D.,et al.,“Genetic Insights Into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Neanderthals”,Nature,2022,610,pp.519-525.。问题的侧重点从外化的基因筛选问题演化为内化的效用感知问题。
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指出了人类道德的演化路径。索伯-威尔逊(Sober-Wilson)群体选择框架修正了达尔文的思路⑦Sober E.,Wilson D.S.,Unto Others:The Evolution and Psychology of Unselfish Behavior,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5.,博姆认为生物进化过程由单纯的自然界基因选择转化为人类的文化传承过程⑧Christopher B.,Moral origins:The Evolution of Virtue,Altruism,And Shame,New York:Soft Skull Press,2012,p.92.,而他心理论(ToM)则指出人类在作出利他救助行为时会受到感同身受与同情心的影响与驱动⑨王华平:《他心的达及问题与直接感知理论》,《哲学研究》2021 年第2 期。。以此推论,跨越亲缘网络的利他救助行为在道德框架下使主体产生了抽象的正义、羞耻和怜悯心,在有限理性框架下出现了非理性的拟亲缘利他行为,进而演化为纯粹利他行为。以复杂系统理论的观点看,这种突变是社会生态演化过程中的某种平衡状态。回到“己”与“他”的划分维度,虽然在客观层面具有独立意志的个体可以认为是“己”,但是在亲缘关系和具有对价的合同关系中,个体很难将其自身利益与其他主体的利益进行完全分离,所以这并非一种纯粹的“利己”。换言之,救助人在是否作出救助行为的判断中,亲缘或对价关系的存在会成为影响因素,但不是其中唯一的影响因素。因此,利他救助行为必须具有突破亲缘关系和对价关系的动因,以及实质上作出了对关系外主体的增益行为。这亦成为支撑现行法律制度设计的深层逻辑。
3.利他救助受到类模糊决策行为机制的影响。尽管动机的产生会受到行为人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损失-回报”衡量机制的影响,但是行为人对行为后果的估算并不是精确的。在共生引发的互惠利他关系中,救助方的动机蕴含有维持共生社会网络存在的目的,本质上是利己的。进而,如果救助行为的作出是基于严密的组织分工或存在先期约定,在不具有明显超越行为对价的情况下,救助行为并不具备纯粹的利他性。这包括个人约定,如雇佣私人保镖的行为;也包括社会职责,如急救医生。同时,利他救助的产生不具有事先的行为规划。因而,利他救助具有被动性,否则可能演化为强互惠或者病态利他行为。另外,由自我救助行为产生的衍生利他行为并不是利他救助,诸如扑灭自家大火防止火灾蔓延的行为。最后,利他救助不应越界进入慈善行为的领域。慈善行为具有明确的贡献(损失)预期,但是利他救助人仅仅是主观预估,这也就决定了利他救助并不必然包含赠予动机。
(二)基于法律解释论的狭义界定
从解释论的角度看,利他救助的法律内涵是对其广义内涵作出的限缩性解释,可以视为基于立法目的对于利他救助的狭义界定。
《民法典》第183 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第184 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4 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受害人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请求受助人适当补偿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害人所受损失和已获赔偿的情况、受助人受益的多少及其经济条件等因素确定受益人承担的补偿数额。”类似的规定在北美和欧陆立法中广泛存在。法律对于利他救助界定的语词边界较广义内涵有所限缩,但是其依然应当符合广义上的深层逻辑,这是制度合理性的基础。《民法典》的规定存在语义模糊和容易混淆之处,需要进一步地解释与剖析。
1.“利他救助”与“无因管理”的差异。《民法典》中,利他救助与无因管理被划分为两项制度。《民法典》第949 条至984 条是关于无因管理的规定,其核心是“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其中也蕴含有“无先期义务+存在利他动机”的内涵,加之其规定较为详细和具体,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利他救助应是无因管理的一种①冯德淦:《见义勇为中救助人损害救济解释论研究——兼评〈民法典(草案)〉第979 条第1 款》,《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 年第2 期。。另外,有学者认为无因管理的逻辑架构呈现了“必要费用偿还(支出的)+损害补偿(发生的减损)”的组合,而利他救助仅仅规定了“损害补偿(发生的减损)”,没有对于必要费用的偿还进行规定,这将产生法律漏洞。基于此,学界提出了两种学说:“法定补偿责任说”和“统一适当补偿责任说”②王雷:《见义勇为行为中受益人补偿义务的体系效应》,《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 年第4 期。。
笔者认为上述讨论具有一定的启示,但是两项制度并不相同。首先,二者在行为目的和动机上不同。利他救助是救助人对于非负有义务的对象在相对紧急的情况下阻止其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失的行为。无因管理行为则完全可以基于为了受益人更好获益的目的而进行,并没有紧急性要求。其次,利他救助具有突发短暂性,对于持续性的危机或者危机后续的处理行为皆不属于利他救助。而无因管理可能在非紧急情况下存在并持续良久。再者,无因管理可转化为委托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典》第984 条,无因管理包含管理人、受益人和标的三者关系,对象是“事”和“物”。如果“有因”,其本就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事后追因并不能掩盖其委托行为的本质。进而,当事人在事后追认的行为使得管理方获取了利润,这不违反法律的本旨。但是利他救助与无因管理不同,不具有事后可以转化为委托合同的可能性,只存在事中转化为普通债权的可能性。最后,《民法典》183 条中的“适当补偿”应作合理解释。相较于无因管理的规定,条文并没有对利他救助行为中的受助人规定合理费用支出的偿还义务,而是使用了“适当补偿”词语。很多学者对此并不赞同①肖新喜:《我国〈民法总则〉中见义勇为条款与无因管理条款适用关系的教义学分析》,《政治与法律》2020 年第6 期。。现有条文对于侵权人使用了“赔偿”,其原因在于其存在违法行为,救助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害+全部费用”;而对受助人使用“适当补偿”,其原因在于受助人不存在违法行为。很多学者认为使用“适当”而非“完全”的原因类推自“公平责任”的分担方式,其中蕴含有受助人无过错和救助人“自愿奉献,不求回报”的纯粹利他行为的双重假设。适当数额的补偿并不是为了弥补救助人的损失,只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救助人可以通过国家和社会的救济以弥补损失,而不是由于救助行为获得正向收益。
但笔者认为这显然与利他救助制度设计的目的相悖,也不符合利他救助的行为逻辑。原因在于,无论是第三人侵权还是意外事故导致的紧急状态,受助人皆是这一事件风险的原始承载者,救助人在进入救助场景之前与此风险并无牵连,受助人虽无过错,但是风险化解与救助人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因此,救助人在作出救助行为时,利他动机指向是甘愿放弃“与风险无牵连”的状态,但并未产生阻却其求偿权的后果。根据损益分析,救助人的利益耗损分为两部分:为了阻却风险付出的合理费用(F)和救助行为导致的自身损害(D1);受助人损益包括:侵权人已经对其造成的损害(D2)、救助行为避免的损失(S)和救助行为带来的获益(Rμ)②Rμ表示直接获益的期望,即获益额(Ri)与获益概率(pi)的乘积加总∑Ri∙pi(i=1,2,3…)。,侵权或意外事件造成的总损失表示为D=F+D1+D2。对于183 条中的“适当”应做如下解释:救助人有权向侵权人请求赔偿“合理费用+自身损害”(F+D1),在侵权人无力赔偿所有数额或者不存在侵权人的情况下,受助人承担补偿责任。比较两个数值:尚未获得赔偿的数额(D′)和受助人的实质获益(S+Rμ),取两个数值中较小的值作为补偿数额下限,较大的值作为补偿数额的上限。对于受助人损害(D2)不能与上述数值进行抵销,而只能向侵权人索赔,在无侵权人的情况下由受助人自留③王泽鉴:《损害赔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115 页。。
2.利他救助与见义勇为、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存在差异。某种观点认为《民法典》183 条和184 条的规定是关于见义勇为的规定④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理解与适用》(下),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年,第919 页。,笔者认为有待商榷。见义勇为一词源自《论语·为政》中的“见义不为,无勇也”,其主要强调“勇”字的价值。《山东省见义勇为保护条例》规定:“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是指非因法定职责或者约定义务,为保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由此而言,“见义勇为”是利他救助的一种,但利他救助却不一定具备不顾个人安危的条件。如在寒冷冬夜,看到迷路的老人帮其回家的行为符合利他救助,但是不构成见义勇为。见义勇为具有较强的社会正向价值,同时具有较高的行为风险。利他救助是一个相对中性的名词,其底线在于不能违反公序良俗。诸如,小偷甲被发现后遭到围殴,在慌不择路的逃脱中摔断腿,乙选择暂时藏匿并控制甲后报警。藏匿行为的目的是避免素不相识的甲遭受更大的人身伤害,既不是甲盗窃行为的帮助犯也不涉及窝藏违法。这种行为是利他救助,但是不构成见义勇为。利他救助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间可能会存在竞合关系,三者相关的法律规则的侧重点不同。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制度侧重于对行为人自身利益的保护,而利他救助侧重于对受助人利益的保护。另一方面,正当防卫以他人侵害为先决条件,紧急避险以存在高损失概率为前提,而利他救助以“利他”为核心要件。利他救助对于“当场性”的要求可以酌情放松。在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中,如果不具备当场性要件,则可能存在事前或事后防卫、事前或事后避险。比如,甲出于利他动机在阻止乙对丙的违法行为后,被乙立即追击报复,甲反击和受伤。甲虽存在两个独立的正当防卫行为,但其受伤与前置事件具有牵连因果关系。根据“but for”规则,其构成利他救助,受益人是丙。
综上,笔者概括性地将利他救助界定为:不发生在亲缘、互惠、契约或职权关系中,为了他人的利益,在相对紧急且具有风险的情况下的救助行为。
(三)问题的核心与难点
无论从行为视角的广义探究维度,还是从解释论的狭义推演维度,“利他救助”范畴和内涵界定的关注点都在于行为目的是指向“己”还是“他”。
囿于科学技术条件,人类在意识层面的内在动机无法被直接获取,只能凭借行为外观进行探知。脱离个体行为动机的离身性探知纵然有助于抽象和归纳出问题的构成因素,但却不完善。无论是基于父爱主义(paternalism)的强制性规定或刻意的全民素质拔高,还是基于“填平原则”或道德判断的事后弥补,其解决的仅仅是第二性问题,即救助行为过程中产生了额外损失应该怎样处理的问题。这种“超越自然”的关注视角纵然有其意义,但是亦存在根本性的悖论:探析利他救助行为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责任划分吗?
现行制度的逻辑是基于均衡各方利益对“收拾残局”的关注,或者是站在填平原则的视角而设计。只有利他救助发生了,法律中关于损失承担的规定才具有意义。从上述双重视角出发,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运行体系中,利他行为并不会单纯由于事后的利益均衡而发生、演化和消亡,当事人也不会由于在事后良好的补偿而愿意去做利他行为。具身性决定了不同行为人在不同情境下的内在动机和主观损益衡量存在差异,故任何个体都不可能脱离于具身而存在,利他救助的发出方向是由“己”及“他”的。纵然具体的动机和行为决策过程只有行为人内心明晰,甚至当事人本身也是模糊和凭借直觉决策的,但是只要最终产生了利他救助行为的激活就达到了制度的目的。
从而,问题的核心凸显为:如何从行为动机角度探知利他救助的促进因素。
二、利他救助内生激励因素探析
“理性人”假设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模型。这个被抽象出来的“人”的基本特征是自私利己并且力图以最小代价去谋取最大利益。自利假设表明个体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自身利益。根据“看不见的手”的经典论断,行为人追求自身利益反而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年,第25 页。。法律亦建立于理性人行为基础之上,将利他和奉献行为规定为义务的做法并不常见,否则其很容易变为一种宣示性却缺乏实效的文字游戏,被贴上“道德洁癖”的标签。故有学者认为法律的目的不是鼓励利他的“善”,而是制约不正当利己的“恶”。惩恶与扬善无法同时兼顾,只能通过惩恶来间接扬善,同时尽量确保善行不带来恶果。根据“损害最小化原理”,若不能保证善最大,一定要确保恶最小②邓子滨:《法律的精髓不是鼓励善而是禁止恶》,《南方周末》2011 年9 月1 日,第F29 版。。
按照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理论,哪怕是溺水之人只需被拉一把就能被挽救,但终究会因为需要救助人付出一点无法获益的成本而难以实现。无论是黑猩猩、人类、蜥蜴,还是真菌,都经过了漫长的自然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基因分布并非随机,生物适应性将成为后代数量的决定因素,得以繁殖的基因在下一代中的数量将更加可观③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卢允中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年,第62—89 页。。而如果以非合作博弈的框架来看,背叛是占优策略,呈现高度稳健性,而利他行为是非占优策略,并不会发生①李海虹、尚思源、谢晓非:《利他行为的遗传基础:来自定量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的证据》,《心理科学进展》2022 年第7 期。。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推论,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即使制度不能强制性地要求“善”,但是至少应该促进“善”的发生。
(一)基于人类行为理性在效用层面的分析
人类行为受到“效用”感知的影响,其中,效用被界定为行为人满足自身欲望的测度。两个人的效用相同,但是满足的方式可能不同,物质上的不均衡不代表效用上的不均衡。在古典经济学中,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所引导的函数求解状态其本质上不只是生产或需求之间的均衡,而是指向各个参与方微观行为所引导的封闭系统内的帕累托最优。这与罗尔斯主张的“差别正义”异曲同工,也与边沁、密尔、诺齐克的思想内核殊途同归。然而,罗尔斯与密尔对正义标准的判断并不相同,其对功利主义的批判来源于以“总体利益”为评价标准的理论,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处理,个体的利益会被忽略,所以必须在原始阶段设立“无知之幕”给予人们选择行为目的自由。其最终达到的是在满足个体差异性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最大多数人获得利益,这是一种类似于康德式的论断。肯·宾默尔通过演化博弈系统“复刻”了罗尔斯的差别正义模型,推导出了社会演化的基本规律②Binmore K.G.,Game Theory and the Social Contract:Just Playing,Cambridge:MIT press,1994,pp.95-96。这是一个宏大的哲学命题,笔者认为从效用论来看,其构成了一个对于正义判断标准的复合矩阵。在纵向维度上,其界定的是“正义”对于行为产生的效用是先验还是后验的;在横向维度上,其界定的是在某个场景下“正义”究竟指向的是实现群体效用的最大化还是个体效用的最大化,参见图1。

图1 正义判断标准的复合矩阵
在具体场景中,人们的经验往往都是先验的,促使行为发生的是应然的效用,在行为发生后,对有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的评估,则是一种对于实然效用的后验判断。行为人无法穿越时空,其只能根据逐渐获得的先验知识来不断修正自我行为。从微观层面看,这是一个从无序到路径依赖的过程,而从宏观层面看,则是系统熵减过程。如果以个体为基本单位进行效用判断,这与罗尔斯的“差别正义”具有相似的根源,而如果以群体为封闭系统进行整体计算,则与边沁的理念有相似性。
在不确定场景下,人类凭借理性对利弊进行衡量③桑本谦:《法律简史:人类制度文明的深层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 年,第108 页。。其直接驱动力是基于先验知识和个体角度对自身效用的判断,尽管在后验的角度看,其实现了对于群体效用的增益。外在的价值评价标准需要内化为行为人在心理账户中的效用判断,进而影响到决策的结果④Sahin R.,Liu P.,“Maximizing Deviation Method for Neutrosophic Multiple 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 with Incomplete Weight Information”, Neural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s,2016,27(7),pp.2017-2029.。这其中较为重要的三个因素包括:其一,利他救助行为与社会主流评价标准的吻合度,将催生合群感、成就感和愉悦感;其二,利他救助行为带来的声誉提高引发的远期效用升高;其三,利他救助行为激发他人的合作动机,有助于整体利益的升高⑤金迪斯、鲍尔斯:《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来自桑塔费学派的看法》,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引言部分。。
由此,建立模型。效用感知的期望值可以表示为⑥笔者在此处采用线性效用模型来解释行为动机构成,这不是精确的。重点仅在于表明行为人做出利他救助的决策过程中,可能考量的因子。:
其中:A 代表社会评价升高的量,α 指个人对社会荣誉升高的效用感知度,此两项的乘积决定了利他救助带来的个人社会评价效用感知的升高量①A 可不可能成负值?存在这种可能性。诸如,在战争时期某人出于同情心对于受伤敌人的帮助,很可能在伙伴中会受到鄙夷。。H 代表利他行为对个人心情愉悦度的提升量,β 代表个体对于心情愉悦的效用感知度。一般情况下,H 是正值,但在“幸灾乐祸”的情境下,H 可能会扭转为负值。m 代表利他行为带来的金钱收益,比如政府的见义勇为奖等。γ 指个人对金钱的效用感知。λ1是收益的概率。n 代表对利他行为预估付出的成本和损失,包括时间成本、救助成本和垫付而无法收回的费用。δ是对金钱减损的感知度。λ2指付出成本和发生损失的概率。Q 是亲缘价值,ε 为随机扰动项。
综合来看,P 是被解释变量,其代表受到解释变量影响的救助人心理账户中的效用值。与P 对比的是P′,其指代如果不去做利他救助行为,救助人在心理账户中所产生的效用感知期望值。基于行为效用感知的反事实因果(counterfactual),P′可表示为:
上式中,P′与P 中的参数呈现负相关变化。行为人比较两者绝对值的大小:当|P′|≤|P|,会激活利他救助的行为动机;|P′|>|P|时,利他救助行为动机未被激活。
行为理性具有个性化特征,其与个体心理账户的激活阈值及环境影响因素相关,此处可以将其称之为“情境”(situated)②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77 页。。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是人类在社会经验层面进行公平正义判断的基础③Allen T.A.,Fortin N.J.,“The Evolution of Episodic Memory”,PNAS, 2013,110(S2),pp.10379-10386.。与之相对的是传统理性人假设,仿佛行为人置身于真空之中,大脑是一台编程完毕的高性能计算机,这是荒谬的④情境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差距多远,仍然是一个值得探寻的问题。参见王晓田、陆静怡:《进化的智慧与决策的理性》,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47 页。。
随着社会网络节点的疏离,变量A 和α 数值呈现明显衰减。这表明个体在荣誉感强的群体内作出利他行为的概率要高于其在荣誉感弱的群体内。心理学家的研究也表明长久的内心强化激励可以加深共情的程度⑤金国敏、李丹:《慈悲冥想对利他行为的影响及其认知神经机制》,《心理科学进展》2020 年第6 期。。另外,根据桑塔费学派“强互惠利他”理论,社会网络的稳定维持一般伴随着惩罚机制,目的是使自利者的社会评价急剧降低,导致其无法适应群体生活而被驱逐。社会网络中的个体如果对于社会网络的估值高于自身短期利益的估值,在损失规避和禀赋效应的双重作用下,社会网络将保持内生稳定。
H 的值与“他心”的情景记忆激活有关。根据马普人类认知与脑科学研究团队基于“他心”的实验与分析,同情心与脑神经中右侧颞顶交(RTPJ)与岛叶部位(insula)有很深的联系。其中,岛叶是脑中控制疼痛的部位。基于他心的情景记忆会激活同样的感受,这是人的本能⑥Bernhardt B.C.,Singer T.,“The Neural Basis of Empathy”,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2012,35,pp.1-23.。“他心”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其同样可以表达为负面情绪所引发的情景记忆。诸如对于社会人情冷漠的感知可能引发“幸灾乐祸”,但也有可能反射性地引发“以德报怨”。从计算社会科学角度来看,虽然社会是复杂系统,微观个体行为动机与行为模式如布朗运动无迹可循⑦克劳迪奥·乔菲·雷维利亚:《计算社会科学:原则与应用》,梁君英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143 页。,但基于宏观统计,即使是复杂系统也会呈现出规律特征。情境的多样性决定了以立法直接规定利他救助的行为模式存在非常大的难度。不同的情境给不同个体带来的效用感知会产生差异,并且是初始值敏感的。深层次的难题在于:究竟公平是社会客观层面上的,还是个体主观层面上的,抑或是群体内基于比较层面的⑧陈劲松、胡若倩、王友春:《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公平感知对机会主义行为容忍影响》,《企业经济》2019 年第9 期。。Q 代表的是亲缘紧密度。随着血缘关系的拉近,数值呈现加速增长。根据《民法典》183 条的规定,Q 趋近于零。Q 还可能会存在效用的自我强化机制,即其平时是不被感知的,但特定情境会提升感知度①叶航、陈叶烽、贾拥民:《超越经济人:人类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86 页。。
值得注意的是,“信息茧房”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对于行为效用的判断。在信息时代,智能手机的个性化推送加大了人们对某一方面信息的获取力度,但夹杂有偏颇观点的信息也会误导信息接受方,即视角有偏的新闻报导会加大公众对于利他救助无法得到补偿的概率的判断,进而扭曲其行为。“只要疑虑泛化为一种社会心态,冷漠必会成为接踵而至的精神并发症。”②桑本谦:《利他主义救助的法律干预》,《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10 期。新闻背后的默认逻辑是认为“人们应该是利他的”,因而强调“人情冷漠”“见死不救”的标签才成为吸引注意力和流量的办法,大数据不断推送会形成对于效用判断的反向助推。遗憾的是,或许直到这种反向助推完成,“伸手相助”等标签才能成为正向助推,但此时利他救助已经成为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了③龚小庆:《合作·演化·复杂性》(两卷本),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119 页。。
(二)基于社会信任和声誉反馈机制的分析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过程是非合作博弈中最常见的类型。参与人同时选择行动,并且每个参与人对其他所有参与人的特征、策略空间及支付函数有准确的认识。这一过程可以记作G={J,S,{ui}},此处将利他救助简化为救助人和受助人参与,由两种策略(合作,背叛)所形成的博弈过程④G 代表博弈矩阵,其中J 表示参与人集,S 表示策略空间,ui表示每个人的效用函数。。对于救助人来说,合作意味着伸手相救,背叛意味着袖手旁观;对于受助人来说,合作意味着感谢,背叛意味着诬陷。“感谢”不但代表完全补偿对方因救助行为所付出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及受益补偿,而且可能还存在奖励;“诬陷”意味着不但不承担对方的任何成本,而且己方的损失还要求对方进行赔偿。“救助”意味着救助行为;“袖手旁观”意味着冷漠观望,在对方选择“感谢”策略时,意味着预先已经拿到对方的救助费用但是不伸手相救。(相救,感谢)是合作解。尽管合作解满足双方利益的最大化,但却不是博弈矩阵的均衡解。令人遗憾的是,(冷漠,诬陷)即(背叛,背叛)策略将成为纳什均衡解,从而陷入“囚徒困境”。
上述假设发生在一个社会信任和信仰极度缺乏的社会中,人们可能会因对蓄意敲诈、恩将仇报、纠缠不清等事情发生的概率评估过高而对利他救助效用的评估下降,冷漠就成为合理的自我心理调适,见危不救似乎就有了合理性⑤桑本谦:《利他主义救助的法律干预》,《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10 期。。另外,对金钱的效用评估异常升高,也助长了不信任和利他救助被规避的可能性。例如,当利他救助人垫付巨额医疗费用后,家属选择不相信行为人会为了一个陌生人付出如此多的成本,推定其不是救助人而是肇事者,而利他救助人则会因为知道家属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而选择不去救助。当这个困境成为现实后,家属又会因行为人不主动先行垫付费用,想要追究其法律责任。最终的结果是恩将仇报,过河拆桥。这种不断迭代的恶性循环使得社会陷入“人情冷漠”的囚徒困境。当人性充满“算计”,γ 和δ 的升高导致金钱因素所带来的效用改变远远大于其他变量因素的值。最终,在没有亲缘和伦理信仰制约的前提下,对金钱的衡量成为了主使行为发生的最主要因素。
道金斯将此过程解释为“自私基因的演化策略”。只有那些自利的生物能够生存下去,选择合作利他的生物都会由于自利个体的背叛而利益骤降,最终因无法生存而被淘汰⑥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第77 页。。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至少公共品博弈实验并不支持这种观点。索博-威尔逊框架也对个体自私论的观点予以驳斥,其认为这可能是辛普森悖论(Simpson’s Paradox)所引发的错觉。广义适合度(inclusive fitness)理论也表明了单纯以最小个体为行为考察单位会忽视个体之间的内生连接网络而错失问题的关键。
利他救助行为动机背后存在着共情和共同体的信任感知,这种感知约束将成为救助人利他行为发生的激发条件。尝试性的反思,可以发现“囚徒困境”和“基因自私论”忽略了“信任”这个关键因素。若加入信任利益将得到以下博弈矩阵(图2)。

图2 加入信任利益的博弈矩阵
在F1和F2等于0 的情况下,T>R>P>S 将产生囚徒困境。
综上,利他救助受下述因素的影响。首先,利他救助人在社会中的获得感。社会评价感知度α 值难以提升将成为行为阻碍因素。这源于缺乏一种机制能固定与记录救助事实,导致当事人心理上很难跨越“支付意愿/接受意愿(WTP/WTA)”的边界。其次,之所以亲缘关系或团体内部容易产生利他救助的原因在于存在未来被救助的反射性心理预期。在这种预期下,救助人会确信在未来面临危机时,团体内部或曾被自己救助过的人会救助自己。其心理账户权衡的对比物,其一是亲缘或互助社会网络本身的价值在未来的贴现;其二是救助成本,显然一般情况下前者是远远高于后者的。而在纯粹利他行为中,救助人心理账户权衡的是救与不救之间的差值,即前述P-P′的绝对值与救助成本之间的比较,并不涉及社会网络价值。再次,救助人对受益人是否诚信存在疑虑,害怕自己的救助行为反遭诬陷。综上,需要弥合信息不对称状态,激发利他救助行为的关键在于增强效用感知和建立信任机制。
三、传统外部干预方式面临的难题
《民法典》183 条和184 条是对利他救助发生后责任承担的规定,但对于通过怎样的制度激发利他救助行为却依然存在空白。传统理论上,为了激发利他救助行为,制度的干预方式大抵分为三种:惩罚式干预、奖励式干预和保障式干预。
(一)惩罚式干预
惩罚式干预的内涵是在紧急情形下,对不进行利他救助的人进行金钱惩罚或追究刑事责任。这相当于设定一个较大的n′值,通过加大不作出救助行为的人的成本而进行干预的方法。其要求公民在他人遭遇人身严重危害的时候,如果施以援手不会对自己产生损害,则必须积极救助,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这种立法最早出现在19 世纪的葡萄牙,随后的100 年,至少被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15 个欧洲国家的刑法典所采纳,美国个别州也出台过类似的法案。其中,《法国刑法典》223-6 条是这种干预方式的典型代表①叶名怡:《法国法上的见义勇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 年第4 期。。
惩罚式干预的困境主要在于对行为人的信息判别。首先,个体对于“处在危险之中”的判断标准存在差异。在很多复杂的情境下,判断是否应该施以救助往往需要专业知识。行为人很容易推脱自己的责任。找一个目击者是不是可以解决?远非如此。目击者的举报行为会受到利他惩罚动机的驱使,这将会出现利他行为迭代引发的逻辑悖论。并且,目击者仅仅是目击而没有去施以援手会构成嵌套的侵权行为,那么其又有什么动机去举报呢?其次,对于自身救助能力的判断错误也会导致侵权责任的模糊不清。再次,由于存在监督成本,谁来监督以及如何控制监督范围和控制成本又回到了问题的初始,逻辑循环使得社会更加混乱。最后,惩罚的度不易掌握,对于不作为侵权或者犯罪惩罚力度一般较轻,而根据前述模型,如果行为人对于惩罚的敏感度δ′的数值较小,即使较大的n′值也不能获得应有的效果。
惩罚式干预还包括对于诬告行为的惩罚。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处罚法》)对侮辱诽谤行为有所规定,但是并不适用于受助人诬告救助人的情境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 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二)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三)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四)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五)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六)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受助人诬告动机一般是不想承担或补偿救助费用,这是一种恩将仇报的不道德行为,法律很难干预。原因在于民法秉承的是填平主义思维,即有损害才有赔偿,而被诬告的救助人所受损害不容易界定。在公法层面,只有达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即欲通过诬告使对方承担刑事责任才能构成违法犯罪,中间存在较大空白地带。另一方面,即使受助人的行为触发了《治安处罚法》的规定,行政处罚的代价和恶意转嫁责任的衡量显然是不对称的。受助人可能会以自己是无意或者误会作为推脱,这也使得规则很难起到效果。
综上,惩罚式干预手段并不高明,即使其具有一定的威慑力,但是并不完善的运行机制,反而会导致法律权威性的降低。这也是现行法律没有使用这种干预方式的原因。
(二)奖励式干预
惩罚式干预方式存在诸多问题,那么,采用对于利他救助行为奖励的方式是否可行?目前,各地都存在对见义勇为或助人为乐行为的奖励性规定。虽然奖励式干预的实施效果较惩罚式的规定更优,但是也存在逻辑上的漏洞。
此处的奖励指的是积极性的奖励行为,即给予奖金、荣誉称号等方式。根据心理学研究,人类怀有奖励预期时,会产生纹状体(striatum)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的活动介导性激活,有关预期奖励和收到奖励的信息在纹状体和外侧前额叶皮层之间传递。这些过程受到神经递质调控,导致5-羟色胺(5-HT)水平的升高,并会由基于移情产生背侧前扣带皮层(dACC)和前脑岛(AI)激活②Marsh A.A.,“Neural,Cognitive,and Evolutionary Foundations of Human Altruism”,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Cognitive Science,2016,7(1),pp.59-71.。有关损失规避的研究发现,纹状体、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和杏仁核(amygdala)在放大损失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利益受损时,大部分受试者的神经区域被激活的敏感度要比在获取利益时更高③罗寒冰、徐富明、李彬等:《基于预期理论的风险决策的神经机制》,《心理科学》2015 年第2 期。。根据“前景理论”,人类对于损失所激发的心痛感受大约是同等数额获益而产生的欣悦感的三倍。
依此推断,好的激励模式是在行为发生前予以小额物质奖励,而在救助发生后给予大额物质奖励。这可以打破“支付意愿/接受意愿”(WTP/WTA)的边界,但与现行奖励制度不相契合,原因在于小额物质奖励固然有利于激活利他行为,但是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多人串通来扮演救助人和受助人而骗取奖励的情形。单纯的事后奖励,在数额无法超越当事人心理损失预期三倍的情况下,无法激活利他救助行为。这与实践中利他救助很难由见义勇为基金所激发,或者见义勇为基金与利他救助行为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现状是相符的。以此推论,有效制度设计的核心假设是:当受助方处在危急时刻应该先支付救助方一定数额的救助定金,救助行为才能发生。虽然这在心理学上是有效的,但是在制度设计上是荒谬的。奖励式介入会导致救助人在事后对行为效用的评价增高,但与行为动机的激发并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面批面改,教师一定要涉及不同层次的学生,选择对象按需重点指导,这样不仅有利于克服教师 “时间不足”等问题,而真正做到“因材施教”。这是因为:
(三)保障式干预
保障式干预是一种责任的转移和缓冲机制。在前述的效用函数中,n 是负值,这表明了在救助人的主观意识中,其可以预料到救助行为大概率会给自己带来损失。这种损失的风险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因利他救助行为本身造成损害而需要担责的风险,第二种是由于救助行为而先行垫付的费用无法得到偿还的风险。对于第一种,《民法典》184 条规定的免责情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仅仅是一种填补机制的作用,并无法形成对利他救助行为的有效激活。而在现实中,第二种风险成为利他救助激活阻却因素的可能性更大。
保障式干预意图由法律赋予政府充当“目击人”和“垫付人”的职责,进而形成双方之间的缓冲地带,以消减个体行为互动导致的“目击者问题”,化解上述的第二种风险。一种可能实现的方式是建立紧急备案机制。在智能手机如此普及的今天,录像取证已较为简便。利他救助人在事件现场进行录像取证,然后将这些证据迅速传至政府的服务器中,形成证据效力。医院将为受助人开通绿色通道,由救助基金或医院先行垫付。事后,相关费用可以由救助基金管理方或存在垫付行为的医院向受助人或其继承人追偿,这样就将利他救助人在这个利益链条中剥离了。据此,损失概率的值λ2会大幅降低,利他行为的效用感知得以升高。如果制度运行良好,则会激发人群的认同感、愉悦感,并演化为内生的良心和道德感,而广泛的道德感所带来的效应就是群体信赖利益(F 值)的升高,也就会越来越广泛地出现合作解。在不断的演化之中,合作和利他会变为内生动机和习惯,自私背叛的行为会逐渐演化消亡①自私背叛的行为并不会完全的消失,而是会在动态平衡中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参见Nowak M.,Sigmund K.,“A Strategy of Win-stay,Lose-shift That Outperforms Tit-for-tat in the Prisoner’s Dilemma Game”,Nature,1993,364(6432),pp.56-58。。
不过,保障式干预方式在现实中依然存在难题。其一,如果由于救助人先行取证而没有马上开始救助,受助人延误救治,那么是否适用《民法典》184 条的免责规定存在疑问。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需要界定先行取证行为是否意味着救助行为的开始。其二,将风险转移给政府和医疗机构的做法会导致政府和医院承受巨大的资金负担,而由于政府和医院缺乏行为激励,故可能落地困难或运行不畅。
四、作为助推的利他救助量化与账户化管理设想
前述三种干预方式在某些场景能起到作用,但是任何一种方式都无法成为完善的利他救助促进手段。为了扬长避短,笔者认为可以借鉴个人信用评分机制的基本思路,同时参考时间银行的运行原理,构建利他救助量化与账户化管理机制②在应对老龄化社会的进程中,时间银行的运行原理是:用某人无偿进行助老服务而获得的时间货币在其老去时换取别人的助老服务,而服务的登记机构类似于银行在储蓄这些时间货币。参见陈功、吴振东:《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时间银行”演变及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2 期。。其基本构建思路不是基于惩罚、奖励或者保障干预手段直接规定行为准则,而是把利他救助行为对于社会公益的奉献度量化为“公益分”,并构建个人账户进行量化分数的储蓄。
利他救助量化与账户化管理机制与《民法典》183 条、184 条并行不悖,其本质上是一种通过政府设立的公开赋分体系。政府作为量化算法的设计者,通过自身的公信力为系统记录的可信性背书。量化分本身的用途可以是多样的,更重要的是,其在具体的纠纷中还具有证据效力。赋分本身并非强制性干预或者直接规定行为后果,而是可以和不同的场景进行对接。学界将这种社会调控方式称之为“助推”(nudge)①在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的男士洗手间,小便器内侧会印上一只逼真的苍蝇,几乎所有使用洗手间的人都会瞄准这只印刷的昆虫而行动。经过一段的实验,设计者发现这种方式比使用警句式提示的方式能提升避免尿液溅出的有效率在80%以上。参见Worktile:《产品设计:如何用助推方式做出最佳决策》,https://zhuanlan.zhihu.com/p/56512324,访问日期:2022年11月20日。,其来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查德·塞勒与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卡斯·桑斯坦所著的同名书籍②理查德·塞勒、卡斯·桑斯坦:《助推》,孙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年,第2 页。。这一机制的核心思想在于探察行为背后的动机,在不使用强制性手段和硬性规定的情况下,引导人们做出更理性的选择。从社会物理学的角度,助推因素改变了复杂社会系统中参与者的行为演化路径,并不强制改变社会运行本身,而是通过微观因子的间接作用引发熵减,使得社会变得有序和稳定。最终,微观行为涌现出符合社会正义的宏观现象。
基于此,设想在实践中构建如下的利他救助量化与帐户化管理的运行模式。
首先,建立公益奉献量化体系,并将利他救助作为其中的一种类型。在广泛视角上,可以统一地对社会中存在的助人为乐、利他救助和公益捐献等行为进行社会公益赋分。几种行为的区别在于:助人为乐可以被认为是助人方和被助方的量化分的转移过程;公益奉献是被赋分的过程;利他救助是社会奉献度较大的善行,其不但是救助人和受助人之间分数的转移过程,而且应获得一定的分数加成。即救助人获取的量化分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被救助人账户中分数的转移,二是作为奖励机制的额外加成,“公益分”体系保持弱通胀。因利他行为而受惠的人需要支付自己账户中的分数,这样可以激励其在后续作出利他行为而弥补账户的缺额,形成一种可循环可持续的利他行为促进机制。
其次,建立利他救助量化的账户化管理机制。利他行为人可以将量化的分数存入个人账户中,同使用存款一样,在需要他人的帮助时支付此分数。另外,其调整了救助人在行为时的心理账户状态,克服了奖励式干预方式的弊端,由出于成本付出的损失感转化为正面获取的满足感,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弥合了由前景理论导致的效用评价扭曲。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系统运转,在制度初次实施前,政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个人账户中的分数初始值,与年龄成正比是一种可取的方式。公益分的储蓄不适用利息机制,不可贷取,如果为了更好地激励人们做出利他行为,可以适当使用负利息。
最后,将利他救助的量化和储蓄演化为一种评价方式。在智能化社会,根据评价标准和具体的算法可以计算个体的数据公益分,而这个分数可以表明个体的道德状况,救助人可以据此判断是否进行施救,同时便于在救助前进行电子化确认。一方面,可以证明双方已互相了解身份信息并认可了此施救行为,杜绝了讹诈的出现。同时,进行电子确认的过程也是“公益分”进行移转的过程。其符合行为发生的心理与神经机制,可以助推利他救助的发生。电子化的确认手段有多样化设计,包括二维码生物识别,无接触识别等。如果人群大多呈现相对的利他,此措施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另一方面,这一机制可以成为人们伦理道德水平的外显标准之一:同等条件下,公益分高的个体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机会。其本质上实现了利己和利他的融合,在纯粹利他外壳下,行为人内在动机可以是利己或互惠,只要这种利己或互惠动机没有变异为恶意串通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此机制的运行将有益于社会。
对于前述的三种外部干预方式的弊端,利他救助量化与账户化管理机制可以克服和弥补。虽然助推机制并没有在根源上解决旁观者困境,但是其对于救助人可以产生效用感知激励,融合了奖励式干预的优点并弱化了其缺点。同时,由于不是直接与金钱挂钩,这一干预方式可以削弱恶意串通的发生,也可以作为后续荣誉或者金钱奖励的先期审核机制,起到“防火墙”的作用。这个机制还可以降低诬告实现的可能性。对于诬告的处罚,公益分作为介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软性评价标准,会成为对被处罚人不利的风险因子,不安的心理会促使当事人主动去寻求弥补途径而做出利他行为,实现了教育和纠正的融合。最后,其本身包含保障式干预的作用。公益分的产生、储蓄和移转行为被记录,本身即为行为证据,同时公益分数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当事人对社会的贡献度以及诚信情况。相关机构对于公益分表现良好的个人应提供更多的优惠待遇。
利他救助量化和账户化管理可以促进利他救助的发生,但仍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当事人无暇顾及公益分的验证和转移,这是否说明此机制只适用于较为平缓的救助情境。另外,防止当事人通过串通或者不正当使用而刻意制造出自身道德水平高的假象仍需重视。通过区块链等技术,在具体场景中加入见证人或者关联行动人以及加强转移过程的真实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上述矛盾。笔者认为利他救助量化和储蓄机制最终将被社会信用体系所吸收。公益奉献量化是一种过渡性的设计,最终目的是建设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提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四方面建设内容。现有社会信用体系主要面向企业运行和金融借贷方面,而对涉及个人社会道德及公益奉献等方面的评价机制尚不够健全,未来道路仍漫长。
五、结语
这个世界会好吗?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的经济理性普遍觉醒,并不是人们见利忘义了,而只是对行为效用的感知比以前强烈了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制度需要唤起人们心中的善念。终究制度和规则所解决的是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问题。人非圣贤,一切社会问题的缘起都在于微观个体复杂的价值判断与衡量问题,最终导致在宏观层面的扩大,但是利他和合作是人类社会得以存续和永恒的价值追求。
利他救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是学界持续关注的问题①2022 年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奖”中,美国圣塔菲研究所Samuel Bowles 和Herbert Gintis 教授所关注的互惠、利他主义和社会合作话题依然是全球社会科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其论文被大量引用。。本文仅仅蜻蜓点水地串联了其内涵界定和促进机制中的几个核心问题。很多讨论尚为猜想与假设,还存在很多未解的问题。仅此为了证明理性人假设与利他救助行为之间并非相斥,但是需要制度的引导、促进与助推,最终目的是带来社会的稳定、合作与共赢。
希望这样的论述不是一种逻辑反复的徘徊,而是能让这个世界变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