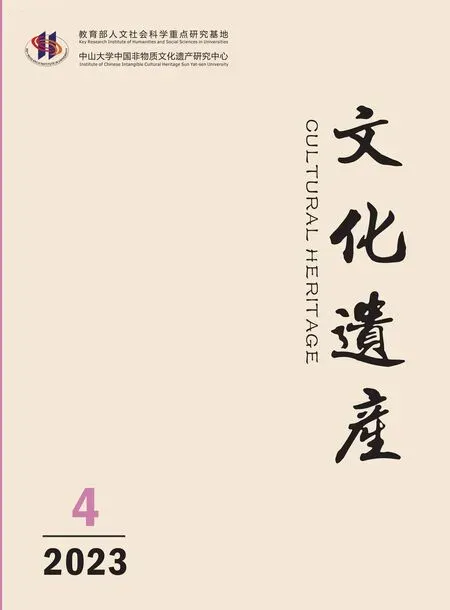“就戏论戏”与董每戡阐释剧本的着眼点
2023-12-24董上德
董上德
引 言
董每戡先生是中国戏剧学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中国戏剧学脱胎于古代的“曲学”,而与“曲学”显然有别。回顾往昔,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已经不等于“曲学”,却与“曲学”还相距不远,具体的表现是王氏论元杂剧之美独以“元剧之文章”为最,曰:“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8页。王氏将“元剧”和“元曲”混用,视为同义词,即可说明《宋元戏曲史》固然与明王骥德《曲律》不在同一个论说的层面上,却在“曲学”话语方面可以互为知音。所谓“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与王骥德的着眼点差不多,《曲律·论家数》曰:“曲之始,止本色一家,观元剧及《琵琶》《拜月》二记可见。……文词之病,每苦太文。雅俗浅深之辨,介在微茫,又在善用才者酌之而已。”(2)王骥德:《曲律》,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第121-122页。无论是王骥德还是王国维,都强调曲文可听可记,贴切自然,不能“太文”,要“如其口出”。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元剧之文章》里举出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无名氏等的曲文为例,说明“元剧之文章”是如何“语语明白如画”、如何“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语言”,其着眼点与王骥德仍大体相同。
董每戡是继王国维之后在中国戏剧学领域有独特贡献的学者。他阐释剧本的着眼点与上述“二王”大不一样,比较自觉地摆脱古已有之的“曲学”藩篱,不再将剧本视为“纯文学文本”;王国维曾不无自得地表述过对元杂剧作为“纯文学文本”的赞美:“若元之文学,则固未有尚于其曲者也。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87页。值得留意的是,王国维称颂元杂剧作为“纯文学文本”时更喜欢使用“元曲”一词。而董每戡研究戏剧的路数是从舞台而来,回到舞台而去,始终不离舞台,这与不喜欢亲近舞台、不爱好看戏的王国维显然有异,其研究戏剧的着眼点跟王国维相比可谓大异其趣。
从王骥德到王国维,“曲学”的演化线索自有其内在的学理逻辑,不能视而不见,也不宜轻易否定。可是,真就只是“这样”吗?
本文拟以董每戡的“就戏论戏”为话题,探讨其阐释剧本的着眼点。观察当下的诸多剧评,以及新出剧本,发觉五花八门,以“就戏论戏”而言,不得要领者并不少见,似乎有必要重新认识董每戡研读剧本的“法门”,以期有所借鉴。
一、“就戏论戏”的提出及其方法论意义
董每戡在《五大名剧论·自序》里明确提出:“我过去认为,现在还认为‘戏曲’主要是‘戏’,不只是‘曲’。‘声律’‘词藻’和‘思想’都必要予以考虑,尤其重要的是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所体现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是必须由演员扮演于舞台之上、观众之前的东西。作者没有向谁说话,甚至扮演者也没有为自己申说什么,他或她们只代剧中的登场人物向观众诉心,跟其他任何书面形式的作品有所不同。我们要谈它具有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应该有别于论其他文体的作品。咬文嚼字不为功,空谈概说欠具体,就戏论戏才成,我就这样练起来了。”(4)陈寿楠、朱树人、董苗编《董每戡集》第二卷《五大名剧论》,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17页。这番话,是夫子自道,也是董每戡论剧之“不二法门”。
仔细琢磨,这里有几层意思需要辨析。第一,面对“戏曲”,“就戏论戏”是董每戡一贯的主张,不论“过去”还是“现在”;第二,“戏曲”并非如以前的词曲研究家所认为的那样只有“曲”,更重要的是“戏”,“戏”与“曲”是统一的,统一在声律、词藻、思想的有机结合之上;第三,声律、词藻、思想,思想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过去的词曲研究家斤斤计较于声律如何、词藻怎样,而忽略了思想,可谓不得要领,而剧作不是论文,必定要借助舞台演出、透过人物性格命运的转化、社会关系的变动、情感取向的调整等等来表达思想,舞台扮演、情感呈现必定要艺术化,故此,“尤其重要的是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所体现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是必须由演员扮演于舞台之上、观众之前的东西”;第四,“戏曲”毕竟是戏剧,不同于其他文体,它不能没有舞台,所有的戏剧时空都呈现于舞台这一“空的空间”里,金戈铁马,花前月下,帝王的宫殿,贫民的破房,如此等等,都可以被容纳在舞台这个“空的空间”之中,千变万化,无所不包,这是除戏剧之外其他任何文体所不具备的,正因如此,剧本作为一种“文本”,永远是处于“尚待最后完成”状态,文本撰写与舞台演出结合起来,才算最终完成了的一台戏,在这个意义上,不是剧作家说了算,也不是扮演者说了算,而只能是完整的“舞台呈现”说了算,“作者没有向谁说话,甚至扮演者也没有为自己申说什么,他或她们只代剧中的登场人物向观众诉心”,这就是舞台演出的奥妙所在,也是舞台不为词曲研究家所理解的一大难点;第五,说一千,道一万,“咬文嚼字不为功,空谈概说欠具体”,这绝对不是研究戏曲的正途,研究戏曲,不可轻视“曲”,更要重视“戏”,“戏”是决定性的,“曲”具有从属的性质,二者关系不可不辩,依照辩证思维的方法,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戏”就是“戏曲”中的主要方面,研讨剧本,得其要领,就得“就戏论戏”,除此别无他法。
提出“就戏论戏”的主张,是董每戡的独到之处,在他之前的“戏曲史家”如王国维、吴梅,没有这样明确提出过;就是董每戡一再表达敬意、在他心目中是戏剧行家的李渔,也没有这样清晰地表达过立场。
上引《五大名剧论·自序》写于1965年冬,董每戡避居长沙。借助“互文性”思维,我们可以将《五大名剧论》与此前董每戡已经完成的两部书稿联系起来看,这两部书稿是写于1958年至1959年期间的《中国戏剧发展史》和《笠翁曲话论释》。董每戡知道限于体例,《中国戏剧发展史》要注重“史味”,不可能将元明清三代的戏剧名作一一论列,于是,采取一个“补救”办法,“选古典名剧若干来论析,作为《笠翁曲话论释》一书的具体实践,免招来只空谈如何作剧怎样评剧的理论而不付诸行动之讥。”(5)陈寿楠、朱树人、董苗编《董每戡集》第二卷《五大名剧论》,第115页。可是,还是限于体例,也不能在以阐释李渔的戏剧见解为主的《笠翁曲话论释》里详尽、完整地解读历代名剧。故而,在写完《笠翁曲话论释》(此书于1966年被抄走,今天所能见到的是董每戡于1974年补写而成的《〈笠翁曲话〉拔萃论释》)之后,于1962年开始写《五大名剧论》,1965年冬完稿,比较详尽、完整地解读了元明清三代的五部名剧,并且在该书自序里明确提出“就戏论戏”的主张,此主张也是他写出《五大名剧论》的看家本领。《五大名剧论》可以说是写于1955年且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琵琶记简说》的扩展版,由《琵琶记》而延及《西厢记》《还魂记》《长生殿》《桃花扇》,董每戡说“我过去认为,现在还认为‘戏曲’主要是‘戏’,不只是‘曲’”,有其内在的、一贯的学理逻辑,而且是自有古代“曲学”以来、继李渔《闲情偶寄》(即董每戡更喜欢用的《笠翁曲话》)之后在中国学术界最早具有“戏剧学”视野的学理逻辑。这一学理逻辑,与其说是董每戡的,不如说是董每戡得心应手运用于其戏剧研究及戏剧批评的“当行把式”,因而也就内含着对于戏剧学者而言的方法论意义。
二、“就戏论戏”之“戏”与“法”的辩证关系
在董每戡的“戏剧学辞典”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戏”,一个是“法”。董每戡写出《琵琶记简说》后,心目中以《琵琶记》为基准,用以衡量其它剧本的剧作水平。肯定有不少是比《琵琶记》差的,否则,他选出的名剧就不会只有“五部”;可是,经过仔细的研究,尤其是运用“就戏论戏”的方法,董每戡发现有的剧作竟然高于《琵琶记》,这就更值得来一番“就戏论戏”,将其中的奥妙说透,于是就有了《五大名剧论》之一的《西厢记论》。且看董每戡写出《西厢记论》稿子后于1973年补写的一番话:“无论法或词,《西厢》的成就确要比《琵琶记》高。”(6)陈寿楠、朱树人、董苗编《董每戡集》第二卷《五大名剧论》,第149页。这番话很重要,董每戡研究剧本,“法”是个重要的着眼点。
董每戡关注的“法”主要有以下意蕴:
1. 创作剧本的出发点只有一个,就是“登场”。
众所周知,传世的王实甫《西厢记》杂剧改编自金代董解元《诸宫调西厢记》,这一点,董每戡是充分认识到的,可是,他又提高声量地表示:“不管王实甫是否以《董西厢》为依据,我始终要称之为创作。”理由是:《西厢记》是演唱本,《董西厢》是说唱本,“演唱本跟说唱本自有不同之处,为了它须在舞台上由演员表演于观众之前,已不是由说唱艺人说唱在听众之前,而是在诉之于耳朵之外,加上了诉之于眼睛这个条件。”(7)陈寿楠、朱树人、董苗编《董每戡集》第二卷《五大名剧论》,第171页。这个理由是过去的“曲学家”和“戏曲史家”所忽略的。不过,能够指出这一点,不是董每戡的厉害之处,他的厉害在于,不能只是看到故事(剧情)与原著相比是加多了还是减少了,不能仅仅注意到故事(剧情)中的某些情节是变小了还是变大了,这些都是次要的,对于“登场”而言,所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董每戡心目中,“登场”不是将“说唱”转换成“演唱”那么简单,“登场”的要义在于在舞台这个“空的空间”里,活生生的“张三”与活生生的“李四”,他们或许是唐朝人,或许是宋朝人,或许是明朝人,都不打紧,打紧的是他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张三,他是无可替代的“那一个”李四,他们各有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成长环境,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遭际,不同的利害关系,由此必然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冲突,这就是“戏”。其中,“人物性格”是第一要素。董每戡比较过演唱本的《西厢记》和说唱本的《董西厢》,前者对后者当然有改动,这不是要点,要点是“实际大动的在于人物性格”。这是他认为《西厢记》不是改编而是创作的立论依据,董每戡在《西厢记论》里有一个专节“主要的人物形象”,对崔老夫人、郑恒、崔莺莺、张生、红娘均有具体、细致的性格分析,并且一一与《董西厢》做比对,说明王实甫在整个创作《西厢记》的过程中“实际大动的在于人物性格”,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读者自可阅读原书。
这里想融汇董每戡的论述,同时受到其启发,也间出己意,申述一下“人物性格”与“登场”的关系。
“人物性格”与“登场”的关系真的那么重要吗?答案是十分重要!试想,舞台这个“空的空间”,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上去的。舞台尽管是“空的空间”,可这也是十分稀缺的空间,在古代的农业社会,年头到年尾,除了节庆神诞,平时没有演出,这个“空的空间”真的是空着,过去的乡间常有“看饿戏”的说法,就是因为人们的“戏瘾”被“饿”了很久,好不容易“开台”,大家争先恐后前往看戏。如果舞台上随便一个个平时也能见到的张三、李四登场表演,却有什么好看?必定是具有典型性的人物遇到了典型性的事件,展开了典型性的冲突,如此这般,满台是“戏”,这才好看,才能让大家过足“戏瘾”。人物的典型性是“登场”的第一重意义。
“登场”的第二重意义是,有性格的人物必有自己的主见和意志,他不服从命运,不服从压迫,不服从欺诈,就如同元杂剧《陈州粜米》里的不畏惧权贵贪官的张氏父子那样,跟欺压老百姓的刘衙内等死磕,誓死捍卫老百姓的权利和尊严,老子死了也要儿子继续抗争,这就是“戏”。要是换了没有性格的人物登场,汤汤水水和稀泥,有什么好看?
“登场”的第三重意义是,人物的性格冲突不是一个回合就能了事,必定是如同“张飞夜战马超”一般,一轮又一轮,一番番的较量方能定出胜负,这样的“戏”谁不爱看!
一个故事,可能是家喻户晓的,但是,高明的剧作家要是下决心搬上舞台,必定有他的“独门秘笈”,为了“登场”,在人物性格上做文章。明乎此,研究剧本,也要从故事蓝本与戏剧新本的比对中考察剧作家是否对人物性格下了功夫,是否有独到的眼光,是否有非同一般的挖掘。
中国戏剧学,在董每戡之前,没有人如此贴近舞台地揭示出上述原理。
2. 戏剧行为的“动力源”只能有一个,就是“主脑”,所有的情节受到“主脑”的牵控;戏剧的“主脑”必定内含“戏剧行动”,否则,就不是“主脑”。
董每戡十分认同清李渔对《西厢记》的基本判断,即“一部《西厢》止为张君瑞一人,而张君瑞一人,又止为‘白马解围’一事。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是‘白马解围’四字,即作《西厢》之主脑也。”(8)陈寿楠、朱树人、董苗编《董每戡集》第二卷《五大名剧论》,第174页。董每戡指出,李渔这一说法“很中舞台演出台本的窍要”,且进一步分析:“所谓‘白马解围’这个关目,就包括在第二本第一折及‘楔子’中,也即所谓‘寺警’。前头所有的种种只不过是整部戏文的‘发端’,‘寺警’才是整部戏文的‘主脑’——大关键,所有的一切矛盾冲突都由它派生出来,而剧本的思想意义也在这一切矛盾冲突中体现出来。也就是说,有老夫人的‘许’,才产生张生的‘望’,由于‘许’变‘赖’使张生失望,才产生红娘的‘勇’和莺莺的‘敢’,由于她的‘敢’使张生不失‘望’,才产生郑恒的‘争’,一环套着一环,一连串的思想产生了一连串的戏剧行为。……行动比诸‘曲子’和‘宾白’更有力量,投入观众的眼睛而钻到观众心里头去的东西,比说话更响亮动人,所以说:‘戏剧就是行动’。”(9)陈寿楠、朱树人、董苗编《董每戡集》第二卷《五大名剧论》,第174-175页。
与某些学者分析《西厢记》的“戏剧动因”时格外关注女主人公的“临去秋波那一转”不同,董每戡与李渔都高度重视“白马解围”,视为“主脑”。“临去秋波那一转”只是内含着一刹那的“感触”,构不成“行动”。可是,确立“白马解围”为“主脑”就如同做豆腐要点卤,没有使得豆浆凝固的介质,豆浆永远也不会成为豆腐;没有“白马解围”作为可以令全剧结合为有机整体的“介质”,张生与老夫人、莺莺、红娘也就不可能有“戏”。换言之,如果缺少“白马解围”,张生就不可能与剧中其他主要女性人物发生交集,男女授受不亲,普救寺内各走各路,各吃各饭,如此而已。上引董每戡的分析,可谓抽丝剥茧,环环相扣,戏剧行为的肌理脉络十分清晰。原书在此基础上还有更为细致详尽的阐释,相当精彩。
不宜将戏剧的“主脑”理解为“主题”。“主题”是不同文体都会有的,在很大程度上,除戏剧以外,“主题”与“主脑”对于绝大多数文体而言起码是近义词;但戏剧不同,戏剧的“主脑”不一定是“主题”,因为戏剧的“主脑”具有“发动机”功能,其功能性很突出,却不一定非要担负起揭示“主题”的责任不可。一部戏剧如同一台机器,一定要“动”,不动就没“戏”;而要让整台机器动得起来,倒是非要有“发动机”不可,这就是董每戡和李渔这样的戏剧行家十分重视《西厢记》里“白马解围”的戏剧功能的原因。阐释剧本,找不到“动力源”,就会徒劳无功。
3. 没有“阻碍”就没有戏剧,合乎生活逻辑和历史逻辑地呈现“阻碍”是戏剧家的必备手段。
董每戡明确指出:“戏剧不同于其他文体……戏剧必须写‘阻碍’,也即‘矛盾’,要不,平铺直叙,生活中本有矛盾也只轻轻带过,在舞台上就难以动人。当然,矛盾不是作者硬制造出来的,凡生活都像一条溪流,绝不是一池死水。活泼泼的溪水流过之处,必有一些小石子、大石头阻挡着,不那么畅通无阻,遇上小石子,可能逗起一些涟漪,碰上大石头,就激出一些浪花,涟漪和浪花,都是矛盾的结果,但正是生活的美。戏情必依据人的生活,有生活才有戏,生活上出现矛盾,由矛盾产生了‘危机’,‘危机’之来临核对解决,都须合情合理,符合于生活逻辑。”(10)陈寿楠、朱树人、董苗编《董每戡集》第二卷《五大名剧论》,第179页。董每戡在分析《西厢记》里的“阻碍”时,自然聚焦老夫人,认为“白马解围”之后,老夫人不兑现承诺,一再赖婚,是有其生活逻辑和性格逻辑的,而且,在深入分析时,董每戡进一步指出唐代郑、崔均为大姓显族,老夫人姓郑,莺莺小姐姓崔,老夫人看不起白衣张生,还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
董每戡具体分析了剧情从“寺警”逐步演化到“请宴”“赖婚”的内在“戏路”,写道:“‘寺警’固然是全剧的主脑,‘赖婚’则是具极大关键性的戏,……‘寺警’只是‘突如其来’的外部矛盾,在现象上很凶恶,相反,在实质上是张、崔婚姻瓜葛之因,也就是若无‘寺警’,哪来这个‘倚翠偷期’的故事?‘请宴’则不同(11)笔者按:此处“请宴”实指《西厢记》第二本第二折至第三折的内容,含有“赖婚”。,是内部矛盾,在现象上看起来不激烈,实质却是婚姻问题上的大障碍,这个障碍之所以必有,不全由于老夫人的个性来,它有‘根深蒂固’的社会根源,和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的社会生活关系分不开。”(12)陈寿楠、朱树人、董苗编《董每戡集》第二卷《五大名剧论》,第190页。戏剧中的“阻碍”或“矛盾”,除了有小障碍,还有大障碍;其生成的原因除了有外在的、突发的矛盾,还会有内在的、深层次的矛盾;除了有生活逻辑,还会有历史逻辑,如果能够一一借助舞台手段揭示出来,这样的戏剧就会有出人意表的深度。同时,只有将外在的矛盾与内在的矛盾沟通起来、交错起来、纠缠起来,深谙此作剧之“法”,“戏”才会充分展开。
这就是“戏”和“法”的辩证关系。
三、董每戡阐释剧本的着眼点是谈论戏剧的“公约数”
董每戡自觉地与“历来的词曲研究家”划清界限,其心理动因是自己阐释剧本之着眼点与“历来的词曲研究家”有着根本的区别。且看他如何表达对“历来的词曲研究家”的不屑。
他在《西厢记论》里有一个观点是相当自信且十分得意的,就是认为在“西厢私会”之后、“长亭送别”之前老夫人再一次赖婚。董每戡重视戏剧里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对撞”,他尊重剧情的实际,提出“赖”是最大的“障碍”,这个“赖”字并没有随着“长亭送别”而消失,相反,老夫人以一种更为狡诈阴沉的方式继续赖婚,明里是“许”,实质是“赖”。董每戡引用了老夫人此时对张生说的一段话:“好秀才呵,岂不闻‘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我待送你去官司里去来,恐辱没了俺家谱。我如今将莺莺与你为妻,则是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我与你养着媳妇,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董每戡在此处“敲黑板”:“注意,这儿老夫人说的最末两句话,不,实则十分重要的只最末了一句话。可笑历来的词曲研究家们居然不稍予深思,竟也会相信老夫人不是在‘刷花枪’,诚信许婚了。读者试想想看,真正的许婚,哪能有这样许法的?真正许婚的人纵怕张生此科落第,定要他赶快回来结婚,并等待下一科再去应举。……真心诚意许婚的人绝不会说出‘驳落呵,休来见我’的话。”(13)陈寿楠、朱树人、董苗编《董每戡集》第二卷《五大名剧论》,第217页。董每戡认为老夫人此处是“明许暗赖”,是有充分依据的,他顺着“寺警”“请宴”“赖婚”以至“传简”“偷期”“拷红”“饯别”等情节线索,看出一直在关键之处左右剧情演化的就是老夫人的“赖”,这就是戏剧家眼中的“戏情戏理”,而“历来的词曲研究家”却无此敏感,也无此意识。
在《五大名剧论》里,董每戡以自己的戏剧家之眼不仅揭示出许多名剧里的奥妙和经验,也点出了一些名剧里的败笔和缺陷,对《西厢记》里张生的某些轻浮举动,对《长生殿》里后半部分的松散拖沓,均有批评。这些也是过去的“词曲研究家”没有提出过的。
“就戏论戏”是董每戡的一个核心主张,表面上,没有故作惊人之语,像一句大白话,可是,要是回顾中国戏剧学走过的漫长路程,要是明白曾几何时“曲学”一统天下,要是知道高明如王国维尚且与传统“曲学”拉不开距离,就可以深感董每戡的“就戏论戏”意涵丰富,具有方法论意义,且对于戏剧批评和戏剧创作均有重要的启示。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片面否定传统“曲学”,“曲学”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学问和真义。可是,“曲学”的确有严重的缺陷,具体表现是说“曲”不说“戏”,重“曲”不重“戏”,见“曲”不见“戏”。重温董每戡的戏剧见解,反观当下的戏剧批评和戏剧创作,我们固然不会满足于“就戏论戏”,但是,如果不“就戏论戏”,失去共同讨论戏剧的前提,戏剧又如何能够满足舞台的需要呢?
董每戡阐释剧本的着眼点已经成为我们今天谈论戏剧的“公约数”,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均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