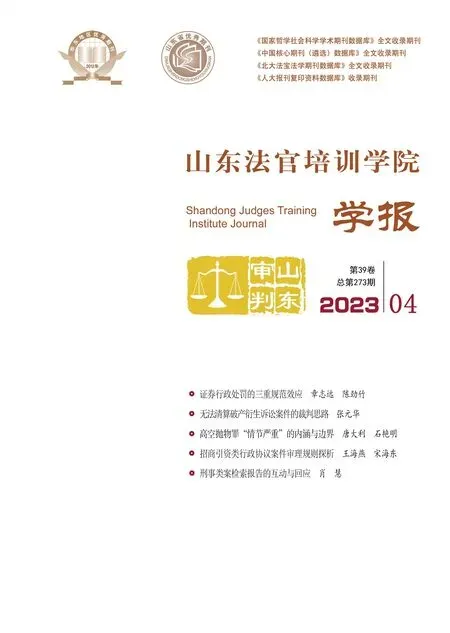高空抛物罪“情节严重”的内涵与边界
2023-12-23唐大利石艳明
唐大利 石艳明
近年来,高空抛物案件层出不穷,保护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更为有效地规制高空抛物行为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高空抛物罪,为惩治高空抛物犯罪提供了更为精准的法律依据。高空抛物罪增设实施两年多来,其惩罚、规范、预防功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挥,但司法实践中对于高空抛物罪“情节严重”在理解适用上还存在一些偏差。本文尝试明确高空抛物罪构成要件要素“情节严重”的内涵和边界,以期探寻该罪司法适用的正确路径。
一、“情节严重”裁判规范的功能失范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全国为范围、以2023 年7 月18 日为截止日期共检索到198 篇涉及高空抛物的刑事判决书。①检索条件:案由为刑事案由,案件类型为刑事案件,文书类型为判决书,全文关键词为“高空”“抛物”。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共检索到212 篇判决书,经甄别,删除关联性不强的判决书14 篇。该类判决书数量从2012 年至2019 年,每年均为个位数;2019 年10 月2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发布后,该类案件逐渐多发,2020 年增至35 件;2021 年3 月1 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高空抛物罪,该类案件更是大幅增长,当年即增至101 件。根据定罪的罪名分析,《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高空抛物罪取代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为规制该类行为的主要罪名。然而,考察高空抛物罪有关判决,其在“情节严重”的认定上存在诸多问题。
(一)“情节严重”规范功能失范的样态
1.“情节严重”中的客观要素体现不明确
高空抛物罪的构成要件为“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笔者分析样本文书发现,大部分判决书对客观构成要件要素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并未明确体现。以“高空”要素为例,198 篇判决书中,列明高度的判决书仅有9 篇,45 篇判决书未提及高度或表述为“高空”,14 篇判决书表述为“顶层平台、楼顶、天台”,130 篇判决书表述为“N 楼”。绝大部分裁判文书并未将“高空”在个案中量化为具体的高度,因而难以明确体现行为人抛掷物品具有何种程度的危险性,是否已经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
2.“情节严重”的主观要素考察不充分
高空抛物罪属于故意犯罪,实践中应区分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主观心态。行为人对行为结果存在希望、放任或者排斥不同的主观心态,直接影响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以及具体量刑。犯罪动机虽然不是此罪构成要件要素,但对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行为恶劣程度及具体量刑仍存在参考意义。样本文书中,多数判决对行为人的罪过、犯罪动机没有描述或者表述得较为概括,对行为人主观方面与行为“情节严重”之间的关系一带而过,考察不够充分。判决书未体现罪过及犯罪动机的为87 篇,列明行为人对抛掷地点有明确认知的仅为12 篇,明确体现主观动机为“发泄情绪”“因楼下吵闹阻止他人行为”“贪图方便”“对抗警察执法”的分别为39 篇、10 篇、9 篇、3 篇。
3.“情节严重”的边界不清晰
高空抛物罪法定最高刑为有期徒刑一年,属于轻罪,但高空抛物行为除扰乱公共秩序外,还可能对人身、财产造成损害,存在与其他犯罪如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发生竞合的可能。然而,由于“情节严重”的边界尚不清晰,部分案件亦未对被害人的人身伤害的程度、财产损失的数额进行司法鉴定,未基于损害后果按照该罪名第2 款的竞合规则处理,而多以高空抛物罪定罪处罚,存在重罪按照轻罪处理的可能。
(二)“情节严重”规范功能失范的成因
司法实践中产生的诸多问题,根源在于对高空抛物罪“情节严重”内涵与边界的把握存在偏差。具体成因如下:
其一,立法供给不足。因高空抛物罪新增不久,关于“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形存在规范缺失,立法层面未予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亦尚未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法院在适用本罪时缺乏相应的规范参考。
其二,罪体理解空洞化。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情节严重”内涵的理解存在空洞化倾向,往往仅遵循扰乱公共秩序的解释进路剖析本罪的入罪门槛,如此各种形态的高空抛物行为均可解释为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情节严重”本应发挥的限缩解释功能未被有效激活。
其三,竞合规则处理僵化。由于对“情节严重”边界把握不够清晰,在部分案例的犯罪行为已经触犯其他重罪时,仍按照高空抛物罪定罪判刑,竞合规则在此处的应用近乎失灵。
二、高空抛物语义射程内“情节严重”的内涵
“情节严重”属于整体性评价要素,须以“高空”“抛掷”“物品”等构成要件要素的语义解释为基础,才能确定“情节严重”的具体内涵。
(一)“高空”之“情节严重”的内涵
1.“高空”的基本内涵
第一,“高空”的规范含义。“高空”,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距地面较高的空间。关于“高空”在法律规范中的具体含义,根据国家标准局发布的《高处作业分级》(GB 3608-83)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的规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 米以上(含2 米)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均称为高处作业;立法机关对《民法典》第1240 条关于“高空”的解读也采用了2 米的标准。①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 年版,第281 页。上述高空标准侧重从高空施工作业的人员的安全角度,根据其坠落受伤的风险程度而确定,而高空抛物罪的高度侧重抛掷物品在多高的标准下会造成他人生命、身体以及财产的损害。仅依照上述规范的标准无法把握高空抛物罪中“高空”的规范要旨。
第二,“高空”的实质含义。探究“高空”的实质含义,应当从该空间抛掷物品是否会对他人产生冲击力或破坏力的可能性来判断,如果存在,即属于实质意义的“高空”。从物理学角度分析,以高空中物体经自由落体运动后下降到地面所产生的冲击力为例,该冲击力为Ft,F 是作用于这个物体上的力,t 是力在该物上作用的时间。Ft=mgt,m 为物体质量,g 是重力加速度(系常量)。在高空中经自由落体运动的物体,在忽略空气阻力的情况下,其初始速度为0,即V0=0,末速度V1=V0+gt=gt,物体下落的高度h=V0t+1/2gt2= 1/2gt2,t=√2h/g。最终,Ft=mgt=mg √2h/g。
从该公式中可知,物体从高处下落,其砸中的人或物品所产生的冲击力Ft,与物体的质量m 和下落的高度h 呈正相关,该冲击力是物体本身质量的g √2h/g 倍。综上,高空抛物罪中“高空”的实质含义是能使物品因高度落差而产生垂直动能的空间。
2.“高空”之“情节严重”的识别因素
第一,“高空”的起点。高空起点涉及的问题主要是高空抛掷物品的起点是否应以地面为参照物。根据冲击力公式可知,物品因落差所产生的动能仅要求抛物点与落点之间存在一定的垂直距离即可。因此,高空不限于以地面为参照物,从地面或地下的高层空间向地下的低层空间的抛掷行为也符合高空的实质含义。抛掷物品的高空起点与落点之间的垂直距离越大,其行为所蕴含的危险性越高,情节也越严重。
第二,“高空”的落点。“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在性质上属于人类活动的公共场所,即从此处抛物才会对公共秩序造成扰乱。因此,高空抛物的落点是否为人员密集或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是否系公共通行的交通路段等情形,均为落点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识别因素。高空抛掷的物品在坠落中所砸中的具体对象也属于评价该行为危险性的重要因素,比如抛掷物品砸到行人、砸中汽车、摩托车等财产,亦应被评价为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①参见李永禄高空抛物罪案,陕西省岚皋县人民法院(2021)陕0925 刑初61 号刑事判决书。
(二)“抛掷”之“情节严重”的内涵
1.“抛掷”的基本内涵
“抛掷”系指以投、扔等动作丢弃、弃置物品的行为。“抛掷”区别于“坠落”,该行为本身包含了行为人对物品从高空下落具有故意的主观心态,并且物品因“抛掷”和“坠落”所产生的物理轨迹亦存在差异。
司法实践中的抛掷行为包含直接抛掷和间接抛掷两种,前者系行为人将物品直接抛出的行为,后者系行为人实施其他行为的过程中导致物品发生坠落的行为,比如行为人因与他人吵架而摔砸室内物品,物品触地后弹至窗外发生坠落的情形。
2.“抛掷”之“情节严重”的识别因素
判断抛掷行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可以根据下列因素识别判断:一是抛掷行为的目标性。存在特定目标的抛掷行为,行为人为击中目标,在投掷时往往对物品施加具有指向性且相对更大的作用力,致使物品降落时的初始速度增加,其所产生的冲击力及破坏性明显高于无目标性的随意抛掷行为。二是抛掷行为的具体方式。直接抛掷蕴含行为人追求或放任物品坠落的结果,而间接抛掷中行为人对物品的坠落结果更多是放任或排斥心态。在主观恶性方面,直接抛掷比间接抛掷更为严重。三是抛掷行为发生的时空环境。比如,在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下的抛掷行为,有可能会对抛掷物品施加其他作用力,物品落地范围及冲击力亦随之增大。四是抛掷行为的次数及频率。抛掷行为发生的次数越多、频率越高,单位时间内给他人人身或财产造成的危险性也越高,情节亦更为严重。
(三)“物品”之“情节严重”的内涵
1.“物品”的基本内涵
根据冲击力公式,原则上有质量的物体均属于高空抛物的物品范畴,故无需对物品的具体范围进行限定,重点是通过“情节严重”对高空抛掷物品的危险性大小进行评价。
2.“物品”之“情节严重”的识别因素
对抛掷的物品“情节严重”的考察,具有过滤出不属于犯罪行为的违法行为以及甄别构成更为严重的其他犯罪行为的双重功能。
其一,“物品”之“情节严重”的归入。高空抛掷的物品能否被评价为“情节严重”,可参考以下因素:一是物品的质量、数量。该因素直接决定冲击力的大小,故而物品质量大、数量多更容易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二是物品本身的危险性。如菜刀、剪刀、玻璃、建筑垃圾等,其对人身、财产的危险性显然更高。三是物品本身虽对他人人身、财产不具有危险性,如粪便、尿液、污水等污秽物,但抛掷该类物品对公共秩序造成严重损害的,亦有可能构成“情节严重”。
其二,“物品”之“情节严重”的边界。行为人从高空抛掷易燃易爆物品、毒害性、放射性或包含其他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如抛掷煤气罐、氢气瓶、灭火器等物品,该行为已经超出高空抛物罪的评价范围,如果已经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程度的,应直接按照爆炸罪、放火罪、投放危险物质罪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行为人从高空抛掷零星纸片、羽绒、泡沫盒等物品,该类物品危险性较低,客观上难以评价为“情节严重”。
三、高空抛物原理属性对“情节严重”的边界廓定
(一)双层法益视域下的“情节严重”
“情节严重”属于高空抛物罪构成要件要素,其边界廓定有赖于高空抛物罪法益的明确,盖因法益对构成要件所具备的解释论机能。
1.法益归属廓定“情节严重”的解释边界
其一,集体法益解释空间外延过大。《刑法修正案(十一)》将高空抛物罪设置于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高空抛物罪的法益即应是公共秩序。公共秩序的法益属于集体法益(超个人法益),其解释空间相较于个人法益更大,解释空间极易外溢,由此容易导致民众自由的萎缩,降低此罪的入罪门槛,故有必要限缩其法益的解释边界。
其二,可还原为个人法益的“假象的集体法益”。假象的集体法益是指实际上系为保护个人法益,但因该行为的危害性较大,因此提前介入形成保护集体法益的假象的法益类型。高空抛物罪增设初衷源于“高空抛掷物品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损害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①王爱立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1144 页。。可见,高空抛物罪的立法原意在于保护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故其法益属于典型的假象的集体法益,该法益内部可进一步解构为属于保护集体利益的阻挡层法益和保护个人利益的背后层法益,②在风险社会,刑法中存在大量为了保护A 法益(背后层)而保护B 法益(阻挡层)的立法现象,只有有效地保护阻挡层法益,才能更好地保护背后层法益。参见蓝学友:《规制抽象危险犯的新路径:双层法益与比例原则的融合》,载《法学研究》2019 年第6 期;张明楷:《污染环境罪的争议问题》,载《法学评论》2018 年第2 期。由此可以发挥双层法益的解释机能,从而廓定“情节严重”的边界范围。③亦如德国学者许遒曼所言:“法益理论首先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实际上只是个人法益,却被认为是集体法益之假象的集体法益提出批评。它能透过简单的法律解释方式提出决定性的理由,对可罚性范围为合理地限缩。”[德]许遒曼:《法益保护原则——刑法构成要件及其解释之宪法界限之汇集点》,何赖杰译,载许玉秀、陈志辉合编:《不移不惑献身法与正义——许遒曼教授刑事法论文选辑》,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版,第244-246 页。
2.阻挡层法益:公共秩序
社会管理秩序法益的外延极其广泛,其限制构成要件解释范围的功能较弱,可能导致在具体案件中,对于某些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界定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或争议性。解决途径主要在于细化公共秩序的类别、把握公共秩序的核心特征、严控仅破坏公共秩序而尚未危害人身财产安全行为的量域标准。
第一,细化类别:不得从建筑物等高空随意抛掷物品的公共秩序。结合本罪构成要件要素的具体特征,可以对集体法益作进一步分类。高空抛物罪法益主要针对高空范围的管理秩序(包括高空不得随意抛物、无人机等飞行器的管理等),因此可进一步细化为不得从建筑物等高空随意抛掷物品的公共管理秩序。
第二,把握核心:“场所性”特征。公共秩序具备“场所性”特征,它是指在社会模型中,公共秩序是各个“场所”运转的统一集合。④参见陈伟、王文娟:《从民生角度完善公共秩序刑法立法》,载《检察日报》2018 年6 月24 日,第3 版。高空管理秩序的“场所性”即要求抛物地点必须是处于存在人类公共生活设施的场所,即公共场所的高处。此处的“公共场所”应当具备开放性(或半开放性)和他人活动可能性两大特征。①正因为如此,《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草案中的“从高空抛掷物品”修改为“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建筑物”的衍生含义就是处于人类经常活动的公共场所,此处的“其他高空”应当参照建筑物做同类解释,即涵盖在公共场所内的高空。比如,行为人在荒野中废弃厂矿的楼上、在人迹罕至的高山、在自家宅基地建筑的屋顶抛掷物品,因其抛物场所的公共性较低,不具备损害公共秩序的可能,故不构成高空抛物罪。
第三,量域要求:达到“临界值”。解构假象的集体法益的内部双层结构并非要求成立高空抛物罪必须同时侵犯阻挡层和背后层法益,既然集体性法益的设立初衷系更为前置、有效地保护个人法益,那么对于仅仅侵害集体法益,尚未直接侵犯个人法益的行为当然也有处罚的必要,但考虑到集体法益的外延性过大,故应对侵犯集体法益的量值作出要求,以此来限制处罚范围。即侵犯集体法益的程度必须达到较大的量值,对应到构成要件层面,就是要发挥“情节严重”的限制处罚的功能。比如,行为人从楼上泼大量的尿液、粪便等污秽物,②参见石祖波:《疫情期间有人高空泼粪?澄迈警方介入调查,查实将严惩》,载微信公众号“南国都市报”,2020 年2 月25 日。其虽然对于个人的生命和身体几乎不会产生危险,但该行为侵犯了公共秩序,达到社会公众能够忍受的“临界值”,故可以认定侵犯了高空抛物罪的法益,在客观方面具备入罪的可能。
3.背后层法益:个人法益
是否侵犯背后层法益,主要根据行为是否具有造成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的可能性来判断。与公共安全类犯罪不同,高空抛物罪背后层法益并不要求必须损害“不特定或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比如,楼下的某个孩子吵闹,为吓唬制止,行为人从三楼将一个啤酒瓶和一双运动鞋抛掷楼下,抛掷物品并未砸中孩子,但法院依旧判定其构成高空抛物罪。③参见韦继全高空抛物罪案,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1)粤0112 刑初1090 号刑事判决书。此案行为人针对的系特定人,但因为高空抛物罪的背后层法益并不要求针对不特定多数人,故而其行为仍侵犯了个人法益,虽未砸中孩子,但结合当时的情境,行为人的抛物行为具备造成危险的可能,故认定构成高空抛物罪。
(二)情节犯视域下的“情节严重”
罪状中关于“情节严重”的表述,是我国刑法“定性+定量”定罪模式的特有产物。置于情节犯理论范畴,高空抛物罪的“情节严重”的解释面临三个问题:一是“情节严重”本身是否需要被行为人所认识;二是“情节严重”是否包含主观要素;三是从实证法的层面,考察我国刑法分则中情节犯中具体情节的类别,以此作为确定高空抛物罪“情节严重”具体情形的参考。
1.“情节严重”是否需要被认识或具有认识可能性
第一,“情节严重”是否需要被认识应区别对待。围绕“情节严重”的性质,学界存在“罪量说”“犯罪成立消极条件说”“整体的评价性要素说”“客观处罚条件说”“区别对待说”等。①参见王莹:《情节犯之情节的犯罪论体系性定位》,载《法学研究》2012 年第3 期。上述学说看似不同,在司法实践的区别意义仅在于是否要求行为人对于“情节严重”有认识或者认识的可能性。如果从理论上严格把握“情节严重”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量域内这一命题,则必然要求行为人对于“情节严重”有所认识,这是责任主义的必然要求。但从实然角度上看,我国刑法分则有关“情节严重”的司法解释往往将诸如行为导致被害人自杀、自残、精神失常等作为“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此类情节超出了构成要件要素的量域范围,性质上类似德国刑法中的客观处罚条件,如此就无需行为人存在认知。至于多次实施或曾经受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等“情节严重”的情形,其情节也超出构成要件要素的量域范围,系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或者刑事政策的考虑而规定,亦无需行为人存在认知。
第二,判断标准:“外行人所处领域的平行评价”。“情节严重”的情形是否需要被行为人所认识或者具有认识可能性,要根据其是否属于构成要件的量域范围内来决定,如果属于构成要件量域范围内的情节就需要行为人存在认识;如果不属于构成要件量域范围内的情节则无需要求行为人存在明确认知。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在高空抛物后造成严重后果时往往辩解其没认识到会造成严重后果,如果该严重后果不属于构成要件量域内,如抛物次数、导致被害人精神失常等后果,则其本身就无需行为人存在认知;如果该后果属于构成要件量域范围内,此时司法该如何判断?可引入“外行人所处领域的平行评价理论”②[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 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 年版,第317 页。,即行为人只要认识到行为手段和行为大致的规模,但是以为尚未达到刑罚处罚的严重程度,则这种错误认识是属于对规范构成要件的认识错误,行为的刑事责任仍然成立,事实上就是通过社会第三人客观评价是否具备认识的可能性即可。
2.“情节严重”主观要素的评价功能
“情节严重”既然属于构成要件的整体性评价要素,如果认为构成要件包含主观要素,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情节严重”当然包含对于行为人主观要素的具体分析和评价。③传统的四要件理论本身就承认罪状中的主观要素。在阶层犯罪理论下,当前德日绝大多数犯罪构成学说亦承认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即使是持结论无价值论者如平野龙一、山口厚等亦承认短缩的二行为犯中的目的属于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133 页。比如,行为人实施高空抛物的手段行为是为实现某种特定的犯罪目的,即该目的已经不能为“情节严重”所评价,行为可能构成其他犯罪。如果行为人的犯罪动机较为恶劣,对于定罪或许不存在影响,但亦应在量刑环节予以考虑。
从检索到的高空抛物罪的判例来看,很多行为人具有“为抗拒调查”“为迫使警察退至楼下”“为制止吵闹”“报复邻居”“为阻止消防人员实施救援”的犯罪目的或犯罪动机,①参见赵明华高空抛物罪案,吉林省辉南县人民法院(2021)吉0702 刑初216 号刑事判决书。有些行为人抛物前还“观察了一下路上是否有人”,②参见徐定威高空抛物罪案,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21)粤0306 刑初339 号刑事判决书。上述主观要素不仅影响高空抛物行为罪过的判断(行为人对抛物产生的严重后果不一定均为故意,也有过失的存在空间),有的可能还涉及牵连犯的问题,但上述案例最终均定性为高空抛物罪,量刑上也未见差异。显然司法实践中更倾向于对“情节严重”的客观方面进行判断,对于主观要素的作用则有所忽略,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案件定性及量刑会存在偏差。
3.“情节严重”的类型化分析
基于我国刑法分则情节犯有关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列举的常见情形,可以对高空抛物罪“情节严重”的类型按照构成要件量域内和量域外作如下分类:一是构成要件量域内的情节,包括抛掷物品质量、数量、特性,抛掷物的落差,抛掷行为的目的和动机。二是构成要件量域外的情节。其中属于预防刑、刑事政策的为多次高空抛物的,曾经因高空抛物受过刑事或者行政处罚后又实施的,经劝阻仍实施的。其中属于客观处罚条件的为因高空抛物行为导致被害人精神失常、自杀的。
(三)不同犯罪类型视域下的“情节严重”
1.双层法益的情节犯定位决定犯罪类型的多层属性
根据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情节犯的“情节”的规定,情节可分为行为情节和结果情节两类,无论是行为情节还是结果情节,只要达到“严重”的程度,均存在入罪的可能。同时,双层法益内容的不同亦会导致不同犯罪类型同时存在于同一犯罪的现象。作为情节犯的高空抛物罪法益的双层属性决定着其犯罪类型的多样化,即存在危险犯和实害犯并存在该罪“情节严重”的各类情形之中的可能。③危险犯与实害犯是用来解决犯罪成立与否的问题,即危险犯以发生对法益侵害的危险(具体危险或抽象危险)为犯罪成立前提,而实害犯以造成法益侵害的现实为犯罪成立前提。故从形式逻辑上看二者似乎无法共存于同一罪名中,但对此存在例外,即双层法益的情节犯中,判断究竟属于危险犯还是实害犯要看其保护法益的内容,法益内部结构不同必然导致犯罪成立标准的不同,比如与高空抛物罪同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类别的污染环境罪,其保护的法益既包括生态环境,也包括个人的生命、身体健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 条对于“严重污染环境”情形的列举,既包括对于环境本身的污染行为,也包括对人身、财产的损害,存在上述情形之一的即可成立犯罪,故在该罪的成立问题上,同时存在生态环境法益下的实害犯和个人法益的危险犯。参见张明楷:《污染环境罪的争议问题》,载《法学评论》2018 年第2 期。从危险犯和实害犯的角度来看,当保护的法益是不得从建筑物等高空随意抛掷物品的公共秩序,则高空抛物罪属于实害犯;当保护的法益是个人法益时,则高空抛物罪既包括危险犯,也包括实害犯。高空抛物罪犯罪类型的复杂化决定“情节严重”内容的多维性,即包括行为、危险、实害等多层次要素,上述要素只要其中一个达到“情节严重”程度,即可认定高空抛物罪的“情节严重”。
2.实害犯与危险犯的“情节严重”
第一,实害犯的“情节严重”。针对公共秩序法益,凡是抛掷物品且情节严重(程度达到一定量值),则构成对公共秩序的实害;针对个人法益的实害犯,凡是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后果,亦可认定产生个人实害。上述两类实害均属于高空抛物罪的“情节严重”的范围。
确定公共秩序实害犯的实践意义在于:解释行为人多次高空抛物、经劝阻仍抛掷以及抛掷粪便、尿液等污秽物且并未造成人身、财产危险或者损害的情形下仍成立高空抛物罪的问题,因上述行为属于行为恶劣范畴,虽未对人身、财产产生实害,但确实严重损害了公共秩序,故仍有定罪处罚的必要。
确定个人法益实害犯的实践意义在于:当行为人的抛物行为破坏公共秩序并未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则可以通过判断该行为是否给个人造成损害后果或者危险来判断入罪的问题。譬如行为人单次抛掷少量生活垃圾(如泡沫饭盒等外卖包装),并未达到严重损害公共秩序的程度,但如果确实产生人身或财产损害,则依然可以认定构成高空抛物罪。①参见王静高空抛物罪案,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2022)辽0302 刑初10 号刑事判决书。
第二,危险犯的“情节严重”。从个人法益来讲,高空抛物罪除包括实害犯,还包括危险犯,该罪属于危险犯中的抽象危险还是具体危险,类似于此前危险驾驶罪性质的讨论,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都存在较大争议,危险性质的不同观点直接决定司法实践中入罪门槛的高低。从高空抛物罪罪状分析,其在行为模式之后增加了“情节严重”的表述,不属于抽象危险犯罪状的典型表述样态,但亦未规定“危害公共安全”“危及公共安全”等具体危险犯的典型表述,故本文借助危险犯三分法理论,将高空抛物罪的危险犯类型定义为准抽象危险犯。②德国刑法称之为“适格犯”,日本刑法称之为准抽象危险犯或直接纳入到抽象危险犯范畴。参见熊亚文:《抽象危险犯:理论解构与教义限缩》,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 年第5 期;陈洪兵:《准抽象危险犯概念之提倡》,载《法学研究》2015 年第5 期;李婕:《限缩抑或分化:准抽象危险犯的构造与范围》,载《法学评论》2017 年第3 期。
准抽象危险犯概念的司法适用意义在于:其兼具立法抽象规定和司法具体判断的特征。易言之,准抽象危险犯不仅要求行为人实施一定行为,亦要求该行为具备一定程度的危险,即在法官认定此类犯罪时仍需判断行为是否会产生相关危险,但不要求危险达到现实、紧迫的程度,即无需达成具体危险的程度。准抽象危险犯的定位使高空抛物罪的“情节严重”在理论上探寻其上下边界成为可能。举例来说,就下边界而言,如果有证据证明抛掷物品的落点为封闭无人行走的道路或者停车棚上,不会对他人造成危险,则可以认定该行为不成立准抽象危险犯,如果抛掷物品行为本身亦未严重损害公共秩序,则不构成高空抛物罪。就上边界而言,准抽象危险犯不要求存在现实、紧迫的具体危险,结合其法定刑配置来看,其惩罚的行为空间主要局限于无实际损害或者轻微损害的抛物行为,故不宜轻易突破高空抛物罪的“情节严重”的上边界,将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行为认定为高空抛物罪。
四、竞合论视域下“情节严重”的边界矫正
以竞合论视角检视高空抛物行为,通过其他罪与高空抛物罪犯罪行为和刑罚的比较,可以逆向矫正高空抛物罪“情节严重”在刑法分则各罪体系中的边界。
(一)法条竞合处理规则的动态调整
1.《刑法》第291 条之二第2 款的定性与实践问题
《刑法》第291 条之二第2 款规定:“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该款规定,存在法条竞合说、想象竞合说、法条竞合和想象竞合说以及转化犯说等。①参见俞小海:《高空抛物犯罪的实践反思与司法判断规则》,载《法学》2021 年第12 期。本文认为《刑法》第291 条之二第2 款属于法条竞合条款。法条竞合的经典处理规则是特殊法优于一般法。从198 篇判决书来看,司法实践中亦是如此操作,甚至对一些高空抛物行为导致被害人轻伤、毁坏财物价值一万元以上的行为亦按照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处理规则,定性为高空抛物罪。如此一来,《刑法》第291 条之二第2 款择一重罪处罚的规范意旨也就无法有效实现。
2.破解之道:法条竞合规则的动态调整
虽然法条竞合处理规则以特别法优于一般法适用为基本原则,但是如果依据该规则导致明显不合理情形出现时,就可以例外允许优先适用重法。②参见阮齐林:《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227 页。高空抛物罪法定刑最高为有期徒刑一年,比较高空抛物行为可能触犯的其他罪名,高空抛物罪显然属于轻罪。在此情况下,应当说“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属于法条竞合处理规则的例外规定。③如果不还原高空抛物罪的法益为个人法益,则高空抛物罪与其他大部分关联性犯罪则构成想象竞合,可按照择一重罪处罚的规则进行处理。本文坚持假象的集体法益可以还原为个人法益的立场,故认定此种情形属于法条竞合,在适用重法优于轻法规则时,事实上与想象竞合犯在实际适用效果并无差异,但在两种处理规则的转换运用上较想象竞合更为灵活。如果出现竞合,则可按此规则择一重罪定罪处罚。但是,考虑到高空抛物罪这一特别法所具备的全面评价双层法益、准确征表行为特性的机能,如果在按照重罪定罪,具体量刑情况却在有期徒刑一年以下的,则还是按高空抛物罪定罪处罚更为妥当,④参见杨万明主编:《〈刑法修正案(十一)〉条文及配套〈罪名补充规定(七)〉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 年版,第303 页。这也是法条竞合以优先适用特别法为基本原则的应有之义。
(二)关联犯罪对高空抛物罪“情节严重”的边界矫正
结合本文对于高空抛物罪语义规范和罪体原理的分析,可以明确高空抛物罪与关联犯罪的区分要点,借助该区别要点可以逆向矫正高空抛物罪“情节严重”的体系边界。
其一,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高空抛物罪属于准抽象危险犯范畴,且从抛物危险的特点来看,一般只是具有对特定人造成危险,不具备放火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中危险的二次蔓延性和不可控性的特征。故高空抛物罪“情节严重”在危险程度的边界上尚未达到与放火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相当的程度且不具备后者危险的二次蔓延性和不可控性。
其二,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当行为人的抛物行为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或者死亡的且对上述结果持希望或者放任态度的,即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故高空抛物罪的“情节严重”在造成人身伤害的程度上一般限于轻伤以下。
其三,故意毁坏财物罪。高空抛物行为造成财物损失5000 元以上或三次以上抛物毁坏他人财物的,应当认定故意毁坏财物罪。故高空抛物罪“情节严重”涉及财产损失的上限为财产损失不得超过5000 元或者多次抛物均造成财物损坏的,次数不得超过三次。
其四,寻衅滋事罪。鉴于寻衅滋事罪的“口袋罪”特征,当高空抛物行为同时构成寻衅滋事罪,如通过高空抛物行为任意“殴打”、“恐吓”他人、任意毁损财物的,应当按照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认定为高空抛物罪,除非该行为按照寻衅滋事罪定罪后拟宣告刑高于有期徒刑一年。
其五,重大责任事故罪、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故意从高空抛掷物品,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认定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在生产、作业中强令或组织他人违章从高处抛掷物品,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则应当认定构成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因此,高空抛物罪的“情节严重”不包含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结 语
高空抛物罪的罪状表述在立法过程中曾由一审稿“从高空抛掷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的”修改为现行的“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情节严重”的规定既打破了“公共安全”的束缚进而扩大了犯罪圈,同时也兼具限缩处罚范围的功能。如何在司法适用中贯彻这一立法本意,即在风险社会刑法前置化保护的背景下,实现风险预防与民众个人自由保障之间的平衡,需要在司法适用过程中不断探索,还原出“情节严重”的清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