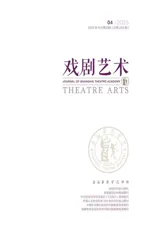论白先勇《游园惊梦》的互文性与中国文学传统
2023-12-22王艳芳
王艳芳 李 唯
众所周知,“互文性”理论由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女性主义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于20世纪60年代创立。她在《词语、对话和小说》(1)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词语、对话和小说》,祝克懿、宋姝锦译,黄蓓校,《当代修辞学》,2012年第4期。收入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符号学: 符义分析探索集》,史忠义等译,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一文中提出了“互文性”这一概念,并在《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2)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黄蓓译,《当代修辞学》,2013年第5期。《诗性语言的革命》(3)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诗性语言的革命》,张颖、王小姣译,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中进一步论述,但克里斯蒂娃并没有给出“互文性”一个具体的定义。由于这一概念产生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型的过程中,应和了当时解构主义所倡导的多元性、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随之被符号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文化研究等批评流派征用并发展为一个内涵复杂、外延不断扩展的文本理论。“互文性指‘种种文本之间的相互转换关系’。它强调任何文本都处于与其他文本的相互关联之中,符号的意义则在文本的交织中演变、发展。一个确定的文本中往往渗透了来自其他文本的话语,这些话语在当下文本的空间中相遇,它们相互吸收、排斥、转化、整合,使文本的意义慢慢浮现,最终完成指意的实践。但即使指意实践完成,也不意味着文本的意义就稳定了,文本随时会与后来产生的其他文本发生关系。每一次的互文,都可能带来意义的更新,符号的意义就是在这种文本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中不断地转换生成。”(4)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主体·互文·精神分析: 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祝克懿、黄蓓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250—251页。具有互文性的两个或多个文本之间,除了具备“互相指涉、互相映射”的同质性之外,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文本之间的“异质性和对话性”,这也就意味着文学艺术中的互文性绝不是为了重复他人的思想,而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分析白先勇《游园惊梦》系列文本中互文性的表现、意涵、特殊性及其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关联。
一、 游“园”: 互文性生成的起点
白先勇小说《游园惊梦》最早发表于台湾《现代文学》杂志1967年第30期。小说描写钱夫人、窦夫人等一批达官贵人眷属的一场久别重逢的家宴,人物、情节和场景设计颇具“三一律”特点,时间是晚上,地点是窦公馆。在极其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演绎了他们由中国大陆南京流落到台湾台北、近二十年的人生韶华流逝和家国情仇变迁。为此,小说不仅采用了意识流手法,让钱夫人蓝田玉借助回忆和意识流动不断重返过去,而且借助平行时空,将此刻台北窦公馆的这群人与十几年前南京梅园新村的他们进行对照书写。于是,游“园”在不同层面展开: 一是台北天母的窦公馆,二是南京梅园新村的钱公馆,三是小说主人公们所演唱的昆曲《牡丹亭》中的杜家“后花园”。当然,其中还穿插了钱夫人跟郑参谋幽会的中山陵桦树林。
尽管已经是“秋后的清月”,但窦公馆辉煌的灯火依然“好像烧着了一般”。为了进一步突出“姹紫嫣红开遍”的盛世繁华,小说极尽铺染窦公馆客厅大大的“牡丹”图案,女眷们的浓艳妆容和奢华服饰;就连餐厅的摆设,也凸显出白色桌椅、银色餐具以及猩红色桌布织就的富丽堂皇。贯穿其中重要的人物钱夫人蓝田玉,本是一名昆曲演员,当年因为清唱《牡丹亭》博得钱将军喜欢而嫁入豪门。事实上,“《牡丹亭》这出戏在《游园惊梦》这篇小说中也占有决定性的重要位置。无论小说主题、情节、人物、气氛都与《牡丹亭》相辅相成。甚至小说的节奏,作者也试图比照《游园惊梦》昆曲的旋律。”(5)白先勇: 《〈红楼梦〉对〈游园惊梦〉的影响》,《白先勇文集第5卷: 游园惊梦》,广州: 花城出版社,1999年,第333页。小说《游园惊梦》是白先勇与昆曲《牡丹亭》结下的最初文字缘。
其后,根据该小说改编的同名话剧《游园惊梦》分别于1982年、1988年在中国台湾、大陆成功上演。剧中,昆曲《牡丹亭》不仅充当人物和故事的背景,还是剧情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样是一个自足的艺术世界。单是话剧《游园惊梦》的舞台布景道具,就与小说和昆曲形成了内在互文性:“不必全照原著《游园惊梦》小说中之描述,但求神似而已。”故而利用“银幕屏风”之“幻灯映射出牡丹图样——如宋徐熙之牡丹图——以增华丽富贵气象,并点出《牡丹亭》之主题。”(6)白先勇: 《游园惊梦》(话剧剧本),《白先勇文集第5卷: 游园惊梦》,第5页。此外,无论小说还是剧本,多次出现昆曲《牡丹亭》的唱段,如[皂罗袍][山坡羊][绕池游][步步娇]等,造成“戏中戏”“戏连戏”的强烈互文效果。特别是话剧《游园惊梦》在台北上演的时候,还穿插了《游园惊梦》的电影片段,即钱夫人与郑参谋于中山陵林间幽会的影像,互文性突破文学文本,进入多元的跨媒介艺术范畴。
继话剧《游园惊梦》1982年首次搬上舞台之后,白先勇于1983年第一次制作昆曲《牡丹亭》,但只有《闺塾》《惊梦》两折;1987年在南京观看张继青主演的昆曲《牡丹亭》、1992年在台北观赏华文漪主演的《牡丹亭》之后皆大为赞赏,但遗憾两者皆为简本。而汤显祖《牡丹亭》(7)汤显祖: 《牡丹亭》,徐朔方、杨笑梅校注,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全本凡五十五折,全演下来要三天三夜,尽管如此,编一出全本《牡丹亭》一直是白先勇多年的梦想——直到2004年4月,经过近两年时间精心制作和严格排练的青春版《牡丹亭》(8)白先勇编著: 《牡丹还魂》,上海: 文汇出版社,2004年。(二十七折,分上中下三本)终于成功首演并引发轰动,并且其连环效应至今未歇,这才终于圆梦。针对汤显祖《牡丹亭》原本,青春版继承原词,只删不改。虽然删去了将近一半的内容,却依然保留了金兵南下、家国离散这一重要背景和故事线索。白先勇以“不信青春唤不回”的执着,终于赢得“游园惊梦”的“月落重生灯再红”。
至此,游“园”成为多个文本故事情节的核心,但都与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游园惊梦”这一流传最广的曲段构成互文性。在上述无论小说还是剧本中,《游园惊梦》不仅是文本的题目、故事的场景、戏曲的唱词,而且直接造成主人公钱夫人的命运转捩:“《游园惊梦》这出昆曲对蓝田玉一生的命运兴衰,亦有重大关联。首先,钱将军是因为听了蓝田玉清唱《游园惊梦》为她才艺倾倒,才娶她为夫人的。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南京的一次清唱聚会,钱夫人蓝田玉在演唱《游园惊梦》时,发现到她的情人郑彦青郑参谋与她的亲妹子月月红一段私情。一阵急怒,蓝田玉失去了嗓音。若干年后,在台北天母窦公馆里,因为听到《游园惊梦》,触景生情,心理上又重新经历了一次她一生中最痛苦的经验,再度失去嗓音。”(9)白先勇: 《〈红楼梦〉对〈游园惊梦〉的影响》,《白先勇文集第5卷: 游园惊梦》,第333—334页。所以,多个层面的互文都离不开昆曲的“游园”。
正所谓在园中邂逅,在园中惊梦,因牡丹而生情,因生情而入梦,因梦醒而夭亡,因生死而惊变,因惊变而得悟。游园是钱夫人的青春期,即作为昆曲名角清唱者蓝田玉的时期;而惊梦则是青春后期,昆曲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的梦中遇合直指钱夫人与参谋郑彦青的一段情欲纠缠的孽缘。现实场景中则将钱夫人的前后青春时期、即“游园”和“惊梦”进行了一番重演,此时的钱夫人已经美人迟暮,而且寡居落寞。三个不同时空的对比,让赴宴的钱夫人再次惊梦,惊觉世易时移,人事沧桑。而与钱夫人命运相映照的则是窦夫人的“游园”——在某种意义上,现在的窦夫人还处在钱夫人命运的首次惊梦前期,或许窦夫人不会完全重复钱夫人的命运结局,但也必然会进入其惊梦人生之下半场。《游园惊梦》小说和剧本都已经透露出她的亲妹子蒋碧月与窦府程参谋微妙关系之端倪。比之小说,话剧中两人之间的亲昵关系更加明朗化——已经为窦夫人重蹈钱夫人的“惊梦”埋下了伏笔。但游“园”只是“梦”的开始,小说和戏剧中的所有人此时犹在梦中。无论风头正健的窦夫人,还是已然落寞的钱夫人,抑或强势嚣张的月月红,都还在梦中。有人或许刚从梦中醒来,有人则刚刚入梦,还有的醒来后要再次坠入梦中,游园的过程就是造梦的过程。台北的这一群所谓贵族遗老,无论经过多少离乱沧桑,还依然活在往日南京的繁华旧梦中。
二、 惊“梦”: 互文性阐释的多层意涵
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白先勇感喟于昆曲艺术的高贵精美,其式微使他起了“美的事物竟都是不长久”的追悼之感。他想起童年时曾经见过一位难忘的昆曲女艺人,即《游园惊梦》里钱夫人的原型。于是,“我替她编了一个故事,就是对过去、对自己最辉煌的时代的一种哀悼,以及对昆曲这种最美艺术的怀念。”(10)白先勇: 《为逝去的美造像——谈〈游园惊梦〉的小说与演出》,《白先勇文集第5卷: 游园惊梦》,第366页。所以白先勇认为《游园惊梦》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美人迟暮故事,“只是写美人的迟暮与苦痛”,但紧接着,他谈到了“来自中国文学传统的沧桑感”对他的影响。迟暮、沧桑,这是每一个体生命必然要面对的存在真相。因此,惊梦的第一层可以理解为个体生命在时间面前的无奈,即生命的有限性面对时间之无涯巨流的无力感。
相对而言,台北版话剧《游园惊梦》比较注重细致感情的变化,隐含了人事沧桑、世事无常的主题——但细心的读者和观众终能发现这一点。大陆版话剧《游园惊梦》虽然情节相似,凸显的却是“人生如戏、人生如梦”的主题。用白先勇的话说:“整体说来,台北版的《游》剧精致、深沉,趋向静态表演,而大陆版则流畅、多变化、富有动感,整体设计比较切题。这两个版本的确风格迥异,但演到最后,却都能给人一种曲终人散的苍凉。”(11)白先勇: 《三度惊梦——在广州观〈游园惊梦〉首演》,《白先勇文集第5卷: 游园惊梦》,第398页。人生如梦,曲终人散,如果说第一层的惊梦是对于“时间”的恐慌和恐惧,那么这一层的惊梦则更多地表现为生命对于世变无常、兴衰变易的无奈和伤悼。
至于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人们更多注意到的是“青春”“情爱”“生死”这些层面的抒情演绎和互文阐释。如果仅仅是上述昆曲之“美”,也许能使白先勇沉浸其中不能自拔,但“昆曲”的深层意涵、特别是经典曲目演绎的“兴亡之感”“衰亡之叹”以及此后的“乱离人生”才是真正打动白先勇并使其耗费晚年精力、鼎力推崇并为之竭力奔走的深层动力——恰恰这一点容易为人所忽略。青春版《牡丹亭》(12)白先勇主编: 《圆梦: 白先勇与青春版〈牡丹亭〉》,广州: 花城出版社,2006年。“上本”之第六出《虏谍》交代: 金帝完颜亮得南宋李全归顺,喜李有敌万夫之勇,封为溜金王,命他暗中招兵买马,准备他日里应外合,入侵江淮,吞占南宋江山。“中本”第三出《忆女》接续前文: 金兵南侵,杜丽娘的父亲杜宝奉旨调往淮扬镇守。杜父、杜母、春香三人同感,思念丽娘。杜母有感离开南安家居后,女儿孤坟只得石道姑看守,感伤不已。在舞台现场演出中,此部分的情感冲击力不亚于杜丽娘《离魂》一段。此外,还有第七出《淮警》。到了“下本”第二出《移镇》: 反贼李全助金兵兴乱,军情紧急,杜宝与妻暂别,领军移守淮安;以及第四出《折寇》: 李全贼众围淮安城,为杜宝固守,久攻不下,杨婆施计遣陈最良使杜宝弃城,却反被杜宝之计上计使其归降……都是非常重要的宋金对峙背景和家国乱离的线索。既然生命无法抵御时间,也无法与世变抗衡,面对着家国离乱,个体更显无能为力。
在观看上海昆剧团演出的《长生殿》之后,白先勇曾说:“洪昇的《长生殿》继承白居易《长恨歌》、白朴《梧桐雨》的传统,对明皇贵妃的爱情持同情态度,基本上是‘以儿女之情,寄兴亡之感’的历史剧。演出本‘儿女之情’照顾到了,‘兴亡之感’似有不足。”(13)白先勇: 《惊变——记上海昆剧团〈长生殿〉演出》,《白先勇说昆曲》,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他认为,原因在于由第七出《骂贼》突然跳到第八出《雨梦》,中间似乎漏了一环,天宝之乱后的历史沧桑没有交代。而洪昇原作中的重头戏第三十八出《弹词》实为《长生殿》中的扛鼎之作,将天宝盛衰从头说到尾,悲凉慷慨,怆然心酸,并认为与孔尚任《桃花扇》中的《哀江南》有异曲同工之妙。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洪昇在剧中将李龟年从长沙移到了南京,其中的重大寓意不可忽视: 洪昇出身于没落世家,一生落寞不得志,异族统治之下,亡国之恨隐隐作痛。而南京恰恰是南明首都,太祖陵墓所在,是明朝遗老们的故国象征。《弹词》中的亡国之恨其实就是洪昇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故而表现得异常深沉感人。据此,白先勇建议“把《弹词》一出插到《骂贼》及《雨梦》之间,或者干脆取代《骂贼》,这样既可加深‘兴亡之感’,而‘天宝盛衰’又有了一个完整的交代”。(14)白先勇: 《惊变——记上海昆剧团〈长生殿〉演出》,《白先勇说昆曲》,第7页。这一方面表明白先勇对中国戏曲“兴亡盛衰”传统的充分理解,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在借洪昇《长生殿》之酒杯,浇他胸中之块垒呢?于是,在青春版《牡丹亭》中,他有意识地保留了杜丽娘、柳梦梅故事“兴亡盛衰”的历史背景。
无疑,个人经历的时代沧桑巨变、兴衰离散,凄怆悲凉以及时空错乱感受,唯有通过舞台上的戏曲表演才能传达和还原,无怪乎白先勇会感慨万千地说:“遽别四十年,重返故土,这条时光隧道是悠长的,而且也无法逆流而上了。难怪人要看戏,只有进到戏中,人才能暂时超脱时与空的束缚。天宝兴亡,三个钟头也就演完了,而给人留下来的感慨,却是无穷无尽的。真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15)白先勇: 《惊变——记上海昆剧团〈长生殿〉演出》,《白先勇说昆曲》,第11页。说的是明皇贵妃,是洪昇,其实何尝不是白先勇自己。除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还有白先勇个人所经历的时代兴衰和幻灭:“我个人可以说是生于忧患;我出生是抗战那一年,童年时经过战乱,看到人事的兴衰,我想对我个人影响很大。”(16)白先勇: 《为逝去的美造像——谈〈游园惊梦〉的小说与演出》,《白先勇文集第5卷: 游园惊梦》,第370页。1946年,白先勇一家从重庆飞南京,抗战刚刚胜利的南京城荡漾着一股劫后余生的兴奋与喜悦。他难以忘记攀爬明孝陵石马石象的亢奋,更难忘那块晶莹剔透的雨花石——甚至成为他对南京记忆的一件信物。特别是“那年父亲率领我们全家到中山陵谒陵,爬上那三百九十多级台阶,是一个庄严的仪式。多年后,我才体会到父亲当年谒陵,告慰国父在天之灵抗日胜利的心境。四十年后,天旋地转,重返南京,再登中山陵,看到钟山下面郁郁苍苍,满目河山,无一处不蕴藏着历史的悲怆。大概是由于对南京的一份特殊感情,很早时候便写下了《游园惊梦》,算是对故都无尽的追思”。(17)白先勇: 《我的昆曲之旅——兼忆一九八七年在南京观赏张继青“三梦”》,《牡丹情缘: 白先勇的昆曲之旅》,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9页。对于他来说,早年经过广州离开中国大陆到台湾,一觉醒来身在香港,四十年后再返羊城,已然三度“惊梦”。这里的互文性就不是简单的文本互涉,而是向历史深处的洪昇致意。故此,当他1987年在南京看到张继青主演的《游园惊梦》,简直有魂飞天外的感觉,只能感慨人生境遇是如此之不可测。
小说《游园惊梦》中的世事兴衰之感,话剧《游园惊梦》中的家国兴亡之叹,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中的家国危难与乱离人生,同样还有早年看《长生殿》对于天宝盛衰的感喟,联系到《红楼梦》中的兴亡衰变、人间生死以及富贵空幻,最终都指向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思想的“生和死”。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生死相依,生死互通,生可以死,死可以生,唯有至性至情才可以有这样原始和神奇的力量,才可以呼风唤雨,穿越生死时空,直至起死回生……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因此“不死”而“永生”。只不过,《游园惊梦》说的是情变、世变,一切都在变,剧中人根本无法把握变的趋势,只能以嗓子的“哑掉”来回应这无法遏抑的时代变异。而《牡丹亭》说的则是变中的不变,因为“情不变”,所以一切改变都朝着剧中人梦想的方向,在某种程度上力求抓住一些东西,改变一些东西,延缓一些东西。因而前者是悲剧的,后者是喜剧的。钱夫人与杜丽娘的结局也不同,钱夫人从名伶到老妇,而杜丽娘始终是一个青春女子;一个阅尽世间沧桑,饱尝人情冷暖;一个则一腔纯真爱美之情,始终天然如一。杜丽娘听从自然的召唤,听从本心的召唤,听从身体的召唤;而钱夫人则是出于种种世俗生存甚至人情世故的考虑,无论是嫁给钱老将军,还是给桂枝香举办生日会。唯一的例外在于“生错了一根肋骨”,与郑彦青参谋的一段情欲纠缠,但仍然是成年人的欲望书写,与杜丽娘的与大自然共鸣完全不同。这两个文本中欲望表现的不同,恰恰透露了创作者白先勇从20世纪60年代到新世纪历史观、生命观的微妙变化,也是白先勇在经历了家国、个人、生死等人生巨变之后的另一种思索和表达。那就是: 唯一能抵御时间、穿透空间、能在时空体中永恒的恐怕只有人的想象力以及这想象力的结晶: 文学艺术,文学艺术中的美和爱在想象中可以穿越一切束缚、阻隔、限制,甚至起死回生,并通过文本口口相颂、代代相传。
三、 以“儿女之情”寄“兴亡之感”: 中国文学的互文性传统
据白先勇自述,写作小说《游园惊梦》的时候,正着迷于昆曲,为其艺术之精美、曲高和寡导致没落而叹惋:“当时我正在研究明代大文学家汤显祖的作品《牡丹亭》,这一则爱情征服死亡、超越死亡的故事,是我国浪漫主义传统的一座里程碑,其中《惊梦》一折,达到了抒情诗的巅峰。由于昆曲《游园惊梦》及传奇《牡丹亭》的激发,我便试图用小说的形式来表现这两出戏剧的境界,这便是我最初写《游园惊梦》的创作动机。”(18)白先勇: 《游园惊梦——小说与戏剧》,《白先勇文集第5卷: 游园惊梦》,第336页。可见,汤显祖《牡丹亭》是白先勇创作互文性生成的第一潜文本,但绝不是唯一。除此之外,他多次强调《红楼梦》对他的影响:“《红楼梦》是我看了很多遍的一本书,对我的影响当然是很大。我想一个人写作的时候,你看过的所有书总有一两本书会影响特别深。《红楼梦》主题也是讲人世的辛酸,世事的无常,这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不只是《红楼梦》;它有一种兴衰感、历史感,这是中国民族文化最具特殊性的一点。”(19)白先勇: 《为逝去的美造像——谈〈游园惊梦〉的小说与演出》,《白先勇文集第5卷: 游园惊梦》,第370页。确实,《游园惊梦》的主题与《红楼梦》相似,表现中国传统中世事无常、浮生若梦的佛道哲理。
再者,就“以戏点题”的手法而言,《游园惊梦》也继承了《红楼梦》的传统。《红楼梦》第二十三回,黛玉在梨香院听到《牡丹亭》的警句:“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惊悟到自己花开花落两由之的命运,为第二十七回《葬花词》埋下伏笔,进一步暗示了黛玉的悲剧命运。同样,第十八回元妃省亲所点的四出戏,不仅是整本书故事的关键,暗示贾府的盛衰以及人物的兴亡,特别是《离魂》一曲,出自《牡丹亭》,杜丽娘的夭折也暗示着黛玉之死。所以,《红楼梦》对小说《游园惊梦》的影响,或者说其间的互文关系,不仅仅是反复出现的《牡丹亭》唱词所提醒的人物命运,而在于“利用戏曲穿插,来推展小说故事情节,加强小说主题命意,……更重要的还暗示出小说主要人物的命运”。(20)白先勇: 《〈红楼梦〉对〈游园惊梦〉的影响》,《白先勇文集第5卷: 游园惊梦》,第332页。何况白先勇对《红楼梦》研究着力甚深,正本清源、整体观照、深度细读,特别强调其“充满了对旧日繁华的追念,尤其后半部写贾府之衰,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哀悯之情”。(21)白先勇: 《正本清源说红楼 前言》,白先勇主编: 《正本清源说红楼》,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然而,白先勇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渊源绝不止于《红楼梦》和《西厢记》,还关乎唐诗、元曲,直到清传奇,他也曾经说过:“《牡丹亭》可以说是一部有史诗格局的‘寻情记’,上承《西厢》,下启《红楼》,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中的一座巍巍高峰。”(22)白先勇: 《牡丹亭上三生路——制作青春版的来龙去脉》,《牡丹情缘: 白先勇的昆曲之旅》,第128页。白先勇从小喜欢昆曲,但在外面看昆曲的机会不多,当他1987年5月在上海看了上昆的《长生殿》精彩演出之后,非常震撼。以至于站起来拍手拍了十几分钟,人都走掉了他还在拍。他说自己“非常非常激动”,认为这个机会“很难得很难得”。演员们演绎的大唐盛事、天宝兴衰令他一辈子难忘。因此他认为:“《长生殿》这个戏是传奇本子里的瑰宝,我觉得它是继承《长恨歌》的传统,这个大传统从唐诗、元曲一直到清传奇,这一路下来,一脉相传,文学上已经不得了了;还在戏剧结构方面,‘以儿女之情,寄兴亡之感’,历史沧桑染上爱情的失落,两个合起来,所以第一它题目就大。”(23)白先勇: 《与昆曲结缘——白先勇对话蔡正仁》,《牡丹情缘: 白先勇的昆曲之旅》,第57页。最终,白先勇的人生遭际、文学修养使他与这一脉文学传统相遇并达成观念上的啮合,从而通过多种艺术形式的创作为这一传统的延续开枝散叶、锦上添花。
四、 从“不变”到“变”: 互文性创作的新质
一般认为,作家作品之间的影响是历时性的,即前辈作家影响后辈作家。但是布鲁姆却并不这样认为,在某种时刻,不是后来者模仿前者,而是前者受惠于后来者。换句话说,“后来的人以特定的方式‘创造’了前人,因为任何对于前人的阅读和理解都创造了一个特定的前人,前人和他的作品就好像是一种等待后人去创造的带有可塑性的、留有空白的‘文本’”。(24)王瑾: 《互文性》,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8页。那么,白先勇的互文性创作是如何“创造”了前人并“重塑”了其作品的呢?小说《游园惊梦》对汤显祖《牡丹亭》的反塑作用早已被研究者揭示:“这篇小说,既引入了昆曲的‘美’,也借助昆曲表现历史的沧桑、人物的命运并与之结构不同的时空,小说的命名也出自昆曲《牡丹亭》——昆曲在小说《游园惊梦》中的作用,可谓大矣!而汤显祖的《牡丹亭》,则经由白先勇的《游园惊梦》,以‘现代’的方式,又‘活’了一次。”(25)刘俊: 《赏心乐事: 白先勇的昆曲情缘》,《白先勇说昆曲·序》,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8年,第3页。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小说《游园惊梦》就已经通过文字将式微了的昆曲艺术复活了一次。
同样,白先勇在创作话剧《游园惊梦》和一晚本昆曲《牡丹亭》时,加入了更多现代元素,使用了大量的现代表现手法,使传统文化翻出了新意,但又绝不破坏它原有的形态和质地。白先勇在接受访谈时说:“青春版《牡丹亭》表现了两个字: 一个是‘美’,一个是‘情’,美和情都是文化的救赎力量。中国文化已经式微很久,今天,中国文化需要起死回生的力量,我们有几千年辉煌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不相信古老传统没有办法被唤醒。我们制作这出戏,就是在唤醒潜藏在我们心中对文化的渴望,一种民族的乡愁。”(26)白先勇: 《一个是“美”,一个是“情”——白先勇访谈录》,《牡丹情缘: 白先勇的昆曲之旅》,第218页。——而这正是“互文性”理论的深层意涵和实践价值所在。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实际上是在一个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重新发现了汤显祖《牡丹亭》,以“青春”为标志的解读和张扬,对汤显祖的原作融入了新的内涵,并在读者和观众的接受与传播中进一步生发出创造性的新质,从而使得旧传统获得新生命——无论是青春版演员,还是青春版读者和观众,都将《牡丹亭》原有的超越生死、纯净自然的青春情爱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彰显。正是因为白先勇在青春版《牡丹亭》中对于“现代性”的植入,使得精致经典的传统文化叠加上了新的元素和质地,唤醒了人们对经典的再认识,文学经典因互文性而被重新赋能,从而得以在当代复活。
互文性研究和影响研究的区别在于:“影响研究是一条线性的单向的路线,‘影响’的放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是不能颠倒的,而且‘影响’还需要有确凿的事实根据。至于交互影响,那可以看作是两次影响过程。互文性是非线性的开放的多向的,呈辐射状展开,所有的文本处于一个庞大的文本网系之中,它们之间没有时间的先后关系,更无须取得事实证据的支持。在互文性理论中,作者死亡,读者再生。只要是读者阅读时涉及的文本,尽可以纳入互文本网系之中。”(27)李玉平: 《互文性: 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45页。汤显祖的《牡丹亭》作为白先勇小说、话剧《游园惊梦》以及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第一潜文本,无疑为后者的解读和创作提供了参照;同时,后者的出现也丰富、深化和更新了人们对前者的理解。当读者和观众对白先勇的“游园惊梦”系列进行互文性解读时,可以激活古今中外所有关于《牡丹亭》的文本,而不必顾及它们之间有无事实上的影响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正是白先勇的作品复活并重新创造了包括汤显祖《牡丹亭》在内的系列中国传统文学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