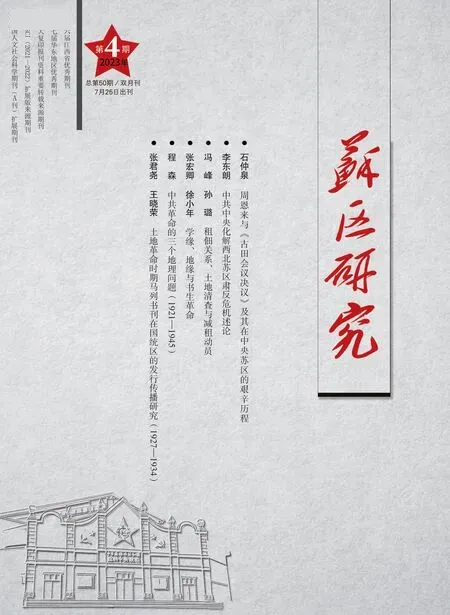中共中央化解西北苏区肃反危机述论
2023-12-21李东朗
李东朗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时,西北苏区正因肃反错误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中共中央迅速采取措施,成功地化解了这一危机。近些年,对西北苏区肃反的研究,取得一些明显的进展,(1)其中魏德平的研究成果显著,相继发表《“陕北肃反”的来龙去脉》(《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5期)、《延安整风对“陕北肃反”的重新定性》(《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3期)、《“陕北肃反”争论始末研究》(《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6年第2期)等十余篇论文。另有黄正林的《1935年陕甘边苏区和红26军肃反问题的考论》(《史学月刊》2011年第6期),张化民、拓宏伟的《“陕北肃反”起因再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4期),张涛的《1935年中央对陕北肃反处理未彻底的原因探析》(《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等。但基本是对这场肃反发生过程及其后来引发争论问题的研究。而关于中共中央化解这一危机的过程,大都是在阐述相关历史过程中作概括的记述,研究成果较少。(2)目力所及,目前仅有魏德平的《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3期)论证了谁是解决陕北肃反主持人的问题,并分析了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的贡献与局限。相关中共领导人的传记和回忆录对此的记述也都较为简略。(3)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程中原著的《张闻天传》均730多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传》仅330余字,《董必武传》不足320字,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也仅有300余字。特别是,在涉及中共中央处理西北苏区肃反问题的一些著述中,关于中央领导人对该事件的处理,存在表述相异的现象。比如参与处理该案的王首道回忆:“直罗镇战役结束以后,毛主席来到了瓦窑堡,我们即将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汇报,毛主席、党中央肯定了我们的看法,并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同时,为严明党纪,毛主席、党中央对制造这起冤案的有关负责人作出了处理。”(4)《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72页。当事人张策也回忆:“毛主席迅速解决了陕北的肃反问题。”(5)张策:《回忆我党几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也有毛泽东、周恩来共同处理这个事件的说法,如李赤然回忆:“在直罗镇战役之后,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到了瓦窑堡,过了几天,就下令释放了刘志丹等同志。”(6)李赤然:《红二十七军战斗历程的片段回忆》,《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页。而郭洪涛回忆是张闻天主持处理:“具体处理过去的冤案,释放刘志丹等同志,这些工作都是张闻天同志领导的……他亲自过问这个小组(指五人‘党务委员会’——引者注)的工作,对纠正肃反的错误抓得很紧。”(7)郭洪涛:《张闻天同志初到陕北》(1985年5月24日),《回忆张闻天》编写组编:《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同时还存在一些时空错位、互相矛盾的表述。诸如此类问题,难以正确反映中共中央处理西北苏区肃反的史实,甚至可能产生认识混乱、以讹传讹的问题。制止和纠正西北苏区肃反的错误,是中共中央奠基西北的一大举措,影响重大而深远,理应得到正确、充分的反映。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谨就此进行一些探讨。
一、西北苏区因肃反而陷入严重危机
1935年9月下旬,西北苏区兴起大规模的肃反。这次肃反,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8)这一判断来自李维汉。(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72页。)李维汉曾在1935年11月参与纠正这场错误的肃反,又在1983年主持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研读大量资料,主持了多次讨论会,熟悉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和基本情况,因此他的评价颇为准确。中共中央解决西北历史争论的〔1983〕28号文件,也是如此定性的。它迅速把西北革命推入极端危险的境地。
第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捕。包括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开创者和领导人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高级干部,红26军营以上干部和陕甘边根据地县级以上干部中的绝大多数,人数在六七十人以上。(9)关于西北苏区肃反中被逮捕的人数,朱理治说根据口供开列的逮捕名单有六七十人,习仲勋说幸存者100多人,《子长县志》说60余人。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点,这次肃反的重点是红26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领导人,所以其领导人绝大多数罹难。但在陕北根据地组建的红27军也受到了重创。红十五军团成立时,红27军改编为第81师。肃反中,该师参谋长任浪花被捕,政治委员张达志调离,师长贺晋年拟调走,并且张达志和贺晋年已经被严重怀疑,不能正常工作了;(10)张达志回忆:“我同贺晋年同志当时虽未被捕,但已被列入黑名单中;并在工作上失去了信任,先是将我由八十一师调换到七十八师任政委,榆林桥战斗后,又调我离开七十八师到十五军团任民运部长。”(张达志:《回忆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二、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资料室编:《中共六十年纪念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34页。)贺晋年回忆:“据说还要把我调到别的师当副师长,削去职权,然后再处理掉。”(贺晋年:《迎接中央红军到陕北》,《中华魂》1996年第10期,第16页。)此时,贺晋年的话已经没有效力,据他回忆:有一次战斗中,一些伤兵没办法走路,我要少共营把他们抬回去。少共营没有吃饭,我说别的部队不要吃,你们先吃,吃了送伤兵回去。但少共营吃饭之事被25军的一个政治干事阻止了。有一次,我没有鞋子穿,就写了个条子,到供给部去领,要他们发给我一双。供给部说,政治委员说了,如果没有政治委员的盖章,谁也不发给。[《贺晋年在西北高干会议上关于陕北党史和肃反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志丹县委员会编:《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23辑(卷2),内部发行,2018年版,第1262、1263页。]该师下属的241团团长刘明山被撤职,政委李赤然和243团政委王国昌被调离,(11)李赤然回忆:我也由241团调出,担任师党务书记,还给我派来两个同志“协助”。这两个同志整天跟着我,形影不离。后来他们告诉我说,“是来监视你的”。参见李赤然:《红二十七军战斗历程的片段回忆》,《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8页。243团团长李仲英在为隔离红27军以对红26军肃反而进行的作战中负伤,241团3营营长李玉亭被撤职,243团两个营长孟寅生、李学臣下落不明。李赤然就此评论:“在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下,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中许多指战员有的被活埋,有的被关押,有的被调离指挥岗位。莫须有的逐陷,不问青红皂白的抓人杀人,使红军内部出现严重危机,军心浮动,群情悲愤。”(12)李赤然:《红二十七军战斗历程的片段回忆》,《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8—29页。
第二,一批忠贞革命的优秀干部被杀害。在大规模部署肃反的过程中,肃反领导人发出了“反革命右派要从肉体上消灭”(13)《郭洪涛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6日),转引自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03页。的指示。由此,西北苏区肃反中发生大规模的错杀、滥杀现象。据长征到达陕北后担任陕甘省保卫局长的郑自兴调查,被杀害者有200多人。(14)转引自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412页。郑自兴属于中央红军,与陕北肃反争论的双方没有亲疏关联,并且是在肃反纠正之时出任陕甘省保卫局长的,以他身份、职责和调查时间而论,人为扩大或缩小其数字的可能性较小,这一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时任陕甘边根据地东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马文瑞就此评论:“200多名优秀干部被错误杀害,这是当时西北根据地的一大灾难。”(15)《马文瑞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第三,陕甘边根据地的工作基本瘫痪。由于中共陕甘边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几乎悉数被捕(仅剩一个新派去的特委组织部长李景林),中层骨干、有水平的知识青年也几乎都被捕;即使未被捕者也因肃反的惊恐而躲了起来,“不少地方干部不敢见省委的人,听说省委来,人就上山‘打游击’,群众也跟着‘跑反’”(16)赵启民:《党中央毛主席纠正错误“肃反”》,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页。,结果使陕甘边特委、苏维埃政府、军委机关基本瘫痪,各项工作都处于停顿状态。陕甘边根据地是西北苏区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削弱严重影响西北苏区的大局。
第四,严重损害了西北红军。由于原红26军主要领导人和大部分营级干部被抓,红27军主要领导人有的被捕,有的被调离,大部分不被信任,而从红25军新调入的军政指挥员对情况隔膜,一些人态度粗暴,甚至打骂基层干部和战士,因此,红26军“士气低落”,“出现了建军以来首次开小差逃亡的严重现象”。(17)高朗亭:《西北红军的组建和党中央拯救西北革命根据地史事纪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第1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5页。红27军亦然,李赤然在回忆红27军当时的状况时说:“搞错误的‘肃反’,伤了红军指战员的心,部队思想混乱,军心涣散,战士自杀、逃跑事件不断发生,各级指挥员也是人人自危,这是红二十七军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18)李赤然:《忆红十五军团第二四一团》,《西北革命根据地》,第371页。特别是为了对红26军进行肃反,肃反领导人专门分隔同属西北红军的红27军(其时改编为红十五军团第81师),强令他们攻打国民党防守严密的据点,结果造成重大伤亡,新任师参谋长路文昌和243团团长、241团政委均负伤。李赤然回忆:“红八十一师在这场无准备的战斗中伤亡比劳山战役要大一倍多。”(19)李赤然:《忆红十五军团第二四一团》,《西北革命根据地》,第371页。贺晋年1942年在西北高干会上说:“伤亡了二百多人。”参见《贺晋年在西北高干会议上关于陕北党史和肃反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3日),《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23辑(卷2),第1261页。
第五,根据地大片沦丧。肃反造成的恐怖气氛,引发严重的叛乱事件和群众“反水”现象。三边地区发生“赤安事件”(又称“三边事变”),中共三边特委和两县19个区的苏维埃政府被破坏,“三边党组织基本停止了活动”(20)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榆林地区历史大事记(1919.5~2000.7)》,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神府苏区几乎全部被敌人占领,1000多名地方干部和红军、游击队员仅保存下200余人。对于关中苏区大量群众“反水”、干部藏匿的现象,习仲勋后来回忆:“由于肃反的错误,捕杀了关中许多干部,加之群众恐慌,使工作是受到很大影响,以至趋于停止的阶段。”(21)《关中党史简述》(1943年1月8日),《习仲勋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肃反还造成三边平叛的很大困难。一方面,叛乱吓得群众四处逃散,平叛工作找不到人;即使遇见一些人,群众弄不清是叛军还是红军,不敢接近,平叛部队也弄不清这些群众是否“反水”,双方都高度警惕。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平叛很难得到群众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肃反把一些领导干部的身份弄混淆了。领导平叛的刘景范曾任陕甘边军委主席,但在肃反中被捕。因此,当他受命平叛、历经危险和曲折找到赤安县委后,被赤安县委视为“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他被缴枪和限制自由,无法开展工作。后刘景范给周恩来写信并得到回信确认他的身份,才能开展工作。三边平叛从1936年3月持续到5月,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肃反也大幅度增加了根据地群众工作的难度。陕甘边东地区群众因领导人马文瑞等被捕,纷纷向国民党地区“跑反”,仅宜川南塬靠近国民党区域的群众就跑了700多户。肃反结束后,中共陕甘省委宣布马文瑞等被释放,但陕甘边东地区群众对新去的干部不相信,“思想情绪仍然很不稳定,陕甘省委工作很不好搞,于是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治专门为此来中央汇报”,中共中央安排马文瑞等前往“安民”,以解除群众的疑惑。(22)《马文瑞回忆录》,第92页。
第六,为西北红军与红25军发生武装冲突潜伏了严重危机。错误的滥捕滥杀引发西北红军强烈的不满情绪(时任第81师政委的张达志回忆说,对肃反,“我七十八师、八十一师全体指战员,都有一股子气”(23)张达志:《回忆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二、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中共六十年纪念文选》,第535页。)。他们认为随之出现的被打倒的地主豪绅纷纷“反水”、部分苏区变成白区等,都是长征过来的红25军造成的,因此对红25军产生很大的不满,甚至认为红25军是假红军。程子华在1943年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大规模的肃反,引发“红26、27军对肃反的不满不安,并拟在肃反继续发展时意外”(24)《程子华给中央的电报》(1942年11月14日),《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23辑(卷2),第1318页。。所谓“意外”,就是对肃反的武装反抗。时任第81师师长的贺晋年在1942年高干会上说:“那时,下面已经布置好了,谁打谁都布置好了。再要开始捉人的时候,就有可能打起来。营长、团长、政治委员都恐慌了,通讯员、特务员,下面通通都准备好了,准备什么时候来抓人,就打,一有动作就打,已经分工了。”如果中央不来,“非暴乱不可,就是说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25)《贺晋年在西北高干会议上关于陕北党史和肃反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3日),《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23辑(卷2),第1262、1264页。他后来坦率地告诉杨尚昆:“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二十五军他们打起来了。”(26)《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时任243团团长李仲英在1942年高干会上也说:“如果是中央要迟来一个礼拜,那或者就要干(打)起来。”参见《李仲英同志的发言——高干会讨论党内历史的发言》(1942年11月14日),《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23辑(卷2),第1314页。1983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也判断:“再肃下去要发生内战。”(27)《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通知》,西北革命历史网:http://www.sxhjhswh.com/zgsl/wxzl/QBzaqq.htm。
其时,蒋介石调集10万大军对西北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值此反“围剿”的关键时刻,在国民党大军压境、军情危急的形势下,这种疯狂的肃反益发加重了苏区的危急局面。这种内部自损的严重错误破坏性特别大,它把西北苏区推向了被颠覆的极端危险境地。
二、中共中央制止和纠正错误的肃反
就在西北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28)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70页。肃反导致西北苏区严重危机,这是当年西北苏区领导人包括肃反领导人在内的共同认识。的时刻,中共中央于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并立即着手化解这场危机。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辨析。长期流行一种说法,说毛泽东到达陕北吴起镇,了解刘志丹等被逮捕后,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但这个首先出自《王首道回忆录》的说法有误。其一,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刘志丹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所有认知来自在哈达铺及其后看到的报纸,而报纸反映的情况不仅有限,而且是几个月前的事。随行者中出身陕北,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的贾拓夫比较了解刘志丹,但他1933年底离开陕西,时隔两年,信息不通,也只是了解过去,不知近况。在吴起镇,向毛泽东和中央报告刘志丹被捕消息的,首先是保安游击支队支队长张明科,随后是陕甘边区游击队第2路政委龚逢春,但他们只知其事,不知详情。革命时期是剧烈变动的时期,曾经的同志叛变革命之事屡有发生。因此,仅听两个红军指挥员的汇报,不知详情而遽然否认或断言肃反错误,让其停止,谨慎的毛泽东显然是不会这样做的。
其二,事实上,直至几近一个月后,在了解更多情况后,11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从前方致张闻天、博古电报中,只是指出:陕北肃反“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8页。,没有完全否定这个肃反。26日,中共中央(当时名称“中共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纠正了对刘志丹等同志的错误关押,指出陕北肃反犯了“严重错误”,但仍说:“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30)《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2页。到这时都未完全否定肃反,在此前则更不会完全否定这个肃反。
其三,在吴起镇见到毛泽东的张明科、龚逢春的回忆不同于王首道的回忆。张明科回忆:毛主席快离开吴起镇时,他再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说:放心吧,中央已派人带电台去瓦窑堡了(后来听说是王首道等几位同志去的),专门办理刘志丹等人被关押的事。(31)张明科:《毛主席赠给我手枪》(1982年),吴起县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吴起县军事志》,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关于派王首道等前去制止错误肃反的地点和时间,不是在刚刚长征到达吴起镇之时,而是在11月初中共中央到达甘泉下寺湾后。龚逢春回忆:“我还向毛主席汇报了当时陕北‘肃反’的情况和刘志丹被捕的问题,我向毛主席表示了我的意见,我认为刘志丹等同志不应被捕,我说我的看法,刘志丹等同志不是反革命。毛主席非常关怀陕北的‘肃反’问题,毛主席亲切地向我说,中央红军和中央到了陕北以后,陕北的‘肃反’问题,刘志丹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正确的解决。”(32)龚逢春:《在吴起镇向毛主席汇报》,《西北革命根据地》,第395页。本文是龚逢春1970年2月13日给吴旗县革命委员会毛主席旧居纪念馆写的信,标题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编者加的。毛泽东向二人的表示,是积极而稳妥的,但并没有涉及整个肃反的问题。
但在此后不久,在证实刘志丹等被捕、许多人被杀的情况后,毛泽东、张闻天等敏锐地感觉到这个肃反存在问题,立即发出等候中央处理的指示。李维汉回忆:“党中央到了吴起镇以后,即派贾拓夫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我与他同行(贾拓夫于一九三四年代表陕西省委到中央苏区参加六届五中全会,会后,留中央白区工作部工作,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并任总政破坏部部长)。我们在甘泉下寺湾遇到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在吴起镇时,曾有同志向党中央反映陕北肃反和刘志丹被捕的事,现在得到证实。我们当即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党中央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3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71页。其时间,应是10月27日前后。(34)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保卫局负责人由常委同志兼,王首道为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页。)在长征初到陕北之时,这个决定应有深刻用意。其一,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进行常委分工后,主要是安排了党务方面的负责人,而政治保卫局属于政府系统,是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唯一对政府系统工作人员的任命。这说明这一工作有现实方面的迫切需要,必须首先明确确定负责人。其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随同中央长征一起到达陕北,但此时另任王首道,说明遵义会议后的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肃反发生的严重错误有清醒的认识;而王首道就是因为“在肃反工作中,曾经屡次表现了他对于AB团反革命分子以及AB团自首自新分子,那种不能容忍自由主义态度”而被撤职的[《中央局关于湘赣省委的决议》(1933年2月5日),《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628页],选用他,说明中共中央对西北苏区肃反的谨慎态度。此外,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派遣贾拓夫等为先遣队寻找西北红军。贾拓夫等到下寺湾见到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等,并从中证实刘志丹等被捕,吴起镇到下寺湾约有300里的距离,按照其行程推算,具体日期也应在26、27日间。
中共中央明确认为西北苏区肃反有问题、要纠正,是在11月初中共中央到达甘泉下寺湾后。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苏区、红军肃反及劳山、榆林桥战役情况的汇报。(35)关于在下寺湾向中共中央汇报的人员,郭洪涛坚持说是他和程子华。他在写于1985年和1993年的怀念周恩来、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文章中说:“1935年10月下旬,当红军十五军团得知中央红军抗日先遣支队到达吴起镇的时候,当时任十五军团政委的程子华同志,和我一起去迎接。在下寺湾……我们向毛泽东同志等简单汇报了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知道中央红军到了陕北苏区,于是我和程子华同志前去迎接,走到下寺湾就遇到了中央。”[《永恒的怀念》(1985年1月8日)、《张闻天同志初到陕北》(1985年5月24日)、《迎接毛泽东到陕北》(1993年5月28日),《郭洪涛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0、22页。]1996年,他又在纪念长征的文章中说:“1935年11月3日,党中央在下寺湾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程子华和我汇报了苏区、红军、错误肃反及劳山、榆林桥作战的情况。”[《迎接党中央、中央红军到陕北》(1996年8月),本书编委会:《光辉的印记——纪念郭洪涛百年诞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页。]在200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他仍说:“见到中央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的布告。我即和程子华同志赶赴下寺湾迎接。”“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程子华同志汇报了苏区、红军和崂山、榆林桥作战情况;我又汇报了陕北苏区、陕北(包括陕甘边)错误肃反是逼供信搞出来的情况。”(《郭洪涛回忆录》,第77、78页。)但时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郭述申和程子华都否认程子华参加了汇报。郭述申回忆:1935年“10月底的一天,我们接到通知,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要来军团部。当时军团部住在陕西省甘泉县道佐铺。军团长徐海东到前线部队去了,准备攻打张村驿等几个土顽据点。我和程子华在军团部,听到毛主席要来的消息十分高兴……子华同志立即派人去通知海东军团长”。[《革命生涯中难忘的导师——回忆毛泽东同志》(1990年12月),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郭述申纪念文集(郭述申文选)》下,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452—453页。]郭述申这里回忆的时间“10月底”不正确,他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的时间是准确的:“10月底,中央派人送来《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11月初,海东同志带七十八师包围了张村驿、羊泉、东村、套通等据点。就在这时,我们接到通知,说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要来道佐铺看望我们。我和子华接到通知,一面着手准备,一面派人去告诉海东。海东同志刚骑马赶回驻地,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司令员就来到了军团部,同时来的还有李一氓、贾拓夫等同志。”[《与陕北红军会师,迎来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1986年6月),《郭述申纪念文集(郭述申文选)》下,第346—347页。]程子华在回忆录中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洛河川特委书记李景林给我写信说:马回回骑兵到了吴起镇,并送来陕甘支队布告。我们即向中央写了报告,讲了陕北各方面敌军部署和我们作战的方针是集中主力打东北军,同时报告陕北正在肃反。我又给李景林回信说,是中央红军到了,望立即动员群众欢迎慰问。十月底,中央派贾拓夫同志送来《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全体指战员书》,并送来一部电台和一些工作人员……十一月初,毛泽东主席、周副主席、陕甘支队彭德怀司令员、政治部主任杨尚昆来到道佐铺十五军团,接见了徐海东、我和郭述申等”。(《程子华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那么,是谁和郭洪涛在下寺湾给中共中央汇报的呢?时任西北军委主席的聂洪钧回忆是他:在得到信息后,“我此即由榆林桥赶往下寺湾迎接。在下寺湾的中央会议上,我把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并编为红十五军团、劳山战役与榆林桥战役及肃反经过,向中央做了个口头报告”。[《半世略记(1905—1955)》,《聂洪钧回忆与文稿》,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张闻天年谱》根据会议记录,也确定汇报者是郭洪涛和聂洪钧。但《张闻天年谱》在1935年“10月底—11月初”中说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在甘泉县下寺湾“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等会面”,这个记载错误,因为程子华一直在前方,未到下寺湾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根据了解的情况,在研究两人的汇报后,认为肃反有问题,需要调查解决。(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页。毛泽东、张闻天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37)《张闻天年谱》上,第272页。
应该强调的是,中共中央的这个决断是在各种信息混杂的情况下作出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其一,郭洪涛、聂洪钧关于肃反问题的汇报都很简略,甚至不得要领。聂洪钧回忆:我把肃反的情况,“向中央作了口头报告”(38)聂洪钧:《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西北革命根据地》,第436页。。郭洪涛回忆,他汇报的“主要是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的创立和发展过程……此外还汇报了陕北错误肃反问题”(39)《访郭洪涛——迎接毛泽东到陕北》(1993年5月28日),张素华等编著:《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下,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69页。这是郭洪涛在1993年的回忆,后来他在200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他汇报了有大段肃反是错误的、他反对肃反的话。联系他在肃反中的表现和40年代的相关叙述,他在回忆录中的这些说法颇不可信。。郭洪涛1942年11月6日在西北高干会发言中明确说:在下寺湾见到中央领导人,“这时候报告中央:许多同志捉起来了,但我没有详细对中央谈”。他在这次发言中还承认:“我过去始终认为(肃反)是对的,他们(指刘志丹等被捕者——引者注)是右倾,右倾机会主义。在整风以前我还是这样的认识。”(40)《郭洪涛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6日),《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23辑(卷2),第1104、1100页。贾拓夫1942年在西北高干会的发言证实郭洪涛就此讲的很简略:“我初次来遇到了,便问他志丹高岗同志怎样?他说抓起来了,说是反革命,也不知道是和法西斯有关系的原故。我问有证据没有?‘他们有证据,有口供’。”[《1942年11月贾拓夫在西北高干会议上关于边区党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1日),《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23辑(卷2),第1196页。]基于他当时的态度和认识,他不可能如实向中央汇报肃反的情况。其二,随后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见面的朱理治、程子华都不认为肃反存在严重错误。朱理治1945年7月10日在西北历史座谈会上说:“中央到了下寺湾以后,我就赶到那里,在一个会上谈了肃反的错误。并和博古谈了1小时,他征求我对此事的处理意见,我说两方面都有错误,我们搞刘、高是错误,刘、高右倾并受右派利用也是错误。”(41)朱理治:《我到陕北后的错误》,《西北革命根据地》,第433页。程子华更认为刘志丹等有问题,他在1942年11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当时,“我对肃反及逮捕刘、高均同意。及中央到陕北后,博古、首道等认为肃反错了时,我在毛主席未到前,还说一定有问题,不会全没有”(42)《程子华给中央的电报》(1942年11月14日),《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23辑(卷2),第1319页。所谓“毛主席未到前”应是指直罗镇战役后,12月13日毛泽东到达瓦窑堡之前。程子华在上世纪80年代回忆,在获悉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后,他给彭德怀、杨尚昆写了一个报告,其中说:“陕北正在搞肃反,刘志丹、高岗是反革命,问题大了。”(宋金寿:《毛泽东:陕北是“落脚点”与“出发点”》,《党史博览》2016年第10期,第4页。)。其三,当时仍有人向中共中央诬告刘志丹等。此人给中央写信,“说刘高是反革命”(43)朱理治判断:“我估计不是郭洪涛写的,就是程子华写的,因这信是由前方发出的。”参见《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23辑(卷3),第1639页。。
这里,不能不令人感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很短时间内,根据零散的、有限的甚至包括反面的材料,就迅速判断西北苏区肃反存在错误。而领导肃反者有着充足的时间和许许多多可资利用的条件,却不辨是非,人为制造了这场危及整个苏区生存的灾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敏捷、缜密和高瞻远瞩与肃反领导人的愚昧、蛮横和教条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彰显出他们在党性、胆识、能力和责任心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为迅速制止和纠正存在错误的肃反,中共中央作出两个决定:一是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等先行前往关押被捕者的瓦窑堡,接管政治保卫局,调查情况,等候中央处理。(其用意是控制事态,以防止进一步恶化。)二是成立由董必武任主任,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为委员的五人“党务委员会”,负责审查肃反事件,由政治局常委博古指导该“党务委员会”。(44)五人“党务委员会”成立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说在下寺湾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一说张闻天率中央机关到瓦窑堡后。两者时间相差无几,但牵涉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是张闻天决定成立的问题。
五人“党务委员会”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工作机构,董必武时任负责监督检查党内违反党章破坏党纪的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王首道为中央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张云逸时任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维汉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郭洪涛为陕北省委书记。但他们是如何工作的?博古是如何指导的?由于资料的原因,目前对其具体过程颇不清楚。然而,中共中央投入很大精力纠正错误的肃反,却是非常清楚的。(45)为了解决错误肃反造成的巨大危机,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张国焘分裂主义危害、亟待休整和统筹复兴革命的中共中央,被迫花费大量精力来处理西北苏区肃反的问题,这也应是这场肃反造成的一个损失,是其危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领导人分为两路行动:一部分由张闻天、博古、邓发等率领中央机关北上进驻西北苏区的后方瓦窑堡,“进行动员工作”(46)《张闻天年谱》上,第272页。按照《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这个“动员”的内容,既有动员群众“开展与深入反右派与一切反革命的斗争”,又有“彻底分配土地、扩大红军、整顿地方武装、发展游击战争等巩固与扩大苏区的实际工作”,还包含着纠正肃反错误的内容。;一部分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中央红军主力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合,进行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的作战。张闻天率领的这一路一到瓦窑堡,就集中精力解决西北苏区肃反的问题。(47)张闻天等到达瓦窑堡的时间,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年谱》记载为11月10日,程中原撰写的《张闻天传》为11月7日。随同张闻天到达瓦窑堡的董必武、刘少奇的著作各异。《董必武传》称:“董必武随同张闻天等于十一月十日到达瓦窑堡,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调查和解决陕北肃反问题的任务。”[《董必武传》撰写组:《董必武传(1886—1975)》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页。]《刘少奇年谱》则记载为:“11月7日,到达瓦窑堡。”[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63页。]张闻天11月5日在下寺湾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部署巩固根据地的工作,依此推算,他最早应是6日率领中央机关出发前往瓦窑堡,他们经高桥、安塞、蟠龙到瓦窑堡。这段路程近300里,很难在6日、7日两天内完成。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在1935年2月平均每天走62.3里,3月平均每天走64里(《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人民出版社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23—425页)。按此推算,张闻天等从下寺湾到瓦窑堡要走四五天,大致应于11月10日到达。另外郭洪涛回忆:“为迎接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到来,我和贾拓夫同志先行回到瓦窑堡,布置接待工作。中央和中央红军到瓦窑堡那天,有数千名赤卫队和群众夹道欢迎。”(《郭洪涛回忆录》,第94页。)但他列席了11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即使他用两天时间回到瓦窑堡,布置接待等工作也绝不可能在11月7日完成。而与张闻天同行的林伯渠在日记里明确记载:11月7日从下寺湾出发,途中宿营高桥、安塞、盘龙,10日“午后三时抵瓦窑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1,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因此张闻天到达瓦窑堡的时间应不是11月7日。郭洪涛回忆:“具体处理过去的冤案,释放刘志丹等同志,这些工作都是张闻天同志领导的……他亲自过问这个小组(指五人‘党务委员会’——引者注)的工作,对纠正肃反的错误抓得很紧。”(48)郭洪涛:《张闻天同志初到陕北》(1985年5月24日),《回忆张闻天》,第96页。率军南下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军情紧急、部署直罗镇战役的紧张时刻,也大量了解相关情况,并据此特从前方致电张闻天、博古,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请他们详察西北苏区肃反中的错误,正确解决。
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指导和督促下,该案迅速得到正确的审理。据王首道、刘向三回忆:他们接管政治保卫局后,立即翻阅刘志丹等被捕者的案卷,找提供材料者和所谓“证人”谈话,和刘志丹等被捕者谈话,一件一件地研究、调查,辨析他们的“罪证”。“在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我们就向戴季英提出:如果刘志丹他们这批干部都是反革命,那么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又怎能建立和巩固下来呢?对于这些问题,他都答不上来。但他仍顽固地坚持有案卷、口供为据。我们仔细地翻阅了那些案卷,发觉其中所列举志丹同志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梢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等。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同志坚持了正确的路线。我们还陆续提问了几个所谓‘犯人’,当他们知道我们是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时候,就敢讲真话了。经过再三审查,证明所谓‘口供’中,除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外,其余都是逼、供、信所造成的结果。”(49)《王首道回忆录》,第169—170页;刘向三:《往事的回忆》,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版,第97—104页。根据王首道等的审理,中共中央很快批准释放了刘志丹等18人。
这里需要做一点辨析。关于刘志丹等获释的时间,一般表述都说是张闻天到达瓦窑堡的当天(张闻天到达瓦窑堡的时间,一说11月7日,一说11月10日,所以刘志丹等的获释也就有两个时间)。但这一日期应该不确。因为这是一个重大案件,依理按照程序,首先应是王首道等的审理,然后经过五人“党务委员会”研究,再经过“党务委员会”的指导者博古,最后经过张闻天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等环节;并且按照张闻天的领导作风,他不可能轻率地对如此重大的问题作出决定。(50)五人委员会成员郭洪涛就此回忆:“五人委员会在听取了王首道同志的审查汇报后报中央批准,决定对刘志丹等受冤同志平反,并立即释放。”参见《郭洪涛回忆录》,第79页。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即使到达最后一个环节,张闻天听取汇报、讨论、开会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些工作很难在张闻天到达瓦窑堡的当天完成。
关于审理此案的具体过程,刘向三回忆:“负责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局长向我们介绍重要犯人的‘罪状‘后,并拿出一堆案卷材料交给我们,作为‘右派’、‘反革命’的‘罪证’……面对这么多的‘罪证’材料,我们需要一件一件地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最后才能证实它的真伪。”(51)刘向三:《往事的回忆》,第97页。为此,他们首先打扫“外围”,与供出刘志丹“罪状”的主要证人进行接触;根据调查的大量事实,与戴季英面谈核对;随后又与被捕者刘志丹见面谈话。在这些工作之后,经过五人小组审理,开释了刘志丹等。就此,郭洪涛1942年在西北高干会发言说:中央到瓦窑堡后,有一天王首道同志找我谈,问刘志丹、高岗等被捕的问题(应是调查过程之一),“以后保卫局开会,参加会的有博古、洛浦(甫)、李德、王首道同志,也找了我去开会。……这个会开完以后,就要放人”(52)《郭洪涛同志在高干会上的发言》(1942年11月6日),《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23辑(卷2),第1104、1263页。。在后来的另一次回忆中,他说出了具体时间:“11月13日,中央听取了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的审查汇报后,决定立即释放被冤同志。”(53)《迎接毛泽东到陕北》(1993年5月28日),《郭洪涛文集》,第22页。黄罗斌回忆的情况大致可以与之衔接:在李维汉、王首道等接管政治保卫局后,我们的处境得到了改善,“不几天,我和刘志丹、习仲勋、杨森、高岗等首批获释”(54)黄罗斌:《在“肃反”中的遭遇》,《西北革命根据地》,第428页。刘向三也回忆说,他们接管政治保卫局后,迅速改善了刘志丹等的处境,“狱中同志能够吃饱,也注意了保暖”。参见刘向三:《往事的回忆》,第97页。。他在回忆习仲勋的文章中,更具体说明了获释的时间:“由中央红军接管后,监狱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可以互称同志,给吃米饭,不打不骂,大小便自由,晚上翻身也不用喊报告了等等,接着又登记了被关押时带来的东西有无丢失。第四天,集合点名,习仲勋、杨森、杨琪、高锦纯、张策、朱奎、宝山和我等被带到王首道办公室,一进门就看到了刘志丹,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然后砸开了脚镣手铐。王首道说:‘中央知道你们都是好同志,受委屈了。’当晚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并安排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55)黄罗斌:《创建陕甘边苏区的习仲勋》,《习仲勋革命生涯》编辑组编:《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张庆孚也有情形相同的回忆:“一天下午,博古来到了我们的牢房,给我们打开了脚镣、手铐。……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天,在陕北保卫局前院的大厅里,摆了两桌酒席,表示对我们的慰问。”(56)张庆孚:《我的革命生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40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张策回忆:“不几天后,中央撤了戴季英的保卫局长的职务,任命王首道同志担任此职。接着,就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干部。”(57)张策:《回忆我党几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74页。根据上述情况判断,刘志丹获释的时间应是11月中旬,最早时间也是在11月13日或14日。此外,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给张闻天等的关于陕北肃反“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的电报,时间是11月18日。此时,前后方联系畅通,如果张闻天一到瓦窑堡就释放了刘志丹等,则毛泽东等应该不会再发如此内容的电报。在刘志丹等获释后,其他被关押的干部也相继分批获释。
11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决定一方面肯定西北苏区肃反是应该的,另一方面对西北苏区肃反领导人提出批评:陕甘晋省委“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58)《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六大以来》下,第327页。1935年11月3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对外称“西北中央局”,故这个“决定”全称为《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应该指出的是,所谓“严重错误”“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等的批评,是很严厉的。
11月30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为刘志丹等平反的活动分子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博古,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邓发、张浩和贾拓夫等,以及五人“党务委员会”成员出席,西北苏区肃反时期的领导人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戴季英,肃反受害者刘志丹、高岗、杨琪、杨森等参加了会议。这应该是一次高规格的会议。会议宣布:过去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处理是一个冤案,应该纠正。(59)《张闻天年谱》上,第283—284页。王首道报告了冤案调查和处理意见,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无罪,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6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72页。会议要求对这次肃反负有直接责任的戴季英作检查;(61)据老同志回忆:戴季英的态度很不好,不承认错误。大家都很气愤……后来张闻天又让戴季英发言,并说如果讲得不好,只能讲三分钟,戴季英的态度仍然不好。董必武、邓发、李维汉等高声制止了他的发言。参见《永坪、瓦窑堡会议》,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编:《红日照陕北——杨和亭回忆文集》,内部发行,1996年版,第110页。同时,公布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定》,指出:“这种错误的责任,应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二同志负责之。”决定对其进行处分,具体是:戴季英给予最后警告,聂洪钧给以严重警告。(62)《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定》(1935年11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资料室编:《内部研究资料》,内部发行,1985年版,第17页。这次会议标志着对刘志丹等的正式平反,对西北苏区肃反严重错误的正式纠正。
三、中共中央化解西北苏区肃反“危机”的意义
应该指出的是,中共中央其时对西北苏区肃反的纠正还是初步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对全党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左”倾的政治路线,但“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对政治路线上“左”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清理,因此中共中央对西北苏区肃反的处理,还是在原来“左”倾框架下进行的。《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总体上还是维护肃反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所谓错误是扩大了,“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26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犯小资产阶级的极端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63)《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六大以来》下,第372—373页。;由此认为刘志丹等不是反革命,所以释放了他们,但认为他们有严重错误,“陕甘边区南区及二十六军部队中有些负领导责任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的错误,以致反革命得以进行有计划的活动”(64)《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定》(1935年11月30日),《内部研究资料》,第16页。。由于这样的定性,结果“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工作的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6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73页。,并且在对肃反错误的责任和相关人员任用等方面也存在很大问题。由于存在这些问题,后来引发许多争论,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再次处理。
尽管存在重大不足,但中共中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及时制止和迅速纠正西北苏区的肃反问题,对党和中国革命、对西北苏区都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第一,解救了西北苏区面临的严重危机。错误的肃反把西北苏区置于极大的危机之中,它严重损害了苏区的党、政府和军队,引发苏区军民严重的恐慌和不满,引发红军内部严重矛盾。(66)直至1935年底,红26军、红27军原有干部对红25军尚怀不安与不满,毛泽东、周恩来因此致电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等,指示对红25军指战员进行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教育,使他们对地方,对红26军、红27军务必发生良好关系。(《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501页。)这不但严重影响根据地的各项工作、红军将士的士气和战斗力,而且严重影响对敌斗争,构成危及苏区生存的危险。如果任其延续,势将摧毁整个西北苏区。中共中央对肃反的及时制止、刘志丹等被捕者的获释,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苏区军民的恐慌和愤怒,错误肃反积聚的严重危机遂被一步步化解,从而把西北苏区从极端危险的境地中拉了回来。
这是历史事实,也是经历和了解这段历史者的基本共识。如任弼时1943年1月代表中共中央在西北高干会上作的总结报告指出:“如果是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央来到陕北的话,那么,全国仅仅剩下的十分之一的苏区——陕北苏区,恐怕也是会损失掉的。”(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01页。贺龙说:“如果不是遵义会议,还能有陕甘宁边区吗?”(68)《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关于整党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2日),《贺龙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页。张秀山则说得非常透彻:“假如中央不来陕北根据地就全完了,我们这些人都要被杀掉,那时坑已挖好了。红军内部准备内战,群众反水,敌人趁势来攻,还不全部完了!如果不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的正确路线我们的革命就完了,西北的革命就断送了。”(69)《张秀山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4日),《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23辑(卷3),第1699页。肃反领导人也是如此认识的,朱理治在1942年和1945年反复表示:错误肃反使“几百人被害,重要首领被捕,中央迟来或不来,前途是不堪设想的”。“事实上如果中央不来,事情就没法结束。”(70)《朱理治同志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补充发言》(1942年12月1日),《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23辑(卷2),第1135页;《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23辑(卷3),1638页。聂洪钧1942年在高干会发言说:“假使没有遵义会议以后中央路线迅速的来陕北,那么陕北的苏区和红军的前途恐怕是不堪设想的。”(71)《聂鸿钧同志的发言》(1942年11月7日),《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23辑(卷2),第1135页。郭洪涛在1945年说:“中央不来,遵义会议不开,陕北苏区完了。”(72)《郭洪涛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5日),《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23辑(卷3),第1597页。戴季英也认为:“在当时主客观形势发展上看,有不可想象的危险,如事实上是内部瓦解分离,外面敌人对我们进行进攻,造成党与群众不团结,涣散。这样肃反继续下去,革命力量一定要大大削弱,以致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肃反错误中埋藏下来这样的危机,如果继续下去,中央不是迅速来了,迟来几个月或半年的话,这些危机都要爆发。”(73)《戴季英同志的发言》(1942年11月8日),《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23辑(卷2),第1262、1263页。把西北的党、红军和根据地从巨大危险中拯救出来,这是中共中央甫到陕北就建立的功勋。西北苏区之可以存在,全赖于此。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历经磨难的西北老革命家普遍存有“中央救陕北”的感激和认识。
第二,为中共中央在陕北落脚创造了重要的内部条件。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高度评价西北苏区的历史地位,指出:“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74)《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而在两“点”中,首先是“落脚点”,它是根本,是“出发点”的基础。但“落脚点”之所以成立,应该具备两个要素:一是有“落脚”之“点”;二是“点”可以(容许)“落脚”。中共中央制止和纠正西北苏区错误的肃反,对这两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它把处于危急中、即将崩塌的西北苏区的局势稳定下来,保全了“落脚”的“点”。错误肃反的滥捕、滥杀,特别是在西北苏区享有崇高威望的刘志丹等的被捕,引得苏区军民群情激愤。王首道回忆:对肃反,西北苏区的“广大干部群众无比义愤,希望毛主席、党中央公道处理”(75)《王首道回忆录》,第166页。。中共中央对肃反错误的纠正,主持公道,彰显正义,因此大得苏区的党心、民心、军心,受到人民的拥戴,“落脚点”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得到扩大和巩固,形成中共中央可以在这个“点”落脚的良好环境。
一定要看到纠正肃反错误对“落脚点”的重要性。其时,中共中央面临巨大的困难。1935年9月,由于张国焘军阀主义的危害,中共中央被迫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但因力量被严重削弱,原来确定的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无法实行,因此俄界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目前的战略方针,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76)《张闻天年谱》上,第265页。但落脚哪里?具体方位并不明确。长征途中任中革军委一局作战参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州军区、成都军区政委等职的孔石泉回忆:在哈达铺看到刘志丹红军消息的报纸之前,“谁也不知道红军下一步该往那里去,长征到底还要走多远”(77)孔石泉:《确定长征最后落脚点目击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等编:《红军不怕远征难——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征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页。他用“极度的疲劳”“历尽磨难,几近绝境”来形容当时中央红军的困难状况,并评论道:刘志丹和西北红军的消息“可以说给历尽磨难,几近绝境的中央红军带来了历史性的契机,我们就像在茫茫夜空之中找到了指路的北斗”。。征途茫茫,目标飘渺,这对一支长途跋涉、孤军行进的军队来说是十分严重和非常危险的事。具体到中央红军,因为已经跋涉二万四千多里,经历了雪山草地行军等一系列的艰难困苦,亟需一个落脚、休整的地点和环境。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曾说,“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78)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表现了党的领导人忠贞革命的坚毅信念,但也反映出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困难的严重程度。在哈达铺收集的报纸提供了刘志丹和西北苏区的信息,中共中央由此决定到陕北去,以西北苏区为落脚点。西北苏区的存在,对长途跋涉的中央红军是天大的喜讯。但如果错误的肃反将西北苏区倾覆,千辛万苦寻找的、急切需要的“落脚点”不复存在,那对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将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将产生什么样的严重损害?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79)《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页。话语简略,但意义深刻,充分说明了西北苏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所谓“陕北救中央”,正是建立在这个意义上的。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如果没有“中央救陕北”,则“陕北救中央”也就不存在了,因为没有中共中央对西北苏区肃反错误的制止和纠正,即无“中央救了陕北”之谓;同样,如果西北苏区的肃反不被制止,西北苏区被颠覆,则“陕北救中央”也就无从说起。所以毛泽东说:是中央救了陕北,也是陕北救了中央。(80)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页。应该说,这是中共党内普遍的认识。比如延安时期著名的“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即持此论:“没有陕甘、陕北根据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便没有立足之地,而没有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来到陕甘、陕北,这个根据地也就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断送了!”(刘景范:《宣传无懈说民权》,中共宁乡县委员会编:《怀念谢觉哉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页。)而这两“救”(互“救”)的关节点,就是中共中央对西北苏区肃反的及时制止和迅速纠正。
第三,为党和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保留了一批中坚骨干力量。错误的肃反如果延续,被捕的西北革命领导人必将罹难。当时,在瓦窑堡已经挖了活埋他们的大坑,因此习仲勋后来说:“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他们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81)《毛泽东与习仲勋》,《习仲勋革命生涯》,第31页。中共中央对肃反的制止,避免了这个严重的后果。而他们的获救,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事业的意义非常重大。
获释的刘志丹、杨森、杨琪后来牺牲了,成为革命烈士。刘志丹更是西北革命的一面旗帜,成为激励、影响当时革命者和后来人的精神动力。习仲勋后来历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绥德地委书记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张秀山历任神府特委书记、绥德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主任、松江省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和国家农委副主任等;马文瑞历任中共庆环分区党委书记、中共陇东地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长和副书记、国家劳动部部长、陕西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张邦英、张策、刘景范、赵启民、黄罗斌、郭宝珊、张文舟等肃反中的蒙难者,后来都担负了党政军的重要职责。(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绍他们后来的情况。)他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分别作出程度不同的贡献,功勋卓著。高岗虽然后来出了问题,但在革命战争年代和东北工作时期颇有建树,因此膺任高位,李维汉在论及西北党史曾肯定地说:“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8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73页。这些西北苏区肃反的获释者后来的作为、贡献,既证明了中共中央纠正西北苏区肃反的正确性,也彰显了其重大的历史作用。
余论
围绕中共中央解救西北苏区肃反危机的问题,还需要做一些辨析和引申。
第一,相关著述对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在处理西北苏区肃反错误、解救刘志丹过程中的和作用,记述颇不一致,基本的情况是,在论述到哪一位领导人时,就突出说明他的相关活动。因此,不熟谙这段历史的读者可能不容易准确把握其脉络。本着厘清历史事实的目的,试就此做一番梳理。
中共中央1935年解决西北苏区肃反错误的过程,大致可分三个组成部分:
一是决定要调查解决。如前面所述,中共中央调查审理西北苏区肃反问题的决定,是在11月3日下寺湾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作出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与会,应该说这是他们的共同认识和决策,比如博古就“认为肃反错了”。(83)《程子华给中央的电报》(1942年11月14日),转引自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413页。根据现在看到的资料,毛泽东、张闻天在此之前对有关肃反情况有比较多的了解,认为其存在错误,有明确的表态,因此在中央这个决定中起的作用可能更多些。比如毛泽东、张闻天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立即释放刘志丹。(84)《张闻天年谱》上,第272页。
二是审理、释放刘志丹等的过程。在11月3日下寺湾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即率军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合,进行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的作战。在直罗镇战役后,周恩来于12月8日、毛泽东于12月13日到达瓦窑堡,其时刘志丹等已经获释。因此毛泽东、周恩来没有参与对刘志丹等人的具体审理工作,但非常关注,在11月18日向后方发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的电报。在瓦窑堡主持审理刘志丹等人案的,是张闻天、博古等,(85)博古做了哪些工作?因资料问题而不很清楚。据林伯渠长征日记记载:“十一月十九日,晴,八时党校开会,博古报告肃反工作。”(《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1,第14页。)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肃反工作问题,“博古做报告”。(《张闻天年谱》,第361页。)习仲勋1942年11月11日在西北高干会的发言中说,中共中央关于陕北肃反的结论是“博古同志做的”。[《习仲勋在西北高干会议上关于陕甘边党史问题的发言(摘要)》(1942年11月11日),《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23辑(卷2),第1211页。]根据这些资料判断,博古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作用突出。如指导五人委员会审理、批准他们的报告,作出相关问题的决议,开平反会等。王首道后来回忆:处理陕北肃反问题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至少洛甫、博古等是顾问了的。……我们就认定这个案子是错误的,随后向中央作了汇报,洛甫、博古、李维汉等都参加了。纠正错误肃反实际上是由党中央直接处理的。(86)宋金寿:《毛泽东:陕北是“落脚点”与“出发点”》,《党史博览》2016年第10期,第6页。宋金寿在上世纪80年代采访过王首道等。
三是对被捕者的安抚工作。错误肃反引起被捕者的强烈愤怒,杨和亭回忆:在1935年11月底的肃反平反会上,“大家都很气愤。杨琪、杨森等边说边哭,大家都流了眼泪。戴季英执行‘左’倾路线,用体罚、拷打、鼻子灌辣椒面、坐老虎凳等法西斯残酷手段迫害革命同志;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他还在下寺湾活埋了不少好同志。到会的很多同志都很气愤,几乎使会议开不下去”(87)《永坪、瓦窑堡会议》,《红日照陕北——杨和亭回忆文集》,第109页。。宋任穷也回忆了这个场面:“参加会议的不少受害同志发了言,有些同志很激动,甚至个别人痛哭流涕。”(88)《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页。
为了平抚这些受害者的情绪,毛泽东、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二人到达瓦窑堡后,都接见了刘志丹(包括刘志丹工作的安排)。(89)据王首道回忆,毛泽东回到瓦窑堡后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五人小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情况的汇报,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释放。他这个回忆有两点不确:一是“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五人小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情况的汇报”,不合情理。二是刘志丹等“应予释放”,因为刘志丹等全部被捕人员已经释放。《周恩来传》称:“他(周恩来)一一接见被错捕后释放的同志。”(此话可能有些绝对,但周恩来安抚许多人应是事实。)比如马文瑞回忆:当时对肃反有点积怨,周恩来同志找我做过思想工作。(90)《马文瑞回忆录》,第91页。此时在前方的张达志、贺晋年因对肃反非常不满,强烈要求离开部队。张达志回忆:“我当时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对这条错误的肃反路线和一些恶劣的军阀习气极端不满,有一肚子冤气,很不安心在十五军团工作,就向党组织写信要求调动。”周恩来到红十五军团找其谈话,但开始并没有谈通,“周副主席耐心地、循循善诱地向我作了解释,说肃反已经停止了,已派人到瓦窑堡把刘志丹等一大批老同志从狱中放了出来,再不会错误地捕人了。并说,以后有什么意见,有什么事,可以直接给他写信……我当即表示愿意继续留在十五军团工作,周副主席很高兴”(91)张达志:《回忆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二、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中共六十年纪念文选》,第535、536页。。
针对当时红25军和红26军、红27军的紧张关系,毛泽东专门发出指示,要求对红25军指战员进行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教育,使他们对地方,对红26军、红27军务必发生良好关系,不应以骄傲而轻视的态度对红26军、红27军,对于红26军、红27军原有干部之尚怀不安与不满应进行诚恳的解释。“徐、程、郭三同志对此项有深刻认识、正确的指导与教育工作,使十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团结如一人一样。”(9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501页。贺晋年曾连续给陕甘晋省委写信,要求离开部队,到地方去工作。为协调关系,毛泽东在红军东征前夕决定第81师归红一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93)贺晋年:《红八十一师东征纪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2,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177页。从此第81师脱离了红十五军团的统属。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为解决西北苏区肃反危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都投入了很大精力。但由于工作、任务之不同,在不同时间他们的活动、作用不同。
第二,有一种观点认为,与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比较,西北苏区的肃反“持续时间最短”“损失最小”。实际上,该论非常错误,它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两点:一是忽略了中共中央在制止西北苏区肃反中的决定性的作用。这是西北苏区肃反“持续时间最短”“损失最小”的至关重要、具有关键性的因素。倘若中共中央未能长征到达陕北并迅速予以制止,西北苏区肃反能够迅速结束吗?而不能迅速结束,它怎么可能“持续时间最短”“损失最小”呢?二是忽略了土地革命时期肃反中具有规律性的现象。中央苏区的肃“AB团”、张国焘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的肃反、湘鄂西的肃反,都是反复多次进行的。一般而言,对无辜者尤其是对功勋卓著者的冤屈、迫害,必然引发大众的义愤和共怒。错误的肃反亦然,特别是对功勋卓著的革命者的错误肃反,必然在革命队伍中引发异议,甚至是强烈的不满和抗争。于是错误肃反的领导人在第一次肃反、打击正确路线的革命者之后,针对有不满情绪者又施行第二次、第三次肃反,如此循环,结果人越肃越多,时间越拖越长,规模越搞越大,最终造成惨重的、令人扼腕痛惜的损失。西北苏区肃反只是因为中共中央的到来,才未形成如此反复多次的可怕过程。
第三,中共中央对西北苏区肃反的制止和纠正,对肃反领导人也是幸事,不但使其错误不再延续,避免了更大错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1935年《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都称其为“犯罪”)的发生;而且使其发动的错误肃反得以顺利收场,并使其从错误的肃反中安全脱身。朱理治后来说:肃反的后期,前方军队和后方都出现不稳的情绪,“我亦焦虑万一暴动,问题便无法收拾”,“曾经想到万一不能收拾时,如何办呢?只有逃回北方局,请示办法了”。(94)朱理治:《关于肃反问题的补充报告》(1942年12月1日),《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23辑(卷2),第1460、1462页。习仲勋1945年发言说:“左倾机会主义者们要不是中央红军到达,恐怕也被群众杀掉了。”(95)《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党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1日),《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23辑(卷3),第1721页。土地革命时期,肃反领导人滥捕滥杀,结果不可收场并酿成自身危机的事例并不少有。综观土地革命时期肃反领导人的结局,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后来的结果不好,如在湘鄂西和红二、六军团疯狂肃反的夏曦,在中央苏区大肃“AB团”的李韶九,均未得善终;二是肃反领导人开始狂暴地肃别人,终因制造的“乱子”太大而最后被别人肃掉,例如在闽西大肃“社会民主党”的闽西肃反委员会主任林一株、副主席罗寿南以及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长张丹川、劳动监察部长熊炳华等8人,在纠正肃反错误中为平众怒,都被执行枪决。在湘赣苏区大肆肃反的湘赣省保卫局长谭牛山,主持鄂东南肃反的鄂东南政治保卫局长明福安,主持江西省瑞金县肃反的该县县委书记、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添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谢在权,也因在主持肃反中滥捕滥杀,最后被公审枪决。而西北苏区肃反因中共中央的成功化解,肃反领导人也就从中安全脱身了。肃反顺利收束、领导人幸免危险,是中共中央解决西北苏区肃反危机的一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