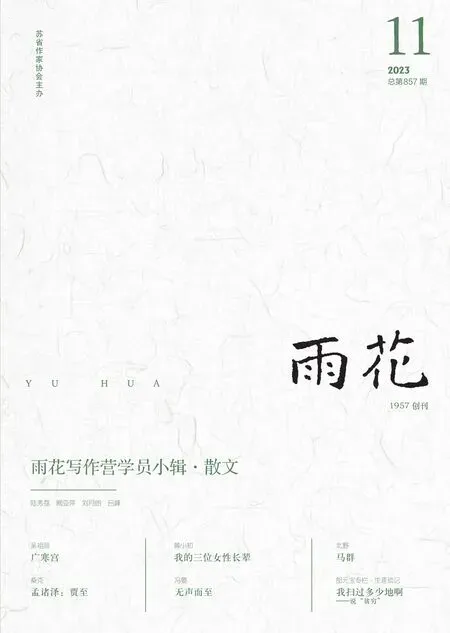浮生只此寄
2023-12-19吕峰
吕 峰
惜君如常
泰山是热闹的,是张扬于世的。无数人慕名前来,为登一次山,为观一次日出,为临一次石刻。我来,为的是看人喝茶。人是俏佳人,茶是女儿茶。佳茗似佳人,以佳人喻茶,有些客套气,若是以女儿喻茶,则多了些亲近味。
俏佳人是我的戏称,其夫妻皆是我发小,一名雪源,一名雪梅,可能从出生之日起,即定下了缘分。两人有青梅竹马的熟稔,有心灵相通的默契,有执手偕老的从容,待人接物,皆淳朴、良善。雪源为雕塑家,雪梅为美学家,说是夫唱妇随也好,说是妇唱夫随也好,两人在泰山脚下的小镇开了一家茶馆。因院中有一棵老柿子树,遂以“一棵树”为名。说是老树,生命力却不减分毫。每到秋天,红澄澄的柿子挂满枝头,耀眼,喜庆。
树下有一木牌,上写:“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的重逢!”遇见即是缘分,遇见即是欢喜。“一棵树”成了无数人的精神家园,来者三教九流,有画家,有诗人,有侍茶者,有参禅者,有制陶者,有古籍修复者。春来树下听鸟鸣,夏来树下享荫凉,秋来树下望闲云,冬来树下晒太阳。茶是一年四季都有的,红茶、绿茶、黑茶、白茶都好,可随心所欲。当然,泰山女儿茶是被隆重推荐的。
泰山女儿茶属炒青绿茶,外形纤巧,耐冲泡,汤色碧绿,有板栗之幽香,有野兰之芳香,颇让人着迷。相传,乾隆登泰山时,途中有一少女献茶,他饮后,清香甘甜,鲜美爽口,遂赐名“女儿茶”。其实,最初的女儿茶为青桐之嫩芽,炮制成茶,可清热解毒,驱瘟祛火。冲泡后,叶形娇美,似藏于幽谷中的丽人,故得此名。此茶不负女儿茶之名,与之有关的皆是美好。
一棵树能携带多少秘密?无人得知。我知道那些秘密无论大小,都是意味深长的,都是引人探究的,都是令人津津乐道的。在“一棵树”下,宜发呆,宜瞌睡,宜冥想,宜谈情,宜做白日梦。还有什么比在一棵老树下消磨掉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更享受的事情呢?每次去,我都在柿子树下打盹、喝茶,一不留神就睡着了。醒来,仰仰头,望望天,继续闭目。院外天下喧,院内壶中寂。清风徐来,胸腔里都是女儿茶的芳香。
院内的柿子不是常见的大盖柿子,也不是所谓的磨盘柿子,外形像西红柿,个小,圆圆的,皮极薄。据雪梅考证,是中原一带的名种,叫火晶柿子。熟透后,圆润丰腴,晶莹光亮,呈朱红色,火一样耀眼。吃时,一手捏把儿,一手掐破薄皮儿,一撕一揭,肉汁便显现在眼前,如美人腮前的胭脂,鲜红、香艳。果肉如蛋黄,如凝脂,吞到口里,无一丝核儿,有一缕蜂蜜的香味,凉甜爽口。
“经手为客倦,半日与僧闲。”雪梅喜欢去山里,且出入频繁,她把山里的树当成了知己,把山里的鸟当成了故旧,把山里的花当成了丽人。坐在那些上了年岁的树下,与它们说说闲话,与它们聊聊前世。茶馆里有数十只猫,有的对来来往往的人视而不见;有的半眯着眼睛打瞌睡;有的已经睡去,呼噜声不断,似老僧念经;有的瞪着眼睛定定地望着你,洞若观火,心中的想法在它们面前无所遁形。
茶馆之猫皆是流浪猫,雪梅有菩萨心肠,给它们提供了庇护之所。每一只猫都有一个名字,名字以中药为名,白的叫白术,黑的叫黑丑,花的叫玳瑁,胆子大的叫龙胆,胆子小的叫毛鸡,跑得快的叫雷丸,跑得慢的叫龟甲,它们也越长越温和,越长越善良。因为那些猫,茶馆看似清寂、静谧,看似生灭无常,实则充满了生机,让人无限牵挂。那些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美好的物,如游鱼般飘忽而来,飘然而散,身体也如在海水里飘忽不定。
雪源则整日与泥巴为伴。我和他从小一起玩泥巴,唯有他把泥巴玩出了花样。幼时,小伙伴玩摔炮游戏,一众人玩得不亦乐乎,飞溅的泥巴弄得满头满脸。他从不参与,一个人捏泥巴,捏人,捏房子,捏小动物,他捏出来的东西让我们大为惊叹。没想到,多年后,他将小泥巴玩出了大花样。只不过,改捏为塑,塑人,塑物,塑佛像。他送了我一尊佛像,低眉,垂目,微笑,不动如山。看到佛像,心便不由自主地安静了下来。
在徐州东南,亦有一座泰山,俗称“小泰山”,也叫“南泰山”。如果说泰安之泰山是山东大汉,徐州之泰山就是小家碧玉了。每一次登山,我都把双脚交给那些古藤般时隐时现的林间小道,任由它们把我带到哪儿算哪儿。小道纤细,弯弯曲曲,是一个又一个人踩出来的。一次,我被带进一处密不透风的林子,空气中弥漫着山野特有的馨香,林间鸟鸣如潮水,藤蔓里间或有几声斑鸠的叫声,像置身于不辨东西南北的丛林秘境。
山上最宏伟的建筑是建于山巅的泰山寺,飞檐翘角,金瓦红墙,几乎占据了整个山顶。泰山寺建于明嘉庆年间,初名显济庙,后更名为碧霞宫,俗称奶奶庙。很久以前,徐州遭遇了大瘟疫,人们向东岳大帝寻求护佑。大帝之女碧霞元君闻知后,不顾年幼,与曹舅爷从泰安结伴而来,降服了瘟神,消除了灾疫。为念其功德,人们在泰山修庙建宇,以人间烟火供奉。
抵达寺庙,需穿过重重古树,需登临步步台阶。入寺,香客如潮,梵音也如潮。泰山奶奶坐于大殿上,像为真人大小的金身像,身披红披风,挽着发髻,面如满月,凤目微张,慈祥地望着红尘中人。我入寺,带的不是香烛,也不是鲜花,而是女儿茶。对泰山奶奶来说,那是来自故乡的茶,以茶问安,亦是我的虔诚。一次,不知什么原因,十几个僧人坐于寺中,阳光打在他们的脸上,庄严肃穆。后来,他们开始念经,清音梵唱,圣洁庄严,一切都静止了,所有的嘈杂声都消失了,连过往的鸟儿也驻足聆听,真像是诸佛菩萨降临,又悄然离开。
山脚有一家推拿所,墙外有三棵槐树,遂美其名曰“三棵槐”,与发小的“一棵树”有异曲同工之妙。外墙上落满了雨痕,斑斑点点,像随手涂下的象形文字,生动,有趣。推拿师姓张,四十岁左右,一米七五的个头,绝对是帅哥,可惜嗓子坏掉了,发不出声。生活在他的前额留下了一道又一道的皱纹,像衣服上的皱褶。他穿着朴素,以高度的洁净,同闪闪发亮的地面、一尘不染的衣架,以及周遭朴素、干净的气氛相互调和。
因长期伏案,我成了推拿所的常客。躺于床上,他的手指像长了眼睛,在我身上抓捕筋络、点击穴位,我僵硬的肌肉开始恢复弹性。推拿完,有说不出的舒坦、愉悦,像一件老旧的机器经过一番敲打,又焕发了生机。时间久了,我和他也熟识了。没生意时,他就置一把竹椅于槐树下,悠笃笃地坐定。然后,慢悠悠地喝茶。茶多是朋友们所赠,他来者不拒,亦不藏私。
一次,我送女儿茶给他,说了发小的故事,他颇为向往,在纸上写道,一棵树有了,三棵槐有了,中间差了一个,你的书房干脆就叫两棵松,多好。“一棵树”收养的是猫,“三棵槐”收养的是鸟,有麻雀、喜鹊、乌鸦等。他时不时将馒头屑、剩米饭等置于墙角。时间久了,那些鸟儿常来此啄食,早飞的鸟,晚归的鸟。然后,不甘寂寞地各占枝头,或来回飞舞,或敛翅静立,或“叽叽喳喳”,让推拿所处于热闹的喧哗之中,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红尘外
一两黄金一两茶,说的是湘西黄金茶。此茶亦不负“黄金”之名,绝对是极富贵之物,藏着春天的秘密,也藏着湘西的秘密。与一盏黄金茶相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落花浮水,是月印湖底。何时饮,都是美事,让我沉于曼妙的春光里,似居于红尘外。
湘西是神秘的,沉潜着神秘的因子,一个又一个,不可数,如筑于高山林间的寨子,如摇着铜铃的招魂巫师,如月光般响亮的苗族银饰,如载歌载舞的篝火。湘西多山多水,因山水相宜,遂有了黄金茶。每年春,廖兄都寄送此极鲜之物。廖兄为湘西人,皮肤黝黑,眼睛油亮,有着苗家人的沉静。其名承文,我戏言是不是想沾一沾沈从文先生的才气。他笑了笑,说,哪敢有那种奢想啊!
廖兄居于凤凰古城,院子不大,匿于市井深处,乃天南海北的文友相会之地。戊戌年春,几个文友相约一聚,有昆明的以西君,有上海的梁涛君,有西安的高崇君,我亦应约前往。春天的湘西,绿色勃发,树是绿的,江是绿的,绿色如潮水,淹没了山,淹没了村子,淹没了古道。唯有一树树杜鹃,如一串串火苗,成为绿潮中的点缀。天地间有沸腾的水汽,夹裹着泥土的腥气,以及草木的芳香气,让我浩然,让我胸肺舒畅。
凤凰城筑于沱江边,是古老的,亦是亮丽的。石板路在光阴中,似一条溪流,路上的脚印被冲走,路上的身影被冲走。行于其上,如静水深流,可于无声处听岁月流逝之声。多年前,无数人在此交集,有去往他乡的山里人,有慕名前来的异乡人,有茶客,有僧侣,有巫师,有士兵,有书生,有美人,有道士,有镖客,有贩夫。青山如黛,江流无声,前途渺茫,心中有说不清的怅惘。沈从文先生当年离开时,也当是如此吧。
苗家人多才多艺,廖兄亦是如此。他会画油画、刻木刻、打银器、斫古琴,亦会烹美食、炒茶叶、写文章、唱苗歌,在我心目中,乃十全十美之人,没有他不会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更像黄永玉先生。他亲制的黄金茶,娇娇的,嫩嫩的,似二八年华的女儿家。茶汤贴着嘴唇卷入五脏六腑,清香,淡雅,俊逸。一叶叶茶像一座座山峰,浮于云雾里。茶汤里也浮荡着星光,浮荡着夜色,浮荡着虫鸣,浮荡着花香,浮荡着四季,浮荡着人情冷暖。
在廖兄的院子,可望星空。窗棂上,瓦檐上,砖隙间,有星光落下来的“沙沙”声,那是星星的心跳,新奇,浪漫,美好。星空下,万物皆是渺小的、短暂的,繁星浮于苍穹,星光落在人的身上,落在花的叶子上,落在砖缝的青苔上,清冷,却又有温度,可温暖灵魂。星光倾泻,喝着黄金茶,说杂七杂八的闲话,说沈从文与张兆和的过往,说沈从文与丁玲的恩怨,说比黄永玉还老的老头。
湘西有两个汉子为我所钦佩,一为沈从文先生,一为黄永玉先生。两人有亲戚关系,两人的人生亦有交集,读沈从文可见黄永玉,读黄永玉又可见沈从文,实在是奇事。两人的经历亦相近,小学尚未毕业即外出流浪,从一个码头到另一个码头,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在船与岸的切换中,在冷与暖的交替中,行走,思索。不过,沈从文先生是内敛的,黄永玉先生则是狷狂的。
泰戈尔在《飞鸟集》中写道:“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沈从文先生的一生当是如此,他活出了人生的最高智慧。小说不能写了,就研究文物,无怨,无恨,默默地活,雅致地活,于日常里洗尽铅华,于平淡中返璞归真,内心充盈、安宁。沈从文先生自称是一名乡下人,他的文字带有牧歌式的纯净,像一粒被江河清洗过的流沙。翠翠、水手、茶峒、凤凰、沅水、湘西,构成了人性之美的最初想象。
时间以液态融进了沱江。沈从文先生是湘西的,亦是世界的。因为他,凤凰广为人知,湘西亦广为人知。哪怕他离世多年,凤凰人或者说湘西人,依然受其恩泽。无一例外,来凤凰的人,都要去拜谒沈从文先生,或持一束花,或携一盏茶,或带一本书。沐风听泉,林荫鸟语里,一坐就是半日。后来墓地周围又陆陆续续立了几块碑,我倒觉得有些多了,有违先生的初衷。
一日,我和廖兄出古城,乘船去听涛山。当年沈从文先生的骨灰即是乘船而下,一半散入沱江,一半葬于听涛山。船是小木船,常年漂于沱江上,捕鱼,装运柴米杂货,偶尔载载游人。船夫人称江老大,船上有一铁皮小煤球炉,上面架着一口双耳小铁锅,炉子旁是一个竹篮,里面放着葱姜等佐料。捕鱼时,炖上一锅水,遇到鲜嫩的白条子,他用指甲刮几下鳞,随手丢进锅里,涮一涮,即送入口中。边吃鱼,边喝酒,边看景,潇洒得很。
江老大随身带一酒葫芦。葫芦也上了年纪,油润,锃亮,散发出古董般的幽光。渴了,乏了,困了,他拧开盖,“滋”地抿一口,人立马活了过来,空气中有酒香弥散。江老大喝酒时,脸眼都闪光,像酒仙,脱俗,忘我,纵情。江老大养了数只鸬鹚,它们栖于木架上,如同处于临战状态。需捕鱼了,跃进水里,“噼噼啪啪”,眨眼工夫,叼上一条条鱼来。鱼还在挣蹦,热闹非凡。江老大也不贪心,只要够一天的油盐钱,即收工。
听涛山,居沱江右岸。说是山,其实只是临江的一堵残崖断壁。崖下有土台,见方不足半亩。因临江,加之野篁杂菁,崖石终年潮润,林间亦多苍苔、槲蕨,极为幽静。墓碑为天然五彩石,石上刻有两则铭文,正面是沈从文先生自书的,“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是张充和、傅汉思伉俪吊唁他的诔辞,“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树梢上是隐隐的啸风,碑崖旁是咽咽的流泉,崖石下是汩汩的水声,显得听涛山愈发地空寂。林间,悬挂着雾露,也悬挂着蛛网。蜘蛛在网里爬来爬去,空气中有牛屎的气息,我想老先生是不会介意的,因为他喜欢朴素的生活,喜欢人间的烟火气。他生前亦是朴素地活着。听涛山是寂寞的,花开是寂寞的,鸟鸣是寂寞的,人来人往也是寂寞的。一出听涛山,则是奔忙的人间,古城更是喧闹。
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一个故园,可能是一座山,可能是一条河,可能是一株树,可能是一盏茶,可能是一碗羹。对黄永玉先生来说,凤凰让他梦绕,让他魂牵,他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中写道:“文学上,我依靠永不枯竭的古老的故乡思维。”眷恋故土是人的本性,哪怕那片土地再荒凉、再贫瘠,也生长着属于这片土地的植物,也能开出属于这片土地的花儿。晚年,黄永玉先生在凤凰建了一栋房子,名为“玉氏山房”,用来安放乡愁。
老木朽于深山,是静守,亦是回归。对黄永玉先生来说,化身山野即是魂归来处。我在写这篇文章时,黄永玉老先生驾鹤西归,享年九十九岁。我觉得他是去另一个世界吃喝玩乐了,继续逍遥。老先生说:“人生嘛,快乐比什么都重要。”面对生,他是快乐的、豁达的,面对死,亦是如此。他说:“等我死了之后,先胳肢我一下,看我笑不笑。”又说:“我的骨灰不要了,跟那孤魂野鬼在一起,我自由得多。你想我的话,就看看天、看看云嘛。”
来了湘西,山野、茶园、寨子都是要去的。湘西的山野是可爱的。廖兄深爱湘西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他无数次地潜入深山,无数次地独坐水边。茶园在山中,如梯田,一阶又一阶,可感受山中甘露之纯,林中清涧之润。寨子是古寨子。数百年前,甚至更早,人们挑筐背篓,翻过一座座山,蹚过一条条河,方来到此处,开辟林田,筑墙搭寨,每一块砌起的石头,都留下了他们的指纹、温度、气息,留下了他们的饥饿、疾病、死亡,也留下了他们的憧憬、向往、期许。
离开时,廖兄笑问我,可愿做一名湘西人?我万分之乐意,在沱江边钓鱼、赶牛,在凤凰古城里种花、吃茶,在听涛山晒月光、淋星光,神游无极限。哪怕实现不了,在我生命的履痕中,我庆幸有过这样一个下午,我立在沈从文先生的墓前,风无声地吹过,树叶在摆动,我单薄的衣衫也在摆动,心却沉静如水中之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