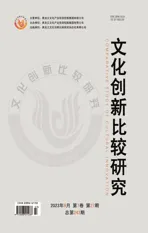甲骨文构造的概念隐喻理据研究
2023-12-19焦丽
焦丽
(安阳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安阳 455000)
中华文化的赓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字这一载体,汉字也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没有间断的文字,自甲骨文时代至今已有3 000多年的历史,为中华文化的历史更替、推陈出新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对国家发展和民族自强自立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我们要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因此,深入挖掘甲骨文背后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因素有助于对中国文化的追根溯源,也是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
甲骨文作为汉字最早期的形态,是华夏先民智慧的体现,与当时的历史和文化因素息息相关,是人们与外部世界互动的产物。通过对甲骨文构字的分析可以窥见华夏先民的思维模式、社会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可以更好地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概念隐喻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之一,探究人类思维方式和语言本体的关系,透过语言现象揭示外部现实,探讨人类心智和语言的互动。概念隐喻理论与甲骨文的构造机制相契合,正如《说文解字》中所描述的汉字创造过程:华夏先民俯仰天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依类象形”而后“形声相益”[1],因此,几乎所有甲骨文字都有“据形索义”的特征[2]。由此可见,从概念隐喻角度来研究甲骨文的内在生成机制有助于深入理解文字背后的思维和文化因素,深化人们对甲骨文的认识。
1 概念隐喻理论
概念隐喻区别于传统的隐喻,不是语言的修辞方式,而是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概念隐喻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理论,该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种语言研究范式,是认知学科和语言研究结合的产物,致力于对语言本质的探索和揭示,其研究对象是语言与人类认知的关系,Lakoff和Johnson的著作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标志着该学科的成立。经过30多年的发展,认知语言学已经形成“理论多元、方法多元和研究范围广阔的综合研究范式”[3]。作为经典理论的概念隐喻也被广泛应用于文字构造分析,通过共时与历时研究来解释语言的成因和发展规律。
文字的创造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如何用有限的符号来传达无限的意义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即语言要具有一定的经济性。概念隐喻是文字和语言形成的重要理据,通过概念隐喻,有限的语言符号可以表达无限的概念系统,同时语言符号也可以随着历史的变迁进行意义的增减。
概念隐喻指人们通过具体的、熟悉的、简单的事物来认识抽象的、陌生的、复杂的概念。其认知机制是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即已知或熟悉的概念向未知或不熟悉概念的映射,在这个过程中认知主体需要将源域和目标域进行并置和比较,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有时候还需要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加深对概念结构的认识[4]。在人类与外部世界互动过程中,人类的认知活动逐渐深入,推动了语言形式的创新和语言系统的完善,逐渐从简单、具体、有限的语言形式发展到复杂、抽象、多样的语言系统。
目前,概念隐喻的分类标准比较多样,其中最经典的是Lakoff和Johnson的分类,即根据源域与目标域映射关系的不同,概念隐喻包括方位隐喻、结构隐喻、本体隐喻[5]。方位隐喻又称作空间隐喻,指将空间位置映射到非空间概念上的隐喻范式,从而赋予后者一个空间方位。例如:“近几年失业率上升了”中,上升的基本意思是物体空间从下向上的位置变化,但是通过向概念域“失业率”的隐喻映射,延伸出抽象的意义。人类的情感也可以通过具象的方位变化来表达,如“情绪高涨”“情绪低落”“心情处于低谷”等。结构隐喻是通过一个界限清晰、结构分明的概念去建构一个界限模糊或内部结构不完全的概念。例如:旅行和婚姻之间具有相似性,因此,两个概念域之间的映射关系在语言中非常常见,“婚姻触礁”“婚姻走到尽头”等都是基于这一隐喻模式形成的。类似的表达还有“生活陷入泥潭”“生活失去方向”等,抽象的概念像是行驶的车辆或船只,而两个概念域的部分结构则实现了关联。本体隐喻也叫作实体隐喻,该类隐喻使人们可以把抽象的事件、活动和情感等视作有形的实体和物质。例如:在句子“谢谢您抽出宝贵时间接待我们”中,抽象的时间概念具有了实体界限和外形,类似于具有重要价值的产品。汉语词汇中和语言相关的“话匣子”“画外音”“言外之意”等都是将语言看作有界限之物,从而有里外之分。
基于概念隐喻这一认知机制,词汇意义得以扩展,语法和篇章结构得以丰富。汉语中多义字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概念隐喻机制。例如:汉字“头”是人体的一个重要部位,但是通过隐喻映射,延伸出丰富的内涵,包括物体的顶端(山头、笔头)、首领(头目、头领)、事情的起点(头绪)、时间的前端(头三天)、排序的前列(头等、头条)等。正是因为人类思维普遍的隐喻性,语言表达才能呈现丰富多样的色彩,人类的思维和体验成果才能够有效地表达出来。隐喻思维使语言符号能够承载更多的信息和情感,人们之间的交流更加准确、流畅。
2 甲骨文的概念隐喻特征
西方现代语言学体系主要以英语为研究对象,但是认知语言学仍然可以为汉字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因为其理论基础和汉字的造字过程具有高度相似性[6]。该理论将语言看作语言社团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结果,反映了语言社团对自身和万物的认识。将认知语言学理论应用于研究甲骨文的形意关系有助于揭示其背后的认知机制。
概念隐喻是汉字构造的重要理据,正如Northrop Frye所言,汉字的解读需要“隐喻性思维飞跃”[7]。目前,尽管以汉语为语料的相关研究并不多,隐喻在汉字构造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因为隐喻在生活中广泛存在,“我们赖以思维和行动的一般概念系统从根本上讲是隐喻式的”[8],语言也不例外。作为表意文字的甲骨文是基于相似性创造出来的,人们通过对客观事物的临摹来以此达彼,这符合概念隐喻的思维。例如:甲骨文“”(永)的字形似流动的河流,其常用义项为“永久”,即以空间中具体的、有形的、容易识别的概念河流来隐喻抽象的、无形的、难以表述的时间概念,意指时间具有河流的特征,奔流不息、永无止境。
甲骨文字形结构和字义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即象似性是其文字创造的重要依据,其中的单一结构字基本上都是象形文字,即对现实世界的临摹,组合文字虽然含有较明显的会意特征,但也是和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经验密不可分的。甲骨文字“”的意思是木,很明显是对客观世界中树木形象的临摹,尽管该字形和实际的树木不是完全对等的,进行了一定的抽象化,但在结构上仍然存在高度相似性,该字的结构具有典型的隐喻思维特征。
与上述案例相似的文字还有很多,尤其是一些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词汇,如 “”(火)、“”(水)、“”(山)、“”(小)、“”(戈)、“”(干)等。前 3 个字为自然现象,以简单的线条来比拟自然存在事物的形态特征。“”字由一些微小的点组成,突出事物体积上的特征。“”为一种兵器,是对该兵器实际模样的简化。“”为一种工具,也是参照实际物体的形状创造出来的。这些字体和现实世界是照应的,是对现实事物的隐喻。
指事字的字形和字义之间也具有典型的隐喻关系,例如:“ ”(一)、“”(二)等表示数量的文字通过简单的笔画描述了抽象的含义,用横线的数量归纳了事物的本质属性,隐喻所描述实体的数量。同样,表示方位关系的空间词汇“”(上)、“”(下)等通过对两个实体相对位置的描述,反映物体的空间方位关系。
甲骨文的隐喻理据反映了华夏先民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和认知成果,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创造出来的。例如,甲骨文的“(买)”字由上部网状结构和下部贝组合而成,其字面义为用网捕贝,意义延伸为买卖。在字形中缺少交易相关的场景或线索的前提下,人们通过隐喻映射也可以推断出含义。因为贝是古代常用交易货币之一,撒网捕贝等捕鱼相关的概念域映射到人类社会的商品交易中,通过具象的动作来指向抽象的概念,撒网捕贝的过程就像通过商品交易来获得利润,“网贝”即是“网利”,该字通过隐喻机制将具体的动作和抽象的概念联系到一起。
3 甲骨文形意关系的隐喻类型和特征
甲骨文形意关系中的概念隐喻包括哪些类型?各个类型具有什么特征?本文以《甲骨文字典》等辞书为依据,参考Lakoff和Johnson对隐喻的分类,对甲骨文背后的隐喻机制进行分析和比较。
3.1 甲骨文字的隐喻类型
3.1.1 甲骨文中的方位隐喻
方位隐喻或空间隐喻和空间方位相关,较为容易理解和识别,赋予抽象事物或概念一个空间方位,继而能够根据方位变化来描述抽象意义。
3.1.2 甲骨文中的结构隐喻
结构隐喻是甲骨文构字的隐喻类型之一,用界限和结构清晰的概念来描述界限和结构模糊的抽象概念。甲骨文的“生”字为“”,其上半部分象征树木,下半部分象征大地,意指树木破土而出,象征生命力。该字的构造具有明显的隐喻特征,人或动物的成长和树木的生长过程类似,从幼小到粗壮再到衰老,因此两个概念在结构上相似,通过树木的生长过程可以隐喻人或动物的成长,故该字指生长过程或活着的状态。
3.1.3 甲骨文中的本体隐喻
3.2 甲骨文字隐喻理据的特征
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甲骨文字构造涵盖了隐喻的基本类型,很多字形不能用单一的隐喻思维模式来解释,往往需要借助转喻或者其他隐喻类型,例如,结构隐喻和本体隐喻,两者具有重合的特征,很多时候相互交织、共同作用。
目前,甲骨文已经识别出的文字很多语义不详,缺少确切的考证,很多字体用于地名或人名,通过隐喻得以延伸的语义比较有限。因此,从独体字的构造上看,毋庸置疑,甲骨文是华夏先民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加工成果,文字和现实具有高度的象似性,即“汉字的创造就是先民将心中的意象符号化的过程”[10]。但是,甲骨文通过隐喻映射向更加抽象概念域的意义延伸是相对有限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甲骨文最初创造的目的是用于人类和超自然力量的沟通,即占卜,而普通百姓接触和使用的机会不多,这也限制了文字的传播和意义的创新;另一方面,文字是基于人的体验而形成的,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人们首先要实现的是简单的意义表达和思想沟通,随着华夏先民体验的丰富和活动领域的拓展,语言和文字也得以不断创新和丰富。
从隐喻类型的案例分析可以看出,时间和空间概念域之间的映射在甲骨文字的隐喻机制中比较常见,抽象的时间概念可以通过空间方位和距离的变化来表达,如“”(永)、“”(翌或昱)等。由此可见,华夏先民对于抽象的时间概念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表达系统。
4 结束语
目前,已有的甲骨文研究侧重于字义的注释,但是很少有文字根源的探索,在文字和文化的追根溯源上还有很大的空间。从甲骨文构字隐喻机制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甲骨文的创造和隐喻思维息息相关,根据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关系可以更好地窥见文字背后的思维模式。通过甲骨文隐喻理据的研究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其背后的思维和文化因素,并将这些理据融入词典编纂、语料库建设、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以推动甲骨文的传承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