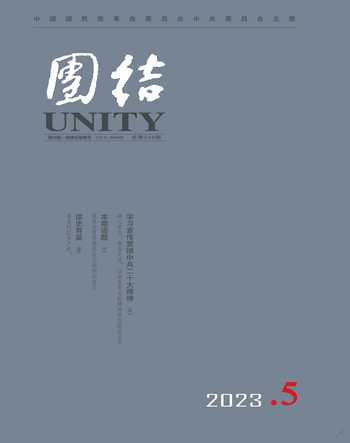《离骚》片论
2023-12-18李广良
李广良
一
《离骚》是华夏诗史上划时代的篇章。《离骚》之前的华夏诗,以《诗经》为代表,但《诗经》实际上是通过“采诗”制度所收集的“歌集”或“歌曲集”删改、整理的结果。这些“歌”或“歌曲”无论是“田园性”的,还是“宗庙性”的,其作者却都是“匿名”的、隐身的,显现于大众之前的只有歌曲本身,而留存于历史中的只是被称为“诗”的歌词。《离骚》的横空出世,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诗体”的诞生,更意味着“诗”和“诗人”的独立。从此以后,“诗”不再是音乐的附庸,而是在保持与音乐的亲缘关系的同时,以“诗意”为其内在的本质;“诗人”亦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是以“诗”成就其内在生命意义、实现其存在价值的人。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是见诸正史的第一个“诗人”,可谓中国诗史上的第一个“诗人”。据《史记》记载,屈原,名平,任楚怀王的“左徒”,“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王甚任之”。由于遭人谗害,“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楚怀王死后,顷襄王即位,屈原的境况更趋恶化,终被流放至南方的沅湘流域。“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在与一“无名”的渔父对话后,屈原乃作《怀沙》之赋,抱石投汨罗江身死。
对于《史记》的记述,后世学者颇有怀疑之者,如胡适就认为历史上并无屈原其人,理由是屈原首次出现就是在此前的二百年间并无人提及屈原。以我之见,根据司马迁的精神品质,他在叙事时或许会渗透个人之想象和情感,但断无伪造或假托历史人物之可能。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文本看,司马迁诚然有夸大屈原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之嫌,未能真正揭示楚国衰亡的原因,但这种“局限性”反而恰好证明了屈原的“存在”。司马迁的叙述和屈原的诗篇都表明,屈原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学识渊博,才气横溢,充满激情和想象,又满怀政治抱负,力图挽救危亡的楚国。然而政治上的不得志,使他只能通过“写诗”来抒发个体的生命激情和华丽想象,从而留下了《离骚》《九歌》《九章》等不朽华章,成就了他“伟大诗人”的“美名”。屈原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一个纯粹的“诗人”也许会参与政治,但其参与方式仍然是“诗意的”,不符合“权力逻辑”的。对政治来说,屈原是“权力场”上的“另类”;对诗来说,屈原则是“个体自由书写”的开创者。而“个体自由书写”则是“诗”的本质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屈原是“第一个诗人”,是华夏的“诗魂”,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杀的诗人”。很多材料说屈原是“政治家”,我觉得这顶帽子是不适合屈原戴的。文学史论著中还有“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是民族诗人”“屈原是人民诗人”“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等说法,这些说法或是“意识形态性”的,或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故均值得商榷。
二
关于《离骚》之创作及其意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如此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返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司马迁对《离骚》的阐释,也许并不仅仅代表司马迁个人的观点,而是代表一种经学传统。洪兴祖《楚辞补注》说:“始汉武帝命淮南王安为《离骚传》,其书今亡。按《屈原传》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又曰:‘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孟坚、刘勰皆以为淮南王语,岂太史公取其语以作传乎?”如此说属实,那么西汉时对《离骚》的理解至少已经具有了“经学式”的经典意义,后世之称《离骚》为《离骚经》即源于此。在“经学”的视域中,《离骚》的创作源自屈原的“忧愁忧思”,而“忧愁幽思”又来自于“信而见疑,忠而被謗”的“怨”,故有“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的判断,显然这是一种经学政治论或经学伦理学的解读。王逸《楚辞章句》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尔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王逸的“楚辞解释学”无疑是西汉以来楚辞学正统的发扬和补充。对屈原之“怨”的理解既须从儒家诗学传统来理解,也须突破经学政治论的局限。屈原之“怨”继承了《诗经》“兴观群怨”之“怨”的精神,此“怨”并不是个体心理上的愤世嫉俗,而是“包含男女爱情在内的种种忧伤、追求、感叹”,是与“仁道的实行相联系的‘怨’”(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但屈原并不是“圣王政治”序列中的“圣人”,其政治观念或来自儒家传统,而其创作的原动力实际上来自本人的生命实践,来自屈原作为“自由个体”的情怀意绪,这种“情怀意绪”的诗性呈现才是诗之为诗的本质所在。在此意义上,太史公所谓“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或可理解为对屈原诗乃至一切诗的本质开示。
三
《离骚》全篇共373句,近2500字。作品以精巧复杂的结构,奇幻瑰丽的想象,优美深情的文字,抒发了屈原平生所“郁结”之“意”。现代学者对此“意”的理解多是政治性的,即把屈原之“意”理解成“政治理想”“政治抱负”“爱国主义”等,这种“政治化”的解读固然有其“艺术社会学”的根据,但也难免遮蔽了《离骚》的“诗性”本质。很多学者把《离骚》定义为“政治抒情诗”,就是出于这种“政治化”的导向,而要真正理解屈原和《离骚》之“意”,就必须超越政治学的维度而进入诗学存在论的维度。
在诗学存在论的维度上,《离骚》和一切真正的“诗”一样,是对人的存在的“保存”和“存在”意义的揭示。首先,《离骚》之所以名为“离骚”者,是因为“离骚”本身就是人的普遍命运。《史记》引刘安曰:“‘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赞骚序》曰:“离,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人不仅在“别离”时“遭忧”,而且在一切活动之中“遭忧”,范仲淹所谓“进亦忧,退亦忧”是也。从《离骚》问世之后,诗人就被称为了“骚人”,就是因为诗人深切地把握到了人生的“忧”,是以在诗人的笔下,即使“欢乐”也是在“忧愁”的笼罩和浸润之下的。其次,《离骚》看似“是屈原自叙生平的长篇抒情诗”,但其实是一切徘徊、挣扎在权力场中的“诗人”的写照。一切人都在权力场之中,权力一方面“成就”人,另一方面“控制”人,故既有悠游于权力场之中“其乐无穷”者,又有深感于权力场之“无可奈何”者。一个“诗人”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进入权力场,如屈原因为其家世,但权力的运行自有其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往往与“诗人”的心性相冲突,为化解此种矛盾,“诗人”或为权力而放弃“诗”,或为“诗”而放弃权力,屈原毫无疑问是后者。
《离骚》全诗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开头至“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第二部分从“女媭之禅媛兮,申申其詈予”至“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第三部分从“索琼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至篇末“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从始至终的整个历程,可以说就是诗人的“精神发展史”或“精神现象学”。
诗篇开首的“帝高阳之苗裔兮”,是对家庭世系或自身生命本源的追溯,这不是阿Q式的“祖上曾经阔过”的“自欺”,而是一种“历史意识”的呈现。随后就是天命的出生时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和父亲赐予的“嘉名”(“正则”“灵均”)。随后就是具有“内美”和“修能”的诗人在权力场中的遭遇和心路历程,在“桀纣猖披”“党人偷乐”“信谗齌怒”的政治现实中,诗人犹然“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其结果自然就是“吾独穷困乎此时”的存在状态。
第二部分从“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开始,婵媛的“申申其詈”表明诗人的无与伦比的“孤独”与“寂寞”。在此深重的“孤独”中,诗人先“就重华而陈词”“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然后开始了其“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历程,穷极想象,气象万千,美不胜收,动人心魄,但无论如何“周流上下”,却发现自己仍然处于“世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的世俗险难中,故不得不沉痛地发问:“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
第三部分是全诗的终结,借灵氛的占卜以述说诗人在去留问题上的内心冲突,“驰骋在云端的幻想又一次掉落到令人绝望而又无法離开的土地上”(马茂元,《楚辞选》)。诗人虽极驰骋想象之能事,终究还是不得不哀叹:“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在“美政”理想破灭以后,他的唯一选择就是彭咸式的生命结局。王逸《楚辞章句》说:“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显然,这是一种“以死全节”的决绝的态度,是与其“帝高阳之苗裔”的生命起源相匹配的“贵族精神”的表现。屈原最终的“投江”即根源于此。
如许多论者所见,《离骚》中描绘了“两个世界”:一个是人间的现实世界,尤其是以权力运行为核心的日常政治世界;另一个则是由天界、神灵、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风、雷、鸾凤、鸟雀所组成的超现实世界。(赵逵夫,《〈离骚〉中的龙马同两个世界的艺术构思》)《离骚》的“诗意”的秘密也许就在这“两个世界”中,前者是通过与“众皆竞进以贪婪”的现实的抗争以维持诗人的“自由”,后者则是通过遨游广阔、雄伟、瑰丽的超现实世界以实现精神的超越。不过以我之见,在《离骚》中还有一个辽远的“历史世界”,这可能是诗人最深沉的牵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