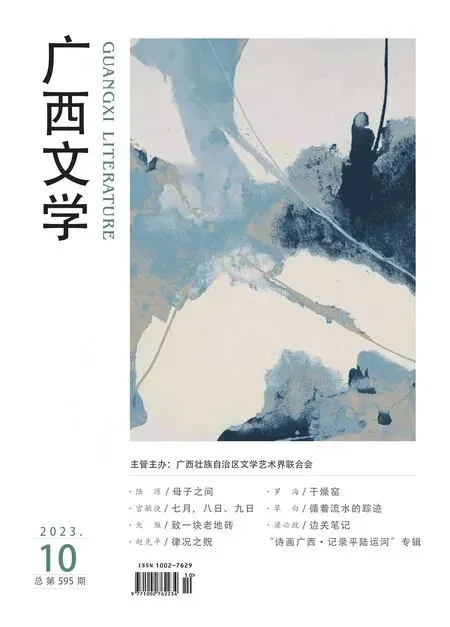融化铁皮的温情方式 评论
2023-12-12杨仕芳
杨仕芳
我不记得和罗海兄是在什么时候认识,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认识,总之他留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刻——简单而憨实的男人。起初,我对他的写作没有多大期待,因为我觉得像他这样性情沉稳的人,凡事守规矩,不会无故冒犯谁,自然也决定着写作上不会冒险,其结果导致作品难有令人拍案叫绝之举。
但是,我看走眼了。罗海兄是个简单而憨实的男人不假,是个真诚而率直的男人不假,是个值得深交的男人也不假,令我始料未及的是,在那张看似简单而憨实的皮囊下,原来包裹着一颗并不安分的灵魂。我一直觉得只有不安分的灵魂才敢于冒险,才敢于冒犯那些顽固的经验壁垒,从而探寻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作之路的可能。
罗海兄就是这样一个人,内心充满热烈的创作激情,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无惧任何写作险境,只要认定一个题材就不管不顾地往死里写。写是我能做到的,写成怎么样是作品的问题,这几乎成了他的写作信条。这些年他创作了一大批优质的散文作品,出版了《城市书:上海生活》《个体户笔记》等,其创作过程是相同的,抓住一个题材作为支点,继而在读者面前明目张胆地撬开一个新的散文世界。《干燥窑》也是如此,这是一篇关于工业题材的散文,是他写下《城市书:工厂生活》的一个篇章。
工业题材作品鲜有令人惊叹之作,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多方面的。首先,与工业题材相关的文学作品容易先入为主地给人以艺术品质不高的印象,从而影响了作家创作这个领域作品的热情与信念。其次,在这个全民自媒体时代,文学行为过于聪明、轻巧,哪儿热闹就往哪儿去,怎样吸引眼球就怎样办,已经很少有人愿意下苦功夫钻进那些被冷落甚至吃力不讨好的题材里,而工业题材更甚。最后,更重要的是作家本身对工厂生活、对现代工业文明缺乏了解,没有与工业文明相关的背景,也跟工业题材的难以把握有关。因此,对工业题材进行深刻思考的作品并不多见。这类文学作品数量不多且影响力相对较弱,跟当下中国飞速发展的工业不相匹配。
罗海兄却像个愣头青一头扎进这个题材,压根不去考虑是否能把这类题材的作品写得令人期待。他在意在乎的只是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无论面对远去的往昔,还是不可预知的未来,他从来都选择真诚地敞开心扉,让独属于他的记忆和念想水银泻地般在纸上四处流淌。
这是令我信服的,更令我信服和期待的是,罗海兄竟然选择与工业题材正面交锋。要写好工业题材作品,不仅需要勇气与毅力,更需要对工厂生活的热爱与慈悲,恰好他具备这些条件。他深刻地认识到工厂是社会生活一条强劲、敏锐的脉搏,它串联着个人、集体和国家命运,进而能够在纷繁杂乱的市场里敏锐地捕捉到社会转型期间,时代在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里投下的巨大影子,个体命运与社会背景在轰鸣的车间里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他能做的是用文学之笔记录和安抚那些散发着温情的灵魂,再冰冷的铁皮和历史也将被捂暖和融化,继而构建出芸芸众生的精神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