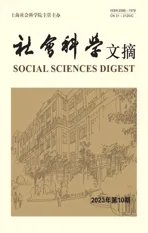触感:书写与阅读中意义生成的重要中介
2023-12-10王琦
文/王琦
任何有意或无意的书写,总会有某种意义发生。围绕书写这个源初的动作或行为,身体、触感、阅读、生存等环节始终缠绕在书写意义的“发生”之中。书写和阅读既是人及其身体的行为,也是人及其身体存在的方式,其间交织着触感、意义和存在等诸多问题。但是,传统观念中的书写往往被当作某种工具性的存在,或者是语音的模仿,或者是理念的再现,或者是意义的呈现。这种观念没有把书写本身当成一个有意义的对象进行思考。事实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中,书写都既表征着人的主体性生成,又显现着意义的生成机制,同时还是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之一。如果不对书写本身进行思考,书写的意义及其生存论价值就无法得到彰显。在梅洛-庞蒂的身体理论和德里达的书写思想的基础上,当代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1940—2021)看到了书写本身的独立价值,从生存论的维度重新思考了书写、阅读跟身体及其触感的关系,为我们揭示了意义的生成机制以及其间身体触感的中介作用。
书写中身体问题的凸显
历史化、经验化的书写观念,激活了书写与语言之间的联系,但也很轻易地就将书写行为中身体的作用、书写结果中感性的意义、书写活动中潜在的阅读经验等问题搁置起来,以至于我们似乎必须经过语言的中介才能理解书写本身。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论文字学》等著述将这种理解视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偏见,并将它命名为“语音中心主义”,而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解构”,使书写成为哲学思想的重要范畴。作为德里达的好友和“解构哲学”的传人,南希进一步在意义的世界化、书写的触感化、生存论的重构等方面重新思考了书写;他将书写理解为意义溢出身体之外的“外铭写”(excription),将书写与身体的关系问题引入对书写的思考,在生存论的高度上重建了书写的哲学框架。
南希书写理论的超越之处是打开了书写理论的身体维度。西方哲学中的身体理论都将身体理解为具体的物化实在。梅洛-庞蒂试图通过“通感”将这种物化的身体转化为活的、生成着的身体,他的身体现象学揭示了身体的始源性作用,以及“身体图式”在世界实践中的展开。德里达则是将“通感”细化为“触感”,并通过对触觉叙事的延异,呈现了身体作为在场的可能性。南希的身体理论实现了梅洛-庞蒂和德里达的统一,澄明出身体作为实体触觉和作为虚体的“意义‘外铭写’”,并以此激活了书写理论的身体向度。南希通过内在逻辑的贯穿和具有典型南希色彩的综合创新,使得书写与身体成为一体之两面,在彼此深化的过程中显现自身,形成了“‘书写—身体’辩证之弓”的独到镜像,重建了书写理论和身体哲学的形而上学,在身体理论的激活下,书写理论成了当代法国理论的显学。
书写既是身体的行为,也是身体之为身体的体现,二者互为生成、互为存在基础。如果我们把书写理解为刻下痕迹的行为或动作,把它与人类获得自我主体秘密的过程联系起来,把它与人本身和人的身体的存在方式联系起来,书写便具有了深刻的生存论意义。南希正是从生存论的维度对书写与身体的关系展开其原创性思考的。他的突出贡献在于,进一步将“书写”从概念史的边缘位置移到中心,通过“书写”将梅洛-庞蒂所主张的身体与世界互惠、融合和交织的感触关系深化为意义溢出自身之外的“外铭写”,也将德里达解构主义的“书写”路向从内在转化为外在,从德里达认为意义的流动性、生成性本身即为书写转化为身体、触感、书写、意义四维的“共在”“共织”。
书写的触感化生成
在对现代性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南希发现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即现代性的发展使身体越来越多地布满整个世界空间。如果说梅洛-庞蒂是通过身体的统摄性和身体的“通感”来展开语言的讨论,那么南希则是从身体本身出发、从身体的“触感”出发来阐释书写何以可能。与梅洛-庞蒂立足于身体的统摄性不同,被南希发展为“外铭写”概念的书写,已经不是关于身体的书写了,不是关于身体的符号、图像或编码的书写,而是身体本身的书写,是实质上的身体书写。
如何思考身体和书写的关系?南希认为,二者都是与生存论意义上的人密切相关的,因为是人的身体和人在书写。南希这里所理解的人,是活生生的、变动不居的、并不具有决定性中心地位的生存论意义上的人。以这个人为中介,身体与书写才能建立起必然的联系。人的中介性首先是通过身体和身体的向外触及来实现的,这意味着书写及其意义的生成首先都必须从触及身体开始。何谓触及身体?南希解答道:“触及身体,触摸身体,触感——始终发生于书写。或许,身体并不完全地发生于书写之中,如果书写事实上具有一个‘内部’。但沿着身体的边界,在它的极限,它的末端,它最远的边缘,只有书写发生。如今,书写在界限上获得位置。因此,如果书写遭遇了什么,那么,它遭遇的就只有触感。更确切地说,是用意义的虚体来触摸身体。因此,让虚体成为触感,用触摸来构成意义。”显然,南希坚持了现象学的基本立场:只有在书写的行为或进程中,在触及身体之外的其他实体的过程中,身体才得以出生。
南希这个观点事实上是在强调从“外部”而非“内在性”的角度去理解身体与书写之关系的可能性。换言之,只有在触感中,书写及其意义才能展现出来,书写与身体都隐秘地联通着人的触感经验。这一触感经验首先落实到一种源初语言和生命触感上。而且,它带来了明显的理论转向:因为触感的介入,书写的目的发生了转移。书写与身体的关系也得以重构。所以,任何一次不断敞开和越界的书写,都是捕捉触感足迹的尝试,是身体自我与他者相互感发的生命活动,是在知识、理性、话语、权力等形式被取消之后的生命触感。这样,书写就与界限、触感、外在性、他异性等结合起来了,书写成了一种揭示界限、触及界限的方式。在书写中,意义需要经由身体及其触感的中介,才能生成出来;生成出来的意义之中也必然包含着身体触感的因素,一切意义必然原初地包含着身体触感的感性因素。
可以看出,南希在书写与意义、书写与触感之间建立了本质性的多维关系:触感作为身体的外展,是更为根本的感官机制,它是意义的发生方式,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世界意义的起点;书写始终发生于界限之上,在对身体的触及和身体的感触之中生成意义。书写不仅仅是建立一种联系或关系,这种联系或关系仍然意味着交流、翻译或交换的理念,书写还在于将意义发挥到极限,也在于将身体发挥到极限。每一次书写都是陌异的书写,都是一种离散、打断和碎片化,都是打开某种间隔化空间的外展。在这个意义上,书写其实就是一种打断和间隔,它不是对过去或当前在场的再现,而是在其专有的在场中追踪生存的他异性,通过踪迹的差异来铭写差异的踪迹。
阅读和触感的本质性联系
书写与阅读,在触感的意义上本身就是一体两面、互为条件的。阅读在南希那里首先也不是作为理论或定义而出现的,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最真切、最独一,因而也最本真的感性经验。南希首先在书写与阅读的交互中,发现了它们跟触感的本质性联系。对于书写与阅读来说,它们都是发生在表皮或者说纸页之上的,正是通过这一表皮或纸页,书写的身体与阅读的身体彼此触摸,而且如此的触摸总是无限地间接和延迟的。书写与阅读在触感维度上的本质联系,并不能解释也不能掩盖书写与阅读之间的差异性。无论如何,两个身体(书写的身体和阅读的身体)无法同时占据同一个位置,身体是不可渗透的,书写与阅读之间永远不是同一的,永远处于差异化过程之中,处于错位和间隔之中。
如何解决书写与阅读在触感维度上的本质联系跟二者事实上的非同一性之间的矛盾?南希的方案是:把书写和阅读“非实体化”,即书写和阅读并非某种实然的、意指的、有特定目的和归宿的“实体”,而是向着尚未来临的在场无限敞开的“虚体”;重要的不是书写和阅读在意义维度上如何实现同一,而是它们都在打开那个“非实在性场域”时所形成的意义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阅读即外展——既是身体的外展、书写的外展,也是阅读自身的外展。阅读首先是身体的外展。但是,身体本身并不是一个固化的预设和意指,而是一个非实在性场域的敞开。在我们的阅读和书写中,始终有某种东西不被阅读和书写,这个不被阅读和书写的东西,就是永远在场又永不在场的东西——这就是身体。这样,很大程度上,我们的阅读与书写总是遮蔽了作为二者之本质或本己特征的身体的在场。
书写和阅读的本己性似乎将它们永远区隔了起来,使它们无法在意义的共同显现中同时在场。然而,南希的共在思想将一切存在都理解为处于共同存在状态之中的共在,虽然保持着独一性,但也永远向着多样性保持开放。书写和阅读的本己性存在本身,也是这样一种共在意义上的存在,也只有在共在之中它们才是共同显现和自我外展的,否则它们便是无意义的。书写与阅读总是在身体的“触”和“触感”之中发生的。书写与阅读中的这个身体,虽然也是一个“意义的身体”,但被剔除了意指重负和神秘象征,被还原到如其本然的本己之中。在这个意义上,阅读就被南希赋予了重新发现身体之意义的使命,身体成了书写与阅读在触感维度上得以交互发生的关键环节,如同书写一样,阅读因而也被南希提升到生存论的高度。
意义生成的四维关系结构
书写与阅读都以身体及其触感为基础,因而都可以从生存论的角度进行解释。问题在于,生存本身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相对性又使这种解释潜藏着虚无主义的风险。需要确立一个既能避免虚无主义陷阱又能将生存论的特色凸显出来的枢纽,才能在身体和触感的意义上有效地解释书写与阅读的生存论意义。南希找到的这个枢纽是“意义”。在南希看来,在实践层面上,人首先是在他者中的存在,而人与意义—世界之关联的发生,永远只能与人的身体的物质性联系在一起。联系对身体及其触感与书写和阅读的关系,南希认为,只有通过书写才可以实现身体的外在性,才能实现世界的意义化,才能完成世界多样化的展开。书写的过程其实也就是身体经由触感走向意义中心的过程,但通往意义中心的途径,是需要与他者的触及和身体的触及的。书写和意义的关系就在于它始终表达意义,又使意义总是处于未完成状态。在每一次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书写中,身体及其触感在给出自身的同时,也超越了自身,激发并分享了存在本身的意义。这样,南希实际上超越了德里达的书写和原初书写的概念,在建基于身体的生存论的高度上,以意义为枢纽把握书写与触感的关系。
对意义的领会是阅读的首要目的。在《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曾经谈到过一种阅读,那种阅读被视为以“常人”方式进行的“闲谈”之接收,这构成了“常人”的“平均领会”。也是在这个“平均领会”的基础上,海德格尔将“闲谈”向“套话”进行了扩展,把言谈的普遍性扩展成书写的普遍性。海德格尔在源初领会与平均领会之间作出了区分,后者不过是对前者的关闭、障碍、抵制或者固化,决断将穿透平均领会的封闭性而通达生存所特有的领会。领会给出又撤回、打开又关闭自身的情态,以及源初领会与平均领会的这种生存论关系,也同样适用于阅读的情形。如果我们在阅读中忽视两者的差异,或者执着于这种差异的打开,都可能使我们因为“常人”的“平均领会”而失去对作为源初的书写的占有,失去对作为生存者之专有和本己的存在的占有。正如我们所知的,阅读往往倚靠领会来获得一种“收获”或“收成”,但这种“收获”既是专有的,同时也是分有的,是对那源初的书写/文本之中的东西的共有和分享。
由此,南希重建了触感—书写—阅读的生存论关系。围绕着意义的生成,书写、身体、触感和阅读被重新建构为不可分割、四维一体的紧密关系。存在之为存在的本己性,此在作为独一多样的共在,作为共同生存的共同显现,只有在出离自身的外展、绽出、微偏、分享、共通之中,才是有意义的,也才能作为意义给出自身。在这个意义上,书写本质上正是对生存者的此在的外铭写,是对身体及其边界的触及和扩展。于是,书写不再可能只被理解为“语音的替补”“文字记录的工具”或“意指行为的表达媒介”,它必须获得自己“本己的”“专有的”语言。书写必然成为一种姿势、一种关系、一种身体的存在方式,归根结底就是人的生存方式。书写的目的也不只是传递或承载给定的意义,而是在意义—世界、身体—书写的关系中去描绘关系的无本质性,去超出任何本质主义的意指行为而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回响。意义的生成也不再是简单的能指—所指间的对应或滑动,而是在书写—身体—触感—阅读的四维关系结构中永不可遏地外展。在后结构主义的语境下,南希的书写思想重新揭示了意义的生成机制,呈现了对人的存在的哲学思考,极大深化了对书写的触感化、意义的世界化、人生在世与创世的多维化等问题的理解,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多元化写作和身体化创造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