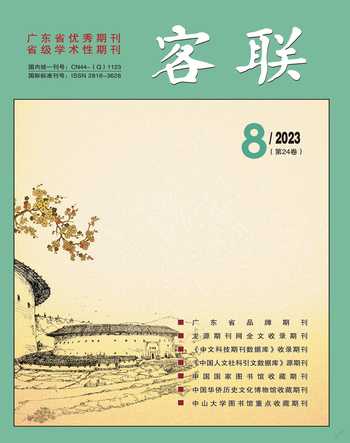垃圾场的隐形人——清洁工去污名化思考
2023-12-08赵泽文
赵泽文
摘 要:罗宾·内葛博士,一位纽约大学的人类研究和城市研究专业的学者,在一次参观中,对垃圾处理的现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毅然作出一个重大的决策:以一种以学者的视角和实践经历为基础的研究,积极投身于环保事业。10年间,当驾驶着能够发出“莫娜”声的垃圾车,勤奋地投身于垃圾桶旁的环卫行业时,他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将自己的身份从一个人类学家的角色改造成一个真正的环卫工。《捡废品的人类学家:纽约清洁工纪实》记录下他的辛勤付出。
关键词:清洁工;污名化;社会建构
一、引言
纽约,一座充满活力的都市,是全球经济、金融、交通、文化和媒体的重要枢纽,也是全球最大的商业区。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着800多万常住人口,拥有6000多英里的街道,每天生產出的垃圾数不胜数。为保持这个世界大都市的干净、整洁,需要每天定期清理两次,每天都要回收垃圾。而完成这些庞大工作的,是纽约市内不足1万名的清洁工。有些人对搬运车的无休止的运输感到厌恶,他们认为这些车辆上所装载的垃圾是垃圾的源头,而且他们也厌恶搬运车在街道上留下的凹坑,以及它们排放的污染气体,但很少有人知道,正是清洁工们每天坚持“让人皱起鼻子的强烈味道”,才让城市居民拥有了一个洁净的环境。
一次偶然的机会,罗宾带领学生们参观了纽约著名的弗莱斯科尔斯垃圾掩埋场。正是这座海洋一般的垃圾场,以及其中波动的“垃圾流”,让她开始对处理这些垃圾的人感兴趣,不由得思考起这样一些问题:“清洁工的现状如何?哪些人在从事这份职业?他们的工作是怎样的?”
随后,罗宾加入了纽约清洁工的行列。获取清洁工的信任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清洁工对人类学家并不了解,他们见惯了带着问题和笔记本而来的各种记者和其他采访者,他们往往蜻蜓点水地待上一天,最多一周,就打道回府。在清洁工眼中,罗宾大概也是走马观花者。只是这次,他们判断错了。当罗宾日复一日开着笨重的大卡车,遵守规则,默默忍受着语言的歧视和身体的伤痛后,她最终赢得了同伴的信任。“我第一次尝试用膝盖来更好地抬起某个很重的垃圾袋时,就被我的搭档立即制止了。‘别那么做,他严厉地说,‘你会被割伤。做你该做的,来把袋子弄上卡车,但绝不要让它碰到你。”从这一刻起,人类学家罗宾,放下了所有的学者“包袱”,成为一名清洁工。
在“清洁工”罗宾的回忆中,有几段特别清晰。第一,“收集垃圾一直被认为是脏的、辛苦的工作……很少有人知道它是最致命的职业之一”。在街道上回收垃圾的过程中,庞大的垃圾车经常会遮挡迎面车辆司机的视线,给回收者带来直接的伤害。而金属垃圾箱边缘锋利的切口、戳穿垃圾袋外露的玻璃瓶碎片、“拉直的挂衣钩、截断的易拉罐盖、裸露的钉子、锯齿状的管道”,还有皮下注射器的针头,加上各种未标明“危险”字样随意抛弃的粉末和液体,都时刻威胁着垃圾回收者的生命健康。第二,“当清洁工忙碌着处理日常琐事时,他们被大众有意识地无视了。”当人们晚上出去倒垃圾时,他们只是把这些垃圾丢弃或倾倒在固定的垃圾桶边,当他们第二天晚上重复同样的动作时,却从不会注意,这些垃圾桶是何时被清空的。老清洁工戏称:“他们认为垃圾仙人会把垃圾都变走。”如果我们的城市缺少水管工、电工,甚至警察,我们只会感觉一时的不方便。可我们不可一日缺少清洁工,即使暴风雨、大面积停电或有火灾、洪水发生,“清洁工像每天早上都会升起的太阳那样一定会来到垃圾场。”第三,你永远不知道清扫街面的工作有多复杂和繁重。当你在清晨的街道,感叹自己早起的敬业和行人的寥落时,你可能没注意,那些刚刚结束工作的清洁工和那些刚刚倒空的垃圾桶。
罗宾结合自己亲身见闻分析了清洁工的职业选择、清洁工社群文化(基于宗教、种族、职业和政治情感的社群组织),探讨了社会对环卫工人的污名化和系统性的边缘化以及清洁工群体对自我身份、外界质疑的应对机制和方法。
二、体验下的垃圾清洁工工作
曼哈顿拥12个街道,华尔街则坐落其间,而且每天都会接待数十辆垃圾清运车辆。55名劳动者、行政官员以及其他服务职能者,他们不断更新着自己的职业,而《捡垃圾的人类学家》“工作单位”则将他们的生活描绘得淋漓尽致。罗宾·内葛位于曼哈顿七区,这里拥挤的5个街道,使得这里变得异常拥挤。早晨,罗宾·内葛就必须提醒自己,准备好早早地赶赴纽约,去处理这里的垃圾。当他们踏入堆积如山的垃圾桶,就能嗅到由于蛆虫滋生的刺鼻异味,但这并未阻止罗宾·内葛继续努力,即使只能勉强把垃圾从桶里拖出,但也无法阻止这股令人难以抗拒的腐烂的气息。由于清洁工需要穿着50美分的针织棉布和一层蓝色或红色的橡胶,所以穿着一双手套显得尤其重要。首先,需要穿一双乳胶手套,然后再穿一双50美分的针织棉布手套,最后,再把一层橡胶贴到手背,以增加它的防护效果。当遭受暴风雨的洗礼时,他们面临一个棘手的挑战:既要穿上防潮的乳胶手套,又要防止湿气侵入;而且,由于棉质的手套不能抵抗潮湿的环境;另外,一旦脱掉,就不可能把垃圾袋的把手紧紧地握紧。穿着手套,清洁工们在无数次地挥舞着拳头,但由于施力过猛,注意力不集中,他们的脸部受到了严重的损伤,甚至留下了“熊猫眼”。然而,对于一些清洁工来说,清理垃圾只是一项工作,而不是最重要的任务,淘货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努力搜寻“宝贝”,这些“宝贝”指的是那些被认为是可以被重复利用、有效利用的资源。清洁工库尔兹认为,街道是“赠品”,工作是获取的手段,可以满足人的需求。清洁工不仅会捡走看起来有价值的物品,还会将它们经过精心的清理、打磨,然后将其送往旧物市场进行拍卖,以此来补贴家用。这不仅仅是他们的日常工作,更是“淘货”的一种乐趣,但它需要他们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为了更高效地完成任务,大多数清洁工都会选择清理他们熟悉的街道,因为他们能够准确地知晓垃圾车和扫帚在何时应该出现。然而,当遭遇恶劣的天气条件,比如设备老化,他们的清洁任务就会变得更加艰巨。
胡里奥·普拉特罗是曼哈顿地区的一位资深环卫工人,他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每天都要巡查扫帚车,并且要与“决战”“霸占”大街的快递员进行沟通,以确保街道的安全。当两者相遇时,没有人会因为距离太近而停下来。由于普拉特罗的工作进度受到影响,工人们无法正常清扫街道和处理垃圾。一旦发生口角,对方就会怒气冲冲地挥舞拳头,甚至准备发动激烈的战斗。在这种情况下,工头们必须为了保持“街道权力”的秩序而努力,因为他们必须遵守一套严格的环卫管理制度。除了手动记录工人的工资,工头还需要熟悉一页纸上的上百个正方形格子,以便更好地了解一个区域的一个垃圾装载员的轮班情况,从而使他们的地位更加稳固,成为环卫局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天早晨,一辆汽车缓慢地穿过一片垃圾堆,经过一辆垃圾回收车。司机停下车,满口唾沫,对清洁工说:“为什么不把这该死的卡车挪动开?”,这种行为显然是粗鲁的。在他看来,清洁工应该意识到,在清理街道的时候,不能占用其他车辆的道路。当司机被“你怎么不滚回你原来的地方,混蛋!”的质问所激怒时,他仍然在发泄自己的愤怒,但是,随着汽车喇叭的响起,司机不得不放弃原有的行为,而垃圾车的卸货工也平静地走向司机,并且温柔地对他说道:“你怎么不滚回你原来的地方,混蛋!”。罗宾·内葛在曼哈顿的街头,经常看到司机与清洁工发生激烈的争吵,导致交通拥堵。由于这种情况的频繁发生,清洁工的工作已经变得非常繁琐,甚至当罗宾·内葛发现,清洁工被无端地责骂时,他们也不会有任何愤怒的情绪,而是能够以一种平静的态度来面对这种骂声。
清洁工作虽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但却鲜为人知,研究视角也相对较为狭窄,而且其成果也未能得到广泛的宣传。正如社会学家韦恩·布雷克哈斯所指出的,清洁工作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而垃圾则是消费经济的产物,它们是人类不可或缺的资源,是一种残留物。“人类所不需要的东西”的清洁工作一直受到重视,但却往往被忽略。
三、清洁工污名从何而来
罗宾·内葛的清洁工人类学研究,也很罕见,经常被问“许多工种的工人都没有受到足够关注,为什么要关注清洁工呢?”清洁工的重要性并不突出,他们活在“污名”之中。例如,老师对学生说这样的话:“现在不努力学习,以后上街当清洁工捡垃圾,这是你唯一的出路。”罗宾·内葛研究清洁工的初衷就是让清洁工被更多人看见,不仅如此,还要是一种带有尊重的“看见”。罗宾·内葛说:“垃圾有一种顽固的本体论式的执拗。”生命会停止,文明会崩塌,但垃圾永在。她坚信一个朴素的价值观,那就是如果一个城市缺少垃圾管理方案,那么这个城市几乎无法繁荣;如果没有清洁工,城市无法宜居,无数人只能忍受街道垃圾残余,还可能死于各种疾病;如果这些空间不被清理出来,那么社会便无法持续消费。尤利克斯在举办“清洁污名”的行为艺术之前曾办过一个名为“触摸环卫工人”的展,她跟随环卫工人去每个街区,看了每一个清洁工具摆放的位置,走遍了每个角落。在旅途中,她遇到了数以千计的清洁工,她热情地与他们握手,并对“谢谢你让纽约保持美丽。”说:“如果你运气好,你可以不用担心警察和消防员,但是你每天都需要环卫工的帮助。”
在国家主义话语下,中国的清洁工通常被表述为“城市的啄木鸟”“无私奉献”“辛勤工作”,他们也偶尔会登报、见诸媒体。但相比纽约市的清洁工们颇具吸引力的薪资待遇、强有力的工会保障之外,很难再想象他们的生活境遇,中国庞大的城市系统为了保持城市清洁或许有一套更加复杂、更加官僚的管理系统,才能维持其极高的效率和实际效果,这是否又是建立在对环卫群体长期以来的无视、压榨之上的呢?
戈夫曼《生活中的个体表现》中提出的“污名(stigma)一词,指的是个体被赋予一种“受损的身分”的形式,它既可以表达个体的负面情绪,也可以暗示个体的身分、价值观、行动方向等,从而给个体带来一种心理上的压力,从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戈夫曼强调,一些污名源自人们对事物本质和形式上的偏好,这些偏好和形式往往源自人们对事物本身的误解、无意识、固定观念,以及出自一定意图。也就是说,一些污名本身根本就没有,只是由人们自身和外界环境所塑造出来。向下比较理论表明,人通过与不如自己的人进行对比和参考,能确保自身的处境安全,此类贬抑他人的倾向能够让个体获得幸福感。这种自我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需要会使公众刻意"挑选"出不幸的人,迫使成为其施加污名的客体,以满足他们的心理平衡。Link(2001)认为社会公众会选择通过人"贴标签"以及施加污名而提升个人自尊水平。
从社会建构视角理解社会问题,关注的是我们如何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建构的对社会问题的定义和理解。这也就是说,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互动过程中创造了不同形式的知识(如社会科学知识等)去探索和解决社会问题,而这些知识在慢慢巩固和散播的情况下,逐渐成为一般人所经验到的“客观现实”,然而,这些“客观现实”又反过来塑造和制约了人的主体性。另外,克拉克和科克兰也提出从社会建构的视角理解社会问题,将关注点放在引起社会问题的社会条件之上,是为现状的改变、改革和推进提供可能性。对于引起社会问题的某些特性进行重新安排,从而解决社会问题,这是社会建构主义理解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也就是说,社会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它表达了其他建构的可能性,也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之一。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清洁工身份建构的动态逻辑如下:首先由权力性话语控制个体的思想与行动,话语在对清洁工进行表达时,往往隐含着消极价值,将差异突出,忽视了在城市中的贡献与优势,形成了清洁工身份建构的维形,在健全者权力话语的压制下,人们按照统一的真理知识认识世界,对清洁工身份产生相对统一的认知,受社会建构论的影响,根据经验化的话语认识,转化成社会性的被排斥和自我排斥的身份认同。最后通过社会体制和社会制度、话语和排斥体系逐新合理化、合法化,角色类型的建构与行动的制度化相关,制度通过角色被镶嵌至个体经验中,从而固化了清洁工的身份建构。通过角色,个体被引入特定的社会客体化知识领域,这些知识不仅是认知层面的,还包括规范、价值、情感层面的知识。在这种动态逻辑中,这三者:话语体系、身份认同还是制度区隔,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并且,这种身份的建构过程往往是循环叠加的,这与社会的相关性和互动性有关,对身份的构建,往往是多个属性结合的结果。
四、结语
纽约艺术家收集了上千个关于清洁工的偏见和诋毁,把它们写在了曼哈顿艺术馆的幕墙上。这些污名最终由190位来自各界的官员、艺术家、教授、银行家、运动员一同洗去。玻璃幕墙上的污名就此洗去,人们心头关于清洁工的污名是否也能就此洗去?一切尚不得而知。垃圾是繁荣消费型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环卫工人的及时处理和清理,我们基于消费的经济发展将无法得到有效推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和知识作为社会中共知的客观化事物,能够给我们的主观体验赋予意义并且使它更为持续而真实。语言可被定义为声音的符号系统,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符号系统,符号和符号系统能超越“此时此地”的主观意向表达,并使其得到有效的客体化。当我们尝试重新审视并解构清洁工的污名化身份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一个有自尊、有权利的个体,我们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实现个人价值。然而,从社会层面来看,话语体系、社会排斥以及制度建构等因素,都加剧了清洁工的污名化身份,并且形成了一种歧视性的社会倾向。通过广泛的宣传、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政策支持,建立一种充满尊重、平等和多样性的社会环境,以激发清洁工的潜力,促进他们的身份认同和自我价值的提升。
参考文献:
[1]Link B. G, Phelan J. C. Conceptualizing stigma.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1, 27: 363-385.
[2]高艺多,文军.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社会工作理论取向的比较与反思[J].社会科学文摘,2020(07):62-64.
[3]周双磊.留守儿童:社会工作视域下去污名化的重要主体[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02):55-59.
[4]于淼.探索内地残疾青年的社会排斥经验: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视角[J].
[5]关文军,颜廷睿,邓猛.社会建构论视阈下残疾污名的形成及消解[J].中国特殊教育,2017,No.208(10):12-18.
[6]戈夫曼.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6-18.
[7]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李国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8]唐薇,李红艳.污名抑或正名?——基于激活-应用框架的网络“污名化”现象研究[J].教育传媒研究,2021(06):8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