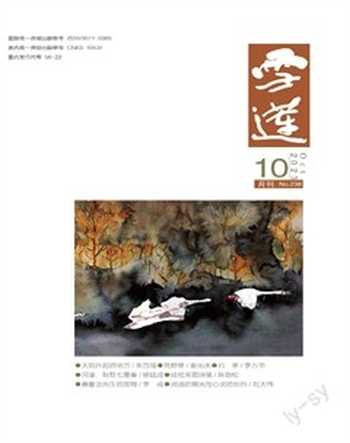穿过山谷的风
2023-12-03贾文清
【作者简介】贾文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八期高研班学员。出版有小说集《银簪子》、散文集《老西宁记忆》《望穿天路》。作品曾入选《21世纪年度散文选》《中国企业职工文化大系》等。作品散见于《文艺报》《儿童文学》《天涯》《飞天》《散文选刊》《北方文学》《时代文学》等。
1
山谷的风呼啸而过,掀掉了他的毡帽。毡帽在山谷中随风滚动,他在后面挥舞着双手奋力追赶,想撵上越滚越快的毡帽。
他追着风和毡帽跑出了山谷,坐在一面缓坡台上休息。抬眼四望,周边群山环绕。一条更大的山谷绵延伸向远方。对面的山头上,矗立着一座别样的峨堡。除了经幡,还有煨桑台、松柏枝。在翠绿的松柏枝条间,穿插着几支五彩神箭,这和他家乡的风马旗大不一样。他知道,他已经来到了另一个地方。
有一对在山坡地里收割庄稼的夫妻正在准备午饭。他们的午饭很简单,在地边拢起一堆火,把收割下来的麦穗放在火中烤熟,搓去麦衣,留在手里的麦粒儿就是他们的午饭了。就着黑陶砂瓶里的茶水,就是一顿美味的午餐。
他看见了半山坡的烟火,循着麦衣草的香味赶了过去。他衣衫褴褛,饥肠辘辘,他太需要一些食物来安慰他焦灼的肠胃。
夫妇俩接待了他,他们把烤熟的麦穗放在他的毡帽里。又提起砂瓶,把茶水斟入黑瓷碗中端给他。
吃一捧甜糯可口的麦粒儿,再喝一碗清凉甘冽的茶水,他佝偻着的腰身挺直了,脸上也恢复了神采,眼眸似一潭深水。他问好心的夫妻。这是什么地方?丈夫镰刀指向远方,这是种庄稼的地方。
他明白了,他从放牛牧羊的地方来到种植庄稼的地方。他离心中的圣地不远了。他又问,大哥,西王母娘娘的仙山在什么地方?夫妇俩同时用镰刀指向远方:在那里,那里是西王母的仙居。不过,我们从来没见过西王母娘娘,我们只见过一位娘娘。丈夫端详着手中的镰刀:她教给我们种庄稼,收庄稼。这把镰刀,也是她留给我们的。他很惊奇:那么,这位娘娘是从哪里來的?叫什么名字?夫妇俩同时说,大唐的文成公主娘娘啊,从长安来的。
2
那时候,他天天跟随着羊群放牧。他的家乡在一面浩瀚无垠的巨大湖泊边上。因了湖水的滋润,这里的牧草长得分外茂盛。他把牛羊赶进像小森林一样密不透风的草丛中,任它们自由自在地吃草觅食。他自己喜欢跑到湖边,看湖水一漾一漾地冲上来,漫过他的脚面,再冲到湖边的草丛中去。随着湖水一起冲过来的,是透明的小银鱼和晶莹的小石子儿。石子停落在湖岸边上,小银鱼则穿过草丛缝隙,灵活地游到牧草深处。游过一段时间,大约觉得牧草不是它的家园,又掉过头来游回湖里。湖边的牧草和野花浸润在水中,像慈祥的母亲一样,任由调皮的小鱼儿在它的裙裾间穿来穿去。
他喜欢看这些灵巧的小鱼儿在牧草丛中快速地游动,不知道它们忙忙碌碌是为了什么。就像他每天早晨赶着羊群出来,天黑后,又赶着羊群回家。一天的时间除了蹲在湖边看小鱼游走,就是躺在山坡,看天上的白云飘荡。偶尔,会有一只苍鹰飞入眼中,在遥远的天幕中打一个旋儿,震一下翅膀,又会飞得无影无踪。他觉得自己还不如一只鹰自由。雄鹰飞得那么高,一定见过很多的世面。而他自己,只守着湖边的一片天地,从来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当然,湖泊的美景绝世惊艳。都说这里是西王母的瑶池,每年夏天,西王母娘娘率领她众多的百官大臣、宫女彩娥浩浩荡荡地来到瑶池边上,扎下帐篷,筑起篱栅,在湖边草原上排开宴席,斟满琼浆玉液,与草原牧民一同欢乐,开怀畅饮,载歌载舞,每个桌子上摆着十二道美味佳肴,被称之为十二筵宴。
十二筵宴只是一个美妙的传说。他没有见过西王母娘娘,更没有品尝过十二筵宴。他听人们说过,瑶池只是西王母娘娘夏日里纳凉的地方,更多的时候,西王母娘娘住在一座叫宗家沟的大山里,那里有她的宫殿、仙阁、点将台,还有能召集所有人开会的巨大石室。那里的人有着西王母娘娘的庇护,吃得好,穿得好,更重要的是,那里的人经常跟着西王母娘娘四处巡游,见过很多世面,看见过很多不同的风景。
晚上,他躺在牛毛帐篷里,透过帐顶的缝隙看天幕。草原上的天和地离得真近啊,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抓一把像碎金子一样闪闪烁烁的星星。他也伸手抓了几次,只是,他没有抓着星星,只抓住了一些黑夜中的雾气,手上湿漉漉的。他把手又伸向身边的牛粪火,牛粪火是这座帐篷里的灵魂,他们一家大小的生活起居都围绕着帐篷中间的这团火光来维持。即便在暗夜里,牛粪火的光焰不那么强烈,它依然发出红红的火光,照亮着帐篷,把丝丝缕缕的温暖传递给围绕着它的一家大小。
他叹了一口气,重新躺回到羊皮褥子上。羊皮褥子很柔软,牛粪火很温暖,他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在这片草原上生活一辈子。可是,他还是想出去,外面的世界,就像天幕上的星星一闪一闪地诱惑着他。西王母娘娘的十二筵宴在瑶池边上一年只摆一次,那么,在她的领地宗家沟,恐怕要天天摆出来吧。他掀开帐篷的一角,偷偷走了出来。
听说西王母娘娘的仙山在瑶池的东边,他不知道东边在哪里,不过,聪明的他很快想了一个办法。他发现,注入瑶池的水都是从高高的雪山上面流淌下来,他听人们说起,他们生活的这片地方,西边高东边低,河水都是从高处往低处流。那么,只要沿着没有河流的方向一直走,不就找到东面了吗?他避开所有的河流,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走。不过,让他疑惑的是,还有一条河流在他的脚边蜿蜒流淌,这条河最终也是注入了瑶池,只是,他不知道它的源头在哪里,都说河水从西往东流。难道是自己走错方向了吗,他迷糊了。向沿途的行人打听,那些戴着高帽子,打马飞奔的人告诉他。你没有走错,这条河是从东往西流的,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倒淌河。他更加疑惑了,河水为什么要倒着淌呢,它的源头在哪里?人们告诉他,没有源头,它是文成公主的眼泪流淌而成的。
3
他茫然环顾四周。他要去寻找西王母娘娘,怎么这里还有一个文成公主娘娘?西王母娘娘能在瑶池边上大开宴席,载歌载舞,文成公主娘娘的眼泪却流成了河,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人间所有的梦想和希望都很美好,西王母娘娘是这片土地上所有人们心中的女神。女神当然很美丽,很慈祥,集所有的优点于一身,受到一方百姓的膜拜和敬仰。那么,文成公主娘娘呢,她是大唐的公主,那年才十六岁。十六岁的她肩负着巩固中央王朝安定和边疆和平统一的重大使命,作为和亲使者,她要嫁给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做妻子。她身穿彩绣嫁衣,怀抱日月宝镜,率领众多的宫女、工匠、商人、绘画师、医官和百行百业的人才,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踏上了和亲之路。
浩浩荡荡的队伍走过了高山,走过了平原,跨过了数不尽的大江大河,走了整整一年之后,走到了一座狭长的山谷中间,公主抬眼四望,山上也有一些树木,但比之家乡草木繁盛的景象,这里显然寥落许多。山谷的风呼啸而过,吹得公主骑乘的马匹嘶鸣长啸。侍卫急忙勒紧马头,宫女给公主披上了厚厚的毡袍,大队人马暂且走到一座侧峰的山间躲避风寒。护送公主进藏的皇叔李道宗,询问吐蕃来的迎亲大使禄东赞:这里是什么地方?禄东赞指着山坡上迎风朝阳的野花,和野花間游走觅食的羊群说,这里是丹噶尔。又用马鞭指向远方的一座山峦说:翻过这座山,就到了。李道宗说,既然快到了,那就在此休整一段时日吧,让公主歇息歇息,调养一下身体。
这片山谷的台地平坦又宽阔,蓝莹莹的马莲花,金灿灿的蒲公英花,还有白色毛茸茸的雪绒花,像一面巨大的鲜花地毯。公主的彩帐扎在这里,宫女们兴高采烈。她们舀起草滩边亮晶晶的山泉水,洗去一路的风尘,再采一两朵盛开的鲜花簪在鬓边。还有一位巧手的宫女,用桦树皮缝制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小花瓶,采来各种鲜艳的野花,注上清水,摆放在公主的彩帐里。
山谷中有一条河,也是从遥远的雪山上流淌下来的雪水,一路上不断汇合兼并别的小河,流淌到这里,它已经是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了。河床中有许多不知什么年代滚落的大石头。河水撞击在石头上,飞溅起巨大的浪花,发出雷鸣般的声音。河水和岩石就像两个仇敌,只要相遇,必定会掀起一场生死搏斗。最终,河水收拾起撞碎的浪花,重振旗鼓,以锐不可挡的气势冲向下一个岩石。撞出更大的浪花。
这条河轰轰隆隆地往前奔流,声势浩大,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叫响河。
每天,都有不少本地的牧羊女来到河边背水,她们远远地望着公主的彩帐,看见衣袂翩跹、笑靥如花的宫娥彩女们进进出出。知道她们是大唐来的,却没有一个人敢近前搭话。
终于,有一个勇敢的牧羊女走进了公主的彩帐,她端详着公主帐内华丽的陈设,禁不住啧啧赞叹。彩帐内唯一不华丽的,就是那个用桦树皮做的四方形花瓶和几枝野花,但却是整个帐篷中最明艳的。她眼前一亮:哈,树皮也可以做花瓶啊,我们都是用牛皮做的。公主也很好奇:牛皮也可以做花瓶吗,怎么做?牧羊女解下挂在腰间的小皮囊:就是这样。
这是一只用牦牛皮缝制的圆形皮筒,姑娘们随时佩戴在身上。给牛挤奶时,它就是装牛奶的奶桶,到河边背水时,它就是舀取河水的水瓢。皮筒是她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件儿。公主手捧着这只小小的皮筒,禁不住赞叹:做得多精致啊,想不到牛皮还有这样的用处。她又说:我想,既然是姑娘们用的,就应该绣上花朵,那才好看呢。公主穿针引线,在这只小小的牛皮筒上绣了一朵玲珑别致的小花。牧羊女眼睛都亮了,她要过公主手中的针线,在小花朵的根部又绣了两片绿叶,使小花朵显得更加饱满生动。
从此,这个地方就有了一种古老又神奇的工艺——丹噶尔皮绣。相传,那是唐朝的文成公主流传下来的。
文成公主流传给丹噶尔的,当然不止是在羊皮牛皮上绣花,她还把大量的工匠艺人派出去,教当地人耕种、贸易、手工制造等等五行八作的手艺。山谷的风一年四季呼啸着,响河的水日夜不停咆哮流淌,它们就像两匹奔腾跳跃的骏马,带给了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人以力量,也使他们本就贫瘠的生活经受着种种磨砺。而文成公主就像慈祥的度母,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在工匠们的指导下,他们学会了冶铁、锻造,用打制出来的农具耕种庄稼,效率比以往提高了很多;他们学会了编织,把牛毛和羊毛捻成线,织出又厚实又保暖的褐子,牛毛褐子做帐篷,羊毛褐子做衣服,还可以做口袋、被褥、毯子等生活用品;他们学会了经商,他们从中原一带过来的商人手中换取茶叶、瓷器、丝织品,从吐蕃和西域过来的牧人手中换取羊毛、药材和马匹,再互相转卖,从中赚取差价。自从文成公主走过后,这条漫长的唐蕃古道同时也变成了经商之道,商业贸易经久不衰,最终,成就了丹噶尔古城。
4
沿着倒淌河逆流而行,他一直往东走。走过倒淌河,便进入一条狭长的山谷。两边是绵延不断,一眼望不到头的山峰。他贴着山根在大风中踽踽而行,不知道这条蜿蜒曲折的土路上,曾经走过文成公主的辚辚车马,也走过各路客商的悠悠驼队。他一心想找到传说中的西王母娘娘王宫。当他走到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跟前,仰望山顶上的皑皑白雪时,一位路过的牧羊人告诉他,这座山叫索日格山,意思就是“大家的妈妈”。他心里怦然一动,大家的妈妈,就是西王母啊,难道已经走到了西王母娘娘的领地了吗?听说那里鲜花盛开,彩蝶飞舞,绿茸茸的草地上有清泉在淙淙流淌。就像他居住的瑶池边上一样。可是,这座山峰陡峭险峻,山顶的白雪终年不化,就像草原上所有的老阿尼头上的白发一样。他问牧羊人:走过索日格山,宗家沟不远了吧?牧羊人挥鞭一指。还远得没信儿呢,你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下走,大约十天的路程,就会看见一座石堡城。你再向守城的兵士打听,他们就会告诉你的。
他面向索日格山跪了下来,大家的妈妈,也是我的妈妈,愿您的慈爱和智慧护佑我。
十天的路程,他走了七天,就看见那座高大巍峨的石堡城了。石堡城依山而建,房屋和碉楼全部用大石块垒就。有的建在山底下,有的建在半山腰上,而绝大部分军事建筑,则在高高的山顶上。山顶上的房屋隐藏在云雾里,若隐若现,只能看见屋檐的轮廓。
城堡大门建在山底下,上书三个大字:铁仞城。门口有身穿铠甲、执戈站立的士兵。他对着士兵弯腰行礼:请问壮士,这里往宗家沟怎么走?那兵士却把眼一瞪:闪开,我不是贩夫走卒。
他只好闪开,转身接着往东走。大约西王母娘娘看他心诚,没有让他失望太久。走不多远,他便看见了在半山腰上劳作的农人夫妻,他用他们的麦穗儿填饱了肚子,同时也打听到了西王母娘娘居住的地方。
他谢过这对善良的夫妻,重整衣服,把破毡帽扣在头上,接着往东北方走去。
当他走到响河边上时,他被那河水的气势镇住了,他战战兢兢地站立在河畔高处看,响河如万马奔腾呼啸着向前奔流,河水撞击在大石头上,溅起的水花在河的上方形成一道美丽的彩虹。水花在彩虹间飞溅,如同彩虹吐露的珍珠。
忽然,他看见河下游水流湍急的地方,有一位姑娘正在往大木桶里舀水。河水那么急,木桶那么大,而姑娘,却是那么娇小,他从河畔的高地上跳下来,在河间石头上跳跃,朝那背水姑娘奔去。
他从姑娘的背上卸下背水桶,挪到自己身上。走过河滩地,走过土路,走到一片绿草茵茵的缓坡地带。姑娘说:靠着石头休息一下吧,我家不远了。她问姑娘的家在哪里?这位满头小辫的少女指着一条沟口说:就在这条沟里。他问这里是宗家沟吗,姑娘睁大了眼睛,你怎么知道的?
姑娘的家就在溝口上,孤零零的一座房子,门口有一小片菜地,窗下拴着几只羊,一只大狗在房后咆哮蹦跳。姑娘跑过去抱住狗,在它头上摩挲了摩挲,狗一下就安静了。他把大木桶背进房里,把屋里的阿妈吓了一跳,女儿出去背水,怎么变成个男人回来了?她停下打酥油的木棍,在前襟上抹着手,喊:梅朵!梅朵!
梅朵笑语晏晏地走进来了。
由梅朵的父母做主,他和梅朵结为夫妻,他成为这家的上门女婿。他和梅朵放羊、打柴、种庄稼。梅朵的父亲闲暇时最喜欢做的事情是捻毛线,他常常坐在房前的太阳地里,一手转动线砣,一手把柔软的羊毛捋起来。那像云朵一样洁白轻盈的羊毛,在线砣的旋转中,就会变成一根粗细均匀的毛线。梅朵的阿爸再把毛线织成褐子,给一家大小缝衣服。他问阿爸,这手艺是从哪里学来的,阿爸说,文成公主娘娘教给我们的。
5
文成公主娘娘率领着她的大队人马继续往前走。
天气越来越寒冷,山谷的风凄厉地吹过,像密集的钢针钻透衣服,刺痛着皮肉。好多人经受不住这风寒,生病了,倒下了。公主只好把他们留在当地,等他们病好了再说。剩下的人马跟着公主缓慢前行。
这条漫长的峡谷真长啊,文成公主的和亲队伍春天来到这里,夏天在谷地的绿草坡上扎下彩帐,休息了一段时间,用响河的水洗去一路风尘,用漫山遍野的鲜花愉悦疲惫的身心。现在,给公主缝制了桦树皮花瓶的宫女也感染了风寒,被留在了一户牧民家中。宫女流着泪说,她养好了病,还要跟随公主去吐蕃。但公主知道,此生她们大概不会再见面了。路途遥远,她追随不上他们的脚步。公主说,你就在此地生活吧,你有刺绣的手艺,你领着当地的姑娘们学起来,将来也许就是一样谋生的手艺。
很快,秋天就到了,寒风愈加猛烈,夹杂着星星点点的雪花。河水隐去了,曾经绿油油的草地也变得枯黄了。公主询问何时能走出这条峡谷,走在前面的管家打马返回,躬身回答:再不远了,等走到前面那座山下,我们就算走出峡谷了。
公主搭眼一望,前面的山还是很遥远,不过,总算能看见一点影像了。远远望去,像一朵盛开在蓝天白云下的红色花朵。管家告诉公主,前面的那座山在众山丛中特别显眼,是红色的,故而叫赤岭。赤岭也是一道重要的地理标志,回首东山尽良田,西望茫茫荒草滩。翻过它,就真的到了。
终于走出了长长的丹噶尔峡谷,来到赤岭脚下。仰望眼前红色的土石山,山并不是很高,却似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暗暗涌动,仿佛无形的手拉扯住每个人的衣襟,仿佛阻止他们攀登这座标志性的山峰。
必须要攀登上去,已经有松赞干布的使者前来送信,他们的赞普和迎亲队伍早已出发,走到了扎陵湖畔,在那里扎下彩帐,准备迎接公主。路途遥远,路上不能再耽搁了,文成公主率领大队人马,踏上了翻越赤岭的盘旋山路。
寒风飒飒,雪花扑打在脸上,是一种凛冽的寒冷,长长的队伍像蚂蚁一样一点一点地往山上蠕动。终于,他们走到山头了。文成公主勒住缰绳,抖落身上的雪花,举目四望,天地一片苍茫,只有漫天雪花在盘旋飞舞,四霭空谷中,回响着凄厉的风声。
护送公主的人马还在半山腰上回旋,贴身侍卫和宫女为公主奉上热茶和点心,请公主歇息一下,养精蓄锐。翻过赤岭,就到牧区了。公主骑在马上,遥望自己的行进队伍在风雪中艰难前行,禁不住珠泪滚滚。想起出发前的那个夜晚,月亮皎洁,丹桂飘香,他的父皇和母后摆酒为她送行。并把一面镜子送给她,说,这是神奇的日月宝镜。此去逻些,长路迢迢,如果想家了,想父母了,就拿出镜子照一照,镜子里会显现出家乡的风物人情和父母的身影面容。可是,浩大的送亲队伍没有宝镜,他们思念自己的家乡父母,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流泪。一年多了,他们跟着自己,从长安出发,一路奔波,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他们和自己一样,也是半大的孩子,他们也会思念父母,想念家乡,他们也会生病、难受,有谁知道他们从长安走到拉萨这一路的艰辛。公主想起留在丹噶尔峡谷中的那位贴身侍女,她是那么活泼,那么美丽,娇俏可人,却没能陪着她走完进藏的路程。公主禁不住大放悲声。彼时大唐明月夜,今朝塞外风卷雪。走上赤岭,就是进入汉藏地区的分界线了。从此,家乡是回不去了,故乡父老亲人们也与自己山高水长、永不相见了。公主哭得越发悲痛,眼泪滑过面颊滚向衣襟,和落在衣襟上的雪一同化为水滴,顺着赤岭的山坡,淅淅沥沥地往下流淌。
正在半山腰的泥泞中奋力攀爬的宫女、随从们看见公主在山顶上失声痛哭。看见漫天雪花飞舞盘旋,遮住了前行的路途,他们也禁不住大哭起来。在苍茫的赤岭山巅,痛哭声惊天动地,泪水和着赤岭的红土咕咕流淌,流成了一条河。这条河聚集着一千多年前这支队伍中所有的艰辛、悲伤和劳苦,没有往东传送给他们的父母,而是倔强地往西流淌,把所有的痛苦就此化解。
当所有的队伍都登上山顶时,雪停了,太阳出来了,蓝天悠悠,白云飘荡。站在山顶上极目四望,东边是丹噶尔大峡谷,峡谷中有村庄,有良田,鸡犬嘶鸣,炊烟袅袅。西边已是另一片天地,四野荒草漫漫,牛羊行走期间。偶尔,会有长长的风从草尖上掠过,漫山遍野的草便会随风起舞。文成公主擦干眼泪,准备启程了。作为和亲公主,此时她已经算是来到了夫家的地界。回眸一望,再回长安已是不可能了,父母此生也难见面。既然我的使命是和亲,那么,就将我的使命继续完成。公主从怀中掏出日月宝镜,她没有照家乡,也没有照自己。她双手举起镜子,把日月宝镜摔在一块石崖上。
镜子裂成了两半,赤岭也从此分开,一半变成了日岭,另一半变成了月岭。文成公主整顿鞍马,告别日岭和月岭,走上了漫漫草原,到扎陵湖畔和她的夫君相会了。
6
他和梅朵生活在一起,很幸福,老阿爸天天转动着线砣捻毛线,给他们一家大小缝衣服、做皮靴。老阿妈捡拾牛粪,烧茶烙饼,负责一家人的饭食。他和梅朵一个种地,一个放羊,吃的用的都有了。后来,他们的孩子陆续出生了,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只要不夭折,活下来的都是老天赐予他们的孩子。
只是,他还是有一些心愿未尽。他当年离开家乡,就是为了寻找西王母娘娘,品尝娘娘的十二筵宴。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吃过锅庄席、圈圈席、上马席、下马席以及各种形式的宴席,唯独没有吃过西王母娘娘的十二筵宴。他在放牧的时候走过宗家沟的每一面草坡;他在捡拾烧柴时钻进过宗家沟的每一片树林;他在采摘药材时攀登过宗家沟的每一道石山,宗家沟已经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像熟悉自己的手掌纹一样,熟悉这座山谷里的每一道山梁沟壑。
自然,他也熟悉这座山谷中每一个天然形成的巨大石室。传说这些石室是西王母娘娘的会客厅、议事厅,还有与众神饮宴的宴会厅。他常常想,西王母娘娘的宴会厅里摆的大约就是十二筵宴吧。
每天,他把羊群赶到山的向阳处,当羊群在山坡上散开自由觅食,他自己则拎着抛儿绳,在各个石洞间穿梭。他期望能找见西王母娘娘的蛛丝马迹,可是他什么都找不见。这些天然形成的石洞,有的幽深,有的险峻,有的则是石洞连着石洞,宛如迷宫一样。人们给这些石洞赋予了特别美好的意义,民间流传着它们的传说和故事。只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石洞,沉默而孤寂地隐藏在宗家沟的各个山坡上。
久而久之,他不再寻找西王母娘娘的仙踪了,他把石室当做羊圈,天黑时把羊群赶进石洞里,再用一块大石板堵住洞口,防止狼侵入。他自己则甩着抛儿,哼着小曲儿回家。顺路采一把野山葱,让梅朵做一锅面片。出锅时,把炝好的野葱花搅进去,顿时,面片就有了灵魂。那滋味儿,他想,王母娘娘的十二筵宴也不过如此吧。
他的孩子们都长大了,有的跟着他放羊,有的跟着梅朵种庄稼,有的跟着南来北往的商人学做买卖。还有一个孩子,从小听惯了他讲西王母娘娘的十二筵宴,跟着一位山西来的厨师学手艺。在学会了肉八盘、海八盘的制作工艺后,他根据丹噶尔地区汉藏结合的饮食特点,最终研制出更符合当地人口味,又经济实惠的十大碗。十大碗是宴席菜,用料、烹饪都十分讲究,他想,吃不到天上西王母娘娘的十二筵宴,能吃到人间的十大碗,也算不错。
7
我到宗家沟前的尕庄村采访的时候,村民老董正在出嫁女儿,摆的宴席就是十大碗。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自然而然的,我们到老董家吃了他姑娘的上马席。
老董有一儿一女,儿子跟随村庄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目前在格尔木钾肥厂。据说收入还不错。女儿大学毕业,自己找了喜欢的工作,又找到了心仪的爱人,可谓幸福美满。老董夫妇以种蒜苗为生,收入也相当不错。
我很惊讶,这里的土地不应该种庄稼吗?怎么会种青蒜?而且你们守在宗家沟旅游风景区的门口,怎么也得挣点旅游的钱呐。
老董是个朴实憨厚的农民,話不多,问一句答一句。老董的媳妇儿却是个热情开朗的人,快人快语。她回答了我所有的疑问。她说,以前我们可不就只种点庄稼吗。地薄,收成也不好,下点雨还动不动发大水,山里的洪水把我们淹了好几次了。幸亏党的富民政策好,前几年把我们从沟里搬迁到沟口,又给我们盖了房子,日子才算好过起来。
我问以前在沟里的时候叫什么村庄?是不是叫宗家沟村?老董说:不是。也叫尕庄村。我们这个庄子小,人也少,现在才六十多户人家。老董媳妇儿抢着说:好着呢,我们的老祖宗一个人的时候是怎么过的?我问你们的老祖先是谁?老董媳妇儿眨着眼睛说:我听老汉们讲过,好像是从青海湖边上过来的。到我们这里后,招成上门女婿,以后,就留下了这一庄子的人。老董说:也不光是一个招女婿,还有文成公主进藏时留下的宫女,还有铁仞城守城的兵士。丹噶尔的姑娘长得漂亮,可能就是宫女的后代吧。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种蒜苗的呢。老董告诉我,大约十多年前吧,也是一个从青海湖边上来的人,他可能见过别人种蒜苗,挣了钱,他自己也学会了这项技术,他便领着尕庄村的人种蒜苗。刚开始没人相信,他就自己租地种。只一年,蒜苗卖了个好价钱。这一下,人们都纷纷在自家地里种起了蒜苗。也可能是这里的土质适宜蒜苗生长,种出来的青蒜品相好,滋味足,而且还是纯绿色无污染食品,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效应,销路也打开了,外地客商都知道尕庄村的蒜苗好。
这一种就种了十多年。现在尕庄村家家户户都在种蒜苗。蒜苗产量高,一亩地能出产一万多斤,按一斤一块多钱计算,每年每亩地的青蒜收入就在一万多。家里只要种两亩地的蒜苗,收入就能达到将近三万。
但是,种蒜苗有个明显的缺陷,就是蒜苗根部粗壮,拔出来时带的土多,土壤肥力消失得快,很容易板结。因而,种两年蒜苗,就要种一年庄稼,倒换着种,给土地一年的休养恢复时间。
老董说,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好在县上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正在推广蕨麻种植。尕庄村也试种了一些,如果产量高,价格好的话,我们这里就可能不再种蒜苗,改种蕨麻了。
8
老董媳妇儿是附近大茶石浪村的姑娘,名字叫英生卓玛。不过,她已不穿藏族人的服装,也不戴农村人喜欢的棉线头巾,她更像是一位时髦的城市妇女,挽着蓬松的发髻,穿一身运动衫裤,显得精明干练。只有脖子上的珊瑚项链,昭示着她是日月山下的藏族人。像所有的湟源美女一样,英生卓玛有一双毛绒绒的大眼睛,顾盼生辉。她笑吟吟地请我们到她家做客,说专门准备了风干牦牛肉,好歹过去吃上一口。
这一阵,她忙得脚不点地。打发姑娘出嫁是一件大事,她既按照藏族的传统礼仪给女儿准备了嫁妆,用十大碗宴请了所有的亲朋好友。又按照当代年轻人的风格,到县城饭店参加女儿的婚礼。女儿、女婿穿婚纱西服,她和老董也是西装革履,妆容明艳,在婚礼现场摆足了丈母娘的款儿。
她家大门前有两棵高高的白杨树,每棵树上都盘着一只喜鹊窝,每天都能听到喜鹊喳喳喳的叫声。她和老董甚至踩着梯子爬上杨树,把喜鹊窝转了个方向,让窝口朝着自家大门。这样,喜鹊每天就正对着他家叫了。前一阵子,喜鹊天天喳喳喳地叫个不停,是因为她家在办喜事。这两天,喜鹊依然喳喳喳地叫个不停,英生卓玛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贵客到了。她认为,我们就是她家的贵客,她不但请我们吃了女儿的上马席,还准备下风干牦牛肉,请我们过去品尝这种古老的藏族传统美食。
她家院子里堆着一些大蒜,是卖蒜种的老板提供给他们的。这些年,尕庄村种蒜苗已经形成规模,外地的供货商和收购商主动联系他们,他们不用考虑销路,而且还能卖个好价钱。即便这样,老董夫妻还在商议,在种蒜苗的间歇,准备上山挖虫草。今年虫草价格好,挖一个月,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呢。
我很佩服他俩的勤劳朴实和精明能干。英生卓玛说:人就像种子一样,风刮到哪里,就在哪里落地生根。比如你们生在了城市,日子就过得好一些。我们生在了这里,日子就苦一些。只是,这个苦是地方苦,人心里不苦。人只要有盘算,肯吃苦,总能过上好日子的。她告诉我,她的祖上是一位出色的工匠,在东科寺做挂面,出售给牧民。她说她的祖上买卖做得非常大。“数挂面跳蹦蹦,钱儿成墩墩”说的就是当年做挂面生意的火爆。
后来,由于種种原因,挂面生意败落了,他们没有气馁,也没有抱怨,转而就寻找另外一个谋生的手段。英生卓玛说,她小时候听爷爷奶奶们常常说起的一句话是,文成公主娘娘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能工巧匠和精巧手艺,我们还能找不到生活的出路吗?有一首儿歌,千百年来一直传唱:蛋儿蛋儿光光,里头坐着个娘娘。娘娘领的尕狗儿,咬了娃娃的尕手儿,尕手儿没咬疼,我们来到门背后,门背后有个尕背篼儿,我俩背上了拾粪走。粪拾着多多儿,炕煨着烫烫儿,灯盏照着亮亮儿,娃娃养着胖胖儿。这就是文成公主留给我们的生存希望啊。
老董说,实话啊,文成公主娘娘路过了,给我们传授了那么多生存手艺。西王母娘娘驻锡在宗家沟里,宗家沟就成了神话故事中的圣地。托西王母娘娘的福,现在宗家沟的旅游搞得很红火。我们守在沟口,每年在旅游上也能挣不少钱呢。
老董家门口的喜鹊一直在喳喳喳地叫,听得人心生喜悦。我望着白杨树后面的石山和马路上呼啸而过的汽车,想起了仪态万方、衣袂翩跹,却从来没有现过身的西王母。又想到了怀抱日月宝镜、一路风尘却沉着坚毅的文成公主。山谷的风吹拂着她们的长发,她走过了万里荒原,将希望播撒在人间,她越过了绚烂星空,抚慰着黎民百姓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