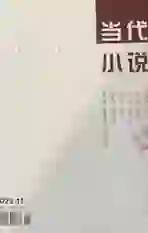熬年
2023-12-03王龙
王龙
1
亮子死在了济南。电话是三叔从济南打来的,腊月二十八,已经是年根了。
父亲还没来得及客套,就如遭雷击似的瘫坐在了沙发上,着实把我跟母亲吓了一跳。愣了半晌,父亲才缓缓地说,老三说亮子没了,济南公安局那边来了电话,老三已经先过去了。
晴天霹雳。亮子是三叔的儿子,也是我的堂弟。亮子只小我四岁,我俩是一块儿撒尿和泥巴的玩伴儿,每年总要见个一两次的。母亲似乎仍然不愿相信,试探性地问,头前还见过的,年纪轻轻的,怎么说没就没了?父亲却只顾着低头喃喃自语,老三真是一辈子没得着好啊。这几年,好不容易日子有了起色,又出了这么档子事。这年可怎么过啊!
三叔的电话只打给了父亲。大伯和小叔,一个在合肥,一个在烟台,离得都太远,好歹我们离得还近些。往常,老家有些大大小小的事,三叔总是愿意找父亲商议,有时候打个电话,有时候直接上门,毕竟从老家到县城也不算远。
我和父亲当晚便赶去了济南。大伯和小叔是父亲在路上电话通知的,三个人很快就达成了共识,不管怎么样,他们想法儿赶回来。安排妥当以后,父亲和我一路上也鲜有默契地共同保持了沉默。我用眼睛的余光,瞥见了父亲终于落下的两行清泪。
毕竟是省会城市,过年的气氛早就营造起来了,一路的五彩斑斓,满街的火树银花,处处洋溢着过年的喜庆。车里车外,仿佛两个世界。车里的空气沉闷而又压抑。我稍微把车窗打开了一点,车里瞬间涌入一股凉风,同时也把外边世界的五彩斑斓带进来一些。亮子的面容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那么阳光,那么爱笑,现在却悄然定格成灰色的头像。
等我们赶到济南的时候,三叔已经在那里了。
出租屋里乱糟糟的。屋顶的一盏白炽灯管,孤零零地亮着,让这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间显得更加压抑。房间内只有一张床,连个衣柜也没有。床头旁有一张不高不矮的小桌,桌子上摆着两三个不同样式的饮料瓶子,里边塞满了被焦油熏黑的烟头。
社区的管片民警,还有上级派来的法医,一起来了好几个,进进出出,忙忙碌碌的。一个身着鲜艳衣服的妇女在忙碌的人群里显得很突兀,正不停地向民警述说着什么。
亮子的遗体就在那张床上,已经用白布盖上了。
父亲没让我跟过去。我远远地瞅着盖在亮子身上的白布,努力想象着此刻白布下亮子的样子,感觉就跟做梦似的。直到此刻,我还都难以相信亮子就这么没了。直到此刻,我也才不得不相信,白布下面盖着的,真真实实的就是三叔的儿子、我的堂弟。
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三叔极其安静地呆坐在那里,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脸上写满了局促,就连影子似乎都蜷缩到了墙根的角落里。面对民警的连番问话,三叔怯生生地答着,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父亲的出现,让三叔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他挣开人群冲到父亲面前,满眼的泪水一下子喷涌了出来,十万火急地宣泄着他心里的悲伤和痛楚。二哥,孩子没了,怎么就没了呢?老三,你得挺住,万事还有我。相比于三叔,此时的父亲似乎更从容一些,也更得体一些。
尽管兄弟四个,但不管大事小情,三叔第一个想到的永远是他的二哥,最能依赖的也是他的二哥。
有些事,三叔解决不了,总是习惯性地要依赖父亲。
父亲也在压抑着他的悲伤,噙在眼窝里的泪水被他硬生生地撵了回去。在自己的亲弟弟面前,他一直堅信,自己的从容和冷静,能给对方带来些许的安慰。
记不清上次跟亮子通话具体是什么时候了,肯定没有超过一个月。亮子告诉我,有同事才跑了两年外卖,就在老家盖了楼房。那时候电话里的他,还在兴奋地跟我讲述着他的未来。我听得出他的努力。
我也记得叮嘱过他的,不要光想着赚钱,钱赚多少才算多啊。只是当时,他说得轻松,我也听得无心,谁也想不到,一切还没开始,就戛然而止。
断断续续地听着父亲和他们之间的谈话。心源性猝死,可因吸烟、饮酒、过度劳累等高危因素诱发;一旦发生,大脑内的糖原和储存的葡萄糖将被快速耗尽,最佳的救援时间只有短短的4分钟。民警和法医不断地向父亲解释着。父亲集中起他此刻所有的精力,仓促应对着接踵而来的信息。我陪着三叔一直坐在那里,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父亲。
当然,三叔是不懂这些的,尽管他也有疑问。我没病,你三婶儿也没这病,你说年纪轻轻的,怎么就突然得了这种病呢?他就是太累了,太着急了。他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我早说不该让他出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三叔的话。他好像是问我,又好像是没问我,更多的时候,他都是在自问自答。我能做的,也只是陪他坐着。亮子发病的时间是前天夜里两三点,直到今天上午,房主过来催要房租,才发现了猝死的亮子。换句话说,亮子在猝死以后,三十多个小时没有被人发现。
我的心一紧,无尽的酸楚涌上心头,我难受到了极致。亮子死前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做了怎样的挣扎,遭受了怎样的痛苦,这些我们再也不会知道了。我回头望向躺在床上的亮子,床头的那堆烟头格外刺眼,像一颗颗要迎面朝我射过来的子弹。亮子的生活,远没有他跟我们说的那般轻松。
问话,签字,再问话,再签字,持续了一整夜,来来回回,父亲的忙碌和三叔的焦虑,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下午。办完了所有的手续,拿到了亮子的骨灰,我们才坐上了返程的车。
2
青年早夭,按我们老家的规矩,是不能报丧的。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老家人把规矩和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白发人送黑发人,终归是一件不好听的事,往往是自家亲戚出面,把人火化了,安葬了,事情也就算办完了。邻里乡亲,知道了的,过来看一眼;不知道的,就权当不知道了。
到老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大伯和小叔早就到了。这次,几家人老的少的,来了不少,三叔家原本不大的院子,挤得都快站不开脚了。上一次这么多人,还是爷爷过世的时候。
父亲在电话里已经和大伯商议过了。三叔家一房四屋,除去主屋和客厅,剩下的两间亮子和姐姐芳子一人一间。亮子的房间在东屋,把东屋空出来,置了香炉,摆了遗像,供了灵位,算是在家里设好了灵堂。遗像是亮子的微信头像,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照片。年根了,又找不到营业的照相馆,是父亲托了朋友,安排芳子临时打印的。
人还没到,就听到了满院子的哭声。门外早已围了一圈看热闹的街坊四邻,正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都知道,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铁定是出了大事了。
车还没停稳,三婶儿、大娘、小婶儿她们一帮子女眷就哭着围了过来。
三叔抱着亮子,确切地说,抱着亮子的骨灰,艰难地挪动了过来。大伯抹了把眼泪,尽力地维持着现场的秩序,拉着三叔径直进了东屋的灵堂。人群和哭声也第一时间跟了进来。大人哭,小孩闹,不大的院子,顿时变得嘈杂不堪。三叔放好了亮子的骨灰,坐在火盆前,难以抑制地哭了起来,声嘶力竭。
三婶儿在芳子的搀扶下,蹒跚地从后面挤进来,也早已哭成泪人。
近几年,三婶儿的脑子变得越来越糊涂,见了人,认得,却不知道叫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反正好多年了。一开始是忘事,总不记得做过什么,又要做什么,后来就越来越严重,饭也不会做了。
有次做饭,竟然把整桶花生油倒进了锅里,差点引起火灾。三叔气得牙根痒,照着三婶儿身上踹了好几脚。后来,父亲坚持让三叔带着三婶儿去医院做了一次全面检查。脑垂体萎缩。医生说,这个病影响记忆力,影响自理能力,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慢慢变得不认人了,也没有自理能力了。三叔急了,这不成傻子了吗?三叔长叹一声,认不认得人也无所谓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我一天三顿饭管着,也饿不着她。
三婶儿只知道蹲坐在地上哭,撕心裂肺地哭。大家看了,心疼,也心酸。终归是母子连心。三婶儿趴在灵堂前,哭累了就歇一会儿;来人了,就又坐起来再哭一会儿。满脸的鼻涕和泪水,也分不清个先来后到。三婶儿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没人说什么。不过想想,也不见得是坏事,真要是脑子清清楚楚的,这心里得受多大的罪。
摊上这么个傻媳妇,村里人说三叔命不好,当年真不如娶了赵秀枝。可三叔从来不把他们的话当回事,也谈不上后悔不后悔的。
三叔当年有个相好的,叫赵秀枝,是村里赵老拐家的闺女。那时候,大伯在部队,父亲去学医,家里六七亩地,满地的农活全指望爷爷和三叔两个人干。
那时候的三叔,刚满二十岁,身体结实,膀大腰圆,一个人顶仨,浑身好似有使不完的劲儿。春播秋收,夏耘冬藏,都是三叔一个人在地里忙活。干累了就蹲在地头上,灌上几口米汤子,再嚎上几句土调子;嚎完了,歇够了,就起来埋头拱腚地继续干。
谁也没想到,正是这几句土调子,让赵秀枝的心里起了涟漪。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说什么也要跟三叔好,就看中了三叔的本分、能干。三叔下地干活,两个人总能碰到一块儿,你给我带个水,我给你捎个馍,一来二去算是看对眼了,但这层窗户纸到底是没捅破。也正是因此,才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
爷爷刚开始是不知道这个事的。眼看着三叔到了年纪,便托了媒人三乡五村地给保媒拉线。三叔不同意,就把跟赵秀枝的事一股脑跟爷爷说了。爷爷气得差点动了镢头。用爷爷的话说,赵老拐的父亲以前是地主,家庭成分不好,那是在村里低头夹尾巴过日子的人。
三叔据理力争。划成分那都是上一辈儿的事了,现在早就不兴论这个了。但爷爷就是死活不同意,咱老王家三代贫农,根正苗红,说什么也不能跟他老赵家扯上关系。
三叔还是不从。爷爷没办法,就拿当时在部队的大伯说事。你要是跟老赵家扯上关系,咱家成分就有问题了,保不齐就影响你大哥在部队的发展。哪个轻哪个重,你自己掂量着办。
三叔到底是同意了,也知道拗不过,后来就托媒人说下了邻村的三婶儿。在那个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比天大的。
爷爷和三叔一块儿去见了一次当年的三婶儿。反倒是爷爷又不太满意,嫌个子矮了,觉得不像媒婆比画得那么高。不知道三叔是不是故意,反而答应得很痛快。就这么定下来了。
听母亲说,赵秀枝后来去找过三叔闹死闹活,村里看笑话的人不少。到底也没能挽回三叔的心。三叔有他的说辞,咱不能今天是枣明天是梨,说话没个准头,媒人牵了线,也定了亲,谁来了也不能改了。但父亲说,三叔的心思可不止这些。
爷爷在村子里干了一辈子赤脚医生,手里就那仨瓜俩枣的家底,掏干了也不够给三叔办婚事。亲戚朋友借了一圈,也没借来几个大子儿。那时候,生活条件都不好,一个钢镚都得从几口人的牙缝里挤。爷爷不想亏着三叔,拉下脸管大伯要了一个月的津贴,虽说就三十五块钱,也算是解了燃眉之急。后来,村里给划了宅基地,父亲又帮忙添置了家具、修砌了房子,小叔也跑前跑后地帮忙打下手,三叔这才算成了婚,立了家。
3
老家是个小村子,一共四百来户,不到一千口人。給我的印象就是穷,到现在也还是穷。就比如村北头那条土路,永远都是坑坑洼洼的,像一块块皱皱巴巴的补丁。父亲有时候也会忍不住抱怨,咱老家这条路呀,那可真是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村子里的人,总是想方设法地往外走,没人愿意一辈子窝在这个穷村子里。
爷爷家也不例外。先是大伯报名参军进了部队;紧接着父亲学医又去了县城;没过几年,赶上做生意的热潮,有些人到烟青地区搞批发生意,听说都发了财。这下惹得小叔也坐不住了,一咬牙一跺脚,结婚第三天就带着小婶儿去了烟台。
爷爷从来不拦着,想拦也拦不住。好歹孩子个个都争气。大伯入伍第四年,就在部队提了干。邻近的十里八村,出去当兵的不少,当了军官的,大伯是头一个。爷爷在村里着实风光了一阵。后来,大伯在部队一直当到正师级干部才退休。小叔在烟台搞批发,规模也不小,头几年回家连大奔都开上了,开着车有意无意地在村子里转了好几圈。父亲算是子承父业,专攻中医,南来北往的病人看了不少,现在在县城也算是小有名气。用三叔的话说,老王家现在在村里也算是高门大户了。老家人每每提起村北头老王家,没有几个不竖大拇指的。说起这些,三叔总是一脸自豪。也因此,三叔在老家村里着实算是有头有脸的一号人物,人人都得敬三分。至少他对我是这么讲的。
但也唯独三叔,一辈子待在村子里,从来没出去过。我曾跟父亲聊过这个话题。我说三叔太老实太本分,要文化没文化,要头脑没头脑,既没啥手艺,更没啥追求,就算出去了也不见得能干成什么。父亲阴沉着脸说,你懂个锤子,你三叔心里挂念的比我们可多得多。没有你三叔,村子里的人都得戳我们的脊梁骨。
奶奶过世早,半辈子肺痨病,走的时候不到六十岁。爷爷去世的时候九十三,算是高寿了。后边的几年,爷爷身体明显不如以前,大病没有,小病倒是不断,隔三差五就有个头疼脑热。大伯常年在部队,一年回不来一趟,就连爷爷过世的时候,也没能回来。小叔一心忙生意,也鲜有回来的时候。我们家虽然离得近,也总不能天天跑来回。因此,爷爷的身边只剩下了三叔。
也多亏了三叔。白天,一天三顿送饭;晚上,就睡在爷爷旁边。爷爷生病起不来床,三叔就在床头支了块木板,垫上几块砖,就当了床。爷儿俩睡觉正好头对头。睡不着的时候,爷儿俩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会儿天,聊困了接着睡。爷爷身体发僵不得劲儿,三叔就坐在床边,从手到脚一遍遍地给他揉。
爷爷走的前一晚,只有三叔在身旁陪着。爷爷晚上睡不着,就把三叔叫起来,说有点东西,放在房梁的东头靠屋檐的地方,让三叔拿下来。三叔睡眼蒙眬地搬了两把凳子摞在一起,小心翼翼地把东西取了下来。是只包好的棉手绢,上面落满了灰尘,早就看不出颜色了。用手一掂量,分量还挺沉。三叔的困意顿时就消了,一脸窃喜地对爷爷说,爹,你这里边藏着什么好宝贝?爷爷让三叔打开。三叔满腹狐疑,打开手绢,定睛一看,竟然是四块小小的金疙瘩,还有五块袁大头。
那一晚,爷爷和三叔一直聊到很晚,也聊了很多。聊困了,人就闭着眼睛睡了,这一睡就再也没醒过来。接到三叔的通知,父亲大伯小叔陆续都赶了回来。倒也不多悲伤,老爷子毕竟九十三岁高龄了,走的时候安安静静,没病没灾,按老家人的说法,这算是喜丧。葬礼的事,兄弟四个意见很统一,热热闹闹地大办,专门从外边找了戏班,唱大戏,搭灵棚,摆了三天的流水席,孝子贤孙们的唢呐一吹一整天。
爷爷最后的那点遗物,三叔都提前分好了。三叔说,按照爺爷的意思,金疙瘩、袁大头一家一块,剩下一块袁大头,放棺材里压底。父亲大气地表示,自己啥也不缺,他的那份留给老三。大伯和小叔也没啥意见,毕竟也值不了几个钱。倒是三叔不同意了,还是坚持一家拿一份,不是钱不钱的事,该是谁的就是谁的,谁也不多占,谁也不吃亏,都是个念想。
最大的难题是爷爷的老房子。三叔又说,咱爹临走前交代了,老房子谁也别惦记,留给老四。老大是部队干部,老了有国家养着,老二、老三在村里都还有块宅基地,就老四什么也没有,所以房子就留给老四,老了有个根儿。
大伯同意。小叔推辞,一家人都在烟台了,老家有房子也住不着。但三叔坚持自己的意见,说这是咱爹临走时的遗愿,不能不遵从。三叔这么说,父亲也没再说什么。小叔说,那爹的葬礼,一切费用都由他来出。三叔不同意,说该谁出谁出,四个兄弟,就得四家出。
爷爷走的第二年,小叔就把老房子重新盖了,一院两层,成了村里最显眼的房子。后来,听父亲说起过,有次三叔喝多了酒,跟他漏了实话。老房子原本是爷爷许给了三叔的,但是三叔没说实话。我说,那三叔凭什么不要?父亲说,怎么要?你爷爷走的时候留的话,就你三叔一个人知道。说留给他,谁能信?就你小婶儿那点心思,恐怕你爷爷走都走不安宁。你三叔一辈子要脸,不想让村里人看咱家的笑话。我说,那三叔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父亲说,你三叔也是心疼你小叔,惦记着你小叔以后要是回来,不能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
4
毕竟是年三十,孬好也是年。老家就这个讲究,出了天大的事,年还是要过的。三叔被父亲他们生拉硬拽地拖到了主屋里。大伯说,可不能让老三一直那样哭,容易把身体哭坏了。三婶儿也在芳子的搀扶下离开了灵堂。哭过了,再把份子钱随一下,各家的心意也就算尽到了。公事办完了,再各忙各的。在老家,历来很讲究这些。
父亲他们简单弄了些饭菜,也算开了年席,一个不像年席的年席。从来不喝酒的父亲,今晚也破了例。桌上没多少话。三叔一杯接一杯喝酒,一边喝一边哭,一边哭一边说。谈到亮子,三叔又恨恨地骂,臭小子不听话,非闹着要出去,他才多大啊。骂完了又接着哭,哭得撕心裂肺,好像把肠子和胃都要哭出来了。
父亲他们听着难受,你一言我一语地劝,可劝了几句又觉得不忍心。都知道三叔心里苦,心里疼,这个时候再不喝点酒,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发泄方式。父亲他们几个就又开始陪着他喝,陪着他哭。一帮老爷们儿,边喝边哭,弄得一帮女眷们又几度落泪。
三叔那晚喝了很多,也哭了很久。仿佛这么多年憋在心里的委屈,这一刻,都释放了出来。父亲眼里的泪水再也憋不住,长叹一声,老三这个命啊!
兄弟四个,三叔和父亲的感情算是最好的,就连三叔穿的衣服,都是捡的父亲穿的旧衣服,哪怕是过年,我也从来没见过三叔买新衣服。我有时候调侃三叔,买件新衣服还能花几个钱?老穿旧衣服,你也不嫌弃。三叔乐呵呵地对我说,这有啥?我和你爹是亲兄弟,分什么你的我的;再说,我天天干工地活儿,买新衣服也是糟蹋了,穿旧的正合适。
这几年,三叔的工地活儿确实干得不错。在我的印象中,三叔啥都会干,这一点,比我大伯、父亲和小叔都强,是他们谁也不能比的。平常,家里换个灯泡,盖个院墙,钉个桌凳,全是三叔干。小时候,总觉得三叔是无所不能的,就没有三叔不会干的事。因此,也总喜欢跟三叔亲,跟在三叔后边,看三叔干这干那。
就这么大的村子,就这么点人。年轻的都出去找活儿干了,没人愿意再待在这个穷破的小村庄里。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学习好点的考个大学也算是走出去了,学习差点的就早早辍了学三五结队地出去找活儿干。反正就一个想法,出去了总比待在村子里强。村子里剩下的多是父亲和三叔他们一辈的人。
这几年,三叔他们也闲不住了,几个人凑成堆儿一合计,就到外村干起了工地活儿,给人家垒个院墙、盖个偏房什么的。慢慢地,竟也有了一些规模。有了规模,就得有个打头的,三叔就当仁不让地成了他们的“把头儿”。以前的工地活儿,总免不了有些偷工减料的事,但三叔老实、本分,派活的主家也都信得过他,因此,三叔他们在十里八村攒下了不少口碑。口碑好了,活儿自然而然也多了。活儿多了,收入也就多了。后来,村里跟着三叔外出干活儿的人也越来越多,刚开始不过四五个人,现在一下子到了二十几个,初具规模。父亲说,三叔这几年的日子过得滋润了些。
亮子从小学习就不好。村子里连个小学都没有,要上学,还得走上五里路,到邻近村里去上。附近几个村,就那一所小学。没办法,就这个条件,不上也得上。在三叔的意识里,还是得有个学上,不管成绩好不好,好歹得把高中读下来。亮子淘气,从小就掏鸟摸鱼的,打架骂人也是常有的事,没让三叔省几天心。后来高中毕业,大学也没考上,实在没地方去,也不能在家里闲着,有时候就跟三叔一块儿出去打个零工。
终归不是长久之计。用三叔的话说,不是个正路子。大伯就打电话回来,意思是让亮子去部队当兵,干得怎么样先不说,好歹能有口饭吃。三叔心里很乐意。对农村人来说,当兵,是一条绝好的出路。但亮子死活就是不去。三叔很恼火,指着亮子的鼻子骂,你看看你大爷,混好了大小都能当个领导。亮子反驳,俺大爷是俺大爷,我是我,他愿意去当兵,我就是不愿意去。
眼看着周围的小伙伴们一个个都走出去了,过年回来的时候,甚至都开上了小轿车。这让亮子羡慕不已,也下了要出去闯一闯的决心。三叔对此是坚决不同意的,按照三叔的想法,还是想让大伯托托关系,先去部队当兵,锻炼上几年再说,总归是条正路子。
但亮子有自己的想法,铁了心要出去,死活不在村子里待了。后来三叔又劝说亮子去跟着父亲学医。父亲也同意,有个手艺,到哪儿都饿不着。但亮子也没有同意,就一门心思想自己出去闯一闯。爷儿俩为这事,吵了不知多少架,每次都吵得不可开交,我不听你说的那套,你也别管我要干什么。甚至于有一段时间,父子俩的关系闹得特别僵,谁也不理谁,谁也不管谁。
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三叔自己说了不管用,就让大伯打电话劝,让父亲打电话劝;再后来,就让我打电话劝。但亮子谁的话也没听。父亲跟我说,亮子这脾气真是铁随了你三叔,爷儿俩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心里认定了的事,就是八头牛也拉不回来。我就说,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你们老一辈管那么多干吗?父亲就冲我说,你懂个屁。再后来,听三叔说,亮子跟几个朋友一块儿偷偷去了济南。三叔气得不行,但眼看已成定局,也就没再说什么,索性由着他去了。父子俩又重归于好。
亮子随了三叔,脾气倔,但也能干能吃苦。找不到活儿,就先当起了外卖员。先干着。起早贪黑,每月拿到手的工资也是不少的,比三叔挣得多。第一个月的工资,就有小一万,亮子自己留了三千,一千五房租,一千五伙食费,剩下的一股脑都转给了三叔。三叔不要,但亮子直接把钱打到了三叔的银行卡上。虽然送外卖很辛苦,风里来雨里去的,但亮子不怕。按亮子的想法,趁着年轻抓紧干几年,攒上点本钱,以后再开个门头,做点批发生意,早晚能混出个样来。
这一干就是大半年。亮子在济南忙活,三五天才来个电话,一开始三叔也没在意。可到了年根,再接到电话已经是天人永隔。三叔一边喝酒,一边懊悔,自己怎么就不知道多打个电话问问?怎么就没多嘱咐他两句?
5
母亲这边也没闲着。熬年夜,可是有不少事:点长灯,烧年纸,敬天地,拜鬼神;还得备上三牲六碗八大碟。
里屋有三叔为过年准备的东西,几副对联和不少“福”字,还有一些鞭炮和黄纸。院子中间也摆上了敬天用的桌子。下午,母亲她们炸了丸子,肉的素的都有,又凑了些买来的成品。水饺是四婶儿带回来的速冻水饺,下锅煮熟,用茶碗裝了,一并摆到了供桌上。亮子的灵堂里也摆了水饺,点了长明灯。熬年的一套活儿,全靠母亲、四婶儿她们里里外外地忙。
三叔这个人,没别的爱好,就喜欢喝酒。平常从工地回来,总是时不时地弄上几个小菜,叫上几个工友,每次总能喝上个半斤八两。父亲烟酒不沾,所以对三叔喝酒这个事就看不惯,好几次,电话里都发火了。可挂上电话,又不停地叹气。唉,老三一辈子出大力,喝点酒,心里身上都能松快些。
终于熬到十二点了,外边像约好了似的,响起了阵阵鞭炮声。又过年了。母亲她们把供奉的物料一应摆在了院子里的供桌上。芳子拿了黄纸。我和芳子的工作就是烧纸、点灯,然后按照母亲的指令,再将燃烧着的黄纸、蜡烛分散到院子的各个角落里,犹如在履行一项神圣的使命。
芳子干活利索,也能说会道,大家都说,不像是三叔生的。高考的时候,芳子考了个专科。在父亲的坚持下,学了中医,现在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当护士。三叔对此是很骄傲的,逢人便说,北京啊,那可是首都,姑娘给咱争气了。
芳子也孝顺,到北京工作刚一年,就趁着五一节,把三叔三婶儿接到了北京,爬了长城,游了故宫,看了天安门。在三叔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一张在天安门前的照片,三叔两手叉腰,特别神气。当然,三叔也没忘了大伯、父亲,还有小叔,给他们分别来了一波图片信息轰炸。走到哪儿拍到哪儿,山也拍,水也拍,哪怕是遇到个外国友人也要拍。父亲说,老三这是巴不得要把整个北京都拍下来;母亲说,这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了。三叔心里高兴,那是三叔唯一一次去北京。
今年的年,真不像个年。往年回来,三叔家里总是热热闹闹的。那时候,不管我们几点到家,三叔总是早早地就在大路口等着了,兴高采烈的,像个威风凛凛的将军。车子还没到跟前,他就在前头大跨步地跑着。父亲在车里喊,老三你上车。三叔像压根儿没听见似的,就那么在前边领着车跑。有时候碰到熟人,三叔就会主动跟人家热情地打个招呼,说,俺二哥一家,回来过年。脚下不停,嘴上也没闲着,也不管对方有没有回应。
那时,我总是会发两句牢骚,又不是不知道路,咱这个破庄子就这么大点地方,三叔还怕我们跑丢了不成?每当这个时候,父亲总会白我一眼。
今年三叔家里人很多,却比往年都清静。三叔其实也准备了一些鞭炮,数量不少,放在里屋了。父亲说,既然买了,总得放两个,再怎么着也是过年。父亲拿了两串鞭炮,去了门外,没一会儿,便听见外面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一串串的鞭炮声,宣告了一年的结束,也昭示着一年的开始。
大年初一是不能出殡的,至少要等过了初三。父亲他们商议的结果是,我们一家留下,大伯和小叔初一回去。三叔说,都安心回去吧,来看了就行了。后半夜,大伯、小叔带着两家人先回去了。大人不睡,小孩子也得睡,毕竟都忙活了一天了。
看着院子里摇摇曳曳的烛光,我有些恍惚。外边的热闹仍在持续,鞭炮声一阵接一阵,此起彼伏。我总觉得三叔这一辈子很亏,可三叔却乐呵呵地即将过完了自己的这一辈子。
芳子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芳子说,她想把北京的工作辞了。我想劝劝芳子,却实在找不到说辞,只好又把问题甩给了她,三叔能同意吗?芳子没有回答我,只是抹去了眼角涌出的泪水,说,反正早晚也得回来的。
东屋昏暗的灯光,隐约照亮了桌子上的遗像。黑白照片上的亮子,此刻依然笑得那么阳光,那么开心。我转头又望向主屋,三叔的身体佝偻着,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