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伦理与消费主义
2023-12-02续芹
续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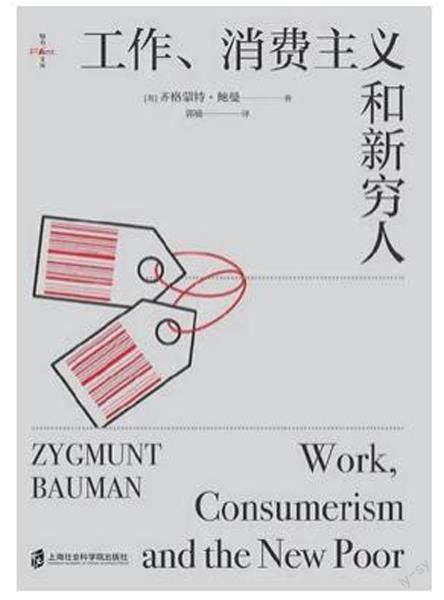
齐格蒙特· 鲍曼/著
之前看过几本书中有提到现代文明建立的土壤是清教徒思想。儒家思想与之有很多相通之处,这两种文化都提倡勤俭节约、克服懒惰、有所作为。人们观察到只有在这两种文化影响下的国家(或地区)才成为了发达国家(或地区)。
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正是类似这种——我的成就是我的努力、我的勤奋换来的,所以你的失败就是你自己的责任,是你的懒惰带来的——来自精英的傲慢,这种隐藏在思想底层的东西,剥夺了失意者的自尊,让我们的社会变得不美好、不幸福。
齐格蒙特·鲍曼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属于后者。
为了让各种机器开动起来,为了给生产线制造合格的工人,资本主义伦理配套创造了“工作的意义”“工作伦理”这样的概念。工作伦理隐含的内容是——不工作是不正义的;安于现状是可耻的。
为了适应生产线上的工作状态,人们必须让自己适应极端规律的作息和生活,重复机械性的动作与要求,原来田园状态下自由散漫的人们被改造成为生产线上的合格工人。《技术与文明》一书中,也提到宗教团体内修道者们的清规戒律为资本主义早期提供了合格的劳动者,使得资本主义萌芽得以产生。
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提到资本主义早期,19世纪20-30年代,“真正的穷人”可以去济贫院里接受救助。但济贫院的条件是令人发指的,这就是为了将人们尽量驱赶去工作。不工作,就会死亡。在这种意义上,资本主义用它的工作伦理驯养出了工人。
发展到现代,工作的类型更加多种多样,工作已然成为人们身份地位的一个象征。工作成为生活最为主要的一个基准和标杆,其他生活安排和追求都要基于它来规划。乃至于失业率成为各国政府普遍重视的指标,因为这个比率一上升,就意味着那些无人控制、无人监督、不受规则约束的人口增多,对于社会稳定是一个冲击。工作,不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上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工作伦理的存在意味着我们无从选择,我们必须献身工厂劳动,成为一颗螺丝钉。
从鲍曼提供的史料来看,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初,工人更多的是一颗生产线上的螺丝钉的状态,工作伦理的确帮助驯化了工人。或者说,工作伦理的确帮助资本主义在发展之初调动了生产力。能够调动起来,其实也说明了它是符合人们想要提升生活水平的内在需求的。作者的行文是要强调这种伦理背后对自由选择的抑制。
工作伦理在“美国梦”里进化成为了“不想当老板的员工不是好员工”,它披上了一层企业家精神的外衣,以实现社会阶层的跃迁为动力,来激发人们工作的热情。
与之相配套的是,之前的“不工作就死亡”的大棒政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不合时宜,此时“胡萝卜”政策更为妥当。给予努力工作的员工物质奖励成为普遍的做法,于是更加强化了金钱在社会评价体系中的作用。对于一个人的价值判断,人们的尺度单一到只有“工资”“金钱”这么一个尺度了。
现代社会价值评价的尺度是如此的单一化——“金钱”,为了得到金钱,人们不得不努力工作。那么人们对自由的渴求和欲望通过什么来得到宣泄呢?——答案是消费。
消费,意味着占有。我占有了,这就是我的私有财产,未经许可,你不能碰。消费,意味着毁坏。我使用了它,它的使命达成,消散于世间。
在前现代社会,人们是以生产者的姿态参与其中的,而在现代社会,所有人的消费者标签都得到了重大升级和强调。
在消费者社会,商家比你更能知道你的需求,不断有新的产品、新的诱惑存在,诱导你的消费行为。让你觉得你很自由,在无穷无尽的消费选择中大感快活,但事实是,你失去了不进入这个轮回的选择。物极必反,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极简生活的理念会兴起的原因。
在经济增长成为衡量现代社会是否有序运转的首要标准时,消费能力、消费热情成为了其中的关键。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在网上晒购物、晒名牌,展示这些消费能力,因为这意味着“有钱”,意味着“人上人”,意味着“更高品质的生活”。仅仅从表象上看,这种消费主义甚嚣尘上已经是全球现象。
在生产者时代,稳定而持续的工作是人们的首要选择,人们以此确定自己的身份认同与社会秩序。但是,原来带有強制性的工作伦理在现代的消费社会中已经显得不合时宜。管制、强制,意味着限制自由,限制自由会扼杀人们的消费能力。于是,身份也成了消费品,人是可以“设计”的,维持人设,或者重造人设都成为一种操作。工作也变得更加灵活和短期化。
如果是一位生产者,那么Ta需要知道自己要生产的东西,Ta需要有目标、有方向,可以说需要有理想。但如果是消费者,Ta需要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处在最喧嚣和热闹的地方,获得更多消费的机会,底色是一种机会主义、功利主义。
当代最流行的思想内核其实是——消费者要尽可能多地履行消费的责任。消费成为一种美学,一种带给人愉悦体验的机会。工作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工作本身,而是由它产生愉悦体验的能力来确定。
传统的工作伦理下,工作本身的意义是不证自明的;但在消费社会,工作被分为三六九等,有了高下之分。那些具有“使命感”的工作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成为精英的标志。这些人7×24小时地专注工作,这些人是新式工作的奴隶。
由于工作的短期化(合同期限),在这种情况下谈奉献精神、谈勤奋努力显得非常虚伪和空洞,这些道德说教失去了它的灵魂和吸引力。运动员持之以恒为了运动生涯努力,结出硕果,一朝获胜,荣誉加身,但之后可能就会沉寂下去,甚至穷困潦倒。这更加摧毁了人们对持之以恒的信念。
弗洛伊德说欲望一旦被满足,就会倦怠,那种个人的幸福状态是很难维持住的。但消费社会给出了这种可能性,它不断创造出新的欲望,人们在不断追求满足的过程中,体验幸福的获得感。于是,消费社会中的消费者生活准则是——不要出现厌倦,赶紧寻找下一个刺激。
产生欲望非常容易,但实现欲望却需要金钱。只有金钱才能治愈无聊。穷人缺钱,Ta可能无法用富裕者的方式消解无聊,于是挑战法律和秩序成为Ta对抗无聊的冒险。
有人认为,福利国家的理念把公民生活与“对社会的贡献”分离开来,认为任何时候都需要保证所有公民“有权”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因此,福利国家理念下,有尊严的生活是一个政治性的公民权利问题,而不是经济绩效问题。
显然,这与传统的工作伦理是存在矛盾之处的。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必然需要去面对这些内部的张力和矛盾之处,现代福利国家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践。
鲍曼提到20世纪中期英国福利国家的主要推动者贝弗里奇的观点,以及随后促成英国national insurance bill (国家保险法案)的通过。贝弗里奇主张一种普遍性的社会保障,致力于消除人们的恐惧本身。但实践中,多是选择性的社会保障,一定的经济审查是存在的。选择性的社会保障带来的后果是,接受保障的人被认为是失败者、懒散者、游手好闲的人、无所事事的人,于是进一步强化了成功者(精英)的道德感,加剧了社会的割裂。
福利国家为什么从20世纪80年代起遭到了颓败、打击和质疑?作者将其归结为全球化下的结果。对于资本的扩张和安全性来说,老套的国家援助变得无关痛痒。他们期待在新的土地(劳动力更加便宜的土地)上获得更多的回报。对于政府来说,就会面临双击局面,一方面本地人口失业,另一方面资本流出。民主制度在这时发挥了作用,社会保障仍有一个诉求的出口。
但从近些年的实践来看,似乎支持“减税”的是绝大多数,即减少福利。为什么原本会投票给“增加福利”的中层选民现在不再支持增税了呢?原来投票支持增税的主力军之所以会投票,大概是源于一种恐惧——担心自己哪天就要变成贫困的、需要领取救济的人。为什么这些人今天不再投票支持增税?这可能也与消费社会下,人们更加注重“选择的自由”有关。从性价比等各方面考虑,他们可能认为这并不划算,还不如自己安排一些私人保险。
福利国家理念的退败,与消费社会理念的崛起之间,是有关联的。
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四类职业。第一类,引导者、发明家、广告商、推广者和商人;第二类,教育工作者;第三类,从事“消费市场服务”的人;第四类,常规劳动者。
第四类是最容易被替代的劳动力,在机器生产日益大规模应用的情况下,这部分职业未来会消失。
第一类人被鲍曼称为四处的“游牧者”,对他们来说,空间不是问题,距离不是问题,他们四海为家,轻盈、灵活、多变,是全球化下的活跃分子和推动者。
人口过剩似乎并不是危言耸听,以现在人类的畅想大概无法想象未来人们的职业和工作状态。
底层阶级出现了,人们甚至认为这部分人群如果消失,整个社会会更加美好。异化后的工作伦理认为,沦为底层,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是你自己的无能导致无法在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中获得体面的生活。这样,就将贫穷定义为一种个人选择。
因为,我们现在是消费社会啊,消费社会的核心就是选择的自由,去满足自己无穷无尽的欲望。你曾经有过这种自由,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无能、你不努力、你不负责、你的行为是“反社会”的,导致如今你的境遇。所以,恶果需要你自己承担。福利国家理念的退化跟这种观念潮流息息相关。
鲍曼对美国死刑犯的增加,以及对相关精神障碍者的案件审判举例,挺引人深思的。作者尖锐地指出,正是基于这些背后的思潮和观念,人们对穷人的道德义务消失了,他们不是被驱逐出境,就是被关进了监狱。作者批评人们丧失了自我反思的能力。
鲍曼还提到了美国的平权法案帮助很多非裔美国人获得了人生前进的阶梯,但这些人并不感激这一法案,他们宣称他们的成就来源于自己的努力。平权法案的发明者秉承着集体关怀、扶助弱者的高尚品德推动法案,但结果是获益的人群不仅失去回馈的动力,反而成为该法案最强烈的诋毁者。
读罢此书,我脑中萦绕着两个词儿:“慈悲的心”和“感恩的心”。
慈悲的心,让我们成为施与者,成为爱的发动机,让爱传递下去;感恩的心,让我们成为接受者,接受爱并传递爱。
我本人主张采用进步主义的眼光看待世界。田园牧歌那么好吗?其实末代皇帝的餐桌可能还没有今天我们普通人的丰富美好,更别提社会的自由度和个人发展的问题了。社会发展到今天,目前的制度存在合理性,有其人性内核的支撑。但问题从来都有,矛盾也永远不会消失。我认为,做事时,需要就事论事,每个人从自己能够想到的位面出发积极争取,多元并进,坚持长期主义和面向未来的做法。
要人类社会更加美好,教育一定是重中之重。我们要将我们的孩子教育成为内心富足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下,Ta能够自洽、平衡、找到生活的乐趣,如果恰好还能够做些对更多人类发展有益的事情那就更好,没有也没有关系,维系好自己和身边人的幸福感觉,本身就是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最后,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提到资产负债表,引起了我的职业病。
作者在第93頁写道:所谓“过剩”的人被标记在资产负债表的借方,而非贷方,因为无论是现在还是可预见的未来,他们都不能增加社会的财富——他们增加的只是社会的负担(公共支出)。他们是“资源黑洞”,是尚无清晰解决方案的问题;从事“经济活动”的那部分人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似乎也创造不出“过剩”的人的工作需求,无法使他们重新就业。
但作者在第154页又写道:消费者社会的资产负债表中,穷人明显是负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们计入现在或未来的资产。
所以,这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呢?不知道是翻译的原因,还是原文如此。作者在这里的表达有些随意和含糊。更何况,对于资产负债表来说,其实是不分借方和贷方的,只有账户才有借方和贷方。
这么复杂的社会问题本身用财报来表达可能无法准确,但作者的表述勾起了一个财务人的兴趣。我试想一下,对于社会资产负债表来说,一个人的出生是何种影响呢?我想应当是资产、负债和权益同增,并在初始保持平衡。个人的权利,对应了社会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个人的义务,对应了社会资产负债表中的权益;个人也作为社会资产负债表中的一项资产存在着。
只不过,对社会有益的人,其作用类似于长期股权投资,可以源源不断地给社会利润表和社会现金流量表带来价值增量;而对社会无益的人,就类似于长期待摊费用,存在的作用是使得社会利润表更差。当然,这里所说的“有益”“无益”,可以超出金钱衡量的范畴,从更加丰富或更加宏大的维度来度量。衡量的维度越丰富,纯粹无益的人群就越少,社会财报就越加厚重和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