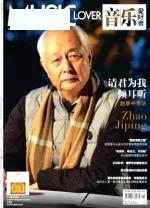自由哲人的孤独喑默
2023-11-24王茜
王茜
“当她的双眼合上之时,也是我的生命结束之时。”面对克拉拉的病情,勃拉姆斯如是倾吐着衷肠。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伟大的自由哲人孤独地吟唱出对信仰、希望与仁爱之沉思的终曲。
《四首严肃的歌》创作于1896年,歌词文本以《圣经》为来源。从前面三首死亡的沉重感悟,到第四首以仁爱之心的欢欣歌颂作为套曲的终结,足见“爱能战胜一切恐惧”的深层用意。其中引人深思的是,完成这部声乐套曲后,翌年勃拉姆斯便驾鹤西去,这巧合地应验了他因为渴望追随克拉拉而许下的死亡预言,同时也印证了“爱胜过一切”的人生箴言。


这部声乐套曲的“严肃”不仅体现在歌词的宗教性来源上,而且体现在暗含其中的告别姿态中:它既是勃拉姆斯创作生涯的最后一部声乐套曲,更是一位充满悲剧意识的作曲家的人生总结。不过,从这部作品所展示的态度来看,作曲家给世人所留下的“保守派”“悲剧性人物”“寡言虔诚的新教徒”等标签,最终都被一一撕去。尽管勃拉姆斯的天资没有像他同时期的部分作曲家那般被低估,但由于他在某些方面的表现过于突出,从而“诱导”我们在面对这位作曲家的成就时,容易形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评判。适逢勃拉姆斯诞辰一百九十周年,我撰写此文,试图通过揭示这部晚期声乐作品的重要艺术价值,引发人们对其艺术之伟大性的再思考。
顽固的保守派?
勃拉姆斯对贝多芬的崇拜无需赘言,其作品中显著的古典姿态已经说明了一切:经得起推敲的严密逻辑、复调和变奏技巧的精妙运用、“纯音乐”形式的美学原则等方面都充分彰显了他对德奥古典传统的深切敬意。在充斥着文学和哲学影响的世纪里,不少作曲家被音乐表现力的新奇实验所吸引,试图在音乐领域中实现“无所不包”的艺术理想。勃拉姆斯意识到了浪漫主义症候将会给这种艺术带来怎样的影响,遂反其道而行之,坚持让音乐回归到它的纯粹本性中去。他在形式中为“绝对音乐”的理想找到了可靠的佐证——不需要依靠文字说明,亦无需借助外在客观事物作为音响描绘的参照,音乐本身就能够言说一切,表现丰富的人类情感。如此看来,他并非是想当然的“形式主义者”,也非顽固不化的守旧派。面对特定的体裁,他总是能够找到与之相适应的音乐表现手段。
《四首严肃的歌》可以说是勃拉姆斯音乐观念的一个缩影。声乐体裁这种“有词的艺术”显然不是其“绝对音乐”观念的主要实践对象,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遭到遮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曲家在坚持纯音乐理念的情况下仍然写下了大量优秀的声乐作品(加之其晚期创作重心向歌曲转变),与此同时他作为“器乐作曲家”的本质也丝毫未被贬损,这难道不是恰好说明勃拉姆斯内心真正坚守的是一种多面且立体化的音乐观念吗?具体来看,一方面,每首歌曲的材料、调性、速度等要素之间的紧密联系共同铸就了套曲整体上的庄重严肃之感,对音乐逻辑性表述的追求显示出了勃拉姆斯遵循传统的一面;另一方面,音乐的沉重之感、钢琴声部偶尔表露出来的独奏冲动、整部套曲的起讫调性安排、节拍的灵活移位等构思,都逐渐远离了该体裁原本简单朴素的性质——在此,形式让位于文本内容,它更像是宗教声乐作品的戏剧性宣叙风格与艺术歌曲亲密的抒情特征糅合在一起的混合体。在这一点上,勃拉姆斯既没有追随贝多芬,当然也不同于舒伯特,甚至迥异于其心目中敬仰的老师舒曼:他不满足于清晰规整的音乐表现,但模糊暧昧、引人遐想的情绪显然也不是他想要的;他努力地传达乐观的纯粹本性,但实际上其积极的态度又总是被其他因素所埋没。勃拉姆斯音乐中复杂的矛盾性可见一斑。

沉迷神学的虔诚信徒?
众所周知,勃拉姆斯生长于德国汉堡的新教家庭,不论是他所要继承的德奥音乐遗产还是家庭生活,都顺理成章地驱使他成為一名虔诚的新教徒。勃拉姆斯的许多作品都显示了与宗教的紧密联系,这对植根于基督教精神的西方音乐艺术而言并非稀罕之事。然而,依托宗教题材堂而皇之地对其加以否定的做法,在西方音乐历史上却是极为少见的。勃拉姆斯曾经公开表示《四首严肃的歌》是如此明确地在亵渎神明,取自《圣经》的歌词为其“异端”行径提供了保护,否则这些歌曲因其内在的“反动性”可能遭到禁止。

的确,只要稍加注意作品中的音乐表现手段,就不难发现埋藏于其中的挑衅意味:首先,从歌词角度来看,勃拉姆斯选择了最有可能发展成“反抗意识”的经文段落,可见第一首《人类遭遇的,兽类也遭遇》中的一句“人不能强于兽类,一切全都是虚空”,或是第二首《我又转念》中的“受欺压的眼泪,无人安慰”,以及第三首中以讽刺的口吻来赞美死亡,甚至是高扬爱心的第四首都在传递人类力量的微茫渺小以及对信仰的质疑;其次,这部套曲的强烈戏剧性张力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在速度和力度方面具有大幅度的对比,而且频繁的离调、严肃庄重的复调织体紧跟着主调织体颇为莽撞的闯入(可见第一首的段落对比),这一切所带来的骚乱无疑是教会明令禁止的;此外,从主题构思的角度来考虑,勃拉姆斯在这部套曲中同样沿用了器乐作品中的主题发展方式,即通过主题形态的相关性来建立音乐整体的统一性。毫不意外,他再次返回到贝多芬那里汲取养分,坚定地采取“斗争性”的主题发展路数,一方面展示着其叛逆的抵抗姿态,另一方面是想依靠斗争方式来获取他心目中的胜利。从第一首以级进为主的主题到第二首和第三首强调音程关系的旋律线条,最后发展成为三者的综合体并赋予音乐以鼓舞人心的欢快性格,这一主题线索推翻了前面歌曲建立起来的阴郁沉闷的情绪,尤其是第四首歌曲中的最后一段优美宽广的旋律,最终挽回了这部作品作为抒发主体情感的艺术歌曲的名声——与之相应的歌词“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心”向我们揭露了勃拉姆斯的真实想法,他真正想要抵制的是那些惺惺作态的教会,而对于赞颂人性、倡导大爱的宗教观念,他始终持以褒扬态度。
自由主义者的最后颂歌
部分学者认为,勃拉姆斯对待交响曲、弦乐四重奏等传统体裁时极为小心谨慎,而面对声乐体裁时则显得有些许随意。但在我看来,正是洒脱随性、没有过多顾虑的创作心态,反倒促进了他在该领域的成功。在《四首严肃的歌》中,起讫调性不一、非方整的乐句结构、节奏和速度以及和声的迅速交迭随处可见。然而,表面上的肆意性却完全贴合歌词文本所表达的内容。勃拉姆斯提醒着人们,在他的歌曲创作中,文学文本的意义居于首位,而形式则是次要问题。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勃拉姆斯在器乐至上的年代里始终坚持让声乐线条(作为直接“传达意义”的声部)占据歌曲的主导地位。他再次选择与时代潮流保持距离。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视古典形式为稀世珍宝的作曲家实际上比我们想象中的要自由得多。勃拉姆斯无比尊重前辈们建立起来的传统,但他从不囿于任何圭臬,因而才能够在“经典体裁”面临危机的境遇下创造出全然属于十九世纪的交响曲奇迹;在面对大型体裁感到力不从心时,他又随即投向符合浪漫品位的小型体裁的创作中,其中所显示出来的轻松自如的笔法和圆润成熟的品格,似乎在宣告作曲家不再背负继承古典遗产的沉重包袱,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与自己达成了和解,并取得了完全属于自己的胜利。
勃拉姆斯罕见地将自己的内心昭示于众:长时间背负着“巨人的阴影”并非说明他在艺术态度上软弱无能——尼采对这位作曲家的评价显然太过激进——而是作为浪漫之子追寻艺术经典的一种自我鞭策手段;作为“纯音乐”的捍卫者,他不甘于堕为绝对的形式主义代言人;作为一个天资过人的艺术家,他又来回踱步在舒适静谧的生活方式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之间……简言之,勃拉姆斯不隶属于任何一个阵营,他只是作为他自己,一位孤独而自由地游走于过去、当下和未来的无“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