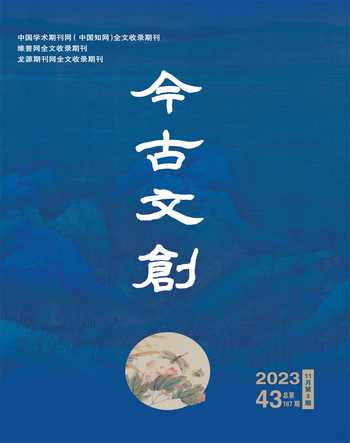马金莲小说中叙述声音类型分析
2023-11-20朱佳苗
朱佳苗
【摘要】馬金莲是宁夏著名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常以西海固乡村的底层女性为小说主角,真实展现她们的日常活动以及心理活动。以往对于马金莲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其小说中的贫困叙事、底层书写的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多为性别批评、社会学批评。本文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出发,对其小说中的叙述声音类型和叙述音强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从中探讨马金莲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关键词】马金莲;女性主义叙事学;叙事声音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3-003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3.010
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是由美国学者苏珊·S·兰瑟和罗宾·沃霍尔共同创立的一门文学研究方法,她们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使之成为后经典叙事学的重要分支之一。21世纪初,中国学者便开始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相关理论著作的译介工作,并将其广泛应用于文学批评实践过程当中。尽管女性主义叙事学进入中国的时间较短,但也发挥着巨大作用。
“声音”这个概念在女性主义叙事学中相当重要,“它指叙事中的讲述者,以区别于叙事中的作者和非叙事性人物。”[1]“在各种情况下,叙述声音都是激烈对抗、冲突与挑战的焦点场”[1],兰瑟认为对“声音”的争夺,就是对话语权的争夺。女性主义叙事学将叙事声音的研究聚焦于女性作家、女性角色之中,这一行为体现出的是对传统男性叙述声音反抗与解构的坚决态度。兰瑟在书中主要研究了三类叙事模式: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以及集体型叙述声音。作者型叙述声音指一种“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支撑意义的叙事状态”[1],在这种叙述模式下,作者不会参与到虚构的文本当中,是独立于文本之外的存在。此时,作者仅仅是书中人物言辞和行动的表述者,但同时也有着全知全能的视点,具有权威性。个人型叙述声音是指“有意讲述自己故事的叙述者”[1],类似于第一人称叙述,即由“我”自述以“我”为中心而展开的故事。个人型叙述的权威低于作者型叙事,但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性和文本的自传色彩。集体型叙述指一系列行为,“或者表达了一种群体的共同声音,或者表达了各种声音的集合”[1],因为对于集体叙述声音的研究仍未形成一套专门的叙事学术语,所以在本文中未曾涉及此部分内容。
马金莲是宁夏20世纪80年代女性作家中的佼佼者,她的小说总是有着独特女性叙述视角,她总是不厌其烦地描绘着西海固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天真无邪的女童形象、勤劳隐忍的乡村妇女形象和“进城”后的知识女性形象。马金莲的创作多以个人型叙述和作家型叙述对应着她的两种视角的选择——幼年女童视角和成年女性视角。首先,她总是采取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来对童年时光进行回忆,对女童形象进行塑造的同时融入了自身幼时的真实经历和真切感悟,使这种书写具有了自传色彩,再加上第一人称带来的亲历性,使这一视角具有了个人型叙述模式的特征。其次,马金莲有许多以第三人称视点塑造的成年女性形象,在这类形象当中,又分为乡村底层妇女形象和城市知识女性形象。此时叙述者不参与到故事当中,对应着兰瑟所说的作者型叙述声音。
一、马金莲小说中的叙述声音
兰瑟认为个人型叙述模式中,“讲故事的‘我’也是故事的主角,是该主角以往的自我。”[1]虽然个人型叙述模式不单纯指第一人称视角,但是马金莲在有关童年叙述的小说中常以第一人称展开回忆,而这种回忆就是她的童年过往。生活在西海固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贫困自然成了大多数西海固作家的表现对象,马金莲也不例外,但是正是自由散漫的童年生活塑造了她独特的女童视角,在表现苦难的同时,也对苦难进行了消解。以女童视角书写自己熟悉的童年故事,是对童年生活的回望和思考。
(一)马金莲小说中的个人型叙述声音——女童视角
马金莲的多篇小说中都可以划分为个人型叙述声音的类型,但是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她对女童视角的运用上。她以女童的视点观察着身边的女性,充斥着饥饿困苦的整个童年中,这些女性始终影响着“我”。在《永远的农事》中,“我”和姐姐从五六岁开始就被母亲教着种地、做饭,培养将来作为媳妇的本事,原本性格蛮横的姐姐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温柔。《赛麦的院子》中,赛麦的母亲因为没有生出儿子不被人看作是女人,儿子终于出生后,却不幸染上重病,为了给儿子治病欠下大笔债务,儿子却没能留住。《柳叶梢》中,父母外出耕作,留下梅梅照顾更为年幼的妹妹,家里没有粮食,只能靠喝着凉水充饥。
尽管成长的过程伴随着饥饿、贫困与责骂,但是苦难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马金莲对童年故事的书写总是覆盖着一层明快的回忆滤镜。“马金莲小说以其不带批判的天真女童视角书写苦难与性别歧视,虽然弱化了苦难叙事的社会批判功能,但更能将读者的思考引向文化内部。”[2]女童视角消解了传统父权在物质、精神上对人的影响和束缚,以童年的无忧无虑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完成了对生活的诗意化改写。在《父亲的雪》中,生父离世,母亲改嫁,“我”和哥哥寄住在二爹家。在一次去看望母亲的返程上,“我”倔强地独身走在雪夜里,却不知道后爸在后面默默守候,甚至因此落下了病根。《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中,“我”和姐姐无忧无虑地唱着童谣,观看奶奶卧浆水,一坛浆水酸菜不仅连接了爷爷和二爷两个大家庭之间斩不断的亲情,也构筑了生活中最容易获取和感受的幸福。
作者站在文本背后以追溯的目光去回忆童年时,不仅真实地再现了苦难,更完成了对苦难的消解。因为与童年隔着相当长的时间距离,所以马金莲在抒写童年回忆时总是模糊不清的。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时间间隔,她得以以审视的、批判的目光去看待童年里的人和事。叙述者作为成年人的思考模式隐藏在天真烂漫的儿童视角之中,在对苦难进行消解的同时,透彻地解析了母亲悲惨命运的根源,预测了姐姐以及“我”自己终将走上母亲走过的道路,“终有一天,风刀子毒阳光,会把我们变成母亲一样的女人。”[3]正是在儿童和成人的双重目光下,马金莲完成了对生活在西海固乡村的女性命运的关切和预测。
馬金莲以成年女性视角进行叙述的小说大多属于作者型叙述声音的范畴。文本是虚构性话语构成的,和现实生活有着一定的距离,马金莲作为小说的写作主体,选择了故事当中的成年女性作为叙述主体。尽管小说中主人公的经历与作者重合,体现着作者思想意志,但仍然是虚构的人物,叙述者并不存在与小说虚构的文本当中,而是站在文本之外的视点对故事展开叙述,不能将书中主人公同作者等同起来,这也就是作者型叙述声音权威性的由来。
(二)马金莲小说中的作者型叙述声音——成年女性视角
1.乡村底层女性视角
马金莲以扇子湾为原型构建起的西海固乡村世界,是她对乡村农耕日常、贫瘠生活环境进行如实的描绘。“她的叙述没多少技巧上故弄玄虚的痕迹,而是得益于她坚实的生活实践与扎实的情感体验。”[4]她总是将自己所经历过的西海固农村媳妇的生动体验全部融入小说创作,对于乡村底层女性形象的描绘贯穿着马金莲文学创作过程始终。
马金莲在平淡的叙述节奏中,诉说式地呈现西海固乡村底层女性生活的不易与艰辛,她对乡村生活展开全知全面的细致刻画,农耕农忙、家庭琐事、妯娌矛盾是小说构成小说的全部内容,并以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为主线而串联起来。正是出自对自我熟悉生活的刻写、对自我经历体验的描摹。这些西海固乡村底层女性是如同作者那样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女性的缩影,体现着这一群体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
马金莲前期作品多回忆童年时光以及抒写西海固乡村家庭琐事,近年来,她塑造了许多知识女性形象,这种转变的发生是伴随着马金莲从乡村到城市的位置转移而发生的。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使马金莲写作的角度与之前有了较大区别,她所塑造的女性也不仅仅局限于乡村底层女性,城市知识女性形象也成了她使用作者型叙述声音所描绘了女性形象的一大类别。
2.城市知识女性视角
对城市知识女性形象的塑造大多沿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其主题仍然是表现和关注西海固女性的生活。我们不难发现,马金莲笔下的知识女性仍然是属于西海固乡村的,她们是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尽管身处城市,习惯于繁忙的都市生活,她们精神内核仍然是坚韧且强大的。在这一系列女性形象的塑造中,贫困叙述的主题不再,这些走进城市的知识女性往往是有着一份行政单位的体面工作,不用再为了基本的生活开支而奔波,因此马金莲书写的主题上升到了展现和关注现代女性精神状态的高度。
《化骨绵掌》中,苏昔收到了同学聚魂的邀请,她精心打扮准备赴宴,却被丈夫一直质疑诘问,因此选择了离婚。《良家妇女》中,在医院照顾女儿的苏于渐渐被三床的男人所吸引,理智控制着她的情感,在男人对二床的女人献殷勤时却忍不住吃醋,最终还是理智占了上风。《午后来访的女孩》中,外甥女致电苏亦要来拜访,却在阴差阳错之间招待了另一位陌生的女孩。时尚前卫的陌生女孩和传统保守的苏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马金莲通过对女性现代生活片段的展示,以一种“以我观她”式的自省对现代社会下知识女性的精神状态生存状态进行了反思。她所塑造的这些苏姓女子,都是以她们的心理意识流动组织故事脉络。乡村底层女性系列中的女性只是默默呈现生活的艰辛、内心的忧愁,城市知识女性对男性父权的反抗则变得坚决,她们追求幸福的意愿也变得强烈,但仍然是对“男性权力中心”温和而含蓄批判。马金莲把女性的苦难、挣扎于反抗直白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以此来探寻男权社会下普通女性的生存道路。
“音强”是语言学的重要概念,将这一概念引入到叙事学中,“音强”便与作家的叙述权力具有了紧密联系,在女性主义叙事学中表现为女作家的叙述权力。马金莲作为众多女作家的之一,她的创作过程也代表着她的叙述权力的提升过程。
二、马金莲小说中的叙述与“音强”
(一)“音强”与叙述中的“音强”
“音强”是语音的四要素之一,“是用来量度声音强弱,声音大还是小、响还是轻。‘音强'更多地用于声学(偶尔用于听感)”[5],讨论语音的声学性质时音强的因素不可或缺,但不起主导作用。叙述中的“音强”可以理解为作家叙述声音的强弱,叙述声音的强弱又彰显着作家权力的强弱。叙述学中的音强与女性作家身份焦虑密切相关,女性作家因其长久以来所处的社会环境,一直在为她们被剥夺的权力做斗争,其中也包括写作的权力。而“作者身份的焦虑”是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一书中,提出的理论。女性的这种焦虑来自复杂的,从根源上来看是女性对权威的恐惧。“在女性艺术家而言,这种权威似乎从定义上看就是不适合于她的性别的。由于作者身份的焦虑是由社会对女性的生物属性所施加的影响造成的。”[6]
(二)马金莲小说中的叙述“音强”
20世纪二三十年,以丁玲、萧红等为代表的女性文学热潮标志着女性作家身份开始获得国人的普遍接受,女作家的叙述权力扩大,女性作家身份的焦虑也逐渐减弱。但这种焦虑至今仍对不少女作家产生着负面影响。马金莲没有对传统父权社会辛辣的嘲讽,也没有激烈的抗议,而是低声的诉说,“低诉式”的创作方式正是叙述“音强”低弱的表现,这也是她小说的一大特色。
马金莲的小说往往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从女孩、少女到乡村女性再到后来的知识女性,这些女性角色无一不体现着马金莲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个人体悟。女童视角以及乡村底层妇女视角下女性角色地位的低微,实际上代表着叙述者对自己所拥有的权力的焦虑。小说中有姓有名女性角色却只有主人公一个,女性普遍存在着一种的无名状态,她们被称为“母亲”、某某女人,某某媳妇。书中的女性角色作为一种符号而呈现,象征着女性低下的从属地位。马金莲笔下的这些女性人物形象社会地位低下,她们只有在作为男人的妻子或者孩子的母亲时才有意义。叙述者在进行叙述行为时的权力也是低微的,叙述音强也是微弱的。叙述者总是采取一种温情的态度来完成对女性艰难生存状态的展现,诉说式地呈现女性的心灵创伤。马金莲刻意放低自己的姿态,以此作为对传统父权制社会的泣诉与反抗。但这种刻意放低自己的姿态,仍是对《阁楼上的疯女人》之前以及后来的女性作家身份焦虑的延续。
与小说中女性的无名状态相反的是,书中的男性角色一般都有名有姓。但男性始终处于一个缺失的地位,对于男性角色的描写也没有像女性那样细致和丰富,可以说马金莲的大部分小说都描绘的是一幅生动的女性人物群像。这其实是女性作家身份焦虑的一种表现,小说中的男性几乎全部都是父权制社会下传统男性的典型形象,原生家庭中父亲的缺席(《赛麦的院子》中赛麦的父亲马三山常年游走在外),婚姻生活中丈夫的缺席(《马兰花开》中马兰的丈夫李尔萨经常在外务工)。马金莲笔下的男性角色的缺失或模糊不清,是女性在物质上、思想上摆脱男性束缚的符号化表现。正是在男性缺位的状态下,生出了女性独立的性格,进一步催生了她们独立意识的觉醒。
总体来说,马金莲的小说发展史体现出她作为女作家叙述权力的逐步提高,但这种提高是在她前后期作品的对比下产生的。因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生活习惯的限制,这种提高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內,在创作方式上体现为“低诉式”写作。
三、结语
马金莲作为宁夏较为出名的女作家之一,同时也在“80后”作家中有着代表意义。在个人型叙述声音模式中,她时常以女童稚嫩无邪的目光去观察周围世界,在作者型叙述声音模式中体现为以成年女性的视角去“观测”周遭一切。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看与被看”的权力始终存在着,尽管叙述者把自己放在一个较低的社会位置上,而这种看与被看的权力实际上就是女性的叙述权力。马金莲长久以来写作过程可以说代表着女性作家叙述声音的“音强”逐渐放大的过程,她以自己的方式对传统父权社会提出了抗议,书写了自己独特的女性特质。在表层的文字之下隐藏着她对新世纪下女性命运、出路的独特思考,体现出的是对女性终极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22.
[2]韩春萍.马金莲小说中的女童视角及其文化意义探析[J].民族文化研究,2016,8(34).
[3]马金莲.1987奶奶的浆水和酸菜[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59.
[4]买莉.作为一种现象的西海固文学——兼论石舒清和马金莲的小说创作[J].回族研究,2021,2(01).
[5]朱晓农.语音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1.
[6]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M].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