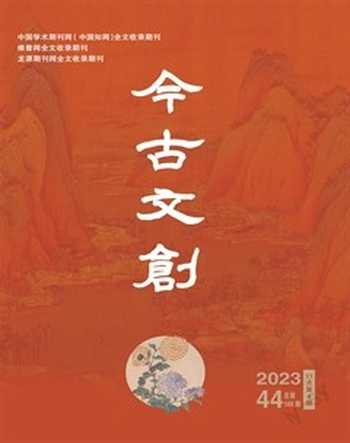文学想象与诗性建构 ——南朝诗歌的洛阳书写
2023-11-20万雅婧
万雅婧
【摘要】在古人的观念里,洛阳居“天下之中”,是政权中心与德治典范。然而在南朝诗人尤其是梁陈诗人的笔下,洛阳城的形象逐渐与固有模式偏离,神圣的中原古都不仅仅只是“德治”的象征,而更多被赋予了富贵、华美、旖旎的气质。都城形象的流变背后反映出南朝文学的新变和南朝文人对于北方故都的文化心态。对南朝诗歌中的洛阳书写进行研究,有助于理解文学与都城文化的双向关系。
【关键词】洛阳;南朝;都城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4-0071-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4.022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项目(2022年)“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洛阳形象书写与人文内涵研究”(项目编号:202210559031)成果之一。
洛阳自古为“天下之中” ①,是多个正统朝代的国都。都城乃是历朝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文人群体有莫大的吸引力,是促进文学生成的重要机缘。而文人作为文学创作与鉴赏的主体,其文学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都城的人文形象,这是都城与文学的交互影响。②南朝政权皆定都建康,偏安江左,但洛阳始终是萦系在南朝文人心头的深深情结,他们虽不能至,心仍念之,在诗歌中运用艺术的桥梁跨越时空的界限,糅合历史情境,对遥远的故都进行文学想象与诗性建构。洛阳的形象也在文人持续不断的书写中发展出新的意蕴。本文以南朝诗歌中的洛阳书写为研究对象,探寻洛阳的人文形象在南朝时期的特点,以及文学与都城文化的交互意义。
一、从写实到想象
西晋末永嘉之乱后,洛阳陷落,中原统治阶层和黎民百姓为了避祸纷纷南渡,迁至江左,在建康设立宗庙社稷。东晋灭亡后,政权又历经宋、齐、梁、陈四朝更迭,始终以建康为都,是为南朝。若以宋武帝刘裕北伐,于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光复洛阳开始算起,至景平元年(公元423年)洛阳失守,其间短暂的七年里,洛阳处于晋宋的政治疆域内。该时期文学中有关洛阳的书写多为随军和行旅见闻,如谢晦《彭城会诗》和颜延之《北使洛诗》,其中后者被钟嵘评价为“五言之警策”。颜延之出使庆贺刘裕北伐的途中经过洛阳,面对光复不久的晋室旧都,他的悲伤却远远胜过欣喜之情。在诗中,他先是自述赴洛的艰苦,从江南行舟秣马,跨越万水千山来到中原故土,然而他所见的是什么呢?入目皆是久经战乱后的凋敝、破败、苍凉之景:洛阳不再是国家的中心,而是位于边防的前线,饱受战争的侵袭。晋宋年间的政治乱局里,“洛阳城不治既久,又无粮食。”[1]1721和前朝的繁华富庶、人稠物穰形成了巨大的对比,在物是人非的萧索场景面前,诗人的飘零之叹、行役之苦、黍离之悲油然而生。
由于常年的战乱动荡,晋宋之际有关洛阳的文学创作并不多见,洛阳的文学形象也因文人创作的时空差距逐渐由具体转为抽象。且元嘉年间的北伐失败让洛阳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北方统治者实际占有,绝大多数南朝文人终其一生都没有踏足过北方的土地,更别说行至洛阳,所以洛阳作为地理空间对南朝文学生成的影响渺不足道。但是有关洛阳的文学书写并没有停止,洛阳的形象依旧活跃于南朝文人源源不断的创作中,流变出新的内涵与意义。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南朝卷中,光是以“洛陽”为题目的诗就有约二十首,而以“金陵”为题的诗仅在全南朝卷检索中出现过四次。可见甚至在数量上,以洛阳为题的诗文比当时的首都建康更多。而且其中大多数写于南朝后期的梁陈时代,离南渡已过去了近两百年,南朝文人对洛阳持续的书写行为本身就是洛阳文化内涵的进一步嬗变。由于脱离了真实的地理环境,洛阳对于南朝人始终有“日近长安远”的距离感,并且随着时间流逝,故地都城的形象也都逐渐变得陌生模糊。因此,“洛阳”在南朝时期相关作品中的书写主要是当时文人进行文学想象的结果,所借助的基础和媒介就是东汉和西晋的相关史料和文献。于是在于南写北、于今写古的双重时空错位中,洛阳形象的人文内涵相比汉晋有所拓展变化,具体表现为由“礼仪德治”转向“风流旖旎”,体现在城内场景和城中人物上。
二、洛城场景与空间形态
南朝文人在对洛阳进行文学建构时,需要将城市特有的意象在物质空间中展开。但由于诗人,也就是审美创作的主体,并没有相关的真实生活体验,因此无论是对于物象的描写还是情感的抒发,他们都必须借助前代文本,虚构出一个“身临其境”的想象主体,体验文化记忆中的故都场景。一些场景的反复书写正是城市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最集中的体现,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洛水、洛阳道和洛阳宫。
洛阳城在地理布局上南枕洛河,临水而建。河流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意义非凡,大河孕育了丰饶的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息的人类,自古以来人们将河流视作文明的源泉,河图洛书更是华夏文明之滥觞,再加上洛水本身也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因此它常成为古人吟咏书写的对象。历史上洛阳人常在上巳佳节去洛水边嬉游玩乐,如陆机《日出东南隅行》:“暮春春服成。粲粲绮与纨……方驾扬清尘。濯足洛水澜。”[2]652西晋诗人在作品中记录暮春佳节洛水边的游娱活动和美人的柔情绰态,具有婉丽韵味和生活情调。魏晋人对于美人、美景孜孜不倦的刻画与追求,正是当时审美意识独立的显现,崇尚美的情感思潮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学风格,促进了诗歌从“言志”到“缘情”的转变,这些文化记忆被南朝人所沿承,并进一步发展。如陈叔宝《洛阳道》:“建都开洛汭,中地乃城阳。纵横肆八达,左右辟康庄。铜沟飞柳絮,金谷落花光。忘情伊水侧,税驾河桥傍。”[2]2506岑之敬《洛阳道》:“喧喧洛水滨,郁郁小平津。路傍桃李节,陌上采桑春。”[2]2549等写洛阳依傍洛水,街道沿着洛水延伸纵横,城中建筑景观和城内人物的活动区域逐步呈现:波光粼粼的洛水之滨、河岸上随风舞动的金柳、洛水边郁郁芊芊的春日道路和路上艳如桃李的绝色佳人、佳人穿行于道路和如梦如幻的宫城建筑之间……由此视角衍生出的洛阳的道路和宫阙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建筑意象,南朝文人乐此不倦地在作品中描绘洛阳宽广开阔、车马骈阗的大道和高入凌霄的宫阙楼台,以彰显气度不凡的名都图景,以提及道路的诗句为例:
相逢洛阳道,击声流水车。路逢轻薄子, 竚立问君家。(沈约《相逢狭路间》)[2]1616
绿柳三春暗,红尘百戏多。东门向金马,南陌接铜驼。华轩翼葆吹,飞盖响鸣珂。潘郎车欲满,无奈掷花何。(徐陵《洛阳道》)[2]2525
铜驼街是魏晋洛阳城的中心街道,因魏明帝置铜驼于此而得名,郦道元《水经注》曰:“渠水又分枝夹路南出,经太尉司徒坊间,谓之铜驼街,旧魏明帝置兽于阊阖宫南街。”[3]398又:“自此南直宣阳门,经纬通达,皆列驰道,往来之禁,一同两汉。”[3]399从中可以得知铜驼街是从宫城正门阊阖门延伸出的大道,直达洛阳城正南门宣阳门,道路纵横通达、宽阔壮观。顺着道路的延展其他城市意象的布局也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春日的绿柳、奔驰如流的车马、妍姿艳质的美人和倜傥风流的翩翩公子……展现出人稠物穰、繁华富贵、风光旖旎的都市风情画。
再如提及宫阙的诗句:
日起罘罳外,车回双阙前。(庾肩吾《洛阳道》)[2]1982
日照苍龙阙,烟绕凤凰台。(王瑳《洛阳道》)[2]2611
从“十二门”“双阙”“苍龙阙”可见南朝诗歌有关洛阳宫殿的描写主要基于东汉时期的洛阳宫城。《后汉书·宣秉传》引《汉官仪》曰:“洛阳十二门,东面三门,最北门名上东门,次南曰中东门。”[4]930另外《后汉书·张让传》曾记载:“又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列于仓龙、玄武阙。”李贤注曰:“仓龙,东阙。玄武,北阙。”[4]2537诗人以神仙所居的“西昆”形容洛阳的楼阙,写日光照耀下的宫门和烟雾缭绕的高台,侧面凸显洛阳宫殿的崔嵬高大、恢弘富丽,而崇高的宫殿建筑天然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让人面对时产生愉悦的审美快感,从中更加深刻感受到雍容华美的帝都气象。
三、洛阳美人:时代审美生态的体现
洛阳城中的美人为南朝文人重点描写的对象,是他们文化心理与审美取向的集中体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美学特征与内涵都被进一步拓展挖掘。早在魏晋时期,曹植著有《名都篇》:“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2]431南朝时诗人孔奂也写下《赋得名都一何绮诗》:“京洛信名都,佳丽拟蓬壶。”[2]2536洛阳城内红颜美人和美少年无疑是名都风情的最佳体现。南朝诗人尤其是梁陈诗人对洛阳美人的描写更是细致具体,将他们的動作情态刻画得妩媚动人,诗作受到当时宫体诗流行的影响而具有浮艳绮软的特点,先以女子为例:
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萧衍《河中之水歌》)[2]1520
日出照钿黛,风过动罗纨。齐童蹑朱履,赵女扬翠翰。(沈约《登高望春诗》)[2]1633
桑萎日行暮,多逢秦氏妻。(萧绎《洛阳道》)[2]2033
《河中之水歌》中的“莫愁”是洛阳佳丽的代名词,从借鉴《孔雀东南飞》“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5]24和《陌上桑》“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5]4上可以看出此乃梁武帝萧衍的对于古辞的改写创作,萧衍所处的时代与地理空间已与洛阳相去甚远,所写的洛阳女子乃是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想象出的艺术形象。大量出现的“采桑”“秦氏”“南陌”一类词可看出美女的形象和采桑密切相关。采桑女子这一人物模式最早出现于《诗经》,如:“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6]144李白《〈诗经·魏风·十亩之间〉主旨辨析》中提及“子”应该是采桑女的丈夫,诗中的采桑女在结束劳动后怀着轻松快乐的心情和丈夫一同归家[7],传递出恬淡自然的美学情趣。把美丽形貌与采桑女形象结合应是源于汉乐府《陌上桑》,讲述的是秦罗敷在采桑时因为自己的姣好容貌受到使君调戏,但她凭自己机智勇敢拒绝并劝退使君的故事,罗敷对丈夫忠贞节烈,行为举止符合儒学教化,具有外表与精神上的双重美丽,被后世用于美女的代称。梁陈诗人笔下的洛阳女子是罗敷形象的拓展,因受到当时社会奢靡的风气和流行的宫体风格影响,洛阳佳丽的姿容形貌和心理情态被着重摹绘,她们的妆扮艳丽夺目,“燕裙傍日开。赵带随风靡。领上薄萄绣。腰中合欢绮。”[2]1620(沈约《洛阳道》)在洛阳街道上寻觅貌比潘安的俊秀男子,行为举止透露着内心的对于男子的思慕,可以说,相比汉代的忠贞烈女,南朝洛阳女的形象更加风流多情,流露出个人情感和情欲意识,道德教化色彩明显减弱,更多洋溢着艳情色彩。
与佳丽同时出现的还有美男子,诗文中对于他们的书写更多是借用魏晋时期的典故,尤以潘岳为最,如:
洛阳美少年,朝日正开霞。(张正见《轻薄篇》)[2]2475
潘岳河边返,情知掷果多。(李孝胜《咏安仁得果诗》)[2]2123
欲知双璧价,潘夏正连茵。(陈暄《洛阳道》)[2]2542
潘岳是西晋著名的美男子,《世说新语》里记载潘岳的美貌:“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洛阳女子为潘岳的美貌痴迷不已,常常在他出行的时候手挽手前去围观。刘孝标注引《语林》:“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8]643“掷果盈车”的典故由此而来。与潘岳并美的还有夏侯湛,《晋书·夏侯湛传》记载道:“每行止同与接茵,京师谓之‘连璧’。”[9]1491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期,由于对内在生命的发现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审美精神也变得高度独立,审美对象的扩大和审美活动的热衷促进了社会唯美风气的盛行。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赋予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0]208南朝文人是爱美者,他们不光懂得鉴赏美,还自己亲身创造美,无论是将美的形象以文本形式记录下来,还是通过文学书写传达理想的美学追求,本质都是通过审美表达对人的生命力的肯定。梁陈乐府中的洛阳佳丽被美男子眩惑,反映出美的确具有强大的征服力,能够唤起人心中最本能原始的情感,体现了南朝文人的审美趣味。
四、洛阳书写中的文学新变与文化心态
南朝诗人着重刻画令人目眩神迷的梦幻景观,描摹城内佳丽和美少年的柔情绰态,使得神圣的中原古都不同于前代“德治”的象征,而更多被赋予了富贵、华美、旖旎的气质,体现出社会尚美风潮的流行和审美的独立化,这与南朝诗歌内容与形式的新变相关。语言和社会的发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材料,推动文学新风格的形成。南朝时期是古代汉语的质变期之一,主要体现在书面语口语化和词汇复音化,涌现出大量的新词,而新词的产生又得益于社会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南朝政权长期偏安江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富足让士人恣情纵欲,社会上弥漫着浮华享乐之风,正所谓“江南久安,风俗奢靡”,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便呈现出绮靡的风格,士人创作时更加注重华丽精美的文辞、讲究文字雕琢,以“辞”来抒“情”。诗人在书写洛阳的过程中,常对词语进行修饰,如芳春、风烟、风尘、环佩、佳丽、蜜意、娇态等,诸如此类的词汇赋予洛阳城风物人情旖旎柔美的特质,使建构出的洛阳想象具有令人遐想回味的动人艺术效果。在艺术形式上,南朝时期的诗歌“好为新变”,在声韵方面追求节奏押韵和谐,联句运用对偶形式增强语言表现力,呈现出向律诗体式过渡的特点。许多诗句对仗工整、遵守平仄押韵,极尽洛阳物象之美。诗人寻觅诗歌语言的魅力,积极探索诗歌的格律,推动诗歌的精致化进程,使得诗逐渐与“托物言志”的传统相背离,走向抒发个体情感的道路,发展出全新的面貌。言“志”向抒“情”的转向使得洛阳的美学内涵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取得了突破。
“情”之转向同时也是南朝士人文化心态的隐秘体现,士人们抒洛阳之“情”本质上是对华夏故都所代表的中原正统的繁华梦忆。田晓菲在《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中提到:“南朝君主自视为正统汉文化的维护者……但文化的辉煌不能保证政权的正统性。”[11]244可见南朝政权虽是“正朔相承”,都城建康坐拥江南,社会民康物阜,但终归“僻陋吴越”,统治者也意识到若不都“天下之中”便很难获得政权的合法性,但南朝中后期的国力和凝聚力难以支持北伐行动取得实际战果,南朝士人也只能依依北望中原故地,遥寄悠悠黍离之情。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他们回避对当时北朝现实洛阳的书写,即便他们可能通过使者往来、僧侣流动、商业贸易来和北地进行文化交流,但他们似乎更愿意沉溺于历史的想象中,毕竟直面文化记忆中的南渡逃亡、回不去的家园和无力改变偏安现状的惨淡现实是残忍而痛苦的,不如在编织的幻想的梦境中且醉且歌。在那个梦里,战争和离乱都远去了,象征着大一统的东汉的巍峨宫殿与魏晋的中轴大道同时出现,富贵人家驾着车马驰骋,美男子与佳人在河边调情,而洛阳城永远停留在春光里……可见,为了转移对政权偏安且恢复无望这一认知,“北伐之志”在南朝的洛阳书写中几乎消隐,“风物之情”成了审美主体主要的抒发对象。洛阳繁华富贵的都市图景乃是诗人自身诉诸历史记忆的心理投射,他们丧失了体验的基础,只能参考依据史书文献中记载的汉晋洛阳空间和空间中的洛阳人物,在自己已有生活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文学想象与艺术创造。这种诗性建构既弥补了创作主体由于现实政治与文化错位而缺失的审美情感,也拓宽了洛阳形象的人文内涵。
注释:
①《史记》中记载,周公营建洛邑时,指出洛阳位于“天下之中”,在此地建都有利于对四方进行治理。反映出统治者在国家的制度设计上的理想:建立起以“中”为尊统御四方的礼制秩序。
②关于都城与文学双向建构的关系,详见康震《交互中的意义生成——都城与文学的双向建构及其文学史价值》,载《文学遗产》2021年第2期,第14-23页。
參考文献:
[1]沈约撰.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徐陵编,吴兆宜注.玉台新咏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毛亨传,郑玄笺,陆德明音义,孙祥军点校.毛诗传笺[M].北京:中华书局,2019.
[7]李白.《诗经·魏风·十亩之间》主旨辨析[J].学术论坛,2009,32(07).
[8]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6.
[9]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1]田晓菲.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