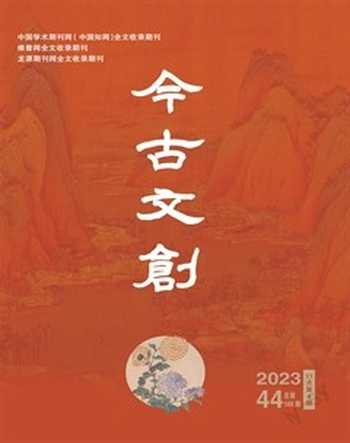“ 小红楼 ” 中有何可观
2023-11-20赵家和
赵家和
【摘要】清代文人沈复的自传体散文集《浮生六记》在民间有“小《红楼梦》”之称,其在书籍命运、故事情节、人物塑造等方面皆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有诸多相似之处。纵向来看,这种相似性乃是《浮生六记》对《红楼梦》的一种“文学延续”;横向来看,在今人的视角下,《浮生六记》在某些方面实现了对《红楼梦》的发展。本文以《浮生六记》为主,通过其与《红楼梦》的具体对比,进一步分析两书的异同点,继而探寻“小红楼”中的可观之处。
【关键词】《浮生六记》;《红楼梦》;“小红楼”;延续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4-0058-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4.018
一、引言
“五四”新文化革命时期,林语堂、俞平伯、林薇等人将目光聚焦至《浮生六记》一书,认为书中的某些特征与“五四文学”中的“人的文学”精神十分符合。为推动《浮生六记》一书的影响力,俞平伯于1923年将《浮生六记》校点后重新刊印,并在后来为德译本作序,林语堂则在1935年将《浮生六记》译为英文,助推《浮生六记》传播到西方世界。这是《浮生六记》在近代受到重视的体现,只不过此时学界的研究视角多聚焦于该书本身,并未在《浮生六记》与《红楼梦》的对比上下大功夫。
改革开放后,有关《浮生六记》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开始逐渐走向人们的视野。1980年,陈毓罴发表在《红楼梦学刊》上的《〈红楼梦〉和〈浮生六记〉》便重点对比了沈复和贾宝玉、芸娘和林黛玉的形象;1994年,张蕊青在《红楼梦学刊》上发表了《〈红楼梦〉与〈浮生六记〉的灵犀共识》一文,重点阐释了两书所存在的共性;2004年,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谭钟琪的《清末人情小说的民主主题层面——〈浮生六记〉与〈红楼梦〉比较研究》则从人物形象与主题两个方面分析了《浮生六记》相比《红楼梦》的可观之处;2007年,内蒙古大学的张晨光以《论〈浮生六记〉的现代性因素》为题,系统地阐释了《浮生六记》于封建社会背景下的进步性因素及其对现代文学的深远影响。
由此可见,关于《浮生六记》与《红楼梦》的对比研究,学术界已然有之。然就目前来看,关于两书的对比研究多聚焦在人物塑造、审美特征、情节内容等方面而较少系统化地阐释,关于《浮生六记》对《红楼梦》的“发展”方面的探究更有待拓展。本文以前人研究成果为基础,意图从“延续”与“发展”两大方面进一步系统、细化地去分析“小红楼”相比“大红楼”的“可观之处”。
二、延续之探 —— “小红楼”之名从何来
(一)时空的延续——历史的“巧合”
“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七年 (戊戌,公元1718年),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公元1763年2月1日),享年四十六岁。” ①而在曹雪芹去世的那一年,沈复出生了。当沈复的《浮生六记》成书之时,曹雪芹的《红楼梦》在社会上已然流行近二十年。
从两书的书名来看,《红楼梦》的题名和开篇便带有梦幻之意味,《浮生六记》的题名则来自“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之句;在书籍命运方面,《红楼梦》的后三十回稿下落不明,后由高鹗等人续补后四十回。《浮生六记》亦曾散佚,后经民间整理仅存前四卷,后两卷则被证实为后人伪造;从情节内容来看,两书皆描写了家族的兴衰史,并以家族之兴衰隐喻着时代之兴衰;就男女主人公关系而言,《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是表兄妹关系,《浮生六记》中的沈复和芸娘是表姐弟关系,两书的男女主人公的恋爱模式分别是“兄妹恋”和“姐弟恋”;此外,两书面向世俗市井的倾向明显,其人物形象的塑造与主题的表露则在相似中透露着明显的反封建色彩。
《浮生六记》与《红楼梦》的“共鸣”,既是两位作者诞生时代接近、成书背景相当的结果,亦是资本主义萌芽日益生长、封建制度“落日余晖”之状在文学上的反映。因此,造就世人心中“小红楼”的,既有历史的巧合,亦有大时代背景下的必然。
(二)反叛的延续——人物形象的反叛性分析
在场面描写与结构营造上,《浮生六记》并不如《红楼梦》之宏大,其以第一人称描写所见所闻,书中鲜活之人物甚少。但是,读者仍能透过两书中的具体人物,看到两书作者在人物塑造方面“反叛”的精神共性。
1.显性的反叛:性别
“《红楼梦》……从反抗传统文学史中女性受压制、被歪曲、被忽略开始,来表现女性意识的觉醒过程,批判男权主义文化。” ②以《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为例,在第二回,宝玉便讲出了那句著名的“水泥论”:“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③在形象塑造上,贾宝玉身上的女性气质显著。在第三回,曹雪芹用“大红箭袖”“长穗宫绦”来描述贾宝玉的穿戴,用“春晓之花”“桃瓣”等词语以勾勒贾宝玉的面貌之美。如此红紫粉嫩之词用在贾宝玉身上,使其本身具有了一种反抗自身性别趋势的女性美;在第二十八回中,贾宝玉通过女子的视角吟诵女性在情感上的悲欢离愁,以此表达自身对女性的共情:“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女儿乐,秋千架上春衫薄。”贾宝玉对女性的这种态度和关怀同薄情的贾琏、豪横的薛蟠等男子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也正是借贾宝玉之口表达了对传统性别观的一种明显颠覆。
在《浮生六记》第一卷中,沈复写到了对芸娘的评价:“芸若腐儒,迂拘多礼。” ④对于陈芸的多礼,沈复以“腐儒”二字形容,并明确地表示“余始厌之”。当陈芸因女儿身而不便随沈复远游时,沈复便告诉妻子:“来世卿当做男,我为女子相从。”至于性别形象塑造上的“反叛”,在陈芸身上则有一定的体现。在书中,陈芸因违背了当時的妇女道德规范而两次被放逐。第一次,芸娘帮助公公纳妾却没有及时告诉婆婆,致使婆婆吃醋不满,后又因在给沈复的信中用了“令堂”“老人”等词,而被公公视为侵犯尊严的不敬行为,遂被逐;第二次,陈芸想要为沈复纳妾,故同一位名妓的女儿——憨园焚香结盟,拜为姊妹。然而,当公公知道此事后便严厉地斥责沈复:“汝妇不守闺训,结盟娼妓。汝亦不思习上,滥伍小人……速自为计,迟必首汝逆矣!”虽然陈芸为男性纳妾之事为男权文化影响下的举措,但通过上述情节可知,芸娘之形象绝非传统“闺秀”之形象,她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人格,为公公纳妾以及和妓女之女结盟亦是其敏感多思和真性情的表现,而公公则作为封建礼教的代表压制着夫妻二人的自由。
2.隐性的反叛:制度
作为封建王朝整合地方力量、促进阶级流动、提高中央权威的重要措施之一,自隋朝以来,科举考试逐渐成为平民子弟翻身做官的不二选择。因此,无论中国百姓的家庭条件如何,多数父母都希望家里有人能够读书科举,以便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贾宝玉的家境,在前期可谓是充实无比,家中有着足够的条件和资源支撑其通过读书的方式走进仕途。然而,贾宝玉本人却对此不屑一顾。当史湘云劝诫贾宝玉去“为官做宰”时,贾宝玉便“大觉逆耳道”:“姑娘请别的屋里坐坐罢,我这里仔细腌臜了你这样知经济的人。”在《红楼梦》第七十八回,贾宝玉也道出了自己对“功名”二字的看法:“无奈今之人全惑于功名二字……我不希罕那功名,我又不为世人观阅称赏”。
沈复的家庭条件并不如贾宝玉富裕,但在前期也可谓是一个“小康”之家,其父以幕僚为业,并且想给自己的儿子安排同自己一样的前途。然而,沈复在《浮生六记》中所描写的幕僚生活甚少,即便涉及于此,也透过字句表达着自己的不满:“余游幕三十年来……惜乎轮蹄征逐,处处随人,山水怡情,云烟过眼,不道领略其大概,不能探僻寻幽也。”“而余则从此习幕矣。此非快事,何记于此”“馆江北四年,一无快游可记。”在《闲情记趣》一卷中,他更是直言萧爽楼之四忌:“谈官宦升迁、公廨时事、八股时文、看牌掷色。”幕僚仅是沈复顺遂父愿、谋求生计的手段,而其则本人喜爱游山玩水,不愿接触官场政治,当他“见热闹场中卑鄙之状”后,也敢于打破传统观念“易儒為贾”。
(三)故事的延续——《红楼梦》的“平行世界”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尽了贾府之奢靡、官场之丑态、人心之多变,而围绕宝、黛、钗三人风月情事的书写则更是让人回味无穷。在故事的最后,林黛玉郁亡,贾宝玉则在被抄家后出家为僧,徒留“终生误”和“意难平”的薛宝钗。《红楼梦》的结局令人唏嘘不已,而沈复的《浮生六记》则为世人提供了一个贾府之外的“红楼”:倘若林黛玉没有死,倘若贾宝玉未曾遇见薛宝钗,倘若大观园不曾存在,倘若贾宝玉同林黛玉趁早出走,一起过上布衣饭菜的生活,这场爱情会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吗?
答案是否定的。虽在某种程度上说,《浮生六记》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红楼梦》的“平行世界”,但在彼时的时代大背景下,每对有情人都难逃被封建社会荼毒迫害的命运。在《浮生六记》中,陈芸和沈复是表姊弟的关系,沈复的母亲常回娘家,故对其内侄女有一定了解。然而,沈母却只看到了陈芸身上的“柔”,却未曾预见其“刚”,加之沈复“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二者的结合乃是两个具有独立思想与叛逆精神的有情人结合。然而,“封建家长不能允许子女独行其是,要扑灭那些叛逆的火花。家长对子女的绝对统治权在法律上得到明文保证,因此在家长和子女的斗争中双方的实力是悬殊的。” ⑤
那么,既然沈复和芸娘在家中不得志,出走是否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呢?《浮生六记》中写到了沈复与芸娘的两次出走:第一次离家后,二人的生活相对来说还算过得去,能够“商柴计米而寻欢”。而第二次出走便显得格外凄凉:丈夫失业、妻子患病,求助亲友而见人情冷暖,凄惨流离而知世态炎凉。在《坎坷记愁》一卷里,沈复写到因无归处而“夜宿土地祠”之事,令人读之无比同情。在封建等级社会里,统治者不恤民情,家庭里等级森严,儿女情受尽压制,如沈复这般乐山水而厌政治的人也不得不做幕僚维生,然当其脱离幕僚身份卖画赚钱时,则“三日所进,不敷一日所出”。因此,沈复和芸娘虽能通过“反叛”的方式逃离封建家庭的桎梏,却逃不出封建社会的牢笼,无论是《红楼梦》中的宝黛还是《浮生六记》中的沈复和陈芸,当个人的思想行为与时代社会之氛围相悖,其悲剧的结局则已注定。
三、发展之探——“红楼”虽小,亦可观焉
(一)两性关系的发展——由情侣到婚姻
陈寅恪先生曾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道:“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艳昵之情景,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复)《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 ⑥回顾我国古代涉及两性爱情的文学作品,如唐之《霍小玉传》、元之《西厢记》、明之《牡丹亭》、清之《桃花扇》等,其情节重点突出了男女主人公为争取恋爱民主与封建父母及社会的斗争智慧,却极少描写“有情人终成眷属”大团圆结局后的婚姻生活,似乎言情文学的作者们只愿诵情侣爱情之悲欢,而厌婚姻生活之实在。然而,沈复的《浮生六记》则将“爱情”从抽象的文学世界拉回了现实人间,仿佛在告诉世人,婚姻并非爱情的“坟墓”。
以“爱情”为线索,《红楼梦》以宝黛的情感悲剧为故事结局,其他在书中出现的年轻女子几乎无一人收获了真正的爱情。《浮生六记》虽同样描写了夫妻生离死别之悲剧,但其重点勾勒的乃是婚后之事。书中的婚后之事有喜有悲,有七夕之日轰轰烈烈的爱情盟约,亦有夫妻二人的日常琐事。在沈复的笔下,爱情并未随着婚姻的成立而消亡,婚姻关系反倒成为两人情感稳固的基础。
(二)审美的发展——由大观园走向民间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美是生活’的论断出发,把美看作是日常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东西。黑格尔虽然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但在他的《美学》中却多次称赞荷兰画派对他们日常生活画面的描述。” ⑦《红楼梦》中便有多处内容描写了人物在大观园内的日常生活,这包含了人物的所见、所闻、所感:写大观园之景则有“帐舞蟠龙,帘飞彩凤,金银焕彩,珠宝争辉”,写红楼之器则有“赤金九龙青地大匾”“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写红楼之食则有“绿畦香稻粳米饭”“茄鲞”,写红楼之饮则有“千红一窟”“万艳同杯”……这些描写极尽奢华,其形容之生动令人读罢后如亲眼所见,在精神文化层面给予了读者一场宏大的“视觉盛宴”。然而,这些场景即便是今人也难有幸亲眼观之,且不用说古代的底层市民。在场面描写上,曹雪芹用尽才华笔墨,力图展示出一幅贵族生活图卷,但后人视之仍难免有一种“雾里看花”之“隔”感。
再观《浮生六记》,其所写场景虽不如《红楼梦》里大观园之宏观,但就时空的变换来说,从闺房之私到流离失所,从小康之家到山水林间,《浮生六记》的空间设置并不限于一“园”之中。在文本里,沈复用朴实的语言写到夫妻二人的住处:“饶屋皆菜圃,编篱为门。门外有池约亩许,花光树影,错杂篱边。”就所用器物而言,书中并没有大肆描写珍珠翡翠玛瑙等稀罕之物,而是多取材于“自然”:“觅螳螂蝉蝶之属,以针刺死,用细丝扣虫项系花草间,整其足,或抱梗,或踏叶,宛然如生。”在饮食方面,《浮生六记》中并无红楼奢华之宴,而是将朴素之“吃”作为情趣的一部分来写。芸娘喜食腐乳、卤味等味道重的东西,沈复最初讨厌此类食物,但尝后又成“喜食”,芸娘对此便做出了“情之所钟,虽丑不嫌”的解释。
“‘雅’在古代社会是封建等级地位的象征,平民百姓难以触及,而‘俗’则是人们真切朴实的生活。” ⑧《红楼梦》里写大观园贵族之奢靡,为读者提供了一朵精神上的“雾里之花”,《浮生六记》则通过更为贴近生活的审美,将文人的高雅幻想与理学的严肃教条抛之脑后,给予读者更为直接纯粹的世俗审美体验。
(三)“小红楼”在近代
当“五四新文学”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部分作家将目光聚焦到了《浮生六记》上。林语堂、林薇、俞平伯等近代大家《浮生六記》赞赏不已,并对《浮生六记》的海内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林薇指出:“《浮生六记》这种无目的、不为什么的文学,独抒性灵,它走出了暴力、道德、肉欲的泥潭,另辟一片芳丘,呈现了灵魂的清芬馥郁,构建了人的文学的小说美学风范……它上承中国古典文学人文精神之正脉,下则遥接‘五四’新文学,民初那些如潮如涌的言情小说皆不足望其项背。” ⑨从文本内容来看,《浮生六记》的现代性因素大抵可言四个部分:
1.男女人物塑造反映了个性压抑之痛苦及解放之需要。
2.由情侣书写到婚姻书写超越了传统多数言情不言婚之文学,某种意义上具有近代鲁迅的“反启蒙”思潮色彩。
3.写实主义成分与近现代西方写实主义创作新文学的倾向不谋而合。
4.审美的世俗化倾向与近代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审美方向一致。
再观曹雪芹的《红楼梦》,其因内容宏大、主旨复杂、解读多样的特点而被近现代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无数解读,“复杂性”成就了《红楼梦》在文学领域中的无上瑰宝地位,但也正因这“复杂性”导致了其“现代性”因素并不如《浮生六记》之纯粹。近代以来,学界多从文学、历史、政治之角度对《红楼梦》进行分析,“索隐派”与“考证派”也因这“复杂性”而争论不休,而沈复的《浮生六记》则因其独特而纯粹的“现代性”因素被作为“文学革命”的有力援助,这可以说是《浮生六记》在影响“纯粹性”的层面上对《红楼梦》的“被动超越”。
四、结语
综上所述,被称为“小红楼”的《浮生六记》虽对《红楼梦》具有文学层面的继承关系,但这并不代表其走不出“大红楼”的阴影。在某些领域,《浮生六记》实现了对《红楼梦》的发展,向世人呈现出了“红楼”虽小,亦可观之的文学状态。
注释:
①裴兴荣:《曹雪芹生卒年推定之新方法——从脂批入手直接推定曹雪芹的生卒年》,《运城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第69页。
②胡适、周汝昌等:《细说红楼梦——红学专家解读〈红楼梦〉》,蓝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③(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12-571页,文中《红楼梦》原文皆出于此。
④(清)沈复:《浮生六记》,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44页,文中《浮生六记》原文皆出于此。
⑤陈毓罴:《〈红楼梦〉和〈浮生六记〉》,《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期,第227页。
⑥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9页。
⑦张行:《小说闲话》,转引自黄霖等《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
⑧倪藤:《〈浮生六记〉的审美世俗化倾向》,《作家天地》2022年第24期,第23页。
⑨林薇:《清代小说论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104页。
参考文献:
[1]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长沙:岳麓书社,2001
[2]沈复.浮生六记[M].北京:三峡出版社,2011.
[3]胡不归.沈复年谱[J].胜流半刊,1945,(09).
[4]陈毓罴.《红楼梦》和《浮生六记》[J].红楼梦学刊,1980,(04).
[5]张蕊青.《红楼梦》和《浮生六记》的灵犀共识[J].红楼梦学刊,1999,(04).
[6]裴兴荣.曹雪芹生卒年推定之新方法——从脂批入手直接推定曹雪芹的生卒年[J].运城学院学报,2003,(05).
[7]谭钟琪.清末人情小说的民主主题层面——《浮生六记》与《红楼梦》比较研究[J].求索,20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