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芜尽处是春山
2023-11-18黎黎松塔
文/黎黎 图/松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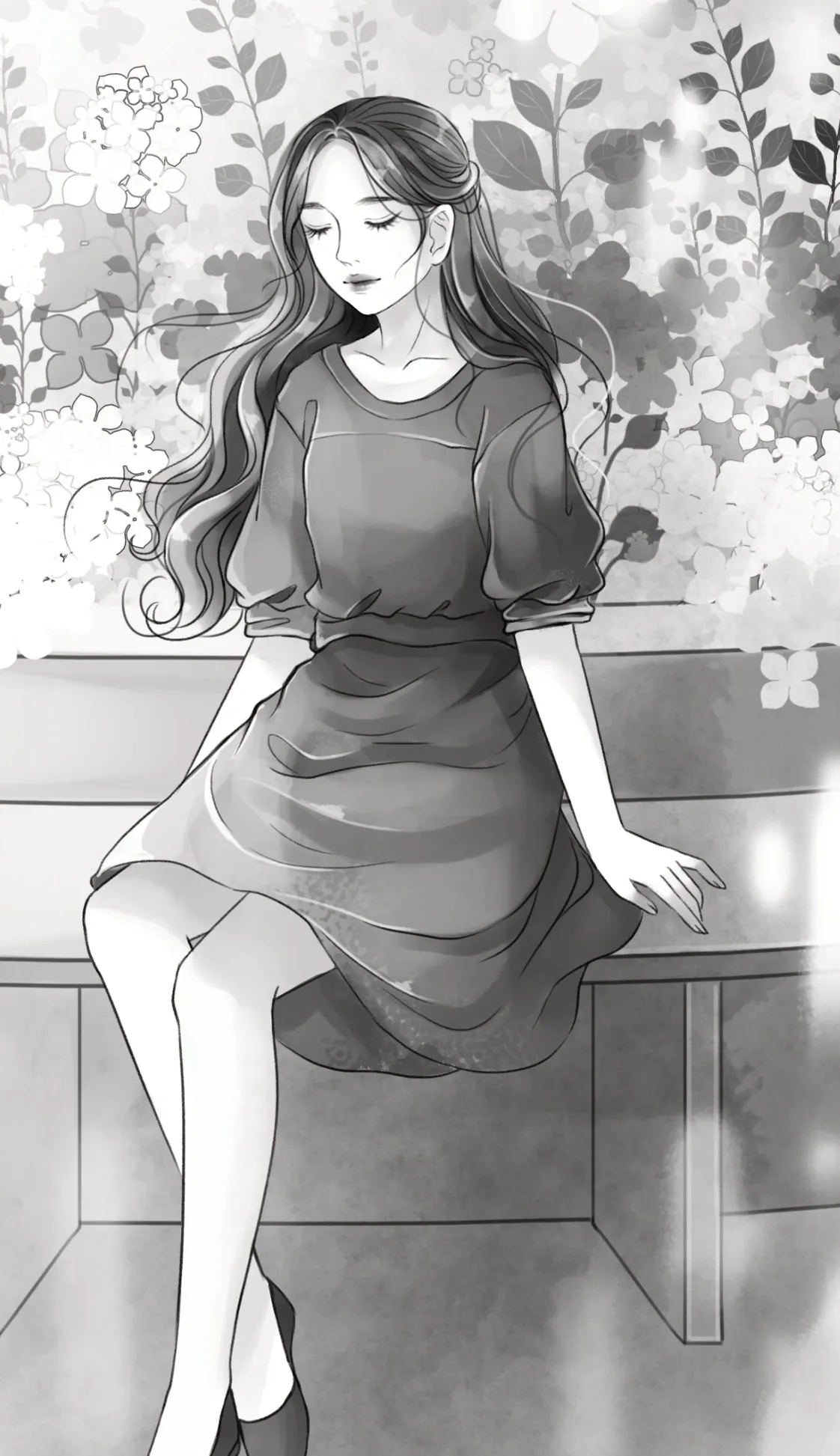
原来他没有一刻忘记过她。那首名为离别的叙事诗,在残破的独白里面目全非。
(一)
苏州的天白得让人感到压抑,像是雾霾困住了自由,怎么也抵不到尽头。每天都有人为生活奔波,没有任何人会停留。
我低着头向前走,迈着很大很大的步子。或许是因为逐渐昏暗的天,又或许是嘈杂人群,我浑身难受不适。
地上的水迹忽明忽暗,我抬起头来。原来,是下雪了啊。
又一年冬天了。
只是这里的一切都不属于我,我只不过是一个到处奔波的小白新手记者。
而我这次采访的人,不是高管公司CEO,亦不是娱乐圈那些花边消息,而是苏州赫赫有名的心理医生:付源安。
公司提前与付医生说过了,我向身边的护士询问,她带我上了楼。
电梯门“叮”打开,我也因这压抑的气氛颤了一下。有女孩子痛苦的抱紧头,有面色凝重的家长,也有穿着病号服黯淡无光的病人。
好像人间就是炼狱,对于他们来讲,度日如年的活着,何尝不痛苦?
总以为专业的心理医生都是上了年纪的,出乎意料,那位付医生玉树临风,风华正茂。可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他的眼神里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愁。
他温和的问候:“你好,请问怎么称呼你?”我出示自己的工作证:“黎黎。”
他的眼神停顿了一下,我像是看到了无数的雾霾蒙住了他,将他卷入一个漩涡里。
“付医生,有什么问题吗?”
他意识到自己失态了,淡淡一笑:“抱歉,没什么。只是想起了一个朋友,她也姓黎。”
“故人吗?”不知为何,我很想了解这个与我同姓的人。深知,十年生死两茫茫。
他没说话,我心便明了。
“付医生,这么多年了,让你坚持在这里的是什么?”
“将那些幻灭后的真心缝补好,”他看着窗外的明媚灿烂说:“我最初在这个位置上时,一心只想拯救更多的人,让他们重新活。只是后来我才明白,返航未必会变好。我现在只是想用我浅薄的医术,让更多的人变得快乐,快乐就够了。”
潮汐返航,不过是重蹈覆辙。
“付医生有过遗憾吗?”
他突然转过来,惨淡的笑了一下,终须有,句难酌。
“黎记者,你知道克莱茵蓝彼岸花为什么不存在吗?一个是绝对之蓝,一个是邪恶的曼珠沙华,就像大多数人容纳不了一个抑郁症患者的无能,弱小以及郁郁寡欢。”
可这到处都是你言我语的时代,谁不想奋飞横绝?
“黎记者,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二)
苏州的春天永远都温柔明媚,微风扶持柳絮去到更高的楼台,春光普照每一寸土地,灰尘四射光芒,淅沥雨点追寻池水的脚步。
付源安仍然记得那天,许久未联系她的妹妹打电话让他去市医院。
他以为妹妹只是闯祸了,直到进病房看到那个消瘦的背影。
“南絮。”
她哭着向他坦白,其实她这些天都在医院,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只好谎称在朋友家。她以为只是小病,毕竟她经常会犯小毛病。只是没想到,她的病情突然恶化,需要做手术。
付源安的手在不停颤抖,但还是笑着对她说:“我们一定可以治好的,我们不怕。”
他好像真的有超能力,突然安抚了她的躁动。
房门被打开,付源安闻声一看,是一个扎高马尾的女医生。她戴着口罩:“请问你就是南絮的哥哥吗?”
“哥,你还记得吗?她就是我常常和你提起的,我最好的闺蜜——黎沫。”他的某些记忆突然被唤醒,似乎有那么一回事。
“你好。”
打过招呼,她示意付源安出去一下,有事和他说。
等到他将房门关上,黎沫开门见山:“付先生,我是这次的主治医生。”她向他说明了情况,付南絮现在已经是肝癌中期,当下必须找到匹配的肝进行移植,这是目前治疗肝癌最有效的方法了。
黎沫停顿了片刻,声音变小:“但在此之前,需要进行化疗,可是……”她说不下去了,眼泪盈满眼眶。
他知道她要说什么,化疗就代表着要剃光头,而付南絮最宝贝她的头发了,平日里他碰下她的头发,就会被推开。
这太残忍了,平时没受过多少委屈的丫头怎么会受得了?这种大部分都是老年人患的病,怎么会落到二十多岁的她身上?
付源安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黎沫:“黎医生,有什么情况你联系我,我怕她接受不了。”
他进了病房后,黎沫看了一眼名片:心理医生。
可能有的相遇,就是触礁的船在等待一个响起汽笛声的港湾,恰逢其时,又如细风呢喃一样,不足以挂齿。
不知不觉付南絮已经在医院住了一周,化疗的日子为期不远,而有的事终究是要告诉她的。
付源安正要告诉她,一进病房就看到付南絮在给玫瑰剪枯枝败叶,她的头发上还粘上了白玫瑰花瓣,少女对玫瑰的热爱永远不止。
他走近她,话卡在嘴边,这只会给她带来不安和痛苦。
“哥,我想在剃光头发之前,去一次游乐园,可以吗?”
付源安愣住,他与付南絮对视了一眼,她只有尽收眼底的平静,没有任何掀起波澜的征兆。她那么聪明,其实一切都知道。哽在喉咙里的安慰终究没有说出来:“好。”
去游乐园的那天,付南絮叫上了黎沫。
车门打开时,付源安看到了黎沫,礼貌性微笑。
到游乐园门口时,付南絮嚷着要吃冰激凌,但是她的身体条件不允许她吃。黎沫立即阻止,哄骗她结束后吃。
付南絮不能玩刺激的娱乐项目,只好把重任交到其他两人身上,希望他俩代替她去玩。而她的说辞是,不能浪费门票。
黎沫脸上闪过难言之隐,欲罢,还是硬着头皮上了过山车。
系安全带的时候,付源安侧身一看,黎沫脸色发紫,紧张的栓住护杆。身为心理医生的他,心里明白:“黎医生,你要是害怕的话,可以拉住我。”
尾随音乐的响起,过山车急驰而过,腾空而起。黎沫条件反射往下躲,一只手死死抓住付源安的衣角,头靠向他的手臂。
过山车迎来第一个环,她整个人完全倾向付源安了,想喊出声却是徒劳,只希望快一点结束这人间疾苦。
下来时黎沫整个人都是软的,走路有点不平稳,付源安扶了她一下。她看到他那被自己弄皱的衣服,有些愧疚的道歉。
他正视着她,她眼里的真诚,惊恐以及将落未落的眼泪,凝结成明亮的琥珀。
“没关系。”
之后南絮提议玩旋转木马,她冲着前方那个高大的身影喊:“付大帅哥,你给我们拍照吧。”付源安还没来得及说话,两人就手牵手跑了。
她们朝着镜头露出灿烂的笑容,摆着各种鬼怪动作,仿佛没有病痛和压力降临到任何人身上,仿佛又回到小时候。
黎沫的眼睛在旭日之下生动得不像话,她向相机镜头比了一个剪刀手。付源安的心猛跳了一下,鬼使神差的为她拍了一张单人照,而这张单人照他并没有发给她们。
恰逢游乐园正在泼水,付南絮被路人泼了小半盆水,胜负欲极强的她在工作人员那里要了两个小桶,给了黎沫一个,黎沫被迫营业。
付源安拿她们没办法,随她们去了,正准备去一旁歇凉,水从头浇到底。他扶额转身,傻妹妹举起桶还想再来,他及时躲过。
“付源安!”黎沫第一次连名带姓喊他,他有些好奇是什么事,让她对他少了一些客气。
小半桶水直击他的脸,落得狼狈不堪,原本格格不入的他也失去了体面和僵硬。他抄起旁边装满水的盆,泼向两人。
顾虑到付南絮的病,他没太较劲,草草收场。
回去的路上,付南絮吃了药,药性上头,她很快就睡着了。黎沫探探她的头,还好没发烧,找了毯子给她盖上。
没料,付源安破天荒连续打了三个喷嚏,黎沫偷偷笑出声。
“付先生,感冒了?”她的语气里带着点调侃。他自己都想不到,多年未曾生病的他,居然会因为一次小小的泼水感冒,这未免显得有些矫情。
他解释:“兴许明天就好了。”她点点头,没再说话。
到黎沫家门口时,她打开车门没有下去,转头对付源安说:“付先生,你等一下,我上去给你拿点药。”
他有些意外,连忙拒绝:“小问题不碍事,等下我去药店买就行。”
“你忘了吗?我可是医生。”说完就跑上楼。
很久没有体会到人情世故带给他的善意和温暖。
黎沫提着一个小袋子朝他走来,他忽然想告诉她这些年所经历的事,但这个想法一出来,他就被自己吓到了。
她给他介绍药的作用和使用方法,她对病人无微不至的关怀,也许是冬日里的一束烟花,绽放出青山折腰的无限光景,也深刻在他心里落下烙印。
(三)
春去秋来,白雪覆盖最后一片萧瑟,落叶糜烂于尘土,海潮归零。
付南絮已经进入了化疗的第二个疗程,黝黑的长发落地,她还是接受不了,带上假发,就好像,什么都没变过。
黎沫偶尔会陪她去花园里散步,付源安也经常来照看她,但大部分都是她妈妈来照顾她,她爸爸在她幼时就病故了。
毕竟各有各的工作和职责,没办法做到寸步不离,他们要面对更多的病人,要面临太多的压力。
冬天的黑夜总来得太快,黎沫下班后独自走在小巷街道,看到苏州的繁华辉映,她突然感到特别的疲惫和无力。
没有什么胃口和精力,索性去超市买些速冻食品。
她选了不少东西,挑速冻食品时不知道该选什么,对着冰柜出神。
“黎沫?”迅速转头一看,是付源安。
她手足无措的挠挠头,有些意外,随后笑笑:“付先生,你怎么在这里?”
付源安看了她一眼,又盯着她的购物车,他皱皱眉,话里藏着不被人发现的笑意:“我来买些牛奶给南絮……黎医生那么喜欢吃零食?”
有意无意藏着购物车,还是被他发现了。倒也没什么,不过她每天灌输给病人不能吃零食的那些话,此时有点打脸。
付源安收收笑意:“这些东西还是少吃为好。”他的语气太温柔了,以至于她差点溺死在里面。两人寒暄了几句,他就先离开了。
黎沫结账的时候,服务人员告诉她,已经有人帮她付过,记在了那个人的账户上。不用猜也知道是谁,她发消息道谢。
有的过程总是早早收场,可世人总是把怀念拉得太长。
新年快到了,黎沫忙得抽不开身回家,今年又要一个人过节了。付南絮的病情化疗期间很稳定,移植的事也有了一些眉目。
付南絮向医院请了两天假,想回家过春节。
除夕那晚,黎沫打了电话给家人问好,想着随便弄些吃的就去睡觉,不料接到南絮的电话:“沫沫,我身体突然有点不舒服,你可以来下我家吗?”
她的话漏洞百出,黎沫也没多想答应了。
礼貌地敲敲门,心里已经演练了无数说辞面对她的家人。出乎意外开门的竟是付南絮,她神气焕发,哪有一点病发的样子,黎沫有种中计的错觉。
下一秒,她拉着黎沫的手向屋内跑,力气大得惊人,根本挣扎不了。
一进客厅就看到她妈妈:“阿姨好。”
“小黎你来了。”黎沫真的很佩服她妈妈,即使年龄已成既定,仍温柔端庄。
刚想开口问付南絮哪里不舒服,嘴里就被塞了一块巧克力,她瞪了瞪。
付南絮把她拉到角落,发出只有彼此能听到的声音:“知道你害羞,所以只好以这样的方式骗你来我家吃饭。”
黎沫狠狠拧了一把她的腰,害自己白担心。
付南絮跑进厨房,对着里面说:“哥,你好了没?我要饿死了。”话音未落,黎沫就闯进来。
四目相对。
付源安主动打招呼:“来了。”她猝不及防,尴尬地挥挥手。
他腰上围着一条粉色的围裙,正在认真做菜。属实没想到他还会做饭,粉嘟嘟的围裙挂在他身上,让他显得有些……可爱。
微妙的情感在她心里发酵的愈发浓烈。
付南絮探究的眼神飘出来,她的脸微红。
她和付南絮坐一起,对面是付源安和他妈妈。一抬头就与他眼神相碰,黎沫心里莫名激动,心虚的盯着菜看。
阿姨一直给她夹菜,热情地招呼她,并感谢她对付南絮的照顾。让以往都一个人在家过节的她,心生出温暖和酸涩,眼泪凝固又凝固。
“菜还合黎医生口味吗?”一抬头,就对上了付源安略带笑意的眼眸。
“很好吃。”这些年漂泊在外,很少吃到这样合她口味的家常菜了。他的笑声萦绕耳畔,她只觉周身好热。
饭后,她和付南絮主动洗碗,付源安没再多说什么,由着她们去。
等一切都弄好,时间不早了,黎沫想起身道别。付南絮看出了她的意图,拉拉她的手:“沫沫,今晚就在我家吧,等下一起放烟花。”
“留下来一起放烟花吧。”付源安端着水果朝她们走来,顿在嘴角的拒绝还是咽了回去,是很久没放过烟花了,她点头答应。
快到零点时,付南絮扯着她跑出门外,看到付源安早已站在那里等待她俩。
她站在中间,付南絮在她左边念着倒计时,付源安点燃烟花就迅速退到她旁边。
“十,九,八,七,六……”
耳边是南絮喋喋不休的倒计时,她魔怔一般,转过头定定地看着旁边的男人,他的视线在逐渐变短的引线上。
她在看他,他在看烟花。
“三,二,一。”
男人转过头来,刹那烟火被搁浅,他微笑着与她对视:“新年快乐,黎沫。”
“新年快乐。”那一刻,她无暇顾及昙花一现的美好,眼里只有他,穿越赫拉克利特的长河,隔着历历在目的过往,她找到答案了。
后面发生的事她没有太大印象,只记得最后付源安温柔地说:“谢谢你,能来和我们一起过节。”
不是青山不妩媚,只是玫瑰在长夜灯火走漏了风声。
(四)
付南絮的移植手术即将提上日子,黎沫和付源安忙前顾后,轮换照顾她。她总是打趣:觉得自己是黎沫和她哥养的小孩。
黎沫表面上假意要揍她,实际上内心还是会如潮涌动。
今年的春天来的很早。
偶尔遇到付源安,他们三个会一起去医院食堂吃饭,或者去楼下散步。苍白平凡的一幕,他记了很多年。
做手术的那天,黎沫是主刀医生。虽说医生面前,病人都一样,但她还是很担心,她怕手一抖……
想到那个场面,她浑身发凉。
付源安看出了她的紧张,轻拍着她的肩膀安慰鼓励。
衣角被拉了一下,她一低头,是付南絮躺在病床上:“沫沫别怕,我相信你。”黎沫的眼泪一下子跑出来,拼命地点头。
“沫沫,最坏的结果我都想好了,要是我出不了手术室,我的遗书已经写好了。”
黎沫捂住她的嘴,紧紧抱住她,向她保证,一定能平安出来。
付南絮哽咽地看着自家哥哥:“哥,我总是给你惹太多麻烦。要是我没出来,要好好吃饭睡觉,还有,替我好好照顾妈妈和黎沫,”
他握住她的手,摸摸她的脸,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
时间到了,她被推进手术室。
付源安站在手术室外来回踱步,都说医院听到的祷告总比教堂多,他只祈祷妹妹能平安度过这一关,她还那么小。
可他除了等待,只有等待。
从嘈杂的白昼到压抑的午夜,手术门终于推开。
看到医生如释重负的笑容,他缓了口气,成功了。手术室里传来“哐”的一声,他回头脑海闪过一个人影,是黎沫。
大步跑进手术室,有一个白色身影蹲在角落抱着头,全身都在颤抖。
他上前蹲下身握着她的肩膀,话语里有些许担忧:“黎沫,怎么了?”眼前的人突然紧紧抱住他,崩溃哭起来。付源安的手顿了顿,别扭地拍拍她的背。
“你知道吗?我真的好害怕,我好怕絮絮突然……”
“她身上好多血,止都止不住,万一突然倒在我的手术刀下怎么办……”
她还是没有办法做到像对待其他病人一样,去对待自己的闺蜜。
他轻轻回抱她,试图缓解她的恐惧:“你已经很棒了,南絮手术成功了,你拯救了她。”他满眼的心疼,用纸给她擦眼泪。
黎沫抬头泪眼朦胧地看着他,情绪转变了许多。他真的太温柔了,动了动嘴想要道谢,不料一股气流从嘴里冒出:“嗝……”
两人相视一笑。
付南絮仍是昏迷状态,白天是她妈妈和付源安照顾,夜里是黎沫。由于白天神经紧绷,术后又到处奔走,黎沫靠在病床边小憩。
熟睡间,有人给她盖上了毯子。突然惊醒看,是他来了。
“付……”付源安对她做了一个“嘘”的手势:“睡吧。”黎沫暗自发笑,他那么大个人在病房,她还睡得着吗?
“你怎么来了?”他明明白天才来过。
付源安似笑非笑地盯着她看,盯得她后背发凉。他靠近她的耳根,温热的气息扑面而来,耳朵酥酥麻麻的,不禁战栗:“我来,是想确定一个答案。”
答案,两人心知肚明。
她在他眼睛里看到了那个假装疑惑的自己,拼命掩饰喜悦却满是破绽的自己。
“当真不知道,我喜欢你?”
算是表白吗?他无比真诚地看着她,她试图从中找到一丝玩笑的意味。可是没有,他是认真的。
“快答应我哥。”
病床上的人突然开口,吓了她一跳。付南絮虽然脸色苍白,但却眨巴着眼睛一副看戏的表情。
“黎医生赏个脸,答应我一下呗。”黎沫转过头,心里的秘密好像被发现了。那就这一次吧,勇敢一次。
“好。”
就这样,因为一个不像告白的告白,她和付源安莫名其妙的,在一起了。
没有意外的尴尬,就像是朋友一样。他们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一起在江边散步,最后,他像情窦初开的少年,牵住了她的手。
很久后,她问:“付源安,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像她这样的人,呆板愚钝,不会讨好人心,什么都不是。
他这么一个明媚的人,应该是被更热烈的人包围。
而付源安却只是揉揉她的头,很平静地看着她,笑得很干净:“当宇宙量子碰撞时,我对你的想念才变得有迹可循。”
一句看似随意的情话,却让她红了眼眶。
做完手术的付南絮不能外出走动,每天拿黎沫和付源安打趣,在他俩之间来回审视。
两人偶尔在她面前秀恩爱,她哪受得了这些刺激,直接放话把人赶出去,在心里骂黎沫重色轻友。
付南絮常常会望着窗外发呆,她那么喜欢到处跑的人,却被困在这张床上,困住了夜莺对海洋的仰慕,也困住了她对夏天的朝圣。
“哥,等夏天到了,你开车带我和沫沫去旅游吧。”
“好。”无论怎样,他永远都支持她,永远做她坚强的后盾。
后来有一天,付源安送了黎沫一对莫比乌斯耳环,简单纯粹。他亲手为她戴上耳环,并郑重其事地说:“莫比乌斯环有很多寓意,没有出口亦没有尽头,但好在这没有归途的旅程,兜兜转转我遇到了你,也庆幸我遇到的是你。心理学上称之为,灵魂伴侣。”
“你不用做任何改变,对我来讲,这就是你最特别的地方。”
“黎医生,你拯救了这么多人,那让我保护你一次吧。”
黎沫的眼泪怎么止也止不住,他真的,总能给她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总能戳到她最敏感的地方。
相似的灵魂总会相遇。
不是所有遇到的人都能冠以“soulmate”,一生能遇一个“soulmate”,百事从欢。
半月后,黎沫和付源安如往日一样约会,正游玩开心时,黎沫接到医院的电话,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快速接听。
电话那头的人依然在说,夹杂着哭声和吵闹声。那一刻她的灵魂被揪起,整个人被透支掉,只剩最后一口气。
她艰难的转头看着身边的他,与此同时,他也接到了电话。
(五)
付南絮是下午三点离世的。
死因是供体肝脏与患者本身产生了排斥反应,导致器官衰竭不幸去世。
黎沫死死盯着床上被白布遮住的人,她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听不到阿姨的哭声,听不到探望人的哀怨声,也听不到那个笑靥如花的女孩喊她的名字。
她听到灵魂摔落高空的破碎声,听到自己没有任何色彩的道歉:“阿姨,对不起。”苍白无力的道歉,显得格外多余。
付源安站在床头沉默不语,看不到任何表情。直到亲人将妈妈安慰走,直到深夜只有黎沫和他时。他蹲在床边拉着付南絮早已发冷的手,用很小很小的声音:
“不是说,一起去旅游吗?小骗子,怎么每次都食言。”
“哥每次都能满足你,能不能满足我一次,醒过来看我一眼好不好?”越来越小的声音,心疼的、痛苦的、委屈的。
但没有埋怨的。这样痛苦的病,对她来讲,算是一种解脱。
“黎沫,我没有妹妹了。”
三天后,是付南絮的葬礼。
黎沫看着墓碑前那个明亮的女孩,刚咽回去的眼泪又难以控制地冒出来,要是南絮还在,肯定又要嘲笑她这个爱哭包了。
她抬头看到深不见底的太阳,晕倒在地。
在一个空旷的房间,她看到付南絮全身是血躺在手术台,她身上全是血,付南絮的血,黎沫不停的做心脏复苏,却怎样都救不了她。
黎沫“啊”的一下子惊醒,全身冒冷汗,原来只是个梦。
艰难睁开眼,手被付源安紧紧握住,靠在床头的他被吵醒了。
“好点了吗?”他的声音低哑得让人害怕,听上去很久没有休息过,事实上他的确没有休息。
“付源安,对不起……”
他抱住她,将头埋在她脖颈间,用气息发声:“什么都别说,让我抱抱你。”让我抱抱你,企图将自己从深渊拉回人间。
好像一切都是梦,他和她还牵着手,付南絮还好好活着,他们在等待那个迟到的夏天。
可游园惊梦,只恨太匆匆。
后来黎沫总会做相似的梦,每次从噩梦中惊醒,只有无休止的失眠和漫长的黑夜与她作伴。
渐渐的,她把付南絮的死归结到自己身上,她是主刀医生,也是间接害死她的人。
黎沫给病人做手术时,手总是颤抖不止,她看到手术刀时,那些痛苦的记忆又被反复撕扯出来,扔在她面前。
时间久了,主任就让她好好调养,短期内不接手术。对于一个外科医生来说,是多么残忍。
付源安听到消息赶来,却发现黎沫蹲在办公室门外发呆。他心疼地抱住她:“沫沫,没事的,都会好起来的。”
黎沫再也忍不住大哭起来,她的脑海里不断回放着南絮的影子,她死前眉头紧锁的模样,让她不断自责痛苦。
“永远好不了了,是我害了她……”无论付源安怎样安慰,她都听不进去,陷入自己盛大的悲伤中。
他只能紧紧把她抱进身体里。
她的话越来越少了,有时候话还未说完,就陷入了沉思。付源安作为心理医生,当然明白她的症状。
有天黎沫拉着他,安静看着他,他差点以为那个活力焕发的女孩回来了,可下一秒又被幻灭:“付源安,能给我一些安眠药吗?”
付源安没有答应她,安眠药这东西,一旦吃上就会有瘾。他决定这段时间陪在她身边,这样或许会让她安心一点。
他睡客房,她睡主卧。门没有关,好让自己能在她害怕时第一时间出现。
黎沫每晚都会做噩梦,惊醒后总会看到付源安担忧的眼睛,让她感到自责无助。在付源安的哄睡下,又沉沉入眠。
一周后,黎沫接受心理治疗。
付源安盯着那个早已没有容色的女孩,心痛到窒息。在他的指引和检查之下,她被查出患有“重度抑郁症”。
他给她开了许多抗抑郁的药物,摸着她的头说别怕。
去吃饭的路上,黎沫看到朝气蓬勃的单车少年,追着捣蛋鬼跑的女同学,天空蓝得没有尽头,只剩沉甸甸的热气,从荒芜里长出绿意。
“付源安,你看,夏天到了。”夏天到了,等它的人却先离开了。
“是啊。”
听不到共鸣的叹息,下过一场就凋零。
(六)
黎沫总是靠那些药坚持下去。
有次她拿起水果刀在手上比划,付源安跑过去抢掉,不小心划到他的手。她握着他的手不停道歉,眼泪没有断过,他只是轻轻安慰说自己没事。
他能理解她,那是她的心病,时间久了会好的。可他最后,还是没等到。
如同往常一样,黎沫被噩梦惊醒,付源安寻声跑过去,看着她抓狂,到处翻找药片,但怎么也找不到。
她似乎忘了,那些药,早就吃完了。
他拉住她狠狠抱住,像是要把她嵌进自己的身体里。黎沫挣脱不了,只好死死捂住嘴巴,压制着声音哭起来。
过了许久,她突然捧起他的脸,眼里出现从未有过的冷静:“付源安,可不可以吻我?”
他愣了一下,温柔地抚着她的脸颊,慢慢靠近她的唇,吻上去。唇与唇紧贴,他和她的气息互相缠绕,冷静的,温暖的,爱护的,安抚的,以及不舍的。
她推开他的怀抱,背对着他,垂下头低低地说:“付源安,我们分手吧。”
她不要成为他的累赘,牵绊他的藤蔓。付源安本来就该生在隐隐青山,陪伴他的应该是无限恩泽,而不是为她失去原则和汪洋。
“好,记得按时吃饭睡觉。”
他还是那样温柔,仿佛刚刚没有人提出分手。她躺进被子里,怕再看他一眼,下一秒就会后悔。
付源安为她盖好被子,熄灯关上门。过了几分钟后,是大门开关的声音。
他走了,她的生活恢复一潭死水。
她重新回到医院上班,休息时间总会想到付源安。她尝试着不依赖他,却还是习惯不了没有他。
她不知道的是,付源安一有空余时间就会来医院偷偷看她,然后又离开。
主任把黎沫叫到办公室,面色凝重对她说:“黎医生,上头有两个无国界医生名额,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意向?”
她这些日子的压抑和愁苦,主任都看在眼里,希望她出去看看更好的世界,散散心,放下那些心事。
“黎医生,你不用急着回复我,做无国界医生很光荣,但同时也有很大风险。这事你先考虑一下。”
她明白的,她知道最坏结果是什么。眼里闪过付源安的身影,他坚定选择她的眼神,他担忧的神情,心心念念,全是他。
“主任,我想去。”她不该困在这里,她不该一蹶不振。
主任深深看了她一眼,良久后,他说:“去准备一下吧,不出意外的话就这两天。”她点头。
黎沫走的那天下起了大雨。
她站在机场四处张望,但是她要等的人迟迟没有出现。候机室突然响起她的班机呼叫,心里空落落的,大概是不会来了。
刚要过安检时,就听到一个急切的声音:“黎沫!”
他还是来了。黎沫放下行李,跑过去抱住那人,她给付源安发过消息,但她不确定他会不会来送她。
好在,他来了。
“去了那里,要好好照顾自己。”她听得出他话语里的担忧和不舍。
黎沫踮起脚尖,亲了他的脸颊,做了认真的告别:“付源安,我走了。”她没说什么时候会回来,他默契地没问。
她笑着消失在他的视野里。
日复一日,他变得忙碌起来,每天咨询的病人很多,休息时间越来越少。只要一闲下来,就会想起那个女孩。
所以他总不停地忙着,不刻意地去想念她。
后来他开展了很多关于抑郁症的公益活动,拯救了无数的抑郁症患者,让那些人重新看到月落星沉。
他希望远在异国他乡,她能畅然释怀,他只期望她功德圆满,长亭古道,定要过得再热烈些。
半年后。
付源安收到主任的消息,她回国了。
主任说他们失联很久了,联系上的时候是他们回国的消息。
放下手中的事务,他特意去花店买了一束玫瑰,与她神似的顽强玫瑰。
听到她的飞机班号响起,他在人潮汹涌中寻找她。找了很久,终于看到与她同行的医生,但没有她。
他到处观望,依然没有她的影子。
她的同伴走到他旁边,手捧一个盒子,面色沉痛对付源安说:“抱歉,黎医生没有和我们一起回来。”
他那一刻心脏抽痛,眼睛发红:“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们在治疗过程中,遇到了战争。”天崩地裂时,他听到身体里的呜咽。
快要抵达永无岛的船只,被退涨的潮打回深海。
(七)
来年暮春,他携海棠去看望她。他蹲在她的坟墓前,照片那头的她笑得很开心。
他想起那个春天,她站在西湖前对他说,好想和他一直这样走下去。他想起那些夜里,被抑郁症逼到末路时,仍然在他面前表现得很平淡。
想起在烟花绽放的那一刻,她眼里藏不住的爱意。他其实,早就知道了。
可是,她从来都不给他机会回答。
“你怎么还真走啊?”
“不是说会变得更好吗?”
“你骗我。”
怎么能说走就走,一句话也没有留下。要是知道结局是这样,他一定不会放她走。
物是人非,事事休。
海棠的花语是,我想你了。
故事到这里就完了,我听得眼泪纵横。我不知道,这么多年的每个夜里,他是怎样度过的。
那么,克莱因蓝最后到底象征什么?
思考之余,付源安给了我一张请帖,我惊喜地看到赫然在目的新郎。
他要结婚了。我那一刻的心情是挺复杂的,这说明,付医生已经从那些过往里走出来了,但我也难过,为什么天地两隔。
“恭喜,付医生。”
他无奈地说:“没办法,家里人等不了。”我想问他,那你,你甘心吗?最终我还是没有问出口。
他继续忙他的工作,我笑着离场。
在明早之前我要把今天采访的稿子写完,虽然累,但我收获颇多。付源安要求在他婚后第二天发表,我答应了。
婚礼我没有去,被周身的工作缠住脚,只能托人送去祝福和贺礼。虽只见过寥寥数面,但在我心里他已是朋友。
文章发表的那天,我去公司时,进门就听到同事的唏嘘声。我很好奇,凑到他们的电脑旁看“心理医生付源安逃婚”以及“无国界医生”。
原来,他早就计划好了。实在难以想象,这么一个完美体贴的人,到底是在经历了怎样的精神内耗后,选择背弃台上的人离开。
那一刻我想到了,克莱因蓝。
他妄图将灰烬构成思念的网,穿渡无人之境,尝试引起她的注意。
“克莱因蓝的谜底是什么?”
“是寂静给寂静渡上一层膜,是窒息在深海里无动于衷,是俄罗斯套娃式的想念,是永无止息的爱。”
原来,原来。
他没有一刻忘记过她。
那首名为离别的叙事诗,在残破的独白里面目全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