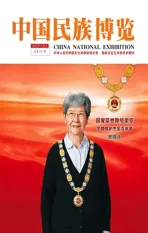词条叙事:文学人类学的新对象与新可能
——以“折毛”的“罗斯宇宙”为例
2023-11-09王鹏
王 鹏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207)
引言
文学人类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从20 世纪60年代末起,文学与人类学学科都难以隐藏双方话语中所具有的一种共通性和互渗性,从各自“母本”中分娩出来,走向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文学人类学。两大学科从泾渭分明到合二为一的过程招致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其实,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开始到后来格尔茨、波亚托斯等学者的出现,该学科都一直属于一项被建构中的系统性宏大工程。
20 世纪80 年代,中国学界陆续引入文学人类学的相关方法理论,国内的文学人类学也在对象域、问题域上出现多次转换和拓展。文学人类学总是试图在没有多少经验和理论参照的、多种要素正在生成和缠绕的领域里,生产出一些新的见解。[1]在这近40 年的时间里,越来越多来自于文学、人类学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们纷纷投入其中,以新思考、新问题、新材料不断推动文学人类学研究向前发展,从而发现学科的新对象,探究学科的新方法。比如萧兵、叶舒宪等运用“原型批评”理论,对《论语》等中华文化经典进行重新阐释。尤其是以“民俗神话学”为核心,[2]独创“四重证据法”等,[3]来对古史、神话等进行文学人类学研究。
除此之外,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还聚焦于口头传统、歌谣、仪式等活态文学形式,形成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有一大批学者借鉴叙事学理论,对小说进行了人类学式的阐释,如:任红红的《莫言人类学书写中的乡村世界》,认为该小说通过对个体故事的不断呈现和强化,从整体上书写了作为人类的一个群落的文化模式[4];马硕的《新时期小说仪式叙事研究》[5];张栋的《新时期以来小说神话叙事研究》[6]等。
相比之下,本文以“新对象的出现”为线索,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关注“折毛”创作古罗斯历史的个案,为文学研究提出一种新的文体——词条体小说。进一步阐明文学作品不能被定义为文学艺术和审美价值的唯一标准,也更不是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认为词条叙事具有破除虚构与真实这组二元对立的实际意义,通过分析“折毛”在历史叙事时依托的形式上的秘密,阐释隐藏在作者叙事实践背后的共享文化符号池,企图在为文学人类学的研究确立新对象的同时,进一步拓展学科的对象域、问题域。
一、从词条叙事说起:环环相扣的“罗斯宇宙”
这些词条不是一些孤立的有关古罗斯历史的意义单元,而是一张庞大的叙事文本网——每个词条之间都有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以“折毛”创作的词条“卡申银矿”为例,根据作者描述:该银矿自1344 年被发现后就成为维尔大公国的重要资金来源。在大公国灭亡之后,莫斯科大公国以及后继政权还在继续开采。不过在现实世界的古罗斯历史中并没有“卡申银矿”的存在,也没有这段挖掘四百多年的史料记载,但是由于文学的在场,作者通过想象、象征等创作方式使得这段地方史更具有形象性、故事性和情感性,引得公众信以为真。
文学作品从来不是枯燥的历史材料堆砌,它会创作出不同的人物在其中演绎人生戏剧。在“折毛”描写的一场长达180 年的“特维尔—莫斯科战争”中,她讲述了数十个家族的爱恨情仇以及上百人的生平传记,还虚构了相应的家族纹章、人口图、地形图。可见作者提供的不是一种干枯的历史性知识结构,而是通过艺术的写作手法将真实的描写与对意象的理解并置,从而提供了关于地方的感性知识。“罗斯宇宙”中包含着作者对人生和人性的理解,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是虚构的内容,为什么能如此轻易让读者信服?这种以词条叙事的文体对文学与人类学的融合以及新兴学科的建设又有什么积极意义?进一步思考,事实与虚构真的是一组决然的二元对立吗?“折毛”创作的虚构文体及其,值得在文学人类学的视域下获得新的阐述与反思。
二、新对象的确立:在虚构与事实之间
20 世纪西方思想界的“语言学转向”引起了新文学观的产生,使得文学的定义不止局限在具有一定程度价值的语言作品之中——文学除了包括小说、戏剧、诗歌等书面文学外,还包括神话、传说、仪式等口头传统和表述体裁。正如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茨维坦·托多洛夫所说:“没有任何特征可以将文学与其他类型的话语区分开来。‘文学’是任何形式的人类生命的表达,它包括人类的思想、观念、审美和想象。”[8]因此,艺术和审美价值不是将作品定义为文学的标准,而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也应包含更广阔层面的娱乐、广告、出版、电影等。“折毛”的词条体小说无疑是一种新的文学探索,其独创的网页词条叙事可以理所应当地成为文学人类学的新的研究对象。
“折毛”的作品逻辑自洽,看似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实则是虚构的小说作品,正所谓“诗比历史更真实”。[9]亚里士多德认为诗和历史都具有真实性,但两者的真实性不在一个层面上。诗所写的是符合可然律或必然律,反映世界本质和规律的具有普遍性的事情。诗人将形式作用于质料体现出的“现实”超越了当下的时空限制,具有预见性和哲学性。而历史则是质料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所描写的只是业已发生的经验的个别事情,处于一种“于事已然”状态。这种状态不需要多加修饰,融入诸多思索,相对于诗而言它只是具有个别意义、未经解构的物质材料,而诗要做的正是对原有历史事件的解构与哲学层面认知的灌输。“折毛”将一个个人物的人性形式作用于质料,然后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书写出来的文本就会更具有逻辑性、预见性,比历史具有更高的“真实性”和“普适性”,也更能引发读者的共鸣,最终成功地向读者传输了他的“罗斯宇宙”观。
“折毛”的个案冲击了我们原本对“虚构”和“事实”的理解中固有的二元对立观念,即假设存在一种有关“真理”的狭义概念,这实质上造成了我们对于“虚构”的本质的误读和贬低。词条叙事的加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文学人类学弥合这种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所带来的嫌隙。这种对于虚构与事实“唯二”的分类路径本就是一种认识论上的缺陷,它实则使我们丢掉了对事物认识的更多可能性和多面性。与此同时,也使得我们将“真理”逼迫至本质主义的危险境地。我们将“虚构”中的所有成分都排除于获取“真理”的方法或路径之外,将想象力在“真理”(更准确说来是“知识”)的方法论中的位置降低,使得我们对人性理解的多重维度被削减了。
“折毛”的词条体小说很好地将虚构与事实拉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因为任何有思想来源的文本在认识论上都是平等的和有用的。正如曼特尔援引19 世纪历史学家麦考利勋爵的话说道,“历史必须在想象中燃烧,才能被理性所接受”,为了“找回历史,我们需要有严谨、正直、不屈不挠的奉献精神和怀疑主义的冲动”,但“如果我们想要增加价值,就不仅仅是想象过去是怎样的,还要去感觉过去是怎样的……”历史学家通常会遵循证据的线索,诗人也会这样做;不同的是,诗人还会把过去的事情重新处理,把使人成为人的形式从档案的框架中解放出来。
三、词条体小说的叙事实践
词条体小说,顾名思义,是以“词条”为载体而写作的小说。其叙事实践包括了口头与书面在内的人类叙述行为和艺术。总体来看,词条体小说的特点有三个:一是该种叙事的文体由词条及其释义构成;二是作者会将各事象按某一框架罗列出来,最终编织成有情节、有逻辑的文本网;三是情节并不连贯且完整,而是一种碎片化、集成化的书写。这三大特点可以用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认定的一个词语来概括,那就是“延异”。“延异”是从时间流变的维度着眼,分析能指在符号生成中发生的迭代性变化。[10]大多数人会武断地认为,一个词语必然有着某种该词汇每一次迭代都捕捉到的本质含义。其实,每个词语的含义都处在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结构主义式的“终点”,我们每使用一次,都可能导致该词的意义发生变化。就像查字典,字典上把“马”解释为动物,而动物本身也是一个需要解释的语言符号。我们为了查清什么是“马”,看到了“动物”后,就再查“动物”,而“动物”又是生物的一大类,就再查“生物”……这样从一个能指到另一个能指无限制地查下去,形成了一张“能指的网”。
这样看来,尽管每个词条的链接都构成一个独立的意义岛,但词条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因为文本中每个独立词条的意义完成都需要其他词条的参与——在其注释内容中需有其他词条进行说明。所以词条体小说的实质就是从词条到词条的过程,是词条意义的相互链接和生发。词条体小说中的每一个词条都处在不断生成且变化的过程,因为符号之间的链接模式使得每个词条所指意义的到来总是被不断延迟,其承载的所有意义也就不能充分地呈现于某一链接定格的网页中。通过词条间的相互联系,小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开放的文本网络,这也为词条体小说作者的写作实践带来了新内容。
虽说每一篇词条体小说的具体文本会根据所描述的不同“他文化”系统而产生变化,但在写作的实践过程中还是会存在一个作者与读者共用的公共文化符号池。在这个文化符号池里包括了作者和读者共享的历史文化知识以及对那个“他文化”的前理解。每当作者进行写作的实践时,便从池中选择、提取文化符号,不同的作者对这些符号有不同的分类、整合与呈现方式,这便在叙事行为、实践或艺术当中有了创新。接着便是对读者进行文化传输,使得读者们装有前理解的文化符号池也泛起层层涟漪。一个电影爱好者,像我一样点击了“托尔金”“指环王”“霍比特人”,他之前或许从没听过这些词条,但他立刻就能认出这些东西属于他所知所爱的那个中土世界。
四、结语
文学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自然也在演绎和述说着关于人、族群、文化、社会的故事。人类学赋予我们认识人、族群、文化、地方的理论和方法,自然也能帮助文学拓展其对象域、问题域。中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者也正尝试生产、创新和发展文学人类学自身的知识体系。
总之,当文学人类学遇到“折毛”的“罗斯宇宙”,人类学可以运用其敏锐的学科视角在田野中发现词条体小说这一新的文学形式探索,并进一步扩大文学的边界,拓展其对象域,提出有关打破虚构和事实惯有二元对立的固有思维模式,使得文学艺术和审美价值的标准不仅仅局限于文学作品。而文学又可以自身的方法,做文本的深层解读,领悟词条叙事的内核“神韵”,总结词条体小说的叙事形式,提升人类学自身的思想深度与理论纵深。在这样的学科氛围中,文学人类学必能担负起更重的学术使命,在面临新机遇、新挑战时显得从容不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