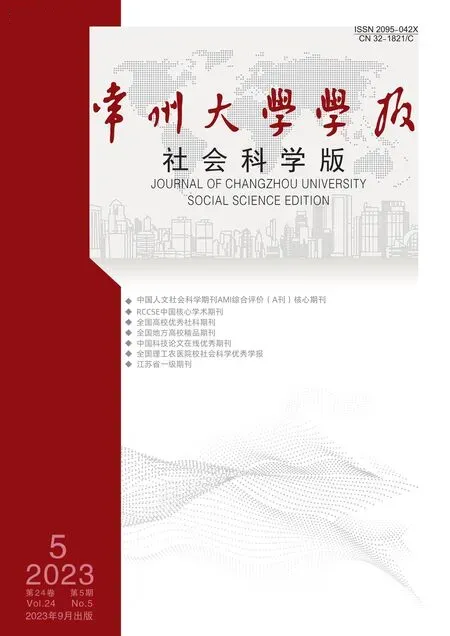论古代人异遇合小说的暗化叙事时空
2023-11-08高阳
高阳
人与异类(1)按照古人的思维,异类通常指神仙、妖魔、鬼怪、精灵等异于人类的智慧群体。作为非人类群体,尽管异类拥有异于人的特性(特殊的生活习性、特异功能等),但其与人同在现世,甚至可能共处同一时空。本研究所涉及的异类更多是指人格化、人性化的异类(或可幻化具有人的形貌,或语言思维举止与人相似),而人格化、人性化的特点也成为人异遇合的前提。超现实遇合的题材在古代文学中源远流长,《诗经·生民》《楚辞·九歌》等先秦诗赋可窥见人异遇合的影子。相较于以抒情见长的诗赋,这一题材在以叙事为主的小说中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从“张皇鬼神,称道灵异”[1]29的魏晋志怪,到“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2]的唐代传奇,及至“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1]172的明清志怪,人异遇合题材久盛不衰。在小说中,人异相遇交往的叙事时空呈现出明显的暗化特征。学界既往研究已注意到小说叙事时间的夜化倾向,而空间暗化尚未得到全面而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对小说叙事时空的分析,特别是小说中光线与视线设置的考量,是小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人异遇合小说入手,分析夜化叙事与暗化叙事的关系,进而深入暗化叙事的时空建构,探讨暗化叙事在人异遇合小说中的作用,以期对小说叙事研究方式的开拓有所裨益。
一、人异遇合小说中的暗化叙事
在认知有限的古代,人们大都认为异类是真实的存在,《左传》《山海经》等史传方志中不乏异类的身影,而文人将其作为创作的素材亦便自然。小说中的异类具有人的特点,如拥有人的样貌、渴望满足自我需求,甚至促狭狡猾;同时,异类也拥有自身的特性,如异于人的生活习性、特异功能。尽管人异有别,但异类的人性化特点为人异相遇、交往提供了可能,人异之间相遇交往的过程就是人异遇合的过程。同时,遇合需要一定的时机,而暗化的时空背景即人异遇合的时机。
(一)人异遇合

随着时间的推移,“遇合”含义有了新的变化,逐渐产生男女相悦爱恋的内涵,如南宋词人吴文英《惜秋华》的“怅遇合、云销萍聚”,“遇合”特指男女爱恋交往。诚然,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人与异类之间恋爱、婚配、交合,这是中国小说史上咏叹不绝的话题之一”[6],诸如《谈生》《绿衣人传》《青凤》等展现人与异类婚恋的古代小说不胜枚举。人异婚恋的发生历经人异相遇、交往的过程。然而,婚恋只是人异交往类型的一种,人异遇合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以“遇合”概念观照古代小说中人与异类相遇交往的故事,无论是人异从相悦到婚恋,还是人异彼此斗智斗勇,抑或人异互助扶持,诸如此类皆符合人异遇合的特点,因而以人异遇合统而言之。
魏晋志怪不乏人异遇合故事,直至明清,人异遇合小说久盛不衰,《剪灯新话》《聊斋志异》等相关篇章是人异遇合小说的典型。值得注意的是,人异遇合往往发生在暗幕笼罩的环境,诸如昏暗化的日暮夜半(《通幽记·李咸》“三更后,云月朦胧”、《聊斋志异·辛十四娘》“薄暮醉归”)、遮蔽性的书斋房舍(《子不语·匾怪》“夏夜读书斋中”),以及阴冷寒凉的天气(《六合内外琐言·二浦二石》“冬月,云曀风发”),遇合的环境呈现出暗化倾向。从早期简略记叙人异遇合的黑夜与荒地郊野,到明清时期详细描绘朦胧暗化的时空图景,暗化叙事贯穿人异遇合小说发展的始终。
(二)从夜化到暗化
暗化叙事关涉小说的时间设置。近年来,古代小说的时间设置问题受到学界重视。21世纪初,李桂奎等人的《论明清文言小说时间设计的夜化倾向》[7]一文首次提出明清文言小说叙事时间的夜化倾向,指出夜化时间既服务于小说朦胧和恐怖美的主旨,又适应限知叙事和内部聚焦的要求。此后,李桂奎通过《〈水浒传〉时间设置的“夜化”与叙事效果的强化》[8]、《〈水浒传〉的“夜化”叙事形态及其文化意蕴》[9]二文正式提出“夜化叙事”,古代小说的夜化叙事研究逐渐进入学界视野。“夜化叙事”被提出后,相关研究大致在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聚焦具体文本,剖析《金瓶梅》《聊斋志异》《子不语》等小说中的夜化叙事形态及作用;另一方面,针对某一题材小说,探究诸如人鬼冢墓遇合小说的夜化叙事。学界既有的夜化叙事研究,特别是针对《聊斋志异》《子不语》等夜化叙事的分析为深入人异遇合小说的暗化叙事提供了借鉴,本文希冀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进。
从魏晋志怪开始,人异遇合小说的时间设置就呈现出夜化倾向。早期人异遇合小说中的夜化叙事较为粗简,往往以诸如“夜”一类的简略笔触一笔带过。随着小说体制的发展,人异遇合小说中的夜化描写逐渐丰富,诸如“月朗风清”(《八朝穷怪录·刘子卿》)、“三更后,云月朦胧”(《通幽记·李咸》)、“时值上弦,幸月色昏黄,门户可辨”(《聊斋志异·狐嫁女》)等。从最初的一笔带过到富有文采的描绘,夜化叙事经历了从无意书写到有意粉饰的过程。然而,人异遇合的时间并非局囿于夜晚,拂晓黎明、云阴之昼、薄暮黄昏也成为小说中经常出现的遇合时间。如果仅以“夜化”一词统摄拂晓、薄暮、黄昏等,难免不够周全。纵观古代人异遇合小说的时间设置,无论是昏黑的夜半还是晦暗的薄暮黄昏,抑或夜幕将尽的清晨破晓,这些时间段在书写的表达与视觉的呈现上皆以朦胧掩映、晦暗不明为主,体现出光线暗化的特点,故而以“暗化时间”统称之。
“凡遇,合也。时不合,必待合而后行”,遇合需要一定的时机,那么,特定的时空背景就是人异遇合的时机。诚如高小康的观点,文学叙事就是“在故事中构造了一个独立的时空结构”[10]。暗化不仅在于时间设置,也在于空间构造。因此,对空间的考察也是全面分析人异遇合的必由之路。从空间的角度讲,人异遇合大都被设置在人的房舍书斋、异类的生活场所以及荒郊旷野等空间。这些空间本身带有一定的视觉遮蔽性与位置隐秘性。在暗化时间的配合下,这些空间进一步遮蔽了光线与他人的视线,成为暗化的空间。此外,人异遇合的环境也时常辅之以晦暗阴冷的天气,诸如“大雪崩腾,寂无行旅”(《聊斋志异·娇娜》)、“每当月黑夜深,风清露冷,林间篱畔,鬼声啾啾”(《子不语·张鬼耳》),这些恶劣阴冷的天气营造了晦暗寒凉的氛围,呈现出暗化的特征。因此,人异遇合的时空图景由昏暗的时间、遮蔽的空间以及特殊的气象三部分组成。
二、暗化叙事的时空图景
昏暗的时间、遮蔽的空间以及特殊的气象共同形塑了人异遇合的时空,人异遇合小说以暗化叙事来展现人与异类之间的相遇与交往。下文将详细分疏遇合时空的三个构成部分,从而探究暗化时空在小说叙事中的功能与意义。
(一)昏暗的时间
时间既是物理现象也是文化现象,“凡是对文化和社会方面感兴趣的人,都必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考虑时间问题和变化规律。反过来说大概也对,凡是对时间问题感兴趣的人,也都不可避免地对我们时代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发生某种兴趣”[11]。时间关乎人的生产与生活,特别是在农耕时代,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具有一定的秩序,这是民间与官方的共同诉求。“时间分配,说到根本处是一个有关‘秩序’的事情。在古代中国的一统社会里面,时间分配是很重要的,无论民间和官方都一样重视。民间关心它,自有民间的理由,这是因为生产和作息需要。……在没有充足照明条件的时代,人们只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顺应自然并不是为了表现‘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情怀。官方重视它,也自有官方的道理,因为对作息时间的管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社会秩序的管理。”[12]人依据光线昏暗与否安排休息与活动,遵循着“明而动,晦而休”的秩序,而异类与之相反。在古人的观念中,光线昏暗时往往是“狐鬼惑人的时候,而且还变怪百出,让人畏惧”[12]。诚然,文学不仅来源于生活,而且反映着人们对生活的认知与思考。鉴于古人认为异类通常出现在视线不甚明朗的晦暗之际,故而在人异遇合小说中,光线的昏暗意味着异类的登场。
人异遇合时间的暗化突出表现在夜晚被设置为主要的遇合时间,这一倾向在早期的人异遇合小说中就有所显现,如《搜神记·苏娥》“夜犹未半”、《搜神记·汤应》“至三更竟”,再如《幽明录·捉鬼》男子“至夜”遇鬼。至唐代小说,人与异类在夜晚遇合也是常态,如《集异记·李佐文》“约三更,晦稍息”、《河东记·申屠澄》“风雪不止”之夜。在明清小说中,发生在夜晚的人异遇合越来越普遍,诸如《剪灯新话·牡丹灯记》“月黑之宵”、《聊斋志异·胡四姐》“会值秋夜”、《子不语·狐生员劝人修仙》“夜读书西楼,门户已闭”、《夜谭随录·某领催》“虽有微月,为轻云所蔽,亦不甚明朗”。虽然光线昏暗之夜是发生人异遇合的主要时间,但人异遇合并非囿于夜晚,不甚明朗的薄暮、拂晓也存在人异遇合的可能,如《甄异记·杨丑奴》“将暝”、《夷坚志·双港富民子》“短日向暮,冻雨萧骚”、《聊斋志异·董生》“冬月薄暮”、《后聊斋志异·药娘》“一夕”等。“暝”“暮”“夕”指日落的黄昏,此时人准备收工休息,异类则跃跃欲试进入人的生活。此外,夜幕将尽的清晨也是人异遇合的可能时段,如《集异记·韦知微》“忽一日晨朝”、《聊斋志异·画皮》“早行”等。
在小说中,人异遇合的时间囊括了夜、暮、夕、晨等,这些暗化时间往往借助表现暗化特征的具体物象来呈现,此即时间物态化的表现。“由于时间本身看不见,摸不着,没有质感,因此要牢靠地把握时间,必须借助某种带有标志性的参照物。基于古老的‘宇宙’观念,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带有物态化的倾向。”[13]16时间的物态化不仅让人异遇合的时间更加具体,而且让读者获得了更加真切的时间体验。小说通常借助有一定光亮的物象来强化不够明朗的日暮夜晚,月、灯、烛无疑是光线昏暗的体现。相对于灯、烛,月是一种自然物象,它常伴随着夜幕降临而出现,“月夜”“浮云蔽月”的月色为人异遇合平添了朦胧。除了月,灯、烛也是古人在夜晚或其他天色昏暗时必不可少的照明工具。灯光、烛火的摇曳不仅是人异遇合时间暗化的体现,而且能够烘托昏暗朦胧的氛围。然而,比之月,灯、烛还发挥着串联遇合情节的作用。以灯为例,其在小说中常成为主人公出场、退场标志,这一功能在《剪灯新话·牡丹灯记》和《聊斋志异·双灯》中有很好的体现。在《牡丹灯记》中,女鬼符丽卿在婢子金莲挑双头牡丹灯的前引下进入乔生的视野,自后但凡符丽卿夜间或云阴白昼出行,必有牡丹灯在前指引,直到符丽卿被押赴九幽而牡丹灯被烧毁作结。因此,牡丹灯引导、见证了符丽卿与乔生的遇合。《双灯》大致如此,魏生结识的狐精女郎亦是伴双灯来、随双灯去,双灯成为魏生与狐精遇合的结构性功能物象,对小说的叙事有着特殊意义。
叙事时间的暗化倾向是构建人异遇合暗化时空的需要,反映了人异遇合对昏暗光线的依赖。然而,光线的昏暗不仅在于时间的设置,遮蔽的空间也是造成昏暗的重要因素。换言之,昏暗是时间与空间共同形塑的结果。因此,深入人异遇合小说亦需要对遇合的空间进行探讨。
(二)遮蔽的空间
小说的空间是一个宽泛的系统,它不仅包括小说的艺术空间(或称为“文本空间”),也包括小说的创作空间,甚至小说的传播接受空间也属于小说空间的范畴。虽然小说的空间体系较广,但最核心的是艺术空间。小说的空间与时间彼此依存,“小说既是空间结构也是时间结构。说它是空间结构是因为在它展开的书页中出现了在我们的目光下静止不动的形式的组织和体系;说它是时间结构是因为不存在瞬间阅读,因为一生的经历总是在时间中展开的”[14]。构建人异遇合的暗化时空不仅在于设置暗化的时间,还有赖于搭建暗化的空间。
人异遇合通常发生在光线昏暗的薄暮夜晚,而遇合的空间也呈现出不甚明朗的特点,诸如家舍书斋、墓冢坟茔、荒郊路途、深山林荫等。以上空间或多或少遮蔽了光线,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空间也隔绝了公众的视线,加之暗化时间的配合,这些空间的暗化特征更加明显。为直观分析暗化空间的特点,根据遇合的参与者与空间的关系,暗化空间可以分为隐私化的暗化空间与非隐私化的暗化空间:隐私化的暗化空间指那些完全属于个人的空间,既可能是家舍书斋等个人的生活空间,也可能是墓冢等异类的生活空间;非隐私化的空间既包括具有一定程度的隐私化又具有一定程度公开化的空间,如自家耕种的田地,也包括完全非隐私化空间,如荒郊山林、古寺庙宇。
隐私化的空间是远离他人干扰的独处空间,加之光线暗淡的时间背景,这一空间既遮蔽了光线,也遮蔽了他人的视线,因而成为异类登场的合理空间。家舍书斋等人的生活起居空间是常见的隐私化空间,小说对这种空间的叙述通常较为简略,常借助相关物象体现,如“展被与榻而炽炭焉”(《聊斋志异·董生》)、“夏夜读书斋中”(《子不语·匾怪》)、“其夜妇独寝,半掩其扉”(《耳食录·上床鬼》)。值得注意的是,家舍书斋中的人异遇合有相当一部分发生在男性主人公与女性异类之间。这种人异遇合的模式通常表现为:当男性独处于隐私化的空间时,女性异类便出现在他们的视野,进入其私人生活。这些女性异类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恪守“男女之大防”的女子,她们往往对男子嘘寒问暖,甚至以身相许。如《聊斋志异·林四娘》中,女鬼林四娘不仅主动接近夜里独坐的陈宝钥,而且“不甚抗拒”其示好;又如《阅微草堂笔记·哑鬼》中书生夜宿自家废园,有艳丽女鬼窥窗,遂“招使入室”。在暗化的空间里,不仅女性的举止越乎礼法,男子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对伦常的背离:一种表现为男子以言挑逗,女性异类或半推半就或直接迎合;另一种则表现为女性异类以身许之,而男子欣然受之。对于双方有违常理之言行的产生原因,后文将详细论之。
除房舍书斋,墓冢也是一种隐私化的空间,只不过其属于异类的隐私化空间。发生在这种空间里的人异遇合通常表现为人在相关物象如灯火(实际上是鬼火)的引导下进入墓冢,人的所见所闻充当叙事视角,人异遇合就此展开,如《青琐高议·范敏》中范敏在灯火的导引下进入女鬼的墓冢。
与隐私化的空间不同,诸如山林、荒亭等非隐私化的空间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尽管如此,这类空间也因地理位置的原因而遮天蔽日、远离人烟。换言之,开放性不妨碍其遮蔽光亮与视线,因而也成为人异遇合的空间选择。于人而言,山林等空间意味着陌生,对陌生空间的好奇乃至恐惧激发了人的想象力,这种幻想是激发人异遇合小说创作的重要心理基础。因此,人宿于荒亭或行于山林时遭遇异类的情形在小说中比比皆是。此外,非隐私化空间还包括远离人迹的古寺庙宇。寺庙因其开放性为行人提供了旅途歇宿的场地,也因其清净为读书人提供了潜心学问的场所,诸如《聊斋志异·聂小倩》《骇痴谲谈·庙中鬼》等,皆是发生在寺庙中的人异遇合。作为遮蔽他人视线的空间,寺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远离道德伦理的暗化空间,特别是当其作为读书的空间时,“书生置身于如此空间场景之下,就可以摆脱道德的约束力,七情六欲禁锢之所便成为放纵情欲的温柔之乡”[15]。
遮蔽的空间不仅为人异遇合提供了合理的场所,而且强化了人异遇合的暗化特征。然而,人异遇合小说的暗化叙事不仅在于设置光线昏暗的时间与视线遮蔽的空间,还在于风、雨等特殊气象的烘托。
(三)特殊的气象
古往今来,人的活动与气象关系密切,衣食住行无不与之关涉。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气象对人的影响尤为突出,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文人捕捉到气象对创作的意义,气象逐渐进入文学领域。古代诗词中有大量的气象描写,诸如“北风其凉,雨雪其雾”(《诗经·北风》)、“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李清照《醉花阴》)一类的气象描写层出不穷。诗词里的雨雪风霜已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气象,而是成为抒情言志的载体。作为叙事性文体,小说的行文也存在大量的气象书写。气象及其所形成的天气对小说的叙事有重要意义,“在古人看来,因‘天时’变化而形成的天气异常意味着宇宙失序,与之发生感应的社会就会发生变故,这给小说叙事带来了很大动力”[13]31,“不仅可以绾合人物的命运、渲染人物情绪,而且还可以用来解释事情的是非成败”[13]34。气象及天气具有“特定的审美价值,在情节构建、人物塑造、文本修饰等方面都有相当助益”[16],因此,分析人异遇合不能撇开对小说中相关气象的解读。
风是人异遇合时空常见的气象,它既可能是月色笼罩下掀起的烟月清风,也可能是阴雨浸润下飘洒的苦雨凄风,还可能是秋冬季节刮来的阵阵寒风。以清风为例,诸如“时春季夜阒,风清月朗”(《博异志·郑还古》)烘托了静谧的氛围,甚至阵阵清风的吹拂意味着人与异类将开启一段浪漫的爱恋。《八朝穷怪录·刘子卿》中,刘子卿“居庐山虎溪水”,于“月朗风清”之夜遇到两位神女并与之建立恋爱关系。无疑,清风烘托了遇合时空,为人异恋爱的浪漫与朦胧增值。又如阵阵寒风,《子不语·三头人》张氏三兄弟晨行旷野遇“大风西来”,随后三人结识三头怪人。西风寒冽,冷冽寒风强化了遇合时空的恐怖,烘托了阴森的氛围。与之相似的还有露。《子不语·鬼伴客》中,孙逢吉于坟墓遇鬼时“凉露侵肌”。因此,无论是朗月清风还是晦暗阴风,抑或侵肌寒露,都发挥着营造特殊氛围的作用。
雨也是人异遇合时空常见的气象,通常与风同时出现,也具有烘托遇合氛围的作用。由于绵绵雨幕的朦胧性,雨的昏暗强化作用更加明显,甚至成为人异遇合时空最为重要的气象。同时,雨也作为制约、阻碍人物行动的主要因素,对情节的构建有重要意义。阴雨绵绵之际,不仅道途泥泞难行,而且光线晦暗,人的行动被阻滞。特别是行于旷野深山而遭遇凄风楚雨,人受阻通常会寻找避风躲雨的空间,或误入荒宅古墓,或在异类的引导下进入异类的生活空间。因此,遇雨受阻是推动人异遇合情节发展的重要叙事手段。这样的遇合情节在小说中尤众,如《志怪·张禹》,张禹行经大泽遇雨,忽见一宅遂求寄宿,此宅实为女鬼的墓冢;又如《夷坚志·双港富民子》,富子在“短日向暮,冻雨萧骚”的暗化时空下遭遇狐精;再如《聊斋志异·阿纤》,奚山“途中阻雨”借宿古家而结识鼠女阿纤。此外,对人的行动产生阻滞的还有雪,如《河东记·申屠澄》,申屠澄行路“遇风雪大寒”,见一茅舍烟火温煦于是借宿,进而结识虎女并与之结为夫妻。可见,雪与雨在小说中发挥着相似的作用。
气象是构建人异遇合暗化时空的重要部分,发挥着烘托遇合氛围、推动遇合情节发展等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气象并非构建暗化时空的主要内容,人异遇合时空形成的关键在于造成昏暗光线的时间与遮蔽视线的空间。虽然风雨等气象可以强化遇合时空的昏暗性与遮蔽性,但其更侧重氛围的烘托,让人异遇合时空的暗化特征更加饱满。
三、暗化时空的叙事功能
与题材内容相得益彰的时空布置有助于小说叙事的展开,而人异遇合小说所搭建的暗化时空契合了人异相遇交往的背景,因而具有很强的叙事功能,在构建合理情节、剖析人性欲望等方面取得了诸多叙事效果。
(一)构建异类的活动主场
尽管人与异类皆是遇合的参与者,但异类在遇合交往中往往充当主动的一方:他们或直接招惹人,如《搜神记·汤应》狶怪与狸怪三更夜半敲门意图谋害汤应,《吴兴老狸》狸怪于田间幻化人形来捉弄农人的儿子;或间接引起人的注意以进入人的生活,如《剪灯新话·绿衣人传》绿衣女鬼每每日暮路过赵源家舍门口以引其注意,《子不语·西园女怪》幻化成美女样貌的精怪在夜晚吟咏诗句从而引起周生与陈生的关注。
异类之所以成为人异遇合中的主动者,原因在于遇合时空是异类游刃有余的活动主场。鬼狐精怪等异类的活动带有阴世的神秘色彩,古人认为异类惑人总是发生在光线昏暗之时,而且要隔绝大多数人的视线,以此维持神秘性,因而暗化时空为异类的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环境。以鬼为例,虽然现代科学认为鬼并不存在,但古人大都相信鬼是存在的,而且认为鬼的力量非常神秘。“从原始社会开始,人们相信鬼灵有三个特点:(一)鬼灵是虚幻不实的影像,(二)这个影像的活动极为轻灵缥缈,(三)这种影像似的鬼灵总是在黑夜活动”[17],这反映了古人对异类生命形态、生存状态的认识。尽管古人认为鬼具有异能,但由于鬼有阴气,光线明亮、人气旺盛的时空会损耗其阴气,其在人世的活动仍有不少限制,只能在暗化的环境中活动。因之,小说中的鬼多出现在夜幕下的书斋、遮空蔽日的山林。不仅如此,晦暗避人的时空也能够掩盖异类的特殊习性与幻化破绽,诸如《甄异记·杨丑奴》獭怪借黄昏及男子的家宅来掩饰其幻化女形不够彻底(“衣裳不甚鲜洁”“手指甚短”)。此外,加之寒风凄雨的恶劣气象烘托,暗化时空成为异类活动的最佳选择。因此,异类的活动不仅未受暗化背景的影响,反而因暗化而如鱼得水。
相较之下,暗化时空使人的能动性被削弱。从时间的角度讲,人于黑夜将尽的晨晓苏醒,在日出高照的白昼劳作,于日落西山的薄暮归家,在黑暗笼罩的长夜入定。时间的变化决定着光线的变换,古人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光线的明暗,明亮则动,昏暗则休。同时,光线晦暗使人对外界的视觉认知能力下降,自我保护能力随之削弱。换言之,人的能动性随着光线趋暗、可视度降低而减弱。从空间的角度讲,无论是家舍书斋还是荒郊山林,这些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也遮蔽了光亮,使人的处境趋暗。更为突出的是,空间的遮蔽决定着外界视线的屏蔽,人被置于独处的空间。因此,人的行动缺少他人的助力,其对外界的防御能力被削弱。此外,阴雨风雪等气象因素阻滞了人的正常活动。概言之,人的能动性在暗化时空受到抑制。
人的能动性被抑制,而异类的能动性反而因暗化时空得以更好地发挥。人异相遇、交往在暗化时空铺陈,昏暗的时空不仅意味着异类的登场,而且成为异类的活动主场。鉴于暗化时空是异类的活动主场,人往往属于被动的一方,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异类成为人异关系中的主导。然而,尽管异类在暗化环境中的活动更加自如,甚至幻化害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异类在人异遇合的关系中永远处于优势,小说中不乏人战胜异类的人异较量,诸如《搜神记》中的安阳亭书生、汤应凭借勇气与智慧除掉幻化的精怪。此外,人异遇合小说亦不乏异类通过进入暗化时空以借助人的力量来达成迁葬、复仇、洗冤等诉求,如《搜神记·苏娥》中何敞不仅帮助客死他乡的女鬼苏娥迁葬故里,而且将杀死苏娥的凶手绳之以法。无论是人战胜异类还是人帮助异类达成诉求,二者皆反映出人能够在不利条件(暗化时空)下通过自身努力而有所成就。这部分小说意在凸显人的勇气、张扬人的智慧以及歌颂人的品质,反映了人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尽管暗化时空是异类的活动主场,但异类往往幻化人形,举止思想与人趋同,人异遇合表现为人与人的相遇、交往。进一步讲,异类的所思所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的所思所想。换言之,人的思想行为披上了异类的外衣,甚至某些隐秘的想法在暗化时空得以“明目张胆”。因此,小说中的暗化时空对展现人性欲望有重要的意义。
(二)折射人性的阴暗欲望
暗化时空为异类提供了天时地利的活动环境,异类的言行随之而从心所欲,甚至肆无忌惮,作祟时见于人异遇合小说。异类作祟的类型众多,恶作剧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搜神记·吴兴老狸》狸怪幻化为农人的父亲,并以父亲的身份“骂詈赶打”儿子,但其无意伤害儿子,纯属捉弄别人而寻开心。又如《子不语·匾怪》,秀才夏夜读书,书斋中的匾怪一副顽劣相“视下而笑”,反复用浓须触人,虽无伤痛但令人烦腻难耐,无法专心读书亦无法安然入睡。恶作剧让被捉弄的一方陷入窘境,而恶作剧的施行者却因他人的窘境获得乐趣。恶作剧是对权力的模拟,施行者控制恶作剧的整个场面,因被捉弄者的无知乃至窘迫获得快感。一如匾怪与狸怪,他们在捉弄人的过程中获得了心理满足。除了恶作剧,小说中亦不乏异类借着暗化环境进行偷盗。诸如《搜神后记·白布裤鬼》中的偷盗鬼,其与现实生活中偷鸡摸狗的无耻之徒十分相像,虽不为大害,但其趁夜色入室偷窃,干扰了人的正常生活。
如果说恶作剧、偷窃扰民是异类作祟的低级玩笑,那么异类害人则属于比较恶劣的作祟类型。魏晋志怪存在大量异类害人的故事,亭传精怪害人是其中的代表。“亭”原是秦汉时期的基层职能单位,汉末以来,其作为旅店停歇的功能更加明显。由于亭作为白昼天气恶劣的临时停歇点或出行半途的夜晚休息场所,加之其常远离住宅群落,因而成为异类的活动主场,如《搜神记》中宋大贤夜宿南阳西郊亭时遇狐怪。时至清代,表现异类作祟害人的故事仍层出不穷,如《子不语·归安鱼怪》中黑鱼精夜入知县家室并吃掉知县,《鬼吹头弯》中女鬼屡在古庙夜晚袭人并致使人颈弯如茄瓢。
由于暗化时空是异类的活动主场,且人在暗化环境中的行动颇为被动,因而异类的行为逐渐放肆,或恶作剧惑人,或凶残害人。可以认为,暗幕笼罩成为异类作祟的庇护。然而,异类无论是恶作剧以获得满足,还是偷窃以求得所需,甚至伤人害人所体现的阴暗邪恶,其作祟与人作恶使坏都有很大的相似性。特别是幻化人形作祟的异类,其本质上是披着异类外衣的人在行恶妄为。古代诸如杀人放火、妖淫谋逆等恶行往往发生在光线昏暗的夜晚,诸此种种就如同异类在暗化时空里作祟。诸如《子不语·大毛人攫女》,毛人怪为满足淫欲夜半掠夺赵氏妻子,后将其折磨致死,行径残暴的毛人怪是强奸犯的写照。同时,异类在暗化环境中为非作歹与人暗中使坏的心理是一致的,是人性中的阴暗面在异类行径中的体现。文学作品的落脚点在于人,“文学是由人而写,为人所写与写人的”[18]106,以人为中心、表现人的思想世界是文学的价值指向。因此,与其认为异类在暗化时空作祟,不如理解为人在暗化环境中作恶,暗幕笼罩实际上为人为非作歹的想法提供了遮掩与庇护,反映了人内心深处的阴暗欲望,故而异类在暗化时空作祟成为人在暗处使坏为恶的投射。
在暗化的时间设置与空间架构下,人异相处交往的环境成为遮蔽照明光线与他人视线的封闭性时空,在一定程度上隔绝了道德规范。相对而言,诸如白日劳作、公众聚集的非封闭性时空受到社会的审视,人的言行受道德规范的监督。小说中暗化的时空为人异遇合提供了远离青天白日下公开无隐私的环境,人异遇合屏蔽了道德规范。此外,道德规范对异类制约作用比人要小,甚至没有约束力,因而异类有违道德规范的言行不受管制,这反映了人作恶后想要逃避惩罚的心理。伦理道德对人异双方的约束已大大弱化乃至消失,而有违道德规范的言行在暗化时空下变得肆无忌惮。因此,人异遇合的暗化时空不仅折射了人性的阴暗,而且对社会伦理道德、公序良俗产生了冲击。
(三)暗示不公的两性地位
暗化时空下的人异婚恋是人异遇合重要的类型,根据人异双方的性别设置及结局走向,人异婚恋又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人间男子与异类女性的婚恋情爱,以给男子带来诸多良益收场;第二类是人间女子被异类男性狎弄,以女性的悲剧收场;第三类是人间男子因垂涎女性异类的美色而被惩罚、报复的故事。在以上三种人异遇合故事中,男性与女性的地位并不对等。暗化时空里的异类佳人为男子的生活带来颇多助益,相较之下,女子于暗化时空遭遇男性异类则下场落魄。因之,暗化时空隐喻着小说叙事的男性立场。
从魏晋至明清,人异遇合小说中表现男子与女性异类婚恋的故事层出不穷。这类人异婚恋的开场情节基本是男子薄暮或夜晚独处房舍书斋,女性异类现身进而进入男子的生活。暗化时空并非普通女子出现的恰当环境,古代伦理道德对女性的约束使得女性不可能在光线昏暗时独自出现在男性的书斋或其他荒郊野外。然而,由于人异遇合的暗化时空是异类活动的主场,加之暗化时空对道德规范的隔离,因而女性异类的登场有了合理性。在此基础上,脱离道德约束的暗化时空助长了女性异类的主动性,封建礼法中的贞操观对她们起不到约束作用。她们一反传统女性的矜持常态,大都主动亲近男子,甚至以身相许。如《搜神记·谈生》睢阳王去世的女儿“夜半……来就生,为夫妇”,又如《八朝穷怪录·刘子卿》中刘子卿于庐山虎溪晚逢花神遂与之欢好,再如《聊斋志异·绿衣女》绿蜂精幻化为美女主动接近入夜读书醴泉寺的于璟。此外,亦有一部分女性异类初遇男子时有所矜持,但在男子的挑逗下半推半就接受示好。这一遇合模式在明清尤众,诸如《剪灯新话》中的《牡丹灯记》《绿衣人传》,《聊斋志异》中的《画皮》《林四娘》等。总之,暗化时空下的女性异类与传统意义上矜持、庄重的女性形象大相径庭,其行为更是表现出有悖惯常的特点。
女性异类的大胆与主动印证了“我们中国的文人学子,总说女人先来引诱他”[19]的观点。暗化时空下的男子本是独处的状态,依照儒家慎独观念,闲居独处更须谨慎行事,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然而,面对异类女子的引诱,男性或直接接受或大胆挑逗的言行违背了慎独。然而,正是因为女性异类的主动,男子言行的失仪被弱化,其不需要背负道德的压力。此外,女性异类还能为男性解决生活与仕途方面的难题。换言之,男性充当受益者,女性充当奉献者。鉴于男性的零道德压力与充分受益,可以认为,男子与异类女子遇合是男性欲望的文学投射与升华,遇合的暗化时空隐喻着男性叙事立场。
小说中女子被异类男性狎弄的遇合类型也是男性叙事立场的体现。对于被纠缠的人间女子而言,男性异类意味着恐怖、惊悚,他们不仅对女性造成身体上的痛苦,而且还有精神上的屈辱。如《聊斋志异·泥书生》中泥书生夜夜闯入陈家祸害陈妻,致使陈妻“形容枯瘁”,又如《子不语·玉梅》中“状如黑羊”的妖怪每夜奸淫丫鬟玉梅。对比人间男子与女性异类的交往,一方面,女性异类满足了男子的愿望,而男性异类接触人间女子却是为了满足自身淫欲;另一方面,与人间男子交往的女性异类无一不是貌美可人、妩媚妖娆,而人间女子遭遇的男性异类形象大都被妖魔化,如大毛人、黑羊怪,其行为也被做了恐怖化的处理。由于异类男性具有人的特征,因而其更多作为展现人性阴暗的形象而存在。这似乎是在宣示,即使在远离道德审视的暗化时空,女性依旧是被压制与束缚的对象,女性难以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此外,人间男子因垂涎异类女性美色而受到惩罚的故事也基于男性的立场——尽管男性受到道德的审判与肉体的惩罚,但女性异类仍作为导致男性作恶的不良诱因而存在。
虽然暗化时空对伦理道德存在一定程度的遮蔽与隔离,人的欲望可以大胆袒露。然而,基于男性的叙事立场,男性与女性的地位并不对等。即使是女性异类大胆表现自我、主动追求幸福,暗化时空依旧为服务于男性而设置,女性的大胆与主动成为满足男性欲望的存在。实际上,暗化叙事隐喻的男性立场也是古代社会中男性特权在文学中的反映。因此,暗化叙事是两性关系不对等、不平衡的表现。
四、结语
人异遇合小说通过昏暗的时间、遮蔽的空间与特殊的气象构建了暗幕笼罩的遇合叙事时空。诚然,叙事是“一种文化理解方式”[18]215,人异遇合的暗化叙事时空亦蕴含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心理。一方面,是对“隔”的朦胧神秘意趣的追求。“隔”是中国传统审美心理的反映,“通常是指文艺创作中写情状物不真切、不明晰”[20],诸如山水画常以淡淡墨色晕染云雾缭绕的氤氲凄迷,文艺作品的美感可以在模糊迷离中营造。人异遇合小说的暗化时空调暗了叙事的光线,小说的色调被点染至晦暗,给人以不甚明朗之感,成为充满“隔”的时空。较之明亮而无遮蔽的时空,这种掩映的时空反而更能激发人的想象力,平添遇合情节的诡谲,甚至暗化时空、环境氛围所营造的神秘朦胧光影效果超越了事件本身的美学意趣。另一方面,是对非合理、悖伦常欲望与行为的愧怍、掩盖和粉饰。暗化时空不仅调暗了光线,而且遮蔽了他人的视线。在隔离光明与公众审视的时空内,人内心的隐秘欲望特别是有违伦常的行径似乎有了发生的可能。尽管异类更多作为人异遇合小说中悖伦常行为的施行者,但其本质上仍是人的思维与心理投射。人并非不明晓反常行为的不合理性,但一切不合理在暗化时空中都摆脱了惯常的道德审视与约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试图粉饰自我,对于自身非合理、悖伦常欲望与行为的愧怍心理。从整体上看,阴暗、朦胧、掩映的暗化时空本质上是小说文本内容的视觉呈现,反映了小说对叙事时空的光线与视线的调度。光线与视线的调度服务于人异遇合叙事,其暗化时空不仅成为异类活动的主场,而且折射了人性的阴暗、暗示了不公的两性地位。因此,小说中的光线设置与视线调度等视觉体验分析对探究叙事意蕴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