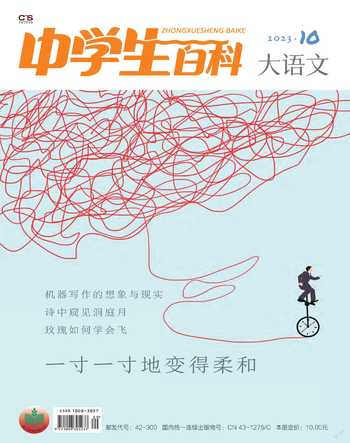机器写作的想象与现实
2023-11-08田可欣
田可欣
《阳光失了玻璃窗》可能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甚至是世界文学史上最特别的存在。作者小冰,师承1920年以来的519位中国现代诗人,学习了他们的上千首诗后,获得了创作现代诗的能力。小冰是谁?她是诗人、歌手、主持人、画家和设计师,也是拥有亿万粉丝的人气美少女……
谁都认识小冰,但谁也不认识小冰。实际上,小冰是一套完整的、面向交互全程的人工智能交互主体基础框架,又叫小冰框架。作为人工智能诗人,小冰的才情是公认的。她写孤独与悲伤,写期待与喜悦,样样都能写到人心坎里去。你看,连《阳光失了玻璃窗》这个极具诗意的书名也是她自己取的。
在人工智能真正进行文学创作之前,很多有预言家天分的作家其实已经料想到了这样的现实。出生于1916年的英国儿童文学作家罗尔德·达尔,他写的童话《查理和巧克力工厂》让小时候的我们爱不释手。最近他频频被提及,则是因为他笔下的另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机器写作”的故事。
罗尔德·达尔大概觉得写作终究是件劳心费神的事,于是琢磨一劳永逸的办法。在故事中,达尔讲述了一个计算机天才是如何实现“作家梦”的。虽然主人公明白“天赋不够,努力来凑”的道理,但他的努力并没有换来收获。一天,迟迟不被文学灵感眷顾的他突发奇想,决定利用积累的计算机专业知识,开发一台“自动语法仪”。毫不夸张地说,这台机器在文学造诣上完美地超越了它的创造者,因为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根据其他作家的作品写出具有获奖潜质的小说。
时至今日,我们都知道,“自动语法仪”所做的事,其实就是人工智能写作。童话作家达尔的奇思妙想,已成现实。作为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最新一代的ChatGPT展示出了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能快速“创作”出高水准的文学作品,正如达尔在童话故事中所写的那样。主人公依靠“自动语法仪”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但佳作频出,还成立了出版公司。更夸张的是,他居然统治了整个出版业,而他所需要做的,仅仅是找到那些有影响力的作者,出钱“收买”他们,让他们不再写作。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很多时候对未来的憧憬会不谋而合。对“创作型机器”抱有美好幻想的,远不止达尔一人。在达尔写下那个看似荒诞的故事之前,不少作家也曾有过类似的创作。
美国作家海因莱恩在科幻小说《沃尔多》中讲述了一个残疾科学家“自我救赎”的故事——他创造机器人沃尔多,以增强自己有限的能力。沃尔多可不是一般的机器人,它在通电的情况下会创作动画。同样来自美国的冯内古特在其社会科幻小说《艾皮凯克》中,以故事的形式展望未来机器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大胆写及了机器在发展中获得情感功能这一“禁区”。作为机器的艾皮凯克被赋以代人写情书的技能,结果阴差阳错地爱上了收信人帕特。后来,因为这种爱无法获得回应和回报,艾皮凯克选择了以自毁的方式结束一生。
科学与想象不是两条平行线,大多数时候二者若即若离,然后在某个节点乍然相逢。就在作家们纷纷于虚拟现实中对人工智能写作这一问题進行不同角度的展望时,科学家也没有闲着。英国数学家,被誉为“人工智能之父”的图灵,通过有关人机对话的设想启发程序员将设计思路扩展到媒体领域。世界上第一台商业电脑费兰蒂·马克1号因为情书生成器在其中运行,而向世人展现了其浪漫、温情的一面——它可以运用定义好的词语和格式写作情书。
此后,人工智能与文学的边界被一次次打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一些作家冲破“文学圈”,与数学家一起使用算法来生成新的文本,特别是在诗歌创作上进行了诸多尝试。大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文学一步一个脚印地登上了科技跃进式发展的时代大舞台。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工智能进行文学创作时的自由度并不高。它们根据明确的模板和规则写诗,或是对经典文本进行“打碎再加工”,程序化痕迹明显。如今,拥有自我学习、自我进化能力的人工智能正在改变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