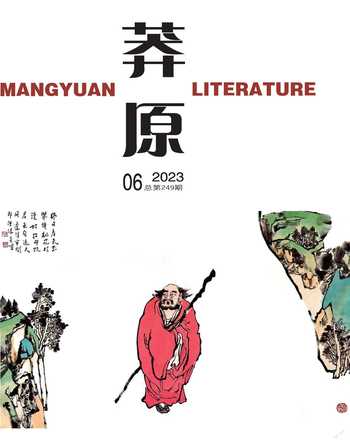绝唱与挽歌(三题)
2023-11-08胡炎
胡炎
庖丁解牛
有人请庖丁解牛。
其时,庖丁刚刚起床。上午睡觉,是庖丁的习惯。近午的日光照到窗棂,在墙壁上投下明亮的光影。庖丁站在光影里,正细细梳发。他听到了来人的声音,并不急,衣冠整齐后,才打了个哈欠,缓步出门。
来人奉上酬银。庖丁瞟一眼,知道酬银不菲。这是他的身价。
“有劳了!”来人赔笑,拱手。
“申时到。”庖丁说,又叮嘱道,“好草好料,别委屈了牛。”
来人诺诺,起身告辞。
庖丁坐在院中石桌旁。石桌一尘不染,光洁如砥。石桌的上方,是一棵老杏树,疏枝繁叶,有鸟雀啄着青杏,自在鸣啭。庖丁沏了菊花茶,轻啜慢品。清苦中的淡香,入喉便浸淫了灵魂。又吃几块茶点,便做午餐了。
庖丁解牛无数,却只吃素食,从不食肉。
然后,磨刀。磨得很细、很轻。磨刀声如风行水上,绵绵不绝。用抹布擦拭干净,刀映着日光,有如明镜。庖丁在刀面上看自己的脸,眉似弯弓,目如朗星。他微微一笑,以食指试刃,似触未触间,一粒血珠饱满如豆。
庖丁把食指含在嘴里,吮了。
牛很壮硕,毛色黄亮。庖丁端详一阵,甚是满意。院中早拥了一众看客,引颈翘首,等待观赏庖丁的绝技。
庖丁仍不急,柔柔地抚摸牛脊。由脊及头,再及面颊。庖丁的手柔若无骨,分明不是操刀的手。牛一动不动,眼神迷离。庖丁退后一步,对牛说:“我们开始吧。”
牛眨了下眼睛,有泪花闪动。
“不怕。”庖丁笑笑,取出刀来。
众看客屏息敛声,四下静得落发可闻。
刀光和着日光,细雨般渗入牛的肌肤。牛像得了雨的滋润,安然而立,却似睡着了,坠入前生来世的梦。刀走在梦中,绵延时,宛若游龙,恰如惊鸿。时光在梦中被拉长。及酉时,刀入鞘内,庖丁背着手,看眼前的牛。
牛依旧站立着,尚有鼻息。
“刽子手!”牛哞然叫了一声,像梦呓。
庖丁一愣,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听到牛说人话。日已偏西,残阳如血。牛被血光涂染,徒增了几分悲壮。
“你说什么?”
“刽子手!”
庖丁说:“不,我是艺术家。”
牛拼尽了最后一丝气力:“刽子手从不说自己是刽子手。”
话落,身体四分五裂,轰然倒地。
暮色黏稠,庖丁在暝晦的路上独行。外物皆似隐去,唯余那头会说话的牛。庖丁看到自己的刀在牛身上开花。美,美极了!打他将解牛技艺练到炉火纯青时,这花已开了二十余年。
可是,牛说他是刽子手。
庖丁忽而泪湿双目,觉得世间事误会颇深,终是知音难觅。月色清寒,浴着落泪的庖丁。庖丁感到很委屈,也很孤独。
牛说:“上山吧。”
庖丁问:“为何?”
牛答:“你曾是我们的朋友。”
山道崎岖,草莽在月色中匍匐。有虫鸣和溪流之声传来,草香雾气一样缭绕。夜空辽远空明,繁星童谣般闪烁。
庖丁一时有些恍惚。他看到一个少年,剃着瓦块头,骑在牛背上,口含柳笛,吹着清亮的曲调。山雀在笛音中舞蹈,甚而有胆大者,落在他的肩上,与他戏耍。
庖丁恍然想起,自己曾是个牧童。
影影绰绰,果然有一群牛。这些牛中,有他牧养过的,也有它们的亲人和朋友。庖丁心头一热,加快了脚步。近了,群牛化作一团乱影,消逝无踪。
庖丁怅然四望,心底忽而生出一股苍凉。
月光漫泄、收拢,在他眼前生成了一面银镜。镜中人气质绰约,欣然微笑。
“以解牛之技而冠天下者,非庖丁莫属。”镜中人说。
庖丁拱手一揖:“谬赞了。”
镜中人庄重了神色,道:“既可解牛,则人亦可解,不错吧?”
庖丁震了一下,无语。
“这般沉默,是不能,还是不敢?”镜中人冷笑,兀自脱了衣服,亮出清朗的肌体。
庖丁也冷笑了。抽出刀,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对着镜中人,若笔走龙蛇,潇洒自如,狂放无羁。不消半个时辰,庖丁收手,掷刀于地上,发出叮当脆音。
“你是个真正的艺术家。”镜中人说。
须臾,头颅坠落,全身作碎银般落入草丛,琅琅有声。
是夜,牛哞雄浑,响彻夜空。公牛、母牛、大牛、小牛,用长吟短歌庆贺一个仇人的死亡。
然而不久,牛们便后悔了。它们迎来了笨拙的屠夫,那些屠刀钝若老牙,毫无章法,但下刀足够凶狠,让牛们痛不欲生,生不如死。
活着的牛们,开始深深地怀念庖丁,怀念那些死在庖丁手里的牛——那样痛快而优雅的死亡,已成世間的绝唱。
不过,也有人说,庖丁没死,午夜时分,他在月色里磨刀。
与虎谋皮
易容师独居深山。然其易容绝技不胫而走。荒野茅庐,常有人趁夜色造访。
一日,来了位不速之客。非为人类,而是这山上的一只老虎。易容师两腿一软,瘫坐在地。
老虎神色凄然,大叹虎族生存之艰,说世人太过狡猾,对其族类退避三舍,且防范甚严。“不瞒你说,我已三月未尝人肉,将忘其滋味了。”老虎说,“请先生以盖世之绝技,将我化作人形,其貌善良敦厚,人见人爱,不知可否?”
易容师惊怔良久,说:“这大变活人之术,难比登天,可否容我研习三日?”
老虎颔首,伸出舌头舔了舔嘴角的涎水。
月黑风高,草莽啼泣。易容师脚下惶急,数次跌倒,手肘、膝盖都磕破了,痛彻肌骨。星光碎在天上,如他的灵魂被恐惧肢解。兽鸣虫唧在寂黑的四野回荡,像是神秘的暗语,昭示着他吉凶未知的前途。
“逃得了吗?”
有声响在耳侧,亦幻亦真,却听得分明。易容师敛了喘息,四下环顾,夜色如墨,古木森森,独不见人。
“谁?”
“不必知晓。”那个声音说,“我且问你,化虎为人,可能办到?”
“不能。”
“既然不能,又为何答应?”
易容师哀然摇头,冷泪潸潸:“虎威之下,我如若不应,还有活路吗?”
那个声音陡然笑了,笑声冷厉而尖锐,穿透力十足,似可洞穿人的灵魂。
“莫急,我来帮你。”
易容师如沐佛光,“嗵”的一声跪在了地上。
二手軀壳市场建在半山腰,旗幌迎风招展,上书一行大字:“活成你想要的样子”。甫一开张,便门庭若市。
三教九流鱼贯而入,有稚童顽少,禽兽杂处,好不热闹。蹒跚老丈变作精壮青年,老迈妪妇化身二八娇娘,貌丑少年须臾竟为翩翩美男,市井恶人脱胎换骨,瞬间凶相不再,美善可亲;作奸犯科者彻底将自己洗白,从容不迫,气定神闲;穷汉换作富贵相,挺胸昂首,趾高气扬:行走世间,谁人不高看一眼?富人换作穷酸貌,皮黄骨瘦,形容卑琐,胸中宽慰:日后再出远门,何虑劫盗滋扰?至于鸟兽异类,则浑然世人,莫辨真伪。
掌柜笑容可掬,坐在雕花木椅上,跷着二郎腿,微笑不语。
这个掌柜,不是别人,正是易容师。
谁都没有料到,一场械斗不久后发生。
易容师感到天空在倾斜,整个大地都在晃动。世界全乱了,父不识子,夫不认妻,劫盗横行,甚而天道颠倒,人伦混乱……他亲眼目睹了木棍、斧叉、菜刀、石块击碎了那些曾经梦寐以求的躯体。天地被血色笼罩,空气里的血腥味令人窒息。
易容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只怕他在劫难逃了。来不及收拾金银细软,便仓皇出逃。但是,一个精壮汉子的钉耙已经悬在了头顶。
“把我还给我!”
易容师的脑袋被钉耙击碎的同时,他手里的尖刀也插进了汉子的胸膛。自然,刀是他早就准备好的。
一只花斑虎躺在山坡上,啃着一只肌肉发达的胳膊。味道真不错。在不远的人间,血腥味依旧浓烈,被疲倦的风带过来,影响了他饕餮的食欲。
又一只老虎走来,通身雪白,这样的毛色在虎族极是罕见。
“真够逍遥的啊。”白虎说。话落,锐利的虎牙卡住了花斑虎的脖子。
“本是同类,相煎……何急?”花斑虎吐出一口血沫。
白虎笑了:“别再演戏了,易容师。”
“你……怎么知道我是易……易容师?”
“很简单,我闻到了你身上的人味。”
花斑虎用微弱的鼻息闻了闻,在脖子被咬断之前,想:我身上还有人味吗?
易容师飘在空中,无法掌控自己的方向。日光穿不透黏稠的血色,形成了无数道毫无规则的折射。易容师很想落在地上,在遍野的尸体中走一走,仔细分辨一下这些尸体的原身。但他做不到,甚至连在树枝上驻留片刻也是妄想。这让他无奈而悲伤。
有歌声传来,似来自天外,又似来自人间:
我非我来你非你,
皆因你我换张皮。
我是何人浑不知,
你归你兮未有期……
自此,世间唯存整容术,再无易容师。
凿壁偷光
匡羽喜月光,不止于喜,堪称迷恋。
匡羽母亲早逝,父亲以捕猎为生。幼时,匡羽常和姐姐在月光下依偎。姐姐的脸沐着月色,愈发白皙,两只眼睛闪闪如星。匡羽还闻到姐姐身上淡淡的香味,他想,这便是月亮的香气吧。
姐姐给他讲故事,说他们的先祖匡衡,凿穿邻舍墙壁,偷得烛光读书。匡羽问,这故事叫什么名字?姐姐说,《凿壁偷光》。
匡羽在姐姐怀中睡去了。恍惚间,他觉得姐姐便是月亮。皎月高悬,月色温柔,如春水,如夏日清风,如山坡上的青草,绒绒软软,熨抚着他小小的生命。后来,在每一个乌云遮月的夜晚,匡羽就想,他要用一只长长的凿子,把云层凿透,偷得月光几许,像花一样,种在无边的黑暗里。
七岁那年,父亲发现匡羽天赋异禀,记忆超群,过目不忘。
事情缘于一次狩猎,他们进入深山,于密林中迷路。夜色深浓,难辨东西,父亲一时手足无措。
匡羽说:“父亲不必惊慌,请随我来。”
黑暗中,匡羽步态从容,东拐西绕,越岭涉涧,从无踌躇。父亲犹疑之时,忽闻水声潺潺,原是林外大河近在眼前。归家之路,赫然在望了。
父亲大喜,始觉小儿乃少年奇人。后数次入山,俱入人迹罕至处,捕猎颇丰。茫茫归程,有匡羽带路,屡试不爽。自此,纵上天入地,也再无后顾之忧了。
匡羽万没想到,父亲后来会成为一名赌徒。
先是微薄家产,后是三间祖屋,尽输于他人。再后来,父亲竟把姐姐输给了一个独耳无赖。
夜月升起,姐姐抚摸匡羽面颊,良久,说:“往后,姐姐便不能照顾你了,你要好好活着。”
匡羽含泪摇头:“姐姐,我们逃走吧。”
姐姐哀然一叹:“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又能逃往何处呢?”抬眼夜空,珠泪婆娑,“以后……想姐姐了,就看这天上明月吧。”
匡羽望着月亮,第一次觉得,月亮也会哭,那满天星星,恰是月亮的泪滴。不知过了多久,匡羽睡着了。
是夜,村中老井一片碎月溅起,姐姐投井而亡。
匡羽自此只喜黑夜。他把自己幽闭于黑夜荒僻处,心才可以静下来。他看着月亮,毛孔舒张,让月光淌进灵魂。姐姐在哭,姐姐在笑,姐姐给他讲《凿壁偷光》的故事……姐姐就住在月亮上,不,姐姐就是月亮。
风起,云来,月亮不见了。匡羽对着云幕,左手前伸,作扶凿状,右手握拳,一下一下击打。在他眼里,有一只神奇的凿子,直抵天宇。云的碎片簌簌剥落,姐姐就躲在云后。月光不现,他便不会停下。
匡羽长大了,父亲早死于债主乱棍之下。一个卖艺的老者收留了他。匡羽的数字游戏让人叹为观止。一来二去,名气日望,竟传到了国君的耳里。
国君先给了匡羽一个账簿,令他即时看完,再让他将所有账目复述一遍。匡羽如数家珍,毫厘不爽。
“你留下帮我经营财政吧。”国君说。
转眼,半年过去。時令已入冬,常有北风呼啸,却无雪。宫里落叶堆了一层,又堆了一层,那些树全秃了,枯枝划着风哨,冷厉刺耳。倒是长空澄碧,入夜,弯月高悬,干净得如姐姐的眼神。
匡羽每于夜深,便出门望月。月亮在天上,主宰了暗夜,想必姐姐在那边,再不会被他人玩弄于股掌了吧。
与他一起望月的,还有宫女小翠。这小姑娘,也生了一双明眸,喜笑,见了匡羽,眼睛便成了月牙。
“羽哥哥,你不困吗?”
“不困。”
“那……你因何喜欢望月呢?”
“……”匡羽欲言又止,月亮的秘密,只属于他自己。
“我也喜欢。”小翠说。
匡羽看着她,心有疑惑:“你倒是为何?”
“羽哥哥喜欢,我便喜欢。”小翠神情里现了羞赧,扭头跑掉了。
匡羽的好运还在继续。
他替国君经营财政,竟成了富商,把生意做到了国外,是许多达官贵人的座上宾,众星捧月,锦衣玉食。甚至连异国的国君,也经常召见他,推心置腹,把酒言欢。匡羽再不是从前的匡羽了。只夜色里醺然归家,便觉得累。
好在,此时总有一碗莲子羹为他解酒。
匡羽拉着小翠的手,笑了:“娘子辛苦了。”
小翠红着眼圈:“你安然归来,我便知足了。”
长夜依偎,临窗望月,是匡羽最幸福的时刻。却不知这般光景,会有多久。
两年后,故国大兵压境,一举吞并异国。匡羽在城中独步,遍地血泊,满目狼藉。蓦地,匡羽跪于街头,泪飞如雨。
国君设宴召见了匡羽。
“而今他国大好河山尽归于寡人之手,先生功不可没啊!”
“小人惭愧。”匡羽接过国君赐的酒,却未马上饮下。酒液微晃,他的手在抖。
国君笑了:“先生莫非疑这酒中有毒不成?”
举起杯,先自饮尽。
“岂敢。”匡羽忙把酒喝下。美酒入腹,其味甘醇,是自己多疑了。匡羽这才发现,不知何时,他已是惊弓之鸟。
醉意朦胧时,国君看定了他:“目前尚有一偏安小国,若将其拿下,便可天下一统。”
匡羽的心一阵颤栗:“小人……定当不辱使命。”
连续数晚,匡羽于梦中醒来。黑暗中,哭声连绵,充耳不绝。
是夜,清月寂寂。匡羽在月色里急行,于人迹罕至处,入得深穴,再将洞口封上。倚于洞壁,四周寂暗无光——这样与世隔绝,最是契合他的心意。
鸩酒饮下,混沌中,与小翠那临别一抱,犹在眼前,那般深情已然刻骨。此去经年,不知小翠吉凶如何,只瞒她说,国君另有秘密任务交付,诸事莫问。他不知道,小翠的腹中,已有了他们的骨肉。
其实,他想过逃,可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又能逃到哪里呢?他只知道,自己死了,万千生灵或可免于涂炭。他不能再错下去了。
匡羽至今还记得,临去异国之前,国君拉着他的手:“我千秋大业,就拜托先生了!”
千秋大业,好一个千秋大业……匡羽在黑暗中,似乎又看到一具具尸体,血肉模糊,死不瞑目。这一切,皆是拜他所赐。在异国,他不过是个可耻的奸细,游遍异国山河,兵营布防、关隘重镇,俱存于脑;结交军政,贿赂权臣,窃得机密无数,神鬼不觉间秘传于故国……什么天赋异禀,不过笑里藏刀,祖先凿壁偷光,他却是个窃国大盗啊!匡羽揪着自己的头发,想,我是个千秋罪人,死有余辜!
匡羽闭上眼,让自己在黑暗中睡去。他听见姐姐唤他。姐姐在月亮上,真的在月亮上。月光将他包围,从皮肤渗入生命,照彻了他的灵魂……
多年后,年迈的小翠在梦境中,依旧能听到神秘的斧凿之声。
自从匡羽消失后,这声音从未中断过。
责任编辑 丁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