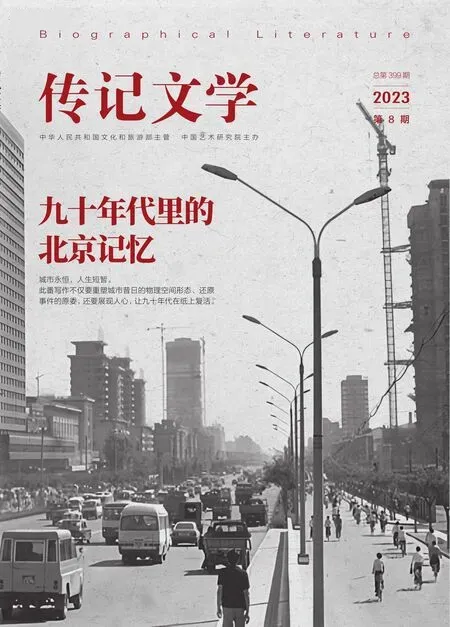编辑家自传启示:以李昕的《一生一事》为例
2023-11-08淡霞
淡 霞
“我这辈子,只从事了一种职业,就是出版。这个职业符合我的人生理想,也能给我带来乐趣,因而它成了我为之奋斗的事业,四十年来乐此不疲。”[1]在人心浮躁、内卷的当下,有一个人却如此平静、如此清醒、如此欣慰地回顾自己的一生。一个人,四十年,四段编辑经历,职业生涯、事业追求、人生理想高度契合,可谓幸事,难怪他乐此不疲。他,就是出版人李昕,其自传性质的纪实作品《一生一事》如同万花筒一般,在腾挪转换间展现出不同认知层次的万象魅力。
师:一本编辑学的教科书
2013 年,一本超级畅销书《邓小平时代》横空出世,社会反响不俗,这是其策划者李昕四十年职业生涯中一个无法绕开的标志性事件,也是编辑与好书相互成就的典范之作。“这本书是我一生经手的图书中出版难度最大的一本,当然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本。说是难度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争夺版权不易,二是审读定稿过程艰辛,三是营销推广压力大。每个方面,都有关键步骤,可以说,走错一步,结果将是另一个样子。”李昕如是说。虽然谈的是特例畅销书的运作,但版权(策划)、审读、营销也是每个编辑工作实践中对每一本书必做的操作流程。在《一生一事》中,李昕将自己四十年的编辑工作细节毫无保留地一一道出,其中揭示的工作经验亦随之呼之欲出。
就策划而言,面对自己不太熟悉的学术书稿,李昕提倡比较阅读,通过翻看不同学者的专著,发现和提炼自己面前这部书稿的独特价值。此书或具备一定创见和新的观点,发别人之所未发;或史料丰富而严谨,掌握他人未曾拥有的第一手资料;或研究方法和写作手法具备独特性。如此,便可发现书稿的价值和特色、弱点和不足,不论是给予书稿积极肯定、高度评价,还是给作者提供可行性修改建议,皆言之有据,令人信服。在组织策划丛书时,李昕凭借敏锐的出版嗅觉,基于自己的积累和经验,判断选择什么样的图书主题和形式较为合适。2013 年,在生活书店恢复建制后,李昕准备策划一套选编作品:“文学书,特别是小说还可以做什么?我是文学编辑出身,认识很多当代作家,可以直接向他们邀约原创书稿,但是想快见效益,需要从编选名作开始。”对待原创作品和选编作品,选用不同的策略和打法,是一个编辑策划智慧和职业经验的体现。
审稿是每个编辑在从业生涯中,时时面对的一项日常工作。审稿时面对的问题种类繁多、千奇百怪,李昕在书中均有披露,并直白坦荡地公布了自己的一些工作技巧。譬如对一本旧书和不成熟的书稿如何改造,李昕会提醒作者必要时重写和补写,使之成为自成系统的作品;一本书的书名太古板,改成简约而接地气的名字,会更贴合市场和读者;必要时,编辑还要代写序言,等等。
审稿无小事,不论是大删大改,还是改动一字一词,随心所欲、自以为是的修改必将贻笑大方。李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工作期间,给著名作家王蒙改稿子,把对的改成错的,被王蒙当场指出来,他反思道:“这件小事,我之所以至今还记得,是因为我引以为戒,从此时开始,我做编辑案头工作,凡是在作者稿子上做的修改,我都要反复校核,至少三遍。”其实,李昕在大学毕业刚入职之初,就得到过武汉大学陆耀东教授的教诲:“要想不留硬伤,唯一的方法是多看资料,多查字典,切切不可自以为是。……这是我走上编辑岗位之前的重要一课。陆老师的话,我真是记了一辈子。”凡修改必校核,多看资料多查字典,这两条审稿原则,当为出版界所有编辑的职业金科玉律,时时勉励。
出版是微利行业,图书出版后的营销活动大多是常规的新书发布会、作品研讨会等,对待这类工作,李昕都是亲力亲为,尽心宣传。例如,他参与宣传《邓小平时代》,和其他同事一起商定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样的国家级媒体刊登广告,这是营销的大手笔,亦成为国内出版业的先例,为这本书畅销50 多万册打下坚实基础,开拓了崭新局面。
李昕做了一辈子编辑出版工作,经手的图书超过3000 种。策划时眼光敏锐,与时俱进;审稿时专业认真,谦虚勤奋;营销时解放思想,大胆突破,书中如实记录的一个个出版案例,大多是他担任责编或深度参与的成果,如此,从案头功夫到做人做事,从担任责编到给作者写信、打电话沟通,体现出一个出色的编辑和出版人的职业素养、专业水准、敬业精神、人文情怀以及学者风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书堪称一本编辑学的教科书,有心的读者自会从中获益匪浅。
识:挖一口深井做品牌
杨绛先生曾在报纸上发文,谈了她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下简称“三联”)文化传统的看法:“三联有它的特色:不官不商,有书香。”李昕1996 年被公派到香港三联书店(以下简称“香港三联”),在那里工作了八年;2004 年回到内地,在北京的“三联”书店继续工作了九年,直至2014 年退休。可以说,李昕与三联的缘分相当深厚,他担任三联总编辑时出版的图书,也大多契合杨绛先生对三联的评价。这“不官不商,有书香”的背后,体现的是出版人、总编辑的识见。
李昕的识见首先体现在作为责编的担当上。他说:“对于编辑来说,强调‘胆识’,并非两者并重,而是‘识’重于‘胆’。有‘胆’的前提,也是不违背政治原则。这就要首先以‘识’来作判断。”这份识,是见识,是阅历,是经验,更是智慧。李昕在三联期间,以善于处理敏感书稿出名,此间考验的是编辑的智慧。面对书稿中的敏感内容,或者是需要报备的重大选题,有没有实际经历过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编辑的判断力,这判断力基于政治智慧的运用。“我觉得,作为编辑是需要有一定政治智慧的。编辑如果没有担当,很多好书就会擦肩而过,但如果他要担当责任,没有足够政治经验也做不到。编辑应具有清醒的判断力,判断自己在政治把关方面能够做些什么,能够妥善处理什么问题……”李昕如是说。
李昕的识见还体现在经营意识的提高和运用上。在香港三联工作的八年期间,当地同事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用数字说话的工作方式,深深影响了李昕的出版经营意识,他开始学习香港三联的精细化管理,取得不错的成效。
与时俱进,是一个编辑乃至出版人必备的职业素质,李昕在这方面充分体现了他的先见之明:20 世纪90 年代,身处与国际出版潮流率先接轨的香港三联,他积极学习图书的社会责任如何落地;读图时代的图文书如何运作;设计师先进的图文制作理念该如何体现;他和同事们在经济萧条时代向日本学习做低成本低定价的小书系列,使得香港三联在出版微利行业杀出一条血路。同时,他们也具有向内地做成品书供货的思路和做法,如此这般,都是李昕主动、敏锐地践行先进出版理念后获得的识见,这为他之后在北京三联大展拳脚,制作出一批批成功的畅销书和长销书奠定了扎实的理念基础和运营技巧。如此,从香港回到内地,李昕已从一名编辑脱胎换骨为一名出版人:“人文社使我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编辑,也仅是一个编辑而已,作为一个出版人,我是在香港成熟起来的。无论是文化理想,还是经营意识,在这一时期,都变得十分明确,甚至我觉得自己的眼界、眼光、眼力都变了。我对于图书品位的感悟力、对图书品质和品格的直觉判断力,也就是我后来常常讲的‘书感’,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和强化的。”
挖一口深井做品牌。作为三联图书选题掌舵人,李昕对此深有感触,也有自己的信念。“不官不商,有书香”是三联的品牌定位,但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浸润下,员工坚守理念传承,待遇却跟不上,长此以往,亦留不住人才。李昕及其志同道合者提出在三联原有学术出版之外,开辟大众读物出版路径。大众读物市场占有率高,更接近社会民生,彰显三联的现实关怀,内容虽接地气但不庸俗,保持较高的水准和品质。这便是李昕深挖一口井做品牌的远见卓识。在他担任总编辑的九年期间,三联的经营利润大幅增长,品牌影响力日益增强。
《易经》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李昕的识见来自他丰富的编辑经历,来自他善于借鉴国际优秀管理理念,来自他与时俱进的市场运作意识,来自他对出版品牌的清醒认识和清晰定位,如此这些,均源自他懂得学习、善于学习的自发意识。任何时候,自主学习都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识见。
史:今天的故事,明天的历史
季羡林先生是自传写作大家,他的自传,最为看重“实事求是”:“我决心听从别人的建议,改变以前的想法,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实事求是地写出来。我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四字,因为写自传不是搞文学创作,让自己的幻想纵横驰骋。我写自传,只重事实。”[2]秉承此创作宗旨,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中详细记载了自己1935 年至1945 年赴德求学的经过,此间亦直接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发展直至结束。对此,他颇为感慨:“我以一个人,在一个极小的地方,管窥二战这样的大事,没有感到一点惊天地泣鬼神的剧烈,我感到的是:大战来得轻率,去得飘忽。”[3]实事求是的自传写作,对个人而言,是对真实生活的回忆,于不知不觉中,亦成为历史的一份宝贵的见证记录。
今天的故事,就是明天的历史;个人的职业生涯,或可串联起一部出版史。李昕的《一生一事》即是如此。书中,李昕按照入职顺序,详细记录了他从大学毕业到退休返聘的四十年工作经历。他的四段编辑生涯既是个人的人生,也是其平台的发展历史。
就一个编辑而言,李昕所就职的出版社都是名社、大社,他的成长也伴随着这些大平台的发展而来。1982 年,他大学毕业后入职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一名校对做起,后来成为编辑直至编辑室主任。在此期间,他与文学名家打交道,见识、结识、见证了一批文坛大家及新秀的成长。譬如,他与著名作家王蒙就此结缘,深厚的友谊持续至今;他为张炜的新作《古船》仗义执言,作为新人的张炜感念再三,感恩至今。日后,王蒙和张炜皆成为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作等身。人文社在20 世纪80 年代、90 年代经历的文学理论热潮,对老中青学者及开拓性著作的支持,李昕都积极支持并深度参与其中。
1996 年,李昕调入香港三联工作。彼时,正值香港回归祖国前夕,李昕所处的香港三联顺应时势,为解答香港市民的困惑和宣传中央的对港政策,他们策划并出版了一系列介绍中国社会生活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图书,为港人了解时势作出正确引导,颇受好评。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出版业萧条惨淡,香港三联危机中求生存,及时策划并实施了一批小成本低定价的小书,针对性和实用性强,经济效益增长显著。如此这些,李昕都是身处其中并将真实感受详细记录下来,可以说他见证了香港出版业从动荡到平稳的全过程。
自2005 年回到北京三联后,李昕致力于重点打造大众读物,出版了大量接地气、反映社会现实和反思历史的纪实类作品,他和同事一起将三联的品牌做深做广做强。他说:“理想的划分,自然是三联书店的品牌以出版学术文化著作为主,出其他书使用其他品牌。在国外,出版社大多是这样做的,一个品牌之下,集中出版某几个类型的图书,以显示清晰的出版定位,因为他们可以随时选择注册新品牌。”2013 年,生活书店恢复建制,李昕担任首任总编辑,又一次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2014 年退休后,他被商务印书馆返聘,在高端学术之外策划的大众读物选题也有不俗表现。
可以说,李昕的每一步都在把握时代的脉搏,同时也抓住了出版业四十年蓬勃发展的机遇。除了跟随平台一起成长,跟着时代一起跳动,李昕的职业生涯还见证了中国版权意识觉醒的发展阶段。在人文社时,他代表钱锺书和别家出版社打《围城》的侵权官司,人文社胜诉,如他所说:“这个案例确实为中国出版界立了规。此后,有关专有出版权的界定变得清晰了。国内再也没有出现因为‘汇校’引起的版权纠纷。”在北京三联时,他代表单位去打李泽厚著作财产权官司,北京三联胜诉,如他所说:“2011 年,我曾分别飞到合肥和南京,专门找法官面谈。事前我写了一篇《李泽厚案要点》,把李泽厚著作财产权转移的来龙去脉详加说明,并阐述三联的观点,同时将各种证据提供给法院。”从人文社到北京三联,从钱锺书到李泽厚,其著作权官司牵涉名社、名人,举世瞩目,影响深远,代表了中国著作权版权意识觉醒的艰难历程。
中国港台作家在大陆出版作品的破冰之旅,李昕亦有幸置身其中。李敖、金庸、梁凤仪的作品,他都引进或曾积极推荐在大陆出版;齐邦媛、王鼎钧的作品,他曾积极斡旋,主动引荐,促成其在大陆的出版事宜。
还原一段段出版史,见证一场场版权纠纷,与各时代各领域的学者、作家迎来送往,书写自己的经历,关照他人的生活,与此同时,李昕亦成为潮流、时代、历史的参与者。个人历史、平台历史、国家历史,生活轨迹、他人轨迹、思想轨迹,融为一部短短四十年的自传,颇有《西江月》中“豪杰千年往事,渔樵一曲高歌。乌飞兔走疾如梭,眨眼风惊雨过”之况味。
示:你中有我,小中见大
刘梦溪先生在《一生一事》“序言”中评价此书:“自传性的纪实文字,写得像章回小说一样好看。高潮迭起,一浪高过一浪,余波后面还有余波。”确实,文字平实,故事生动,人物鲜活,可读性强,是此书的亮点。这得益于作者文笔的特殊魅力,因着这魅力,我们领略了故事、历史、公案,更多的是值得玩味的人生启示。
如刘公所言,这是一部自传性的纪实文学,既是自传,便具有自传的特色。自传乃回忆往事之作,往事不可能事事正确如意,审视之下,必有反思和悔悟。李昕谈到编辑《胡风评论集·后记》时说:“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我们的确删得太多了。这显然和我思想不够解放有关,也和胡风当时尚未完全平反有关。”谈到与金庸作品失之交臂,他遗恨:“所以人文社失去了与金庸合作的机会。由于观念束缚和反应迟钝而怠慢金庸,这大概要算是我在出版生涯中的一个重大疏漏。”谈到曾经对作者的失礼,他忏悔:“不过,从另一角度,我也作了反思。若干年后,当我具备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以后,每每想起当年与潘旭澜谈论书稿修改问题时的情景,我都颇为惭愧和反悔,觉得自己的做法,对潘先生是一种失敬和失礼。我引为教训,意识到与作者交往,言谈举止都应注意分寸,得体最重要。”“我与我周旋”,自传作者摆脱不了的宿命,或曰,此为其使命。
自传作者除却对自己开刀,剖析自己的弱点和缺陷,对别人的缺点和不足,亦应不必隐瞒。这一点,李昕做得较好,榨出一些著名学者“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或者说真实还原了他们的所作所为。此外,自传作者秉笔直书的底气在于,所有事件他都身临其境,并存有大量书信作为证据。纪实文学,写出事实,讲清楚来龙去脉,是非由读者去判断,作者的本意大约如此。
自传作家的写作,自觉或不自觉地大多带着任务而来。传记研究学者赵白生在《传记文学理论》中谈道:“简单地说,自传作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呈现两种关系:一、我与别人的关系;二、我与时代的关系。在呈现这两种关系的过程中,他不断地揭示自我。要展示我与别人的关系,需要的是传记事实;要说明我与时代的关系,自然少不了历史事实。”[4]
“我与别人的关系”,莫过于李昕在书中记述的自己的书缘,在近半个世纪的编辑生涯中,他既与著名学者和作家打交道,也不断发现和提携新人作者和作品。他发掘杨义初出茅庐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本书从要退稿到被列为教材,两度获得大奖,杨义的学术生涯随之被改变,人生之路更顺畅,后成为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家。此乃编辑改变作者的案例。退休后,李昕和商务印书馆的同事一道,与韩启德就出版《医学的温度》多次沟通,改变其想法。此书成为屡屡获奖的畅销书,“这本书的出版,坚定了我一个信念:编辑的选择和策划是可以改变一本书的命运的”,学者韩启德从学术领域和领导岗位走向大众,为更多读者熟知,亦为一种改变。
“我与时代的关系”,放在任何一部自传中,都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对此,李昕在经历生活的磨炼之后,在退休感言中感慨地说:“我赶上了一个出版业勃兴的时代,这个时代不仅允许,而且激励出版人有所作为,在此前的时代,或者今后的时代,都未必如此。”时代,成就了李昕。在工作中,李昕在策划纪实类作品或回忆录时,一再强调作品中小人物与大时代、宏观线索与微观线索之互相纠缠关系,可曾想,在他自己的传记中,体现的也是如此道理。
所有自传,大约都有个人品牌意识贯穿其中。从1982 年写到2022年,书中完整地呈现了李昕的所有职业经历,这是一条编辑之路,也是一条人生之路。一路上,李昕不断地在打造图书品牌,强化平台品牌,也在无形中塑造了自己的个人品牌,这个人品牌即出版人和作家。当年他大学毕业,初入职场时,即得知人文社社长韦君宜非常提倡编辑要“一手编,一手写”,鼓励编辑自己搞创作和研究。如今,年逾古稀,李昕做到了。
编辑帮助新人出书,新人成名后协助编辑;编辑为作家出书,自己也成为作家;善于发掘书稿中宏大叙事的微观视角,自己的传记何尝不是演绎了小人物与大时代?一部自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小中见大,大自小成,正所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人生或亦然。
沈从文说自传写作:“既然是自传,正不妨解除习惯上的一切束缚,试改换一种方法,干脆明朗,就个人记忆到的写下去,既可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也可以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5]李昕和他的自传《一生一事》揭示的,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