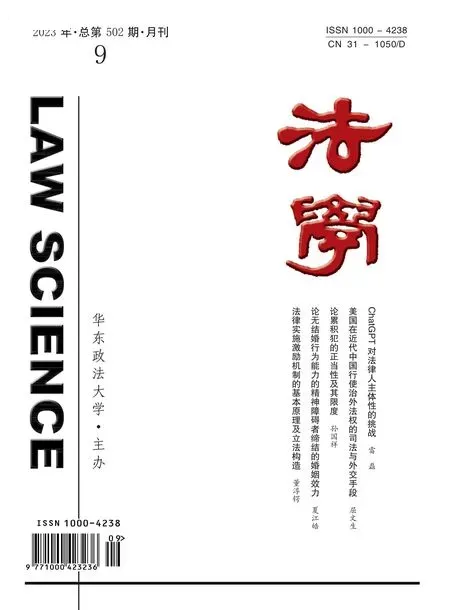论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效力
2023-11-06夏江皓
●夏江皓
一、问题的提出
《民法典》修改了原《婚姻法》第10 条关于婚姻无效的规定,将“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情形的婚姻效力由无效婚姻修改为隐瞒重大疾病的可撤销婚姻。这一立法修改尊重和保障了当事人的婚姻自主权,其进步意义毋庸置疑,然而却引发了一个不期而至的问题,即在《民法典》的规范体系中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效力究竟如何。
精神障碍又称精神疾病,是指“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造成的心理功能失调,而出现感知、思维、情感、行为、意志及智力等精神活动方面的异常”。〔1〕《精神障碍者民事行为能力评定指南》(SF/Z JD0104004-2018,以下简称《评定指南》)第3.1 条。对精神障碍的定义还可参见《精神卫生法》第83 条。在《民法典》实施前,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效力问题基本上可以通过原《婚姻法》第10 条得以解决,〔2〕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原《婚姻法》第10 条要求精神障碍的严重程度、“婚后尚未治愈”等条件,严格来说,原《婚姻法》第10 条也无法完全解决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效力问题。申言之,通说认为依据《母婴保健法》第8 条的列举,有关精神病属于“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即属于原《婚姻法》第10 条规定的无效婚姻事由之一。〔3〕参见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1 年版,第33-34 页。而《民法典》第1053 条对疾病婚的规定进行了规范意旨的根本性调整,由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的政策考量转变为对受欺诈的婚姻当事人一方知情同意权的保护,〔4〕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46-48 页。在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情况下,只有不如实告知对方,对方才有权请求撤销婚姻。显而易见,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效力很难再被一概囊括于《民法典》第1053 条的适用范围之内,而《民法典》第1051 条关于无效婚姻的规定也并未直接涉及此种情形,由此产生了一个无法忽视的法律漏洞。以“林某1 与王某婚姻无效纠纷案”为例,法院判决认为,尽管当事人已经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缔结婚姻关系时精神发育迟滞,不具有辨认能力,但该情形不属于《民法典》规定的三种婚姻无效情形,故对原告关于确认婚姻无效的请求不予支持。〔5〕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2)京0105 民初18221 号民事判决书。类似案例,参见四川省蓬安县人民法院(2021)川1323 民初965 号民事判决书。
目前学界鲜有对《民法典》背景下精神障碍者婚姻效力的系统性研究,在研究其他议题论及该问题时,观点也存在诸多分歧:有观点认为精神障碍者有权缔结婚姻,只要双方当事人知情,婚姻即为有效;〔6〕参见李雅琴:《论精神障碍者的婚姻家庭权利》,载《人权》2018 年第6 期,第46-47 页。有观点从民事行为能力的角度出发,认为欠缺民事行为能力人缔结的婚姻无效〔7〕参见夏吟兰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第3 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81-82 页。或者可撤销〔8〕参见马忆南:《民法典视野下婚姻的无效和撤销——兼论结婚要件》,载《妇女研究论丛》2018 年第3 期,第28 页。;有观点提及除法定年龄外,民事行为能力不应影响婚姻效力,否则可能造成误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不规定此种瑕疵类型是合理的;〔9〕参见龙俊:《〈民法典〉中婚姻效力瑕疵的封闭性》,载《社会科学辑刊》2022 年第4 期,第74-75 页。还有观点指出结婚行为能力不同于民事行为能力,结婚行为能力欠缺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无效〔10〕参见李昊、王文娜:《婚姻缔结行为的效力瑕疵——兼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的相关规定》,载《法学研究》2019 年第4期,第110 页;田韶华:《身份行为能力论》,载《法学》2021 年第10 期,第138 页。或者不成立〔11〕参见冉克平、陈丹怡:《被拐卖妇女婚姻的效力分析——兼论被拐卖妇女的权利救济路径》,载《湖湘法学评论》2022 年第1 期,第22-23 页。。
在司法实践中,有法院认为欠缺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无效,〔12〕参见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2022)豫0527 民初2962 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法院(2014)巫法民初字第01058号民事判决书。在认定婚姻无效时,有法院直接适用了原《民法总则》第144 条(即《民法典》第144 条)关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13〕参见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6 民初5804 号民事判决书。有法院认为以精神障碍者欠缺民事行为能力为由请求确认其婚姻无效没有法律依据;〔14〕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8 民初47137 号民事判决书。有法院认为精神障碍不属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的婚姻无效情形,应当驳回确认婚姻无效的诉讼请求。〔15〕参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2 民初14419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01 民终5110号民事判决书。
以上争议和讨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更为基础和宏大的理论问题,即婚姻家庭法回归《民法典》之后如何与其他各编进行衔接与协调。质言之,《民法典》总则编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是否可以直接适用于结婚行为?相较于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结婚行为是否具有以及有何特殊之处?这些特殊之处使得在认定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效力时需要在《民法典》中进行何种解释路径的选择?
为了厘清这一系列问题,本文将以《民法典》的规范体系为基础,运用解释论的方法探讨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效力问题,并借此分析《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和总则编之间适用关系的相关问题,一方面尝试填补《民法典》制定时留下的法律缺口,另一方面促进《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和总则编的互动与体系融贯。
二、《民法典》中结婚行为能力的认定
(一)结婚行为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关系厘定
法律行为制度的意义是个体基于意思自治形成法律关系,具备意思自治的能力是法律行为生效的前提。〔16〕参见[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214 页。质言之,只有当行为人能够充分理解和判断自己作出的意思表示的后果时,行为才是有意义的,这种理解和判断能力即行为能力。从自然人个体的角度看,一个人的理解和判断能力需要结合具体的行为条件才能确定,〔17〕参见李国强:《论行为能力制度和新型成年监护制度的协调——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制度安排》,载《法律科学》2017 年第3 期,第132 页。尽管结婚在性质上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中的身份行为,但结婚行为能力应当区别于一般的民事行为能力,属于民事行为能力中的特殊情况。民事行为能力主要是指当事人对具有计算性和功利性的财产行为的理解与判断能力,其本质是以经济理性为基础的计算能力,〔18〕参见田韶华:《身份行为能力论》,载《法学》2021 年第10 期,第128 页。这一点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6 号,以下简称《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5 条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认定时“标的、数量、价款或者报酬等”考量因素的规定中也可窥见一二。与之相对,结婚行为能力则是当事人对结婚这一极具人伦和情感色彩的身份行为的理解与判断能力,产生爱慕情感并步入婚姻与市场交易之间存在天壤之别,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计算能力至少不是结婚行为能力的主要或实质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也有法院使用了结婚行为能力、结婚能力、结婚意识能力的表述,〔19〕参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09)闵民一(民)初字第14283 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2)金义佛堂民初字第22 号民事判决书;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15)龙新民初字第5656 号民事判决书。或者在认定婚姻效力时提及精神障碍者对结婚这一行为的概念和目的均缺乏理解和判断能力。〔20〕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2)浦民一(民)初字第10999 号民事判决书。
结婚行为能力的相对独立性在比较法上也有据可循。例如,在德国,结婚行为能力和遗嘱行为能力是民事行为能力中的分支或特殊情况,〔21〕参见[德]汉斯·布洛克斯、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第33 版),张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3-174 页。合格的婚姻当事人需要对结婚行为的性质和影响有充分的理解和判断能力,当事人可能对生活中的某一个或几个领域出现了(部分)无行为能力的状态,但如果其对结婚行为具有理解和判断能力,就应当肯定其婚姻效力。〔22〕Vgl.Wellenhofer,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9.Aufl., 2022, § 1304 BGB Rn.3.英国《婚姻诉讼法案》第12 条规定的可撤销婚姻的情形之一是对结婚行为不能作出有效的同意,其中包括欠缺相关的心智(或者称为精神能力)。〔23〕See Matrimonial Causes Act 1973, Section 12(1)(c).法律要求当事人必须在精神和智力上能够理解与婚姻有关的义务和责任,如果没有这种程度的心智,当事人就不能对结婚行为作出有效的同意。〔24〕See Park v.Park [1953]3 W.L.R.1012.类似地,新西兰《家事诉讼法案》第31条关于婚姻无效的规定中也包含了因为欠缺精神能力而无法对结婚行为作出有效同意的情形。〔25〕See Family Proceedings Act 1980(New Zealand), Section 31(1)(a)(ii).
尽管我国《民法典》总则编以提取公因式的抽象立法技术统领整个法典,但各分编另有规定的,在逻辑上应排除具有一般性的总则编而适用分编的特殊规定。〔26〕参见王利明:《论〈民法典〉实施中的思维转化——从单行法思维到法典化思维》,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3 期,第10 页。虽然财产法和亲属法都包含在民法中,但两者的“性格相当不同”。〔27〕参见[日]星野英一:《现代民法基本问题》,段匡、杨永庄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 年版,第66 页。基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调整对象具有的身份性和伦理性等特殊属性,在婚姻家庭编对当事人因婚姻家庭产生的人身和财产关系有规定时,应当优先适用婚姻家庭编的规定。“结婚是具有高度人身属性的法律行为,并且涉及个人的法律地位,所以结婚对人的能力有强制性的要求。”〔28〕[德]迪特尔·施瓦布:《德国家庭法》,王葆莳译,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第44 页。对于结婚行为能力,《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法定婚龄作出了区别于总则编划分民事法律行为能力年龄界限的规定(《民法典》第1047 条),从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看,法定婚龄的确定既要考虑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人口状况等宏观因素,也要考虑自然人的智力和身体情况等微观因素,〔29〕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28 页。也即达到法定婚龄的当事人被认为其身体和理性都已发育成熟,对结婚行为具有完全的理解和判断能力,能够以自己的意志决定是否缔结婚姻并承担婚姻的义务及其他相应的法律后果。由此,结婚行为能力与一般的民事行为能力的区分并非仅停留于理论层面,同时也具有现行法的直接依据。
然而,年龄并非结婚行为能力的唯一认定标准,结婚行为能力的关键是当事人是否有能力通过自己自由、真实的意思表示有效地缔结婚姻关系,而法定婚龄仅仅是判断有无这种能力的一种外部形式化标准。《民法典》第1046 条特别强调“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此处的“自愿”应解释为当事人作出的结婚意思表示自由、真实,〔30〕参见贺剑:《意思自治在假结婚、假离婚中能走多远?——一个公私法交叉研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 年第5 期,第23 页。这是婚姻有效的要件之一,而此种意思表示的作出系以当事人具有结婚行为能力为前提。有趣的是,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写的释义书在解释《民法典》第1046 条时也明确将当事人具有结婚行为能力(而非民事行为能力)作为婚姻有效的要件之一。〔31〕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27 页。最高人民法院则指出,对于男女双方是否自愿的判断标准,除了考察当事人是否受到强迫或干涉外,还应审查当事人是否有能力完全理解结婚的性质、后果和意义。〔3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年版,第53 页。职是之故,尽管《民法典》并未明确对结婚行为能力作出单独规定,但通过对《民法典》第1046、1047 条的解释可以认为,结婚行为能力系区别于一般民事行为能力的一种特殊民事行为能力。
(二)结婚行为能力的认定模式与认定标准
与民事行为能力一样,采用何种模式对当事人的结婚行为能力加以认定是该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毫无疑问,最准确的当然是一概进行个案认定,然而这种做法可能导致的成本升高和法律上的不确定性使其不具有技术上的可操作性。因此,法律以法定婚龄作为一个重要的规律性衡量标准并进行了明文规定,除此之外,已达到法定婚龄的当事人的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也对结婚行为能力有实质影响,这正是本文聚焦的问题所在。
根据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的不同,精神障碍者可能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33〕参见《评定指南》第5.1 条。依据《民法典》第24 条第1 款,其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需要由利害关系人或有关组织提出申请,并由法院进行司法认定;法院在受理申请后,必要时应对被申请人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司法鉴定(2023 年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第199 条)。但对于精神障碍者的结婚行为能力,相应的认定机关和认定程序都付之阙如,由此构成了现行法框架下区分结婚行为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一大障碍。
对该问题最容易想到的方法是由婚姻登记机关承担该项职责。然而,这种方法可能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婚姻登记条例》(国务院令〔2003〕第387 号)第7 条和第13 条关于婚姻登记机关在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时审查义务的规定系为形式审查。〔34〕参见夏吟兰:《婚姻家庭编的创新和发展》,载《中国法学》2020 年第4 期,第76 页。婚姻登记仅是对婚姻关系是否存在这一私法效果进行确认与公示,而非设立或消灭婚姻关系,对于该私法效果的终局判断权应属于法院而非婚姻登记机关,〔35〕参见王世杰:《论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效力》,载《政治与法律》2019 年第9 期,第80 页。婚姻登记机关的公法行为不应作为法律行为的内容。〔36〕参见朱晓喆:《论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民法总则〉第135 条评释》,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 年第2 期,第151 页。因此,将当事人结婚行为能力的实质审查义务赋予婚姻登记机关有过于苛责之嫌,也与婚姻登记行为的性质存在龃龉。以“孙东亮与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结婚登记案”为例,法院指出,对于结婚登记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法院仅就结婚登记程序进行审查,婚姻效力不在审查范围内,要求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结婚时的心智进行实质审查过于苛刻。〔37〕参见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3 行终456 号行政判决书。其次,《民法典》第1052 条修改了原《婚姻法》第11 条,将婚姻登记机关排除出有权撤销婚姻的机关之外,从而将婚姻效力的认定机关统一于法院。据此可以看出立法者对婚姻效力的重视态度,对婚姻效力及其相关问题(包括结婚行为能力)的认定十分复杂,婚姻登记机关没有能力也无需越俎代庖地介入这一事宜。〔38〕参见《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编写组编:《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477 页。最后,根据《民法典》第24 条第1 款,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机关为法院,如若结婚行为能力的认定机关却为婚姻登记机关,这种在认定机关上相去甚远的安排并无充分的正当性理由。
那么,转而将结婚行为能力的认定向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看齐,由法院启动民事诉讼法上的特别程序对结婚行为能力进行司法认定似乎是更为可取的方法。然而,这种方法的弊端在于,一个人在从事每一项法律行为之前,不可能对其和相关当事人都进行某种“成熟度测试”,这不利于法律交往的便捷,也会提高法律交往的成本。〔39〕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第410 页。更为显而易见的是,一方面,不分情形地对民事行为能力和结婚行为能力进行双重认定会极大地加重法院的诉累,并且由此进行逻辑推演的后果是,遗嘱等其他身份行为能力是否也都需要法院逐一单独认定?另一方面,由法院启动特别程序专门认定当事人的结婚行为能力也缺乏现行法依据。
有鉴于此,在现行法的框架下一种可能的权宜路径是,结合民事法律行为能力制度对结婚行为能力进行具体判断。展开来说,就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而言,其辨认能力完全缺失,没有判断和自我保护能力,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和行为后果,〔40〕参见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法(办)发〔1988〕6 号]第5 条、《评定指南》第A.3 条。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不宜认为当事人仍然具有结婚行为能力。〔41〕对结婚行为能力的划分无须采取民事行为能力的三级标准,仅以结婚行为能力的有无作两级划分即可。类似观点,参见李霞:《论成年非完全行为能力人的类型及其法律行为之效力》,载《政法论丛》2010 年第5 期,第21 页。申言之,婚姻不仅是两个人感情和性爱的结合,更是一个相互照料、共同生活的团体,一个生育子女的合作场所,一个经济生活的共同单位。〔42〕参见[英]霭理士:《性心理学》,潘光旦译注,商务印书馆2009 年版,第378 页。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结婚行为能力应当考察其是否有能力理解和判断缔结婚姻这一行为的性质和后果,其中当然包括理解和判断婚姻赋予当事人对配偶、子女和家庭的义务、责任以及可能带来的财产和人身关系等一系列后果。〔43〕See Jonathan Herring, Family Law,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11, p.62.具备结婚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必须能够理解婚姻的目的以及随之而来的责任,〔44〕See Johnson v.Johnson, 104 N.W.2d 8, 14 (N.D.1960).如果当事人仅对结婚后可能与配偶一方共同生活有理解和判断能力,而不能辨认结婚具有的其他意义和法律后果,则其不应当被认为具有结婚行为能力。当然,此处的理解和判断能力是针对结婚行为一般意义上的性质和后果,而非与特定人结婚的后果。对结婚行为能力的要求并不比对民事行为能力的要求低,〔45〕类似观点,参见杨立新:《论亲属法律行为》,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5 期,第4-5 页。这不仅体现在婚姻具有的上述涵盖事项的广泛性和重大性上,还体现在相较于一般的民事法律交易具有的单发性和短暂性,通常而言婚姻给当事人带来的影响是持续和长期的。在英国的一个案件中法官特别提及婚姻并不总是为当事人提供温暖、照顾和保护,结婚行为能力的要求过低可能使当事人陷入剥削性和虐待性的婚姻中,从而使当事人遭受难以修复的伤害,包括可能使其成为性犯罪的受害人。〔46〕See KC and NNC v.City of Westminster Social and Community Services Department [2008]EWCA Civ 198.我国《民法典》第1047 条规定的法定婚龄标准高于《民法典》第18 条规定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年龄标准,以及《民法典》第1143 条第1 款规定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这一较高身份行为能力标准也可作为佐证。由此,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即完全缺失辨认能力、无法理解和判断自己实施的一般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及后果的当事人自然也无法理解和判断结婚行为的性质及后果。换言之,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应当直接被认定为无结婚行为能力。
就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而言,其辨认能力不完备,不能完全辨认自己的权利、义务和行为后果,不能全面、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47〕参见《评定指南》第A.2 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具有较大的容纳空间和弹性空间,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与其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后果等因素进行认定,〔48〕参见《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5 条。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法律行为既可能是购买食品、图书等日常生活行为,也可能是将房屋赠与亲属等重大行为。〔49〕参见常鹏翱:《意思能力、行为能力与意思自治》,载《法学》2019 年第3 期,第114-115 页。由此,尽管结婚行为能力的标准高于民事行为能力,但由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界限本身的巨大张力,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精神障碍者的结婚行为能力,很难采取与无民事行为能力精神障碍者类似的将结婚行为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直接对标”的方法,而只能采取个案审查的方法。这种个案审查并非如同《民法典》第24 条第1 款规定的专门性司法认定,而是在个案中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请求法院确认婚姻无效时,由法院具体判断已被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是否具有结婚行为能力。
另外,若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精神状态正常〔50〕《评定指南》第A.1.1 条规定:“精神状态正常,指以下情形:按CCMD 标准诊断为无精神病;既往患有精神障碍,但进行民事活动时无精神异常表现;伪装精神病或诈精神病。”或者虽然能建立明确的精神障碍诊断,但并不影响其对所进行民事活动的辨认能力,能够良好地辨认自己的权利、义务和行为后果,完整、正确地作出意思表示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51〕参见《评定指南》第5.1.1 条、第A.1 条。其也具有结婚行为能力。然而,基于结婚行为能力的较高判断标准,在特殊情况下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也可能缺乏对结婚行为性质和后果的理解和判断能力,欠缺结婚行为能力,同上述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婚姻被请求确认无效,应由法院对当事人的结婚行为能力进行认定。但对上述特殊情况的认定必须格外慎重,否则可能造成对当事人结婚行为的不当干预。这种情况实际上还包含了精神障碍者虽然事实上欠缺民事行为能力,但尚未被法院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52〕在法院认定之前,任何成年人不得被视为欠缺民事行为能力。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第2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6 页。由此也可弥补民事行为能力认定中的遗漏。
综上所述,对精神障碍者结婚行为能力的认定应采取以民事行为能力为参照的“直接对标”和“个案审查”相结合的双轨制模式。质言之,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无结婚行为能力,无须另行审查;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的结婚行为能力,由法院在依据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申请确认婚姻是否无效时进行个案判断。由此,一方面可以较大地减轻对所有精神障碍者的结婚行为能力都逐一认定的负担(暂且价值无涉,仅从事实角度来看,司法实践中对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数量远大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53〕参见彭诚信、李贝:《现代监护理念下监护与行为能力关系的重构》,载《法学研究》2019 年第4 期,第63 页。);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现行法的框架下兼顾结婚行为能力的特殊性,使得对结婚行为能力的认定尽可能精准、灵活和周延。
(三)结婚行为能力个案审查的考量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结婚行为能力的个案审查往往发生在婚姻缔结之后,这就意味着法院作出的判断是在事后进行的,由此给当事人的举证和法院的判断都带来了较大困难,并且当事人结婚与法院审理之间间隔时间越长,这种困难就越大。〔54〕参见彭诚信、李贝:《民法典编纂中自然人行为能力认定模式的立法选择——基于个案审查与形式审查的比较分析》,载《法学》2019 年第2 期,第142 页。因此,有必要借鉴《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5 条并结合相关司法实践的有益经验,对法院在审查结婚行为能力时可能的具体考量因素进行列举和分析,为司法裁判提供相对清晰和统一的参考依据,一来有利于减轻实务中的操作负担,二来有利于防止法院自由裁量权的不当扩张。法院在对结婚行为能力进行审查和判断时应当结合个案的实际情况,综合考量以下因素。
第一,精神障碍者的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法院在考察精神障碍者的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时,最直观和直接的方法是对其进行观察、询问,特别是针对缔结婚姻这一行为的意义和权利、义务等后果进行询问。观察和询问与结婚的时间间隔长短和对精神障碍者心智状况判断的准确程度呈反比。如果精神障碍者在结婚后不久就具有极端异常行为,例如自言自语、情绪暴躁、对配偶或其他人进行人身侵害等,〔55〕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武鸣县人民法院(2021)桂0122 民初1984 号民事判决书。或者在服用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56〕参见四川省岳池县人民法院(2021)川1621 民初589 号民事判决书。则有可能其结婚时就因心智状况问题而不具备结婚行为能力。当然,通常来说仅通过观察和询问远远不够,具有相关资质的医疗机构作出的医学诊断、鉴定证明以及病历资料(特别是婚前作出的)等,〔57〕参见江西省安义县人民法院(2021)赣0123 民初1731 号民事判决书;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1)桂0226 民初556 号民事判决书。以及残疾人证〔58〕参见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0 民初9383 号民事判决书。、婚检证明〔59〕参见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2019)闽0581 民初4689 号民事判决书。等也可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在必要时应当对精神障碍者进行司法鉴定,对其精神障碍的类型、程度和持续时间,精神障碍对其理解和判断能力的影响等进行鉴定。
第二,精神障碍者在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时的具体情况。包括其在进行结婚登记时是否有监护人陪同或辅助、精神状态、对结婚意愿的表达情况、《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与《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的填写情况等。〔60〕参见《婚姻登记工作规范》(民发〔2015〕230 号)第36、41 条。
第三,精神障碍者在婚姻生活中的境况。尽管结婚后婚姻生活的境况与当事人结婚时结婚行为能力的有无并无必然关联,但基于法院对结婚行为能力的审查一般均为事后审查,将精神障碍者在婚姻生活中的境况作为考量因素之一对结婚行为能力进行反推,也不失为一种与一般社会观念和常理相符的做法。如果通过当事人日记、社交账号等的记载,亲属、朋友或邻居的观察、描述,家庭监控视频或其他载体的记录等能够确认精神障碍者的配偶对其较好地履行了扶养义务,夫妻生活和谐、幸福,那么很可能缔结婚姻的行为是一个有相应理解和判断能力的当事人实施的。〔61〕参见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鄂03 民终255 号民事判决书。反之,如果精神障碍者的配偶没有对其履行或充分履行扶养义务,甚至存在虐待、遗弃、家庭暴力等行为,明显通过结婚获得了某种自己无法获得的重大利益,例如户口、购房资格等,精神障碍者因为婚姻遭受了较大的人身或财产损害,夫妻关于婚后财产(包括积极和消极财产)关系或离婚财产关系的约定显失公平等,那么对于精神障碍者是否具有结婚行为能力、是否能够完全理解结婚行为的性质和后果并作出相应的决定,则应当予以慎重考量。
三、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婚姻效力的解释路径
根据上文对结婚行为能力的划分,具有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有效当无疑义,需要深入探讨的是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效力,对此《民法典》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在《民法典》体系下“找法”,为这种类型的婚姻效力提供解释依据是接下来要完成的工作。
(一)婚姻不成立:一条走不通的解释路径
一种值得探讨的观点是,无结婚行为能力人因为无法与对方达成结婚的合意,因而其缔结的婚姻不成立。〔62〕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01 民终5110 号民事判决书。严格来说这并非婚姻效力的问题,而是婚姻关系根本不存在。这种观点的可商榷之处在于,一方面,根据《民法典》第134 条第1 款,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需要当事人和达成合意两个构成要件;与之类似,婚姻成立的要件为男女双方当事人和达成结婚的合意,后者实际上是指外在的、客观上达成合意,至于当事人是否真的达成合意则属于已成立婚姻的效力问题。〔63〕参见余延满:《亲属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142 页。将对当事人结婚行为能力的认定作为是否达成结婚合意的考量因素从而据此判断婚姻是否成立,与成立要件中“达成结婚合意”的意旨不符,由此推演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将对结婚意思表示和合意的所有实质性考量(例如意思表示是否自由、意思与表示是否一致等)“前移”,不必要地混淆婚姻的成立与有效。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 号)第1 条第1 款第1句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也可作为成立要件认定的佐证。更为清晰且关键的是,《民法典》第143 条明确规定,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要件之一,以此为参照,当事人是否具有结婚行为能力应当是认定婚姻是否有效而非婚姻是否成立的要件。
另一方面,相较于婚姻存在效力瑕疵,将无结婚行为能力人缔结的婚姻(特别是存续时间较长的婚姻)解释为不成立(即不存在),似乎更不容易为一般的社会观念接受。此外,尽管从理论上看婚姻不成立和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并无明显差异,但对于前者《民法典》没有明确规定,在现行法没有增设婚姻不成立制度的前提下,从方便法律适用和为当事人提供充分法律保护的角度来看,不宜采取婚姻不成立的解释路径。〔64〕参见韩世远:《财产行为、人身行为与民法典适用》,载《当代法学》2021 年第4 期,第37 页。
(二)婚姻无效:在《民法典》总则编与婚姻家庭编中进行解释选择
对于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效力应当转而诉诸于婚姻效力瑕疵中的无效路径。《民法典》第1051 条规定了婚姻无效的三种事由,依据文义解释,该条对婚姻无效事由采取了封闭式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法释〔2020〕22 号,以下简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17 条第1 款也明确指出:“当事人以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一条规定的三种无效婚姻以外的情形请求确认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据此,有必要对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效力作出进一步解释。
《民法典》第144 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一条可能的解释路径是直接适用该条认定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无效。然而,问题在于一方面,结婚行为能力是民事行为能力中的特殊情况,尽管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也无结婚行为能力,但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不一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民法典》第144 条只能涵摄部分情形。另一方面,即使是对于既无结婚行为能力也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也不宜直接适用《民法典》第144 条认定其缔结的婚姻无效。原因在于《民法典》总则编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多是以财产法的逻辑为基础构建的,其与以身份性和伦理性为基础的身份关系存在本质区别,〔65〕参见谢鸿飞:《民法典与特别民法关系的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2 期,第113 页。有鉴于此,将《民法典》总则编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直接适用于婚姻效力的确认不乏商榷余地;况且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婚姻无效事由已经作出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更不宜越过身份法中的专门性规定而直接诉诸总则编中的法律行为无效制度,否则可能违背婚姻家庭编基于身份关系的特殊性而进行的特别考量。〔66〕参见冉克平:《论婚姻缔结中的意思表示瑕疵及其效力》,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5 期,第119 页。此外,如前所述,尽管可以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与无结婚行为能力“直接对标”,但这仅是基于操作性层面的考量而在认定结婚行为能力时采取的认定标准上的参照与妥协,而非民事法律行为规定的直接适用,这并不影响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在婚姻效力判断层面对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规定的排斥。
另一条解释路径是回归《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婚姻无效的规定。《民法典》第1051 条规定婚姻无效的事由之一是“未到法定婚龄”,这一规定看似无碍,但从《民法典》整体脉络看,却因欠缺依制定法的调整计划应当预期被设定的特定规则而存在法律漏洞,而这种制定法的调整计划可以通过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的方式探寻。〔67〕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6 版),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 年版,第469-471 页。
首先,从历史解释的角度看,《民法典》第1051 条将原《婚姻法》第10 条中的“疾病婚”从婚姻无效事由中删去,并通过《民法典》第1053 条受欺诈(针对患重大疾病)的可撤销婚姻规定进行调整,其目的是尊重当事人的婚姻自由,但忽略了此种立法变化导致的对不存在欺诈情形的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婚姻效力的遗漏。从此种遗漏所引发的理论争议和实务混乱可以推知,这绝非立法者有意为之,而是无心之失。而且查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写的相关立法资料也无法看出立法者存在遗漏此种情形的意图。〔68〕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46-49 页;《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编写组编:《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26 页。与之相关,《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17 条系延续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11〕18 号)第1 条而来,该条的主要着眼点实际上是对结婚登记程序瑕疵的处理,明确了仅以结婚登记存在程序瑕疵(而不存在《民法典》第1051 条规定的情形)为由主张婚姻无效的,法院不予支持。〔6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 年版,第162-164 页。以此着眼点为指引,最高人民法院强调了以《民法典》第1051 条规定的三种事由以外的情形请求确认婚姻无效的,法院应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而并未注意到《民法典》的立法修改导致的情形遗漏,由此导致了现在的尴尬处境。
其次,从目的解释的角度看,设置法定婚龄的一大原因是当事人只有达到一定年龄,其生理和心理才发育成熟,才具有理解和处理婚姻事务的能力,否则可能很难承担结婚后对配偶、家庭和子女的责任。〔70〕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40 页。法定婚龄实际上是立法者对结婚行为能力的要求(当然也包括对一个国家人口状况、风俗习惯等因素的考虑,两者并无龃龉),对当事人的结婚行为能力一般应当通过其年龄和心智状况进行判断,《民法典》第1051 条只规定了前者,而遗漏了后者。
最后,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民法典》第144 条对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采取了“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而《民法典》第1051 条对婚姻无效却采取了仅属于无结婚行为能力情形之一的“未到法定婚龄”的规定,从整体脉络来看显然不利于《民法典》的体系融贯。
综上,《民法典》第1051 条“未到法定婚龄”的规定违反制定法计划的完整性而存在需要填补的法律漏洞。为了充分实现制定法规则的目的以及避免不正当的评价矛盾,应当将《民法典》第1051条婚姻无效情形中的“未到法定婚龄”目的性扩张为“无结婚行为能力”,由此,对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应直接依据《民法典》第1051 条认定为无效。〔71〕在特殊情况下,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可能同时符合婚姻无效与可撤销的情形,由于《民法典》对胁迫结婚和患重大疾病的欺诈结婚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很可能直接适用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在理论上,婚姻无效与可撤销属于规范的择一竞合,当事人可选择行使其中一项权利,该权利实现则不得主张另一项权利。在面对《民法典》第1051 条的法律漏洞时,之所以采用目的性扩张的方法而非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44 条,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基于前述结婚行为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差异,认为两者满足类推适用要求的“在所有的评价具有本质意义的方面上都是一致的”〔72〕[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6 版),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 年版,第501 页。存在难度;另一方面,《民法典》第1051 条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17 条第1 款对婚姻无效事由封闭性的规定实际上排除了对《民法典》总则编(第144 条)的直接适用或类推适用,因此在面对必须填补的法律漏洞时采用目的性扩张的方法更为合适。诚然,此种解释路径虽然瑕瑜互见,但在民法典时代立法论工作暂且“退居二线”的背景下,也不失为一种既有利于尊重婚姻家庭编和身份关系的特殊性,又有利于周延解决现实问题的解释路径。
(三)婚姻无效和可撤销的比较分析:基于价值衡量的视角
尽管如前所述,《民法典》第1052、1053 条关于婚姻因胁迫和隐瞒重大疾病而可撤销的规定无法涵盖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婚姻的情形,但基于价值衡量的视角,仍有必要探讨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效力是否可以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053 条而可撤销。在方法论层面最直观的否定理由是,《民法典》第1053 条的规范意旨是对欺诈婚姻效力的认定,与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在事实构成上并无本质相同或相似之处,无法进行类推。然而在价值层面,由于婚姻可撤销和无效的解释路径背后承载着不同的价值立场,对这两条路径及其背后的价值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回应不同解释路径的选择争议,同时也为婚姻无效路径提供合理性支持。
婚姻效力的价值体系蕴含着对个人婚姻自由(意思自治)的尊重、对婚姻家庭利益的保护和公权力对婚姻的管控或限制三种价值维度,〔73〕参见申晨:《论婚姻无效的制度构建》,载《中外法学》2019 年第2 期,第459-460 页。婚姻无效和可撤销在体现和承载这三种价值方面存在侧重程度的差异。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无效,目的在于通过公权力的干预更多地实现对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的保护(保护其免受自己行为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损害)〔74〕参见[德]汉斯·布洛克斯、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第33 版),张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4 页。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申言之,公权力介入婚姻家庭,通过婚姻无效的制度安排实现对家庭中弱势群体的保护这一底线道德的维护。〔75〕参见夏江皓:《家庭法介入家庭关系的界限及其对婚姻家庭编实施的启示》,载《中国法学》2022 年第1 期,第64-65 页。而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可撤销,则更多地体现了保护婚姻自由和婚姻家庭利益的价值立场。
首先,尽管法政策很难一概绝对地勾勒出所有价值位阶的谱系,但某些价值更为优先是得到普遍认可的共识,典型的就是对个人生命、健康的保护,当保护个人生命、健康的价值和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其他价值都应当退居其次。〔76〕参见王利明:《民法上的利益位阶及其考量》,载《法学家》2014 年第1 期,第82 页。相较于一般的普通人,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本身在智力和精神健康状态方面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更容易受到结婚行为的伤害。特别是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旨在通过婚姻获取特定省市的户口、购房资格、购房优惠、拆迁补偿款等利益的情况屡见不鲜。〔77〕参见金眉:《论通谋虚伪结婚的法律效力》,载《政法论坛》2015 年第3 期,第183-184 页;贺剑:《意思自治在假结婚、假离婚中能走多远?——一个公私法交叉研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 年第5 期,第21 页。更有甚者,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可能会因婚姻的缔结而遭到配偶长期的虐待、性侵甚至沦为生育工具,〔78〕参见张强:《论智力残障者性权利的司法保护》,载《残疾人研究》2018 年第1 期,第64-66 页。其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到侵害。因此,在以婚姻自由和婚姻家庭利益为一端的天平上,另一端即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的生命、健康是更为重要的价值,同时涉及防止政策漏洞或政策盲区被不当利用从而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的不良影响或损害。诚然,对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侵害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不会发生在所有婚姻中,但法律的制度选择应当慎重地采取底线考量,以防止可能发生的重大价值减损。
其次,在进行价值衡量和选择时,比例原则是通常使用的分析工具。申言之,如果为保护某种价值而必须侵害或减损另一种价值时,不得超过必要的程度,或者至少是“合理的”。〔79〕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6 版),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 年版,第518 页。对于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效力,由于婚姻无效与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不同,婚姻无效制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无效的解释路径对婚姻自由和婚姻家庭利益的影响或限制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是合比例的。
具体而言,其一,与婚姻可撤销一样,婚姻无效制度采取了宣告主义,而非当然无效。婚姻无效需要婚姻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请求,法院经过审理确认后婚姻才属无效(《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9 条);反之,若婚姻未经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当事人的近亲属)请求、法院确认,则不得被视为无效。以此为据,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如果未经上述法定程序确认,则仍为有效。如果意欲保持婚姻效力,则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不向法院请求确认婚姻无效即可。其二,尽管提出婚姻无效的请求不受除斥期间的限制,但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10 条,当事人请求确认婚姻无效,如果无效情形在起诉时已经消失,例如结婚时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在起诉时已具有结婚行为能力,则法院不予支持。其三,婚姻无效与可撤销之间的法律后果相同,《民法典》第1054 条对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双方当事人的财产和亲子关系作出了明确规定,婚姻无效后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的财产和子女权益可以得到妥善的保护,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本人符合法定条件也依然可以得到其子女的赡养,由此将最大程度地降低婚姻无效对婚姻家庭利益的负面影响。其四,如果利害关系人(例如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的父母)有意愿向法院请求确认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无效而使其脱离婚姻关系,那么在通常情况下也有意愿为其提供来自家庭的保护,而不致使其因原婚姻家庭利益减损而面临无人保护的状态。其五,就婚姻自由价值本身而言,如前所述,对精神障碍者结婚行为能力的认定并非笼统地采取与民事行为能力同质化的“一刀切”做法,而是将两者进行区分后采取以民事行为能力为参照的“直接对标”和“个案审查”相结合的双轨制模式,从而使得对结婚行为能力的认定更加准确和慎重。由此,在结婚行为能力的认定层面更好地践行了对精神障碍者婚姻自由的尊重。基于上述五点,与可撤销相比,婚姻无效并未对婚姻自由和婚姻家庭利益造成不合比例的过大影响或限制。
最后,反过来看,如果对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效力采可撤销的解释路径,则会对保护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这一价值带来较大影响。原因在于,其一,与请求法院确认婚姻无效的主体包括婚姻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不同,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的主体只能是婚姻当事人。对于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精神障碍者由于其心智状况的限制,自己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的可能性不大(身份行为也无法适用代理),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撤销婚姻的主动权就只能由配偶一方掌握,保护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的价值可能会落空。其二,因为婚姻撤销权的行使受到一年除斥期间(不变期间)的限制,如果撤销权人由于侵害行为还未发生或者其他客观障碍而在除斥期间内未行使撤销权,婚姻将终局地有效,这可能有悖于保护无结婚行为能力精神障碍者的目的。
此外,还需澄清的观点是,婚姻无效可能会侵犯或剥夺精神障碍者缔结婚姻的资格和自由权利,存在歧视精神障碍者之嫌。〔80〕参见王竹青:《论残疾妇女的自主权》,载《人权研究》2020 年第2 期,第37-40 页。这种观点并不成立,其混淆或者模糊了行为能力与权利能力之间的区别。具言之,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平等,所有人(包括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都有平等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其中也包括结婚的资格;而具有结婚行为能力则意味着能够有效地缔结婚姻,法律上对无结婚行为能力人缔结婚姻的效力进行否定评价并不等于否定其享有结婚的资格。《世界人权宣言》第16 条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第23 条在强调当事人享有结婚和建立家庭权利的同时也都明确要求双方结婚须有自由和充分的同意,而此种同意的作出系以具有结婚行为能力为前提。所以,婚姻无效仅仅是在婚姻效力层面对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进行必要的调控,而非对其结婚自由权的实质侵犯或剥夺。
综上,《民法典》对于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效力并非“有意沉默”而欲将其纳入《民法典》第1053 条的涵摄之下,这一“违反立法计划”的法律漏洞需要通过解释论的努力予以填补。婚姻无效和可撤销的解释路径背后蕴含着不同侧重的价值立场,尽管二者瑕瑜互见,但基于价值衡量的视角比较分析后可知,对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效力选择无效的解释路径不仅在实然的方法论层面更为恰当,在应然的价值层面也更为合理,在现行法的框架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解释方案。
四、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
《民法典》第1054 条对婚姻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后果进行了规定。根据该规定,无效的婚姻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所生子女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的规定,不因婚姻无效而受到区别对待。对于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22 条,除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以外,按共同共有处理),当事人协议处理不成的,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予以判决。可见,婚姻无效后对子女和共同财产分割的规定与离婚后对子女和共同财产分割〔81〕根据《民法典》第1087 条第1 款,离婚时法院对夫妻共同财产根据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进行分割,该规定比无效或可撤销婚姻同居期间所得财产的处理多出“照顾子女和女方”。根据《民法典》第1041 条第3 款“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基本原则的指引及《民法典》第1071 条第1 款“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的规定,无效或可撤销婚姻同居期间所得财产的处理也应当考虑对子女和女方的适当照顾。的规定之间实质上并无极大差异。
需要特别讨论的一个差异在于对“无过错方”的认定,《民法典》第1087 条第1 款和第1054 条均未明确何为“过错”,对此需要结合其各自的规范意旨和相关条文的规范脉络进行解释。就离婚财产分割来说,相较于原《婚姻法》第39 条第1 款,《民法典》第1087 条第1 款增加“照顾无过错方”分割财产原则的目的是加大对导致离婚过错方的惩罚力度和对无过错方的保护力度。申言之,在《民法典》第1091 条已经就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出规定的基础上,再在离婚财产分割中增加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有利于有效回应惩罚婚姻当事人过错一方的现实需求。〔82〕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175 页。依据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民法典》第1087 条第1 款中的过错情形既可以是《民法典》第1091 条规定的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重大过错情形,也可以是与他人有婚外性行为、赌博等影响婚姻家庭生活导致离婚的一般过错情形。〔83〕参见薛宁兰:《民法典离婚救济制度的功能定位与理解适用》,载《妇女研究论丛》2020 年第4 期,第94 页。
就无效和可撤销婚姻同居期间所得财产的分割来说,对过错的认定需要结合构成婚姻无效和可撤销的具体情形判断,因此《民法典》第1054 条中的过错情形主要包括胁迫,针对患重大疾病的欺诈,针对重婚、未到法定婚龄、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欺诈。〔84〕参见杨立新、李东骏:《婚姻缔结之际的损害赔偿责任》,载《法学论坛》2022 年第5 期,第10 页。在实践中,过错方可能是与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结婚的配偶,例如其存在胁迫行为;而既无民事行为能力也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一般不具备过错能力,〔85〕Vgl.Neuner, Allgemeiner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12.Aufl., 2020, S.131.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无结婚行为能力精神障碍者在确认婚姻无效的个案审查前无法知晓其有无结婚行为能力,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不会成为过错方,不存在因不如实告知对方自己的心智状况而存在过错的情况。
另外,值得追问的是,除了构成婚姻无效和可撤销的具体情形以外,在无效或可撤销婚姻的双方当事人同居生活期间,如果一方(在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婚姻无效的情形中,通常是其配偶一方)存在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行为,是否应属于《民法典》第1054 条规定的过错情形?答案是否定的。诚然,从一般的公平观念和保护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的角度看,似乎需要作出肯定回答,但回到《民法典》第1054 条的规范意旨就会发现,该条规定的过错应当特指对婚姻无效或可撤销有过错,〔86〕参见薛宁兰、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婚姻家庭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 年版,第101 页。正如《民法典》第1087条第1款和第1091条中的过错特指对离婚有过错(《民法典》第1054 条第1 款和第2 款规定的同居财产分割时照顾无过错方和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分别比照《民法典》第1087 条第1 款和第1091 条规定的离婚财产分割时照顾无过错方和无过错方的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8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年版,第107 页。因此,对过错的解释不宜偏离《民法典》第1054 条惩罚导致婚姻无效或被撤销过错方的立法目的。如果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的配偶存在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行为,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165 条第1 款的一般侵权责任条款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由此也同样能够实现对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如上所述,《民法典》第1054 条第1 款和第2 款分别规定了同居财产分割时照顾无过错方和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两者在适用上不存在优先顺序,而应当考察保护无过错方的目的是否能够有效实现。也就是说,法院需要甄别在同居财产分割时因为照顾无过错方而对其多分了多少财产,如果多分的财产难以弥补无过错方的损失、实现对无过错方的救济,则应当支持其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当然,无过错方也可以放弃主张在共同财产分割时对其的照顾而径直寻求损害赔偿。〔88〕参见刘征峰:《结婚中的缔约过失责任》,载《政法论坛》2021 年第3 期,第54 页。
相较于配偶,受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在同居生活期间在外从事职业劳动的难度可能更大,相应地,其在家较多从事家务劳动的可能性更大。基于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认可和对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的保护,可以考虑在婚姻无效后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088 条,对负担较多家务劳动的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作出一定的补偿。至于《民法典》第1090 条规定的离婚经济帮助,由于其规范目的主要是夫妻扶养义务在婚姻关系结束后的延续,这恰与婚姻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之间没有法定夫妻权利义务的效果存在根本龃龉,因此不宜对其类推适用。
五、结语
《民法典》实施后,相关研究逐渐转向了解释论,对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效力进行探讨正是对《民法典》相关具体规则的不完善进行解释论上“裂缝修补”的一次尝试。以结婚行为能力为标准对精神障碍者所缔结婚姻的效力判定固然存在一定的解释论难题,但也是对身份行为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作出必要厘清与区分的必经之路。在攻克难题的过程中,应当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婚姻无效的既有规定为基点,同时辅以对总则编民事法律行为规定的参照适用,通过两者的配合,一方面可有效填补法律漏洞,另一方面可实现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特殊性的坚守和与其他各编一般性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