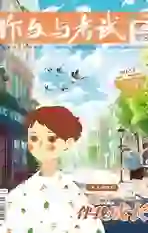麦地春秋
2023-11-05孙雨菲
孙雨菲
听长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们可以借助“倾听对话”和“表达记录”的双通道走进长辈的童年记忆。表达记录的形式是多样化的,除了采用不同人称,语言风格也可以结合自己的写作特点进行。有的同学喜欢简练清爽的叙事推进,有的同学擅长诗意浪漫的抒情表达。同样是以“麦田”为素材,上一期的《麦田少年》和这一期的《麦地春秋》,你发现表达上有什么不同吗?
(本栏目由浙江省杭州市王铁青运河特级教师工作室策划)
北方,人人脸颊上都是一片红,这是春季播种的痕迹。我沉在梦里,直到窗外的清光打碎梦影,队长的声音又一次响起——
“今天早晨,背上麦种,有锄头的扛锄头,有铁锨的扛铁锨,到北山的五亩地去播种。”
“诶!上工哟——”
凛冽的北风呼呼地刮着,似狮子疯了般的怒号,似烈马颤栗般的嘶啸。
我裹上了那件打满补丁的棉袄,扛起铁锨,跟着望不到头的队伍,向前行进。
到了地儿,大家放下东西,三人一伙儿地排着:一人挖坑,一人撒种,一人埋种。
北风吹来,霎时间尘土飞扬。很快,一缕阳光划破晴天,在白云红海的边缘,懵懵懂懂的空气中掺杂着一颗颗微尘。
恍惚间,该我埋土了。我拽起铁锨,把两边的土都给扒下去,一块,两块……一列干完又是一列。
这时,一个老社员带了个铁耙子走过来,他弯下身子把地一遍又一遍地溜平。一道道的纹路刻在朴素的泥土里,我觉得这里面有艺术的影子。
“太阳落山了,吃饭喽——”队长卯足气,大声吼道。
大家赶忙收工,纷纷回家。
吃完饭已是夜晚了,我拾了一张小板凳,坐下来唱起了歌。不一会儿,就有人加入进来了,这首歌仿佛是美丽而神秘的语言——在宁静的夜里回响,如许愿一般,满是憧憬和期盼。
风穿过窗子的缝隙,掠过我的身旁,我一次又一次地望向那座高山,那片麦田海。
时间如风筝的影子,一晃而过。转眼间,秋带着所有人的期待,匆匆地来了。
“诶!上工哟——”
“拿上镰刀,收麦子喽——”
我一脸兴奋,揪了揪边上王嫂的棉大衣:
“这队长说的话当真?”
“那肯定呀!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儿!”
“太棒了!”
扛上锄头,我拔腿就跑,赶趟儿似的。
站在田埂上,东看看,西望望,眼前是一片黄色的海洋。我飞奔过去,一阵阵麦香扑鼻而来。
正午的阳光,像碎金子似的在麦尖上摇晃,荡漾。
我拿起镰刀,胳膊一圈儿一圈儿地抡着,手起刀落,轻松地把一缕缕麦秆割断了。
“诶!那边还有片地哟!”
“收收收,去那边儿收地喽!”狗娃扬着眉喊道。
“真是的,到处跑,换个远一点的地儿不行吗?”王嫂阴阳怪气地数落着。
我不好意思地收拾东西,灰溜溜地跑到另外一片麦地,重新开始收割。
有了前面割麦子的经验,這次就更加熟练了。胳膊抡了一个圈又一圈,金黄的麦子“歘歘”倒下。很快,麦子都收完了,只差最后一步用绳子打捆的工序。我看着老社员熟练的动作,有些眼馋,便恳求道:“社员师傅,让我来捆剩下的吧!”
“你?”
“对,我来!”我自信满满地对老社员说。
“就你?你要是能行,我都成队长了,哈哈哈——”王嫂不知何时来到了我身边。
听了王嫂的这番话,我立马急了,争辩道:“我为啥不行?嘁——”我一扭头,找了根绳子便开始捆起来。
“太阳落山了,吃饭喽——”
我一脸得意地提着自己捆的麦子,打算去王嫂跟前炫耀一下。结果还没走几步,“刷”的一声,绳子松了,麦子散了一地。我心头一紧,停下脚步,东张西望,确定边上没人之后,赶紧蹲下身来一顿拾掇,重新研究怎么捆才能结实。
“呦——”身后突然传来王嫂的声音,我吓了一跳。本来我就是特意避开她的,结果“墙”到底还是透了“风”,怕啥来啥。我攥着手不知所措,只感觉后背发凉,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沉闷。
“那个……你……你怎么还在这儿?”我结结巴巴地问道。
“怎么,怕我笑话呀?”王嫂盯着我的眼睛,叹了一口气,“来吧!我来教你。”王嫂低下头,俯下身子,三下五除二就把麦子重新捆好了。动作之娴熟,让我目瞪口呆。
“你拿着呀!难不成还让我拿吗?”
“啊?哦哦!”我缓过神来,竟然忘了说声“谢谢”。接过王嫂捆好的麦子,我的手里紧紧实实的,心里再也不慌了。
我抱着金黄的麦子,笑了。王嫂也笑了,她脸颊上的“高原红”,在夕阳的辉映下,熠熠生辉。
(注:文中的“我”系作者的奶奶。)
(指导教师:王铁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