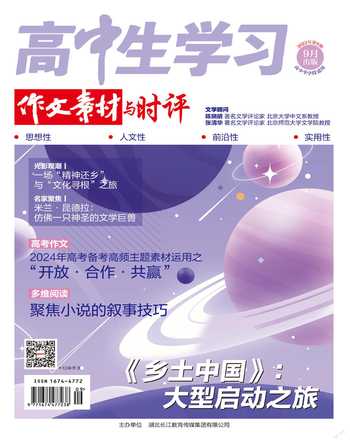米兰·昆德拉:仿佛一只神圣的文学巨兽
2023-11-05
文学巨匠米兰·昆德拉2023年7月11日因病辞世,享年94岁,其作品被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有无数拥趸,法国《费加罗报》7月12日誉其作品“超越意识形态和哲学分歧,仿佛一只文学的神圣巨兽”。

法国总统亲授国籍
昆德拉1929年4月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在身为音乐教师和钢琴家的父亲熏陶之下,他爱上音乐和文学。1948年,昆德拉在布拉格学习哲学、音乐和电影,并出版自己的第一本诗集《人:一座广阔的花园》,之后留校任教并出版一系列作品,凭借超现实主义风格获得该国文坛的认可和荣誉,尤其《玩笑》令他声名鹊起。然而到1968年,这本《玩笑》却被列为禁书,昆德拉也一度被骂“庸俗”,不仅失去教职,而且被禁止发表任何作品。
1975年,在他的支持者、法国议会主席埃德加·伏奥雷的邀请下,昆德拉和妻子薇拉获准前往法国生活,在雷恩大学任教。1981年,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亲自授予昆德拉法国国籍,昆德拉也将巴黎视为“第二故乡”。1984年,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获巨大成功,4年后被改编成电影《布拉格之恋》。
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涉及相当多的哲学概念,对诸如回归、媚俗、遗忘、时间、偶然性与必然性等多个范畴进行了思考。《纽约时报》曾这么评价此书——米兰·昆德拉凭此书奠定了他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在世作家地位。
影片《布拉格之恋》讲述了布拉格外科医生托马斯与两位女性——画家萨比娜、女招待特蕾莎之间的情爱纠葛,并辅以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作为电影背景。由好莱坞演技派丹尼尔·戴·刘易斯和法国女星朱丽叶·比诺什、瑞典女演员莉娜·奥琳主演,斩获奥斯卡等诸多奖项,也让昆德拉火“出圈”。电影并不失败,但爱情片的主题却跟原著主旨大相径庭,这不但让很多书迷愤怒,据说也让署名第一编剧的米兰·昆德拉感到失望。
2019年捷克大使在巴黎授予昆德拉公民证,正式恢复其捷克国籍。2020年,昆德拉获得该国著名的卡夫卡奖,他表示对此感到非常荣幸。
“影响几代读者”
捷克总理彼得·菲亚拉悼念称:“米兰·昆德拉是一位影响了各大洲几代读者并享誉全球的作家。”法国总理博尔内在社交媒体上追悼昆德拉:“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次深刻的探索,充满人情味,若即若离。”7月12日,欧洲议员在斯特拉斯堡默哀一分钟,以纪念昆德拉。
《巴黎人报》评论称:“作为为数不多在世时即入选‘七星文库’的伟大作家,昆德拉是一位擅长讽刺人类的作家。”法国《解放报》称:“昆德拉是阅读量最大的作家之一,讽刺和幽默在他的手中成了面对绝望最后的武器。他的人生格言是:无足轻重就是存在的本质。”
昆德拉是对中国当代文坛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之一。在东欧文学研究家、翻译家景凯旋看来,昆德拉的影响重点在思想上。“他让中国作家们从关注群体到关注个人自身,少作空洞的宏大叙事。”“他启迪中国文学界:真正一流的作家应该首先是思想家。”
200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迄今为止销量已突破300万册。评论认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影响了一代中国文学青年的精神之书,莫言、王安忆等作家都专门写过关于昆德拉的文章,昆德拉作品的译者曾表示“有个时期,几乎言必称昆德拉”。
“被诺贝尔文学奖遗忘的大师”
米兰·昆德拉的文学成就斐然,多次获得国际文学奖,并6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然而他却说,每年10月的诺贝尔文学奖热潮,对他来说都是一种骚扰。
昆德拉根本不在意,所谓的那些外界赋予他的价值。他常年远离媒体、拒绝抛头露面,只选择用作品说话。
他曾毫不留情地表示:“传媒的精神与文化的精神是相悖的,至少对现代欧洲所认可的文化是如此:文化基于个人,而传媒导向单一化;文化照亮事物的复杂性,而传媒使事物简单化;文化只是一种长久的拷问,传媒则快速回答一切;文化是记忆的守护神,传媒则是时下新闻的追逐者。”
昆德拉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也是一个成功隐身的作家。近40年来,由于一直拒绝在媒体上露面,并且极度注重个人隐私的保护,他从公共视野中消失了。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到《生活在别处》,再到八十多岁高龄时创作《庆祝无意义》,他笔下的故事和提出的问题让读者难以忘怀,而他本人却为自己的生活以及与他的经历有所牵连的百年历史贴上了封条。
法新社称,昆德拉只希望人们谈论他的作品,他与妻子薇拉低调地生活在巴黎,也因此曾多次被传出“死亡”谣言。薇拉是这位“山中高士”的重要伴侣,不仅充当他的翻译、社交秘书,还是他與外界接触的“桥梁”。
(综合环球时报、中国新闻网、上观新闻、澎湃新闻、羊城晚报消息)
1.永恒轮回之说从反面肯定了生命一旦永远消逝,便不再回复,似影子一般,了无分量,未灭先亡,即使它是残酷,美丽,或是绚烂的,这份残酷、美丽和绚烂也都没有任何意义。
2.如果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得无限重复,我们就会像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样被钉死在永恒上。这一想法是残酷的。在永恒轮回的世界里,一举一动都承受着不能承受的责任重负。这就是尼采说永恒轮回的想法是最沉重的负担的缘故吧。如果永恒轮回是最沉重的负担,那么我们的生活,在这一背景下,却可在其整个的灿烂轻盈之中得以展现。
3.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4.当初她太幼稚了,原以为国外的生活会改变她。她以为,经历了在占领的日子里她所经历的一切之后,自己已经不再平庸,已经长大、懂事、变得勇敢,但她过高估计了自己。她成为了托马斯的负担,而这又正是她不愿意的事情。她想在不可救药之前承担后果。还请他原谅将卡列宁也带走了。
5.人只有一次生命,绝无可能用实验来证明假设,因此他就永远不可能知道为自己情感所左右到底是对还是错。
6.我们都觉得,我们生命中的爱情若没有分量、无足轻重,那简直不可思议;我们总是想象我们的爱情是它应该存在的那种,没有了爱情,我们的生命将不再是我们应有的生命。我们都坚信,满腹忧郁、留着吓人的长发的贝多芬本人,是在为我们伟大的爱情演奏《Es muss sein!》(非如此不可!)。
7.在我们看来只有偶然的巧合才可以表达一种信息。凡是必然发生的事,凡是期盼得到、每日重复的事,都悄无声息。惟有偶然的巧合才会言说,人们试图从中读出某种含义,就像吉卜赛人凭借玻璃杯底咖啡渣的形状来作出预言。
8.人生如同谱写乐章。人在美感的引导下,把偶然的事件变成一个主题,然后记录在生命的乐章中。犹如作曲家谱写奏鸣曲的主旋律,人生的主题也在反复出现、重演、修正、延展。安娜可以用任何一种别的方式结束生命,但是车站、死亡这个难忘的主题和爱情的萌生结合在一起,在她绝望的一刹那,以凄凉之美诱惑着她。人就是根据美的法则在谱写生命乐章,直至深深的绝望时刻的到来,然而自己却一无所知。
9.自学者和学生的区别,不在于知识的广度,而在于生命力和自信心的差异。
10.那些画表面总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现实主义世界,而背后呢,就像是舞台背景的那块破布后面,人们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某种神秘的或者抽象的东西。表面是清晰明了的谎言,背后却是晦涩难懂的真相。
11.他们为彼此造了一座地狱,尽管他们彼此相爱。的确,他们彼此相爱,这足以证明错不在他们本身,不在他们的行为,也不在他们易变的情绪,错在他们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因为他强大,而她却是软弱的。正因为弱才应该知道要强,才应该在强者也弱得不能伤害弱者的时刻离开。
12.我可以说眩晕是沉醉于自身的软弱之中。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却并不去抗争,反而自暴自弃。人一旦迷醉于自身的软弱,便会一味软弱下去,会在众人的目光下倒在街头,倒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
13.也许现在更容易理解萨比娜与弗兰茨之间相隔的鸿沟了:他热切地聆听她讲述自己的人生,她也怀着同样的热望听他倾诉。他们完全明白彼此所说的话语在逻辑上的意思,却听不到话语间流淌着的那条语义之河的低声密语。
14.假若人還年轻,他们的生命乐章不过刚刚开始,那他们可以一同创作旋律,交换动机,但是,当他们在比较成熟的年纪相遇,各自的生命乐章已经差不多完成,那么,在每个人的乐曲中,每个词、每件物所指的意思便各不相同。
15.忠诚是第一美德,它使我们的生命完整统一。若没有忠诚,人生就会分散成千万个转瞬即逝的印迹。
16.第一次的背叛是不可挽回的。它引起更多的背叛,如同连锁反应,一次次地使我们离最初的背叛越来越远。
17.当初背叛父亲,她脚下展开的人生就如同一条漫长的背叛之路,每一次新的背叛,既像一桩罪恶又似一场胜利,时刻在诱惑着她。她不愿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决不!她决不愿一辈子跟同一些人为伍,重复着相同的话,死守着同一个位置!这就是为什么她反而为自己的不公正而兴奋。过分的激烈并没有让她不舒服。相反,萨比娜觉得自己刚刚获得了一次胜利,仿佛某个看不见的人在为她鼓掌叫好。
18.在这座教堂里,她无意中遇到的,不是上帝,却是美。与此同时,她很清楚,教堂和连祷文本身并不美,而是与她所忍受的终日歌声喧嚣的青年工地一比,就显出美来。这场弥撒如此突兀又隐秘地出现在她眼前,美得如同一个被背弃的世界。从此,她明白了,美就是被背弃的世界。只有当迫害者误将它遗忘在某个角落时,我们才能与它不期而遇。
19.人生的悲剧总可以用沉重来比喻。人常说重担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背负着这个重担,承受得起或是承受不起。我们与之反抗,不是输就是赢。压倒她的不是重,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20.追求的终极永远是朦胧的。期盼嫁人的年轻女子期盼的是她完全不了解的东西。追逐荣誉的年轻人根本不识荣誉为何物。赋予我们的行为以意义的,我们往往对其全然不知。萨比娜也不清楚隐藏在自己叛逆的欲望背后的究竟是什么目的。
21.世界在变成一个集中营。特蕾莎几乎从童年时代起就开始用这个词来表达她对自己的家庭生活的看法。集中营,就是日日夜夜,人们永远挤着压着在一起生活的一个世界。残酷和暴力只不过是其次要特征(而且绝非必然)。集中营,是对私生活的彻底剥夺。普罗恰兹卡虽在自己家里与朋友喝酒聊天,但却无处躲避,他是活在集中营里。特蕾莎以前和母亲住在一起,也是活在集中营里。从那以后,她明白了集中营绝无特别之处,没有什么值得让人惊讶的,而是某种命定的、根本性的东西,来到世上,就是来到它的中间,不拼尽全力,就不可能从中逃出去。
22.在这座短命的城市里,一条河一个世纪复一个世纪地流淌而过,他们根本就无所谓。她重又凝望着河水。她感到无尽的悲哀。她明白她所看到的,是永别。永别生活,生活正带着所有的色彩逝去。
我最喜欢米兰·昆德拉早期作品《玩笑》,里面有一种女性才有的痛苦而温暖的情感。在世界的男作家里面,只有昆德拉才具备了这样的柔情和矛盾。没有哪个作家像昆德拉那样做了对个体的感情的关怀,这些都会让人感到温暖,这也是昆德拉的文学价值之一。
——王安忆
据俄新社、塔斯社12日援引法国媒体消息报道,欧洲知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去世,终年94岁。昆德拉作为一位中欧小国的作家,其影响力已经超出文学范围,他的作品常年受到关注与谈论,可见他的思想必然和世界当下语境产生了联结和呼应。
最早向大陆介绍昆德拉的是美籍华人学者李欧芃先生。1985年,他在武汉一学报上发表文章,将南美的马尔克斯和东欧的昆德拉并称为当代最重要的两个作家。不同于马尔克斯强烈鲜明的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带给读者的震撼,昆德拉给读者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批判角度,他重新阐释了“刻奇”,认为刻奇是极权下的伪崇高,是自我感动的不真实的激情。
这一思想与他生活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捷克汇合了斯拉夫、天主和犹太人三大文化,又接受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所以捷克人不喜欢绝对的事物,天然追求多元多态的生命世界,反感极权和民族主义情绪压迫下的刻奇心理,这在他们看来是失去自我的表现。
《玩笑》是昆德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很好地呈现了他“反刻奇”的思想。青年学生路德维克想抖抖机灵,在给女友的明信片上写了句玩笑话,但没想到被开除党籍,进了苦役营。路德维克以为给举报自己的人戴上绿帽子,就能大仇得报,但没想到恰恰帮对方甩掉了一个包袱,自己却差点背上一条人命,另外还发现那人对正统意识形态的鄙弃现在比他更激进。情人埃莱娜以为吃了一瓶安乃近就能让路德维克内疚甚至回心转意,但没想到误服的是泻药,最终在路德维克面前出了一次大洋相。
昆德拉用捷克式的幽默表达现实的荒诞,用夸张的手法完成对夸张事物的反讽。在小说中,所有人都试图用宏大的意义和情感绑架别人,最终发现一切行为都是无意义的挣扎,收获的只有洋相。昆德拉认为“刻奇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他将其无限放大,最后导致对一切意义价值的否定。
反思“刻奇”能让我们对极权下的宏大情感保持警惕,但人生总归需要一个意义寄托,这就需要我们自己去继续探索、追寻。
《玩笑》是米兰·昆德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不落传统的写作风格令他一举成名。
(来源:澎湃新闻2023-07-16)
⊙ 米兰·昆德拉
重读《百年孤独》的时候,一个奇怪的念头出现在我脑海里:这些伟大的小说里的主人翁都没有小孩。世界上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小孩,可是这些伟大的小说人物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直到小说结束都没有繁殖下一代。拉伯雷《巨人传》的庞大固埃没有,巴奴日也没有后代。堂吉诃德也没有后代。《危险的关系》里的瓦尔蒙子爵没有,梅特伊侯爵夫人没有,贞洁的德·圖尔韦院长夫人也没有。菲尔丁最著名的主人翁汤姆·琼斯也没有。少年维特也没有。司汤达所有的主人翁都没有小孩,巴尔扎克笔下的许多人物也是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也是,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追忆似水年华》的叙述者马塞尔也没有。当然,还有穆齐尔的所有伟大人物──乌尔里希、他的妹妹阿加特、瓦尔特和他的妻子克拉丽瑟和狄奥蒂玛;还有哈谢克的好兵帅克;还有卡夫卡笔下的主角们,唯一的例外是非常年轻的卡尔·罗斯曼,他让一个女佣怀了孩子,不过正是为了这件事,为了将这个孩子从他的生命中抹去,他逃到美国,才生出了《美国》这部小说。这贫瘠不育并非缘自小说家刻意所为,这是小说艺术的灵(或者说,是小说艺术的潜意识)厌恶生殖。
现代将人变成“唯一真正的主体”,变成一切的基础(套用海德格尔的说法)。而小说,是与现代一同诞生的。人作为个体立足于欧洲的舞台,有很大部分要归功于小说。在远离小说的日常生活里,我们对于父母在我们出生之前的样貌所知非常有限,我们只知道亲朋好友的片片段段,我们看着他们来,看着他们走。人才刚走,他们的位子就被别人占了──这些可以互相替代的人排起来是长长的一列。只有小说将个体隔离,阐明个体的生平、想法、感觉,将之变成无可替代:将之变成一切的中心。
堂吉诃德死了,小说完成了。只有在堂吉诃德没有孩子的情况下,这个完成才会确立得如此完美。如果有孩子,他的生命就会被延续、被模仿或被怀疑,被维护或被背叛。一个父亲的死亡会留下一扇敞开的门,这也正是我们从小就听到的──你的生命将在你的孩子身上继续,你的孩子就是不朽的你。可是如果我的故事在我自己的生命之外仍可继续,这就是说,我的生命并非独立的实体;这就是说,我的生命是未完成的;这就是说,生命里有些十分具体且世俗的东西,个体立足于其上,同意融入这些东西,同意被遗忘:家庭、子孙、氏族、国家。这就是说,个体作为“一切的基础”是一种幻象,一种赌注,是欧洲几个世纪的梦。
有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小说的艺术似乎走出了这场梦,注意力的中心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整列的个体。这些个体每一个都是独特的、无法模仿的,然而他们每一个却又只是一道阳光映在河面上稍纵即逝的粼粼波光;他们每一个都把未来对自己的遗忘带在身上,而且也都有此自觉;没有人从头到尾都留在小说的舞台上;这一整个氏族的母亲老乌苏娜死时一百二十岁,距离小说结束还有很长的时间;而且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彼此相似,阿卡蒂奥·霍塞·布恩蒂亚、霍塞·阿卡蒂奥、小霍塞·阿卡蒂奥、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小奥雷连诺,为的就是要让那些可以区别他们的轮廓变得模糊不清,让读者把这些人物搞混。从一切迹象看来,欧洲个人主义的时代已经不再是他们的时代了。可是他们的时代是什么?是回溯到美洲印第安人的过去的时代吗?或是未来的时代,人类的个体混同在密麻如蚁的人群中?我的感觉是,这部小说带给小说艺术神化的殊荣,同时也是向小说的年代的一次告别。
(来源:收获微信公众号2020-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