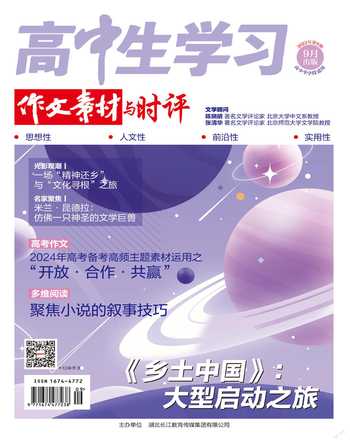现实映照:城乡问题之思
2023-11-05
⊙ 张冠生
《乡土重建》是费先生学术高峰期一本影响广泛的著述。该书由观察社于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初版,逐一讨论了如下话题——
“回不了家的乡村子弟”“乡村靠不上都会”“怎么会穷得没有资本的?”“资本从哪里来”“提高农民生活程度的道路”“乡土还是我们复兴的基地”……这本初版于近七十年前的书,居然在讨论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
中国农耕社会有个基础,叫叶落归根,构成社会的有机循环。生活中的所有产物,即便弃物,也都加入循环过程,如落叶化作春泥。天长日久,这一循环滋生出一种情感,桑梓情谊,形成告老还乡的传统。华侨漂洋万里,锱铢积蓄都寄回家,死后也要回乡安葬。
漫漫历史中,出自乡村的文人、官员,更多的是生前即回乡。或卸任而还,或辞官而返,殊途同归,更有一直晴耕雨读、终老家乡者。这一群体绵延相续,为乡村社会保持着地方治理和发展所需人力资源。数千年形成的这一循环,已在近百年历史中被打破。费先生描述这一过程说:“以前保留在地方上的人才被吸走了;原来应当回到地方上去发生领导作用的人,离乡背井,不回来了。一期又一期的損蚀冲洗,发生了那些渣滓,腐化了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
乡土损蚀始于人才流失。人才流失始于教育失当。由传统进入现代,社会需要改造,改造需要新知识。新知识要从教育获得,而偏偏教育上出了偏差。一方面,传授的知识与社会实际需要脱节;另一方面,灌输的观念使学生不愿回去。进入二十一世纪十多年后,有人想起当年费先生“乡土重建”的话题,觉得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且更迫切。客观地看,这确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里的一项根本性的建设工作。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探寻一个好机会:费孝通说乡土中国》)
⊙ 周飞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
中国城镇化最突出的特点表现为接力式的发展,即农村地区的人口和产业向城市大规模的集中,是分步骤、分阶段展开和完成的。
城镇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被概括为“工业城镇化”(1980-1994),其中最重要的特点是工业发生在农村,具体是指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由此中国开启了一段增长速度较快的工业化进程。由乡镇企业发展领衔的城镇化之路,被费孝通先生概括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到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国城镇化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土地城镇化”(1995-2012)。这一时期,分税制改变了央地财政关系之格局,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探索出一条以土地为城镇化发展总驱动力的新模式。这套模式以土地、财政、金融为核心,实行“三位一体”的运作,非常有利于基建投资和城市建设。
从城镇化的形态来看,在“工业城镇化”阶段,大城市的发展速度较慢,中小城市的发展速度较快,这和乡镇企业的繁荣有很大的关系,也和国家严控大城市规模的政策有关系。而在“土地城镇化”阶段,大城市、特大城市是发展的重点,小城市的发展速度较慢。这主要表现在小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相对落后,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大城市病”也日益严重。
到了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提出建设新型城镇化的总体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两点要求是“流动人口市民化”和“就地就近城镇化”,这标志着城镇化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即“人口城镇化”。
如今,距离2012年提出的两大目标已经过去了十年,而流动人口“落地”依然十分困难。换言之,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仍然困难。学界通常将这种融入困难的原因归结为房价过高、户籍制度限制、土地制度束缚与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由此来看,人口城镇化的目标面临着重要挑战。
为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
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有两大影响因素一直未被重视。其一是家庭本位文化,其二是集体土地制度(包括农地和宅基地)。这两大因素对于流动人口的“落地”及中国人口城镇化的走向发挥了关键作用。其实早在1996年,费孝通先生就已经关注到了这两大因素的重要性。费先生认为,巨大的民工潮之所以并未引起社会动乱,是因为民工“有家可回”。费先生将其形象地概括为:“农村现行的制度是建设现代都市的支持。我们不就是摸着农村里有家可归的石头在渡工业现代化的河么?”
我们应该反思和调整关于流动人口的一些误解。人口流动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血液”,是发展的动力和稳定的基石。这与其他国家情况不同。一直以来,人口的高流动性被视为社会稳定的重大威胁,但中国存在体量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不仅表现稳定,还能创造出巨大的社会经济财富,主要是中国人口流动的特点所致。中国人口流动是个体化流动,不拖家带口,老人与子女都安置在家乡。这种个体化流动受到资本的极力青睐,因为资本只需要关注和利用个体化的劳动力即可,而不用花费额外的精力和成本顾及农民工的家属。另外,个体化流动是以“家庭本位”为前提的。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家庭本位的“心态”与家庭伦理的作用之下,表现出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品性。在农民工心中,养育下一代出色的子女是工作及其忍耐的最大驱动力。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流动人口不仅不是威胁社会稳定的力量,反而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力量。他们虽然背井离乡,但是人人心有所安。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家庭本位的文化是数千年以来的文化传统,是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之一,它能够起到维系农民工辛勤劳作、吃苦耐劳的强大作用,进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但仅有文化还不够,文化发挥作用与特定的制度架构有关。具体言之,家庭本位的文化要发挥作用,与农村的现行制度,尤其是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家庭本位的“制度外壳”。之所以称之为制度外壳,是因为它对家庭的完整性有特别强烈的保护作用。这一观点建立在对国家—农民、城市—乡村之间的复杂关系认识之上。在传统社会里,农民分为小农和地主。国家是防止大地主去侵蚀、消灭小农而导致土地兼并的一个重要力量。因此,在传统社会中,国家不能简单认为是大地主的代理人。大国小农一直是我们国家的历史现实,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注意这一问题。而农民对国家的认同也正是建立在国家对其土地保护的基础之上。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大规模的城市资本开始下乡。我们常常关注到的是,资本下乡带来了农村发展的活力。但更要注意的是,倘若没有国家在背后作为强大的后盾,农民极易被资本所侵蚀。所以,传统社会中国家与农民关系之框架,仍然适用于新时代背景下国家与农民关系之研究。历史维度的延续就体现在国家与农民关系一以贯之的脉络之中。
当代的农民是以农村集体的形式呈现在国家和资本面前。无论是国家还是资本,与农民打交道之时,都不是直接和单个的小农接触,而是通过“集体”这样一个单位。需要指出的是,当下的“集体”一词有其历史维度和现实意义。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是集体所有的农地和宅基地制度,而这正是体现了国家对于“家庭”的保护。换言之,在国家和农民之间,存在着土地集体所有制,它对家本位的文化起到了重要的维护和保持作用。
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应超越城乡对立。城乡之间的地带,城乡之间的人群,城乡之间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这些东西并没有被大规模地改变,而是深深扎根在中国历史文明的水土中。
(来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微信公众号2022-05-26,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