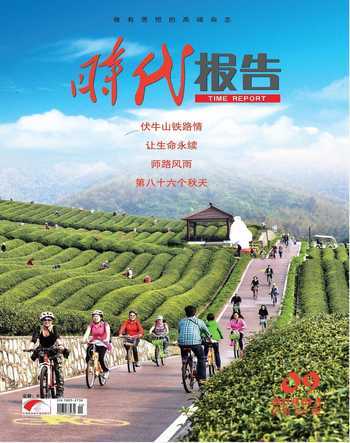山在虚无缥缈间
2023-11-04张冬梅
张冬梅
夜归时雨落,心想明晚避暑胜地鸡公山上的民谣音乐节是否如期进行?
“记得那是夏季,天气多风又多雨,也许纯粹是偶然,在这山中遇见你。”雨打屋檐,听这首《小站》,不禁想起仙门山之行。
那日去渑池仙门山的路上,看群山重重,山石嶙峋,心想“峥嵘岁月”就是这模样吧?
进山的盘山路依山而修,山脚是蜿蜒河谷,潺潺溪水,我不知道它源于何山,归于何水。但我知道远古的人们选择在此围屋而住,一定和这水有关。
而我重返仙门山,是赴一场文坛的盛会。
我在大别山长大,见惯了大别山的秀丽。走近太行山,同是八百里山系,如果让我形容,大别山温润如江南翩翩公子,太行山系则如吼着“大江东去”的北方汉子。
抵达仙门山时,雨落。烟雨蒙蒙,山水迷离,在初夏,感受湿润的仙门山,倒比燥热要好吧?
雨中的仙门山,哦,虽然它与两年前并无二致,但多了让人心旷神怡的凉爽:那次酷热难耐,雅兴全无,原本最想看看代表仙门山的“一线天”,因为炎热而作罢。
雨,让仙门山多了份灵韵:仲夏的一场雨,一切都清清爽爽的,较之两年前的热,我更爱这雨中的仙门山:小雨来的时候,落在身,也落心田,仿佛文学对灵魂的滋养。
我是因为山而来吗?不是,山在这里,不会离去;我来这里,是因为人:那些于我需仰視的文坛名家而来:在此召开2022年度河南省散文学会、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年会。
这是一场文坛盛会——寻根仰韶文明,攀登文学高峰。
我本寂寂无名,有幸见证文坛盛事:感觉所有的努力都有了意义!
不必说文坛盛会的隆重,不必说文坛名家的风采,因为在电视,在报刊,在大小媒体网站都有他们的身影。我看见的文坛名家,有山一样的气魄,又有山一般的深沉;我在,又仿佛不在,却如溪水,快乐地奔流在山脚。
早晨,下榻的仙门山酒店推窗见山,一丛从石缝中冒出来的野草郁郁葱葱,触手可及,只是,那明亮的窗成了障碍。索性,走出酒店,去接触这仙门山的晨。
酒店门口顺势而下的山泉水量骤增而奔腾,仿佛“时代的奔流”;而山呢?山在虚无缥缈间,雨后的仙门山,缭绕的雾仿佛是仙女遗落人间的洁白飘带,让巍峨的山,变得妩媚!
悄悄的,我又来了,来到仰韶酒洞,想起两年前的“仰韶之夜”,许下的诺言:一醉七千年,约定再见,如果不记得我,就吟句“把两个泥人打破,塑一个你,再塑一个我……”。
哎,我是不是醒得太早?无论怎么呼唤,这些酒罐罐儿都不言不语,仿佛秦俑!
洞里待久了,有了冷意,出了洞门,看见几位女子快乐地拍照,仿佛回到人间:遗憾沉睡的酒罐罐儿错过了人间的欢乐。
顺溪流边的登山道前行,摘几颗还没熟的山楂果吃,那爬墙玫瑰附着山,如女子铺展的裙裾。这山间的草木花卉,与大别山大致相同。遥想远古的人类,在这大山的怀抱,日出而耕,忙碌一天,日落围着篝火,对月饮酒,恣意歌舞,是何等的恣意人生。
我回头看看那仙门山酒店,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非常舒适的酒店,感觉自己一直游离在现代文明与远古文明的缝隙里,总不知自己身在何时何处!
登山路边,顺山直下的瀑布散发着水雾,山,变得迷离;走进充满浪漫气息的如驿站的小屋,一个人走进,可惜了这浪漫时光;远远的,看见了山顶的悬空玻璃栈道,我知道,登上那山巅,必定要过“一线天”:通往山顶的登山步道,最窄处石阶陡峭,仅容一人侧身而过,看天如一线这是仙门山最独特的一道风景!
因为时间,也因为雨后怕有泥石流,登“一线天”是不可能了:留个念想吧,期待下次再攀登!
折回的途中,遇见几个文坛名家正如我一样步行,且走且看看山景,我笑着调侃:“因为天气不能攀登‘一线天’,登上山巅,一览众山小。如‘不到长城非好汉’一般,到仙门山仿佛白来了!”
那几个人兴致很高,还打趣我:“你胆量挺大的,一个人漫步山道。”我呵呵一笑:“这里有什么好怕的?有人的地方才让人害怕呢。”
那几个人继续去登山,他们很快融入了山间,不见踪影,间或有谈笑声还在山谷回响。
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见我应如是。
仙门山,位于太行山系边缘,神奇的黄河仿佛分界线:黄河对岸就是地貌完全不同的黄土高原,那里有因为《白鹿原》而让我魂牵梦绕的塬上人家。
远古剧烈的造山运动和千百万年的冰雪风侵,使得太行山上随处可见落差巨大的断崖峭壁和深不可测的深山峡谷。
天下第一脊 万仞峥嵘峰
云自卷又舒 溪清水且急
左侧是绝壁 右侧为深渊
清风徐徐来 深山尽凉意
由于自然的风雨洗刷与河流切割,寒武系至奥陶系的石灰岩层,在数百万年如鬼斧神工,造就这奇峰突兀、峭壁临空,不由得叹息人类好渺小!
随着文坛盛会缓缓落下帷幕,请教是没有机会了,我斗胆与心仪的文坛名家合影,心里想着下次再见不知是何时。
离开仙门山,返程路上,同车的几位信阳报告文学的前辈趣谈文学事,近5个小时的路程不觉得枯燥。
只是,心里有点怅然:散文家王剑冰先生讲到仙门山地貌与七千年仰韶文化时,说数千年农耕文化时期,人类一天劳作之后享受自酿的美酒,对月而饮,围篝火歌舞,他们很快乐。现代人的生活固然舒适,但古人若穿越时空到现代,或许认为现代人活得很可怜,因为,人人埋头看手机,活在科技提供的冰冷而又虚幻的世界里,忽略了世界,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温饱后感受自然之美之趣。
一样的山,一样的水:两次跋山涉水,来到仙门山,急急来,匆匆去,只为赴一场人与自然的亲密融合的盛会: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只是,暗中困惑:是文字需要我们,还是我们需要文字?是我们推动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人类极力发展的科技文明的尽头是什么?
谁能告诉我答案?此番重返仙门山,不禁翻出两年前走进渑池仰韶文化遗址及仙门山的旧作,试图从杂思里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