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是不是问题?
2023-10-28喻军
喻军
谈到中国画的创作,笔墨问题恐怕是最重头、最首要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剥离了“笔墨”的中国画,或可称之为“彩墨画”,属于串味、变异的品种,早已不复地道的口感了。
中国画的“笔墨”是自成体系的,除了技巧层面的东西,还与创作者的性情、审美眼光及综合素养相表里。吴冠中当年说“笔墨等于零”,引起轩然大波,后来他一再强调完整的句意是“脱离了具体画面和造型要求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其实从当今院校教育的现状来看,偏重物象再现的工笔化和素描化倾向,实质上与传统笔墨所强调的写意造型观、书写性早已同床异梦。也就是说,吴冠中所提之事除当代抽象水墨或实验水墨外,在传统水墨领域并不构成实际的矛盾。宋以前中国画注重状物,元以后偏向文人写意,认为笔墨具有不依附于表现对象的独立审美价值,但仍未脱离造型艺术的基本范畴。其实,吴冠中自己的“彩墨画”除具一定的“形式美”外,为人所称道者还是他的“笔墨语言”。能脱离“笔墨”看中国画吗?能为笔墨的表现设置前提条件吗?窃以为并不符合中国画的审美特性。
那如何理解“笔墨”二字呢?
首先得说材质,就毛笔丰富的表现性(四德:尖圆齐健)而言,可以形成各种点线面,这是其它画种媒材所不具备的。所以说三寸管毫,如何用之得当,是穷尽一生都不敢说达到了极致的一门学问。书法基础、性情禀赋、自身学养、取法偏向等种种差池,决定了用笔的取舍、能力和效果。王右军有四句话:“平腕竖锋,虚左实右,意在笔先,字居心后”,虽指书法,但书画的笔法本无二致,可互为参照。而“墨”与“笔”的结合,即经调水研墨后再经宣纸的渗化功能,可以表现出十分丰富的层次气韵关系。笔、墨(含色)、水三者合一并共同作用于宣纸媒材,才形成了画面所依托的笔情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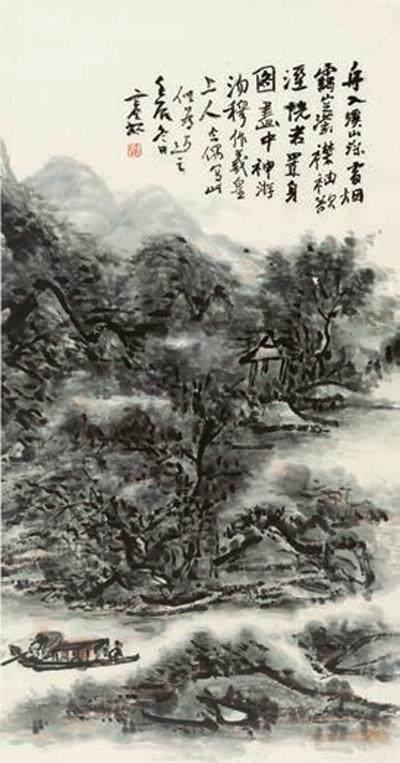
常听人说某画家“笔墨好”或“有笔无墨”“有墨无笔”“无笔无墨”,实质上构成一种对画家创作水准的高度简括的评价体系。笔墨功夫既包括技法问题,也包括境界問题、哲学问题,黄宾虹所讲的“五笔七墨”,即用笔须平、留、圆、重、变;七墨即浓墨、淡墨、破墨、积墨、泼墨、焦墨、宿墨,可见笔墨义涵之丰富。他晚年将“积墨法”改为“渍墨法”,又强调了“渍色”“铺水”的重要性。在黄宾虹看来,笔法是有秘诀的,这个秘诀就是太极图,合阴阳八卦之道、行天地五行之气,实在是把笔墨问题讲得透彻不过了。
传说黄宾虹在收购古画时,有时仅打开画卷的一小角,就说“这个不要了”。古董商不解:“您只看了一小部分,怎就说‘不要了’呢?”黄宾虹答曰:“我已经看出画的水平不行了。”其实也就是从几粒“点苔”上,他即看出画家的笔法不精到,所以收藏欲也随之消失了。他曾强调,一小点中,须“有锋,有腰,有笔根”,是不是好难?这里只想强调一点,对于写意中国画笔墨堂奥的探寻,倘不以书法为切入口,似乎很难找到其它的南山捷径。
远的不说,近代以来,许多聪明和有才能的画家,虽可称大名家,终因笔墨不过硬而未能臻至大师之列;而金字塔尖的那些大画家,又有谁不是笔墨的圣手?想起黄宾虹所言:“笔墨精神,千古不易,章法面目刻刻翻新”,也就是说,须分清什么可以因时而变,什么又必须“千古不移”。
近日,“现代主义漫步:柏林国立博古睿美术馆馆藏展”在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群上海空间举办。展览汇聚了毕加索、保罗·克利、马蒂斯、贾科梅蒂、塞尚、布拉克等6位20世纪现代艺术巨匠的近百件作品。此次展览以时间为序,通过编年结构对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及多种抽象表现形式的呈现,追溯20世纪欧洲现代艺术的发展历程。通过时间线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艺术家在同一时期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