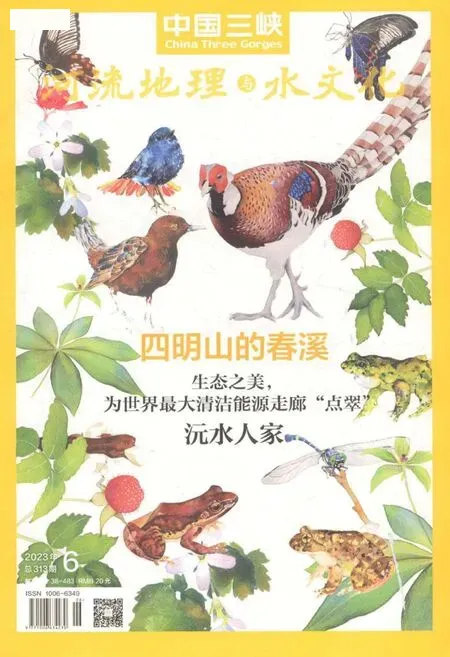从植物看世界
2023-10-25周琰编辑柳向阳
◎ 文 | 周琰 编辑 |柳向阳

白杨树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我们对植物的认识,以及植物在我们的世界中的角色和位置,从来不局限于科学和实用知识。人们使用植物作为食物、草药、穿着、装饰、建筑、器物、书写的材料,也把它当做是人类认识和表达自我与世界的媒介。

葫芦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我最早的植物记忆
白杨叶子簌簌飒飒,那密匝匝雨点的脚步,那匆匆忙一阵阵卷过的风,让人心口开始发慌。梦里的我突然在梦里醒来,车窗外,朝阳刚刚苏醒,大地和事物如此的明亮。并没有下雨,只是晨风一片片拨动这高原上的白杨叶,难怪有诗:“东邻多白杨,夜作雨声急。”古人给白杨别名“高飞”“独摇”,说它性情劲直,能够用作盖房子的材料,就是折断了也绝不会弯曲。
这景象和白杨夜雨的声音,是很小的时候我和妈妈坐长途汽车行经陕北黄土高原的记忆。两排白杨树镶着一条细带子般的沥青公路伸向远方,路边的田野种着麦子、高粱和玉米。耕作的田地消失了,天地间只有蓝天、白云和黄沙,黄沙梁上是一丛丛的红沙柳。妈妈指着窗外说:“他们还在那儿种树!我从小上学种树,当了老师还种树。有几年,每年在同一个坑里种树,根本种不活。”——这是好几十年前了。后来,不管我走到哪里,在世界哪一个角落,常常在梦里,白杨叶子沙沙沙,声声又带我回到故土。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中秋,我们的语文老师请我和另外两三个女孩去她城墙外的家里过节。我们靠着窗子坐在窑洞外,天渐渐黑了。老师在小木桌上摆好月饼、蜜瓜、葡萄,还有我们很少见到的葡萄,身旁的葫芦架上挂着拳头大的金黄的小葫芦,老师给我们讲嫦娥后裔的故事。

玫瑰花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月出东山,我们和老师告别,她从葫芦架上给我们每个小女孩摘下一个葫芦做礼物。我们拉着手回家,天上的月儿皎洁孤清,星星一颗颗像礼花一般炸出。那时,月宫嫦娥在我们心里就和真的一般。而葫芦、葡萄、蜜瓜、藤蔓,它们都因为那个夜晚,从知如不知的溟然中显现,和毫无心机的善与传承交织而有了意义。
后来我家搬到另一个城市,新小学里到处有花圃。五月初,玫瑰、月季……种种花苗花树都开了。那一年我开始读莎士比亚,他写:“最美的造物让我们欲望越多,美的玫瑰永不死亡……”——什么是欲望?什么不会死亡?还有花儿怎么会像溃疡一般,玫瑰的颜色怎能和药酒相比?为什么花儿的死亡是最甜蜜的芬芳,诗又怎能提炼青春的真实?
我不理解,又感觉神奇,这是植物和诗相遇的时刻。
这些是我最早的植物记忆,当然还有更多。
春天,我和小伙伴们剥开苹果和核桃叶子的表皮,闻它的清香,再把叶子做成书签。夏天吸鸡冠花的甜蕊,或者用指甲花染指甲。在北方生活一生的爸爸,年年要种南方的香花——栀子、木香、米兰、茉莉,等等,他也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街邻们在阳台上、院墙边种着杂花和小青菜、韭菜、葱、丝瓜等蔬菜,而路边墙内是高大的槐树、梧桐,等等。冬天去寺院看梅,春天看樱花,和尚念经、晨钟暮鼓、画梁飞燕,都只是寻常。后来,他们把整条整条大街上的老槐树砍掉,种上了桂花树,可是那名贵的南方香花树在西北并不容易活。我骑车穿过那些街道常常像丢了魂一般,突然一天明白了,原来那从春天到深秋槐叶槐花的味道没有了。
猬实与上海
我现在生活在多伦多,每年从四月中旬一直到十一月,就像乡间逢年节的戏台,各种花轮流登台献艺。五月的时候,院子里有两三株或粉或白的花树盛放,而我不知其名。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查一下名字,发现它叫“猬实”(Linnaea amabilis)。
这花树源自中国中部,意大利方济各传教士和植物学家朱塞佩·吉拉迪19 世纪末在陕西和湖北发现它,1901 年植物猎人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把它寄回英国的苗圃,逐渐流传欧美各地,成为常见的园艺花树。我把这花树的照片发给朋友诗人卢·伯森,她回信告诉我她小时候加州家里的花园有几株猬实树,那是她外祖母从中国带回来的。
卢写过一篇散文《上海》,讲述她在 2002 年去上海寻找外祖母生活过的痕迹的故事。卢的外祖母在1907 接受了上海圣约瑟学院的邀请,抛下未婚夫到上海做私人声乐教师。可是在三个月海上航行之后,当这位名叫朱迪的年轻女子踏上黄埔岸边,却等到了一个陌生人拿着一纸通知,圣约瑟学院不办了,她没有了工作。朱迪流落在上海市中心的一个弄堂里,贫寒交加。一个富有的美国商人后来听闻她的经历,收留了她和另外一个同样流落上海滩的女子,两年后朱迪回到了美国。
卢虽然没有见过她的外祖母,但是她从小在外祖母留下的中国记忆中成长。这样的故事并不罕见,还有其他朋友跟我讲述过类似他们的先辈从中国带回植物和记忆的故事,它们往往只依稀在隐秘中流传。这些小故事和记忆片段,我称作 “植物事件”(an event of plant),是植物参与和维系而改变了人生认识和经验的事件,常常贯穿人的一生。

猬实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一朵野花见一天堂
几年前我要在国内做一个和风景有关的展览,为此我邀请了加拿大艺术家和园丁罗恩·本纳参与《风景之变》展览。本纳大半生漫游世界,追寻植物全球流动的轨迹。2014 年夏天他在西安做了一个花园,种植了几十种他研究发现欧洲人传播到中国的植物,包括土豆、玉米、红薯、木薯、腰果、巴西坚果(鲍鱼果)、花生、木瓜、红辣椒、芸豆、向日葵、烟草、草莓、蓝莓、覆盆子、西红柿、南瓜、青瓜、梨果仙人掌、番荔枝、刺果番荔枝、南美洲番荔枝、美果榄、香子兰、可可树、龙舌兰、佛手瓜、矮牵牛、旱金莲、蓝花鼠尾草、百日草、秋海棠、草茉莉、烟草花、金鱼草、万寿菊、大丽花、大波斯菊、醉蝶花、牵牛花、太阳花、苋菜花、藿香蓟、马鞭草花等。和他的合作交流让我意识到,风景绘画突破欧洲古典想象和全球殖民有直接关系;而相比陆路的欧亚丝绸之路,随着大航海时代出现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即“植物之路”(The Plant Route),促使植物、种植文化、知识、思想、生态环境和依赖于这些的经济政治全球流通而整合,彻底改变了世界。
马可·波罗之后的大航海时代,植物猎人从海上而来,绕过好望角和红海,经由南亚和东南亚,跨越陆地,经历数年,抵达中国,他们中很多人是探险家、商人、传教士和殖民者。我们了解他们接触、获得中国植物知识的历史痕迹,从某一个中心作为出发点,不如跟着他们的足迹,看他们如何从好望角、马达加斯加、非洲、雅加达、新加坡、果阿、曼谷、越南等地曲折而来。范发迪将早期现代世界植物和知识传播视为不同地区之间的动态、交互联系的网络。欧洲港口城市如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塞维利亚、里斯本、马赛和伦敦是联系欧洲与其他世界生命线的转运港,加勒比群岛港口城市是大西洋沿岸的一串串珍珠,而在东半球,孟买、加尔各答、马六甲、巴达维亚、马尼拉、澳门、广州、长崎如星座一般,形成了一个海上贸易的复杂网络,所有这些贸易转运港都是塑造现代世界的积极参与者。这个网络中还有许多节点应当补充,包括非洲大陆、圣赫勒拿岛、加那利群岛、毛里求斯、澳大利亚大陆、夏威夷等地。
意大利学者朱利亚·卡内瓦认为植物包含一种类似建筑的结构,它有空间与时间发展的脉络。与我们共生的植物世界的知识,并不局限于单一生态、地理、社会生活和历史构成,它是深度多层和丰富多样的知识。我们可以像了解一个植物的根、枝干、每一叶片、每一个花瓣一样,也可以像万千彼此映照的因陀罗网镜面一样,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理解事物的不同方面和它们的相互联系。
“一粒沙中见一世界,一朵野花见一天堂。”布莱克这句诗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自然世界任何一个存在本身都是无限的,二是自然之物,特别是植物,是人的想象、情感和信仰世界的媒介。
我们对植物的认识,以及植物在我们的世界中的角色和位置,从来不局限于科学和实用知识,特别在古代,人类与自然世界和象征世界的关系是密切一体的。在生活中,人们使用植物作为食物、草药、穿着、装饰、建筑、器物、书写的材料,也把它当作是人类认识和表达自我与世界的媒介。譬如在安达曼群岛,女孩青春期开始时会起一个 “花名”,也就是当时附近开花的一种植物的名字;人们用不同花木描述不同季节,这些花都是蜜蜂采蜜的花种,有强烈的香气,而年历实际上是香味的年历。
20 世纪以来,我们与自身历史的象征资源联系发生了断裂,人们通常翻译、挪用西方的象征和话语来认识、解释本地问题。我们儿时浸染其中的故事与传说、象征与感性,被排除到次文化和民间文化的范畴内,不再进入主流话语之中。舶来文化传统的象征虽然提供了与世界交流和论述的话语合法性,却没有在不同象征传统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这种情况让话语脱离了历史,也造成强化了阶层隔膜。20 世纪苏格兰植物猎人和植物学家、园艺学家尤安·希尔豪斯·梅思文·考克斯谈到这个现象时说,不仅中国的植物品种与欧洲不同,中国人使用植物和赋予它们的美学价值也不同。欧洲人引入中国植物的时候,不仅带回了花木,也带回了启发欧洲思想和审美的象征形式。
作家高希将包含着整个帝国殖民掠夺血泪的肉豆蔻还原,将它比喻为行星,被一层层气体、固体和物质包裹,需要一层层破开,才能看到内里那成为香料的内核。它也像行星,你不可能一下子看到它的全部。一个肉豆蔻同时拥有两个半球,一半在光明中,一半在黑暗中,人眼看到一部分,而另一部分总是暂时隐藏的。这是历史、世界和每个人、每个存在的生命的隐喻。希望我们像仰望行星周行一样,不断看到黑暗变为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