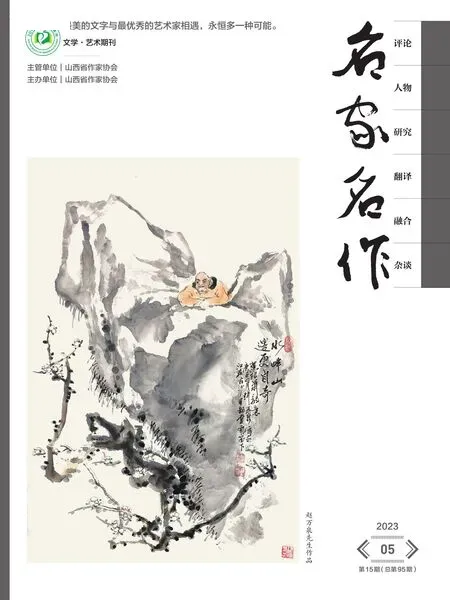从祭祀到展演:“非遗”语境下土家“撒叶儿嗬”仪式的变迁
2023-10-23董鑫
董 鑫
“撒叶儿嗬”又称“撒尔嗬”或“撒忧祸”,是湖南常德武陵地区清江流域一带土家人为吊祭亡者而举行的传统丧葬仪式,其历史久远,被誉为土家人的“生命之舞”。如今依然活跃在清江流域中下游地带,其中,以巴东、长阳和五峰等县市区域内“撒叶儿嗬”的音乐舞蹈形式最为丰富且最具代表性。学界认为“撒叶儿嗬”乃古代巴人所创[1],且为一种极其古老的民族民间艺术。“撒叶儿嗬”在2006 年以“传统跳丧舞蹈类”成功申报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2]。学界围绕其起源、内涵、功能及变迁相继展开讨论。有学者认为,“撒叶儿嗬”源起于廪君文化,分别从宇宙观、伦理观和生死观论述“撒叶儿嗬”的深厚内涵,且赋予其家族凝聚力、获得人生价值、传承传统文化以及享乐艺术的功能[3]。也有学者更多关注“撒叶儿嗬”的历史变迁,例如,从生活仪式和舞台展演的角度分析“撒叶儿嗬”在仪式结构、功能和社会关系中的变迁[4]。在“非遗”保护语境下,“撒叶儿嗬”传统的祭祀功能逐渐弱化,原生态中的神圣禁忌性被打破,其集歌、乐、舞三位一体的舞台展演进入公共生活视野。纵观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撒叶儿嗬”从神圣到世俗、从生活到舞台的当代嬗变,关于其展演的经济效益凸显的相关研究较少。由此,探讨“撒叶儿嗬”仪式从祭祀到展演的变迁而产生的经济效益,旨在进一步为“非遗”传承与保护做出尝试。
一、作为原生态的“撒叶儿嗬”
“原生态”一词原本用作表示原生态唱法、原生态舞蹈一类的艺术表演形式[5],近年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下,其更多与地方性、历史性的民间民俗文化相联系。作为原生态的“撒叶儿嗬”,是土家人民至今保存较好的传统民间文化艺术。土家人相信万物有灵魂,有公德的人会在死后升入天上,因此,只有当有后代子孙的老人正常去世时,才会被看作功德圆满之人而“飞升”,土家人称之为“走顺头路”。当老人去世之后,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纷纷自发前往主孝家参与“撒叶儿嗬”仪式,大家在堂屋内围绕灵棺击鼓而歌,男性绕臂起舞,现场一片热闹欢腾的景象,这也是土家人丧事喜办的典型,称之为“白喜事”。功德圆满之人去世被看作是另一种新生命的开始,老人的灵魂不会消失,反而会在“天上”继续保佑其子子孙孙多福多寿,因而,后辈应该“欢欢喜喜”地送老人最后一程,以敬孝子之礼与祈求保佑之情。
“撒叶儿嗬”仪式举行之时,前往吊唁的亲朋好友会带着自家产的粮食,例如豆腐、白菜、玉米等,自发前往参与跳丧活动,而孝家会热情地用饭菜招待客人,并在跳“撒叶儿嗬”过程中为大家分发小红包。即使此前哪一家与已故之人或其主孝家有矛盾,当亡人已故,这一家也会放下从前的恩怨前往主孝家参与“撒叶儿嗬”仪式,并到堂屋内对亡人进行祭拜,主孝家会在一旁进行接待。由此,此前有积怨的两家人因为共同悼念亡人而冰释前嫌,不管从前有什么过节,这一天“亡人为最大”。仪式过程中的参与者处于“阀限”[6]阶段,大家的社会身份被弱化,其共同情感得到强化,即表达对于已故之人的祭奠之情。当仪式结束后,参与者重返社会角色,但参与者与自身亲人、邻居的关系得到了巩固,且道德约束进一步加强。由此,“撒叶儿嗬”仪式作为一种传统民间习俗对社会具有道德制约、紧密家族、协调社区的多种功能,是土家人智慧的结晶。
二、作为舞台展演的“撒叶儿嗬”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彰显民族自信的重要性。“撒叶儿嗬”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其完整的表演内容主要包括击鼓、歌唱与舞蹈三种形式,表演者踩着鼓点的拍子而歌舞。歌师所唱内容多与土家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反映土家人生产生活以及伦理观念等内容的唱词,这些唱词又可分为三小类——文歌、武歌和情歌;第二类则属于即兴创作,如唱亡人生平业绩[7]。其中传唱频率较高的属文歌与情歌两类,例如文歌类别的《哑谜子》《劝世文》和情歌类别的《十爱》《郎在高山打伞来》《相思歌》等。“撒叶儿嗬”的舞蹈动作多由土家人狩猎时模仿动物所创,如“凤凰展翅、犀牛望月、黄龙缠腰、猛虎下山、燕儿衔泥、水牛抵角、鲤鱼扳滩”等;其舞步形式也各色各样,如摆身步、拧身步、左右撒步、点步、踏步等。“撒叶儿嗬”的舞蹈对舞者脚下功夫有极高的要求,民间常流传“丧鼓丧鼓,三槌半为鼓,脚走三步半,跳得才好看”,即是说舞者下半身需稳重有力、步伐变化要快,才能带着上半身更好地舞动,使感情奔放热烈。
“撒叶儿嗬”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舞蹈类”,其原生态的祭祀功能逐渐弱化,更多强调其艺术内涵。在2010 年举办的青歌赛原生态组中,来自“撒叶儿嗬”组合的七位土家农民在决赛中一路领先,以高亢饱满的土家歌舞表演轻松摘金。“撒叶儿嗬”组合深受观众喜爱,其主唱谭学聪是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先后在多个城市进行演出,推动了土家“撒叶儿嗬”歌舞在民间的进一步流传。“撒叶儿嗬”作为土家人民的“民族符号”出现在更多媒体新闻中,被更多人所熟知喜爱,其中的部分舞蹈还改编到广场舞中。地方政府打造“撒叶儿嗬”表演舞台,进一步为旅游地提供可观赏性的景点,表演者获得认可后会更加积极参与表演班子培训等活动,进一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再生产”。
三、从祭祀到展演:“撒叶儿嗬”的文化变迁
“撒叶儿嗬”作为一项传统文化事象,其历史悠久、文化内涵深厚,从祭祀到展演的文化变迁依赖国家、地方和各级传承人的有力推动,也得益于文化自身的张力。“撒叶儿嗬”不断进行内部的调适与整合,逐渐从充满神秘禁忌的传统祭祀中脱离,走向适配于现代公共生活的舞台,被更多人知晓熟悉。
(一)“撒叶儿嗬”仪式的禁忌性被打破
“撒叶儿嗬”被传统土家人看作是一项神圣且具有禁忌性的祭祀活动。丧鼓不可随便敲响、女性不可参与跳丧,“撒叶儿嗬”这一名称也不可在日常生活中随意被提及,这些禁忌与土家人传统文化生活息息相关,成为传统土家人的伦理观与生死观。而“撒叶儿嗬”随着社会转型而发生文化变迁,人们的观念也发生转变,“撒叶儿嗬”更多被当作娱乐的歌舞表演,在公众场合不再受到避讳,其时空与性别上的禁忌性逐渐被打破。
一方面,“撒叶儿嗬”仪式不再受到严格的时间与空间限制。就时间来看,“撒叶儿嗬”仪式不再局限于老人去世之后的丧葬仪式,而是作为歌舞表演随时可以进行。“撒叶儿嗬”表演的时间随民间艺人的事业而自由发生,有专业的表演班子进行表演。就空间来看,“撒叶儿嗬”作为祭祀仪式时,其表演场所由堂屋延伸至场外院坝。专业的“撒叶儿嗬”表演班子自带的鼓、音响、舞台器械等大型设备需要空间大的场域才能满足,且有时表演人数因成对地增至六或八人时,对空间的要求也更高。“撒叶儿嗬”作为舞台展演时,其表演空间形式较传统时更富多元化。“撒叶儿嗬”的歌舞要素被民间艺人广为改编,与摆手舞、喜花鼓、苗舞、肉莲响相融合,创造出清江舞[2],之后分别进入校园与广场等场所,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歌舞。
另一方面,在“非遗热”背景下,“撒叶儿嗬”以歌舞表演的形式走向舞台中央,女性表演者也逐渐出现在大众视野。如今,在市场经济发展与非遗传承人推动下,民间出现了专业从事“撒叶儿嗬”表演的文化团队,代替左邻右舍进行跳丧。笔者在巴东、五峰等县市的调研发现,“撒叶儿嗬”班子不仅越发产业化,其班子内部的女性成员也占据其总人数的一半之多。农村的女性多为家庭妇女,平常主要进行农业耕种和教养孩子的工作,因农闲与孩子上学的原因,女性的时间较为自由松散。女性从事“撒叶儿嗬”既能满足自身时间要求,又能满足家庭日常开销的需求,女性更愿意主动学习“撒叶儿嗬”将其作为副业展开。
(二)“撒叶儿嗬”仪式的经济效益日益彰显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撒叶儿嗬”逐渐脱离原生态的文化环境,其传统祭祀功能逐渐弱化,而其舞台展演的经济效益却日益彰显。“撒叶儿嗬”从祭祀到展演的文化变迁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伴随着国家、地方政府与各级传承人等多方外力的推动,以及其本身丰富内涵的文化张力,在日积月累的时间中沉淀并发扬的,分别体现在“撒叶儿嗬”的舞台展演与丧葬仪式中。
首先,“撒叶儿嗬”的祭祀功能失去了原本的话语权,而因其艺术价值被赋予一定的经济价值。由于现代人的审美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追求标新立异的风格,“撒叶儿嗬”在舞台展演中以其粗犷豪迈的风格赢得观众的喜爱。舞台上的“撒叶儿嗬”更具经济效益,例如利川县(今利川市)的腾龙洞景区内打造的大型舞台实景剧《夷水丽川》,其中的“白虎雄风”舞蹈部分即是土家“撒叶儿嗬”表演。据统计,《夷水丽川》自2005 年开演至2017 年以来,演出共约6000 余场,直接经济收入过亿元[2]。“撒叶儿嗬”已经成为一项文化资源为当地旅游经济提供动力。另外,“撒叶儿嗬”依然作为一项丧葬仪式活跃在人们的公共生活中,由原来巴东一县逐渐扩展至恩施州内区域。在经济效益可观的情况下,“撒叶儿嗬”各级传承人积极参与表演和培训。例如,“非遗”传承人黄在秀在2017年创办的“三里城传承基地”就获得了120 万元的资金资助,从2018 年5 月到2019 年1 月,免费培训“撒叶儿嗬”学员270 余人,其中女性占据总学员人数的一半。黄在秀的徒弟刘邓将“撒叶儿嗬”表演商业化,成立了专门的公司从事红白喜事一条龙服务的商业活动,年活动场次约200 场,一场活动可得四五千元收入。据笔者调研发现,在巴东、五峰、长阳等县市分别有多个专业“撒叶儿嗬”表演队,长期活跃在清江流域一带,其具有大需求的经济市场为从事人员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撒叶儿嗬”表演队日趋产业化,拥有一套内部的运作逻辑。由此,“撒叶儿嗬”的经济功能使其在社会转型中不致萎靡,反而催生传承主体的动力,以起到传承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
四、结语
“撒叶儿嗬”一直是土家人生礼仪的重要部分,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底蕴与文化内涵。“撒叶儿嗬”这一土家文化符号与其他文化事象相结合,以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进行传承与保护。“撒叶儿嗬”表演队日趋商业化与产业化,且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如今,“撒叶儿嗬”的舞台展演与祭祀仪式都由专业表演队和班子进行传承,产业化的团队在其表演内容上更多关注大众需求,在对传统唱词与舞蹈动作进行学习与改编时也更多会基于现实的考虑,将“撒叶儿嗬”传统表演中一些高难度的舞蹈动作简化,许多暗含教育意义的唱词被截取、改编,无法再现土家人民此前狩猎务农的真实场景与充满智慧的人生哲学。所以,“撒叶儿嗬”作为一项文化资源得到了一定保护与传承,但其文化真实内涵还有待深度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