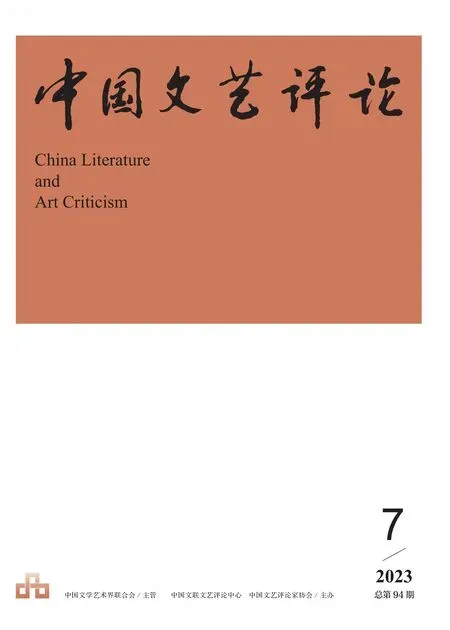“喷空”的乡土生存哲学
——论新世纪刘震云小说的叙事策略与动力
2023-10-23■韩越
■ 韩 越
故乡的风土人情是刘震云小说创作话语的主要资源。但是如今刘震云自己再回看那洋洋洒洒二百万言的《故乡面和花朵》时,也坦言“我走了弯路了”[1]纪录片《文学的故乡》第五集,张同道导演,2018年6月8日,https://www.bilibili.com/bangumi/play/ep371388?spm_id_from=333.788.videocard.2。。新世纪后刘震云把关注的重点转向“话语”,河南人市井闲侃的“喷空”被他直接引入创作中,这种充满民间智慧与活力的语言模式成为他创作构思的起点、小说叙事的重点。故乡的花朵不再是用面和成的,而是直接在人们的口齿之间盛开。
当刘震云把这个方言词汇引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时,他就把自己的坐标摆放在一个日常而传统的维度上了。他注定会是一个主动向中国传统叙事模式复归的作家,自从在文坛崭露头角至今的几十年里,他坚持用底层民众的眼光去审视历史与社会,捕捉隐匿在言语背后的各种复杂关系,将中国文学的旨趣和西方现代文学技法糅合在一起,怀着“贵民”的传统精神去思索独属于当代中国乡土的精神困惑。
一、作为元叙事的“喷空”
“喷空”这个方言词汇直接被刘震云引入了他的小说中,它在河南方言里本意为“聊天”“侃大山”。虽然意思相近,但它区别于东北的“唠嗑”或是山东的“拉呱”,“喷空”还蕴含着河南式的插科打诨、讥诮与调侃。2013年,河南方言相声剧场在洛阳创立,即用“喷空”为名,如今喷空剧场在河南已经遍地开花,这既说明了“喷空”是一种对话性的“活”的语言,又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这种话语体系与生俱来的幽默感与民间性,这种特性恰巧合乎了作家唤醒乡村的创作意图。
作为一个言必称“我舅”的河南本地人,刘震云早就在写作中融入了这种富含机变、妙趣野性的“喷空”。[1]参见刘颋:《“三人行,必有我舅”——刘震云畅谈小说之道》,《文艺报》2012年9月19日,第3版。甫于文坛崭露头角时,他就以平实幽默的语言风格著称,这种文风的根底其实就是河南田野消闲时的对侃,故而难免显得油滑、琐碎和痞气,但刘震云显然不愿放弃这种“琐碎”,他曾表示一直希望选择一种比较符合“我们村里人”的叙述方式和思维结构的叙述模式,试图去触及中国乡间文化的核心。所以,“喷空”衍生而来的具备古典特色的叙事结构正是目前符合刘震云创作初衷的选择,最能展示来自河南乡土的风趣、野性与生命活力。
进入新世纪后,刘震云挖掘出了这个词背后隐藏着的乡土生存哲学,他直接将“喷空”引入了小说文本,但却不仅仅是原来单一的意义。“喷空”第一次出现在刘震云笔下是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这里保留了“聊天闲侃”这一层意思之余,又赋予了这个词“讲故事”的新义,在《一句顶一万句》里他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一个叫杨百利的人从学习“喷空”、到“喷得好”、最后“喷空”即生命的全过程,活脱脱就是文学创作者从初学到入门的真实写照。
由此,“喷空”在刘震云笔下变成了一种具有元叙事特征的有结构的文学话语,而“杨百利”就成为了兼具书中人和叙述人的多义角色。当然,其中一层是刘震云自己的影子,像是作者躲在名为“杨百利”的面具后的一个分身,悄悄地对自己的小说创作过程进行了解密。杨百利初学“喷空”时,作者就解释“喷空”是“有影的事,没影的事,一个人无意中提起一个话头,另一个人接上去,把整个事情搭起来”[2]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53页。,仿佛是市井闲侃、隔空对吹,但又别有文章。这“对吹”不能是演讲式的大而无当的话,而要形成一个有情节有内容的故事,话头(故事的开头)是从生活里来的,却不能等同于日常生活;转折处要有想象力,要拐向生活里实现不了的事,正所谓“虚实结合”。等到“喷空”喷得好了,就像修建好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水渠,实际上这便使叙述者形成了一种具备个人特色的叙述风格,这时语言就如河流一般,叙事者让它往哪里流,它就往哪里流。风格若是不同,必定不能兼容,故而小说中杨百利和他最初的伙伴注定要分道扬镳,开始了自己与自己“喷空”的日子。他是如此专注以致于荒废了做工,惹得主家不快、周遭厌恶还浑然不知,脑海里云山雾罩,胸腹中云积雨蓄,活脱是一个寻觅到了灵感在打腹稿的作家陷入了废寝忘食的艺术思考。杨百利完全活在了叙述的世界,已经难以顾及实在的生活,为了有个能听自己“喷空”的人来到了火车上,日行千里,劳碌漂泊,却不是为了“奔命”,而是为了一张能“喷空”的嘴,或者说,“喷空”就是命,是文学创作者的生活和命运。
在杨百利的“喷空”生涯里有一件事颇值得玩味。他满腹的故事无处倾吐,终于在哥哥的婚宴上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将婚礼上的大人物们当成听众大“喷”特“喷”了一场。可惜,这位喷空大师非但没有博得满堂喝彩,反而以尴尬收场,原因是宾客们觉得这故事太“张致”。此处,刘震云又引入了第二个河南方言词汇——“张致”,解释为超过了极致,可理解为过度、过火,小说里讲杨百利的“喷空”太“张致”,还没说到精彩处,一个小孩子就已经被吓哭了。刘熙载曾在《艺概·文概》中说:“叙事要有尺寸,有斤两,有剪裁,有位置,有精神”[1][清]刘熙载:《艺概》,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年,第77页。,这里的“尺寸”和“斤两”指叙事的分寸感和适度感,杨百利在婚宴上的喷空就是典型地失了分寸的叙事,导致说者犹未尽兴,听者已经疲乏。能创作出这种桥段,不知是否因刘震云回忆起自己早年创作时遇到的困窘?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利喷空的情节无处不闪耀着元叙事的光芒。依照王洪岳曾指出的,杨百利虽然不是第一主人公,但是把有关他的部分全部提取出来,就构成了一个类戏仿式的元小说。[2]参见王洪岳:《元叙事与互文性》,《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3—8页。“喷空”脱胎于生活,是现实的添枝加叶、无中生有;它具有艺术的创造性,不能是大家都想得到的,“大家都想得到的,就不叫‘喷空’”[3]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79页。,它追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好的“喷空”要求有风格、有调性,它的语言如同河水自然流淌;它要求有分寸、有剪裁,是艺术的审美加工而不能让个人的情感喧宾夺主。这已经从闲侃对话衍生为一种严谨的叙事模式。作者戴着书中人的面具混杂在故事里,是文本中的活跃者,发表了如何叙事的幕后设想,生成了一种叙事的生动性,让“杨百利”超脱出这个线索庞杂的故事而独具魅力。
刘震云在《一日三秋》中又一次直接提到“喷空”,如果说“喷空”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是叙事的叙事,那么在《一日三秋》里的喷空则是作为次要文本与主文本之间产生了文本间性,形成了互文。
《一日三秋》虽然写了父子两代人的故事,但陈明亮却是这本书里当仁不让的第一主人公。陈明亮这一部分开头写奶奶喷了三个“空”,一是关于奶奶儿时的玩伴——有了灵性的小黄皮;二是关于一头比犟牛还犟的牛;三是奶奶自己的故事,关于她与父亲最后的一面之缘。这三个民间传说在后文陈明亮成长的过程中均有呼应,每一个短小精悍的“空”都在指涉提示着主文本里陈明亮的命运。首先,第一个“空”里,生活在猪圈中的小黄皮不愿长大,是因为“我是猪,不是人,一长大,就被人杀了”[1]刘震云:《一日三秋》,广州:花城出版社,2021年,第123页。。长大就意味着要承受生活的磋磨,作为凡人的陈明亮没有永驻童年的神力,16岁(恰好是迈向成年的重要年龄)辍学走上了社会,失去了庇护,开始艰难地谋生计,他到猪蹄店去拔猪毛、学炖肉,在某种角度上看也有反讽的意味。第二个“空”里的牛比主人还勤劳,耕地时主人嫌它快,它反倒嫌人太慢,主人一句杀牛惹恼了它,跑到山上不见踪影。这又与陈明亮在西安开店时收留的狗异曲同工,陈明亮还未去揽客,狗先到街上去主动拉客;及至衰老弥留之际,它要寻一隐蔽处默默死去,陈明亮后来遍寻不得。第三个“空”的寓意则在全书中都具有精神统摄力,《一日三秋》里的一众人物都在忆往昔、追故人,却求而不得。在“空”里,奶奶的父亲临终时说“我们还有一面之缘”,奶奶就时常怀着这个念想,哪想到再见竟只是遥望故人背影。后文中且不说配角董家父子直接复刻了这个情节,只说陈明亮与樱桃、陈明亮与奶奶,不也是惦念追寻半生,却只在戏里梦里追踪到一个不能触摸的幻影吗?
西方叙事理论认为互文性是从元意识与元小说当中生发出来的。[2]参见王洪岳:《元叙事与互文性》,《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3页。克里斯特瓦把互文性作为小说本体论来看待,“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拼凑,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3][法]朱 莉娅·克 里斯 特瓦:《词语、对话和小说(1966)》,李万祥译,《文化与诗学》2011年第2期,第250页。,她认为小说对民间生活中市井言语的引述也属于文本间性的内容。进入新世纪后,刘震云更加重视对民间对话与民间叙事的收编与引用,并在创作中用“喷空”加以概括。此时,“喷空”已经不再是方言里所指涉的无意义的对吹,而是一种具备元叙事特征的叙事结构。从整体去审视刘震云的小说时,这似乎又是一个结构复杂、意蕴丰富的长篇“喷空”,保留着来自乡土的对话性、民间性与来自底层的朴素生存方式。
二、缀段:“喷空”叙事的衔接方式
如果我们把刘震云的长篇小说视作一场如杨百利梦呓般的大型“喷空”,那么就能十分清晰地洞察刘震云小说的一些标志性特质之来源,比如带有隐喻性的俗语、黑色幽默,等等。但我们不能忽视“喷空”在方言里的原义“聊天”,既然是闲聊胡扯、闲言碎语,难免芜杂与分散,作家写作时就要在衔接上费些思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刘震云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叙事特征之一——缀段式结构。明清章回小说多是由看似缺乏有机联系的故事连缀在一起,没有大的结构上的“头、身、尾”,而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片段,表现出“缀段性”。[4]参见段江丽:《譬喻式阐释传统与古代小说的“缀段性”结构》,《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第81页。这种叙事方式曾一度被秉持西方文论观点的批评家所诟病,认为其缺乏结构张力,直到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指出,虽然中国古典小说不具备“西方名著里的structure——即那种‘大型’叙事架构所拥有的艺术统一性——它处理的其实是奇书文体所特有的段落和段落之间细针密线的问题”[1][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8页。,浦安迪称之为“纹理”,各类大小片段经由“草蛇灰线”“横云断岭”“奇峰对插”等各种各样的纹理交织联结成篇。
杨百利在婚宴上那个未能“喷”完的“空”就是一个典型的缀段式故事,分别由小媳妇被火车轧死后化狐、女鬼因化成的仙树被砍而怨怼、男人骑在火车灯柱上喊冤这三个片段组成,每个片段都是相互独立的,而杨百利又用因果逻辑或空间逻辑(如同一辆火车)将它们连缀在一起,与古典志怪小说的审美趣味相契合。
刘震云在新世纪以前就已经在使用缀段式的结构进行写作,比如在《故乡相处流传》中刘震云选取了故乡延津的四段并不相连的历史,选择了三国、明朝、清朝、大跃进时期的一干人物,让一代帝相及其奴才、帮闲和他们分别繁衍的后代一一开口,但这一张嘴还是乡间胡侃般的“喷空”,把“无”喷成“有”,把“好”喷成“坏”;或者相反,把“有”喷成“无”,把“坏”喷成“好”,以语言狂欢的戏谑姿态解构严肃的权力话语,以看似相同的情节连缀表现历史的循环,讽刺民族的劣根性。这种结构被整个故乡系列一直沿用,每个片段之间都很相似,显得重复,这也是“故乡系列”令人产生阅读疲劳的原因之一。
重复是缀段式结构常被诟病的特征,但赵奎英在考察中国古典小说的结构时说,从大结构上来看,起结事件在性质上具有相似性,就是从局部来看,它也主要是根据相似性原则来结构的[2]参见赵奎英:《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看传统叙事结构的空间化倾向》,《文艺研究》2005年第10期,第63页。,也就是说,相似情节的复现不仅是中国古典叙事凝结各部各章常用的手段,而且已经上升成为了一种美学原则——情景情节重复,情调意蕴却不重复。刘震云在演讲中谈到《西游记》时也曾说过:“我30岁之前觉得《西游记》写得很差,重复……我觉得吴承恩没有创造性,在30岁之后我突然读懂了,我觉得吴先生是非常伟大了,因为《西游记》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重复。”[3]刘震云:《当故事告诉现实——林冲遇到了拼爹的人》(长江讲坛讲座),2014年4月26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55618164。《西游记》里师徒四人在取经路上经历了具有类同性的八十一难、遭遇了大同小异的妖魔鬼怪,但在戏剧性处又有不同。刘震云将相似与类同解读为“日常”,将转折与不同解读为“关键”,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需要处理好日常与关键、重复与不重复的关系。
在《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每一次告状的叙事结构都以其第一次见到某级干部为开头:“李雪莲头一回见到王公道”“李雪莲头一回见到董宪法”“李雪莲见到法院院长荀正义”,等等,同样的开场,同样的结局(伸冤不成),同一种叙事模式不断复现。但同中又有异,在李雪莲见法官王公道的时候,两人虽有身份差别,但还不是什么巨大沟壑,毕竟王公道是李雪莲拎着鸡就能堵在家里的人,还算是乡亲,王公道还能完完整整听完李雪莲假离婚变真离婚的来龙去脉。然而随着后来的官员级别升高,身份差别越来越大,李雪莲面临的权力话语更加难以撼动,因此其逐渐在这一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到了市长一级时,叙事的开头已经不再是“李雪莲见到市长”,而是市长蔡富邦见到李雪莲,看到她头顶“冤”字静坐的场景,正是因为这种逐步的失语,李雪莲的冤情才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采取的行动才会越来越偏激出格,事态也随之一步步升级。李雪莲每一次告状的情节都可单独提炼出来,成为一个带有留白而意味深长的短篇,连缀在一起,看似是重复,其实互相之间存在着时间和逻辑上的递进与升级。除去各小节之间的连缀,《我不是潘金莲》里各章之间的连缀关系更为明显。小说三章讲了三次上访的故事,李雪莲20年前、20年后的两次上访和史为民的假上访,三部分各自独立,真上访和假上访又形成对比和反讽,对比、反讽恰恰就是前后连接的针线。小说看起来基本上遵守了线性的时间发展,但刘震云别出心裁地把第一主人公李雪莲的两部分称为“序言”,却把篇幅不长的史为民部分称为“正文”,还取名为“玩呢”,这种顺序的排放不乏市井“喷空”里的谐谑调侃。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在主题上和《我不是潘金莲》有重合之处,在结构上更是异曲同工。刘震云选择了四位原本毫不相干、素不相识的人作为主人公,书写了四个其实完全可以独立成章的故事,由于一种蝴蝶效应般的命运联系,让四条好似平行的命运线交织成网;不明全貌却沉浸在语言狂欢里的网民以附录形式出现,再加上因只有一句话为内容而标题对话感极强的第二部分:“你认识所有人”,读者顿觉自己的日常网络生活就折叠在那一页纸的空白中,成为了小说的一个部分,被连缀其间。
纵观刘震云的创作历程,自故乡系列之后的所有作品都采取了缀段式的写作,通常是基本遵循时间的线性发展(以一代人为一章节连缀在一起,仿若戏剧的一幕,父辈的故事落幕又有子辈登场继续上演),再根据每部作品的主题以及追求的美学表现、哲学表达的不同来调整连缀顺序,如《手机》里先讲了父辈、子辈打电话的故事,后又笔调一转,写祖父辈当年捎信传话的困难,在此不再赘述。利用古典文学里的缀段技巧,通过对一代代人相似的命运轨迹的书写,刘震云在创作上完成了重复中的反重复。
三、双构:“喷空”张力场的编构方式
“喷空”具有强烈的民间性,潜藏着我们民族群体意识里的一些质朴的心理逻辑。两极对立共构的思维模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族心理与思维方式,使我们只要看到一极,心中就隐隐地默认另一极的存在,这种古老的整体性思维和双构性思维也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叙事模式。
我们的汉语并不喜欢非黑即白的直线表达,造就了中文词汇的多义与含混。以“结构”一词为例,虽多用为名词,指已完成的一种范式,但在古汉语里原指结绳、构屋,是动词,杨义就指出“结构”实际上也含括了作者构思的动态过程,动名双性使“结构”的意蕴成为开放的而非静止的。“喷空”目前在本文的论述中已经被认为是一种带有刘震云风格的元叙事结构,恰巧“喷空”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动词,而是动名短语,可以拆分成“喷了三个空”,小说中还有“杨百利的喷空”这样的名词用法,所以“喷空”既可指涉处于完成状态的具有独立性的故事,又可以指涉叙述人谋篇布局的具备开放性的动态过程。
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把古典叙事文本的“双构性”归结为道与技的双层并行,“结构之道用以笼罩全文,结构之技用以梳理全文”[1]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1页。,提醒读者在考虑叙事的顺序、位置、联结方式之余,不能忽视文本背后的哲理性结构,这正是所谓的“结构之道”。刘震云的叙事在“道”的层面仍可以用两极共构来概括,他钟爱语词的捉对厮杀,在《手机》里是“远”与“近”,《我叫刘跃进》里是“狼”与“羊”,《一句顶一万句》里是“一句”与“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里是“名”与“实”,《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里是“傻子”与“聪明人”,《一日三秋》里是“一日”与“数年”。他特意选择一个维度上两个背向的端点,然后把主人公随意地抛掷到这个场域里受这两端的撕扯,看他们在这种宿命般的磋磨下如何挣扎沉浮。正是因为在这样的张力场里艰难谋生,刘震云笔下的人物才生长出种种形态各异的“拧巴”,比如刘跃进的小狡黠、杨摩西的难安分、李雪莲的不通融……难怪,刘震云总是感叹不是人拧巴,而是事儿拧巴。
所谓的“事儿拧巴”,原因之一是事物的两极总在不断地偷换着,这天儿聊着聊着,事儿就不是原来那个事儿了;“空”喷着喷着,话头也不是原来那个话头了。随着事态发展,枝枝杈杈意外横生,相悖的属性多次暗自转换,一件一件的新事端堆积起来,覆盖了生活的最初的面貌。
《我叫刘跃进》里的小偷青面兽以为自己是“狼”,然而嫖娼遇上仙人跳、偷东西惹到权贵被追踪,落魄狼狈的境遇让他成为了只是待宰羔羊一般的角色罢了;打工人刘跃进在小说开端是“羊”,被偷被欺被背叛,但生活的颠簸让他时刻保持着戒备,并具备了一种略显狡黠的灵活,总是在关键时刻上演“羊”变“狼”,当然,他身无长物,全无依仗,最大的资产是一张不知能否兑现的欠条,这样在底层挣扎的刘跃进所展现的一切“狼”性都仅供自保,从来变不成真正的食肉动物。小说结尾刘跃进在火车上又被堵到,又要被迫卷入风波里,这种场景立刻让读者感受到他仅仅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罢了,且不禁让读者又去追问,小说里的那些“大人物”们真的是狼吗?
与在漩涡中为了生存随波逐流、被迫在两极之间反复横跳的刘跃进相反,李雪莲是想要守住生活真相的人,她对真相的执着已经变成一种难被世人解喻的偏执。“名”与“实”原本不是一对反义词,但名不副实了之后,这两个词就变成了“谎言”和“真实”这一对反义词的代称。在李雪莲假离婚变成真离婚的遭遇里,存在两个连续的谎言,在她试图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又被前夫泼了一盆脏水,“李雪莲”变成了“潘金莲”,导致她的正名之路不可终止。但小说第三部分,20年后的史为民就不在乎那么多了,他可以用上访之名拿到顺利归乡的实利,而后来又为了“事情的严肃性”仅仅在书面上实现名实相符,至于真相究竟如何,他不去计较,一计较人人都冤枉,人人都是“李雪莲”。如此,“名”和“实”彻底分离,构成了充满张力的两极。
《一句顶一万句》里的两极就写在题目中,那“一句”是有用的、真心的话,“一万句”是日常的琐碎的话、没用的废话,有时甚至是假话,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精神的生活与庸常的生活之间的对立。小说里所有的人物都在为了追寻那一句真言而流连迁徙,却被淹没在那“一万句”里,抑郁愤懑,孤独百年。可是倘若不是为了找那“一句”,“一万句”话也不必说了;若没有那“一万句”,这“一句”肯定也就迷失了,因为“一句顶一万句”——那最珍贵最知心的“一句”需要有“一万句”话在后面顶着才能凝练出来。于是,这二者形成了一个新的辩证关系、一种话语的两极,彼此承托又互相抹杀。
《一日三秋》延续着《一句顶一万句》的思路,精神性的生活由“一句”扩展成了“一日”,那琐碎庸碌的“一万句”连绵交织成数年,即“三秋”。但陈明亮比杨百顺清醒,他自一开始就知道那珍贵的一日是永不复返的,因为奶奶已经离世,永不能再复生,也许这是他比杨百顺展示出更多坚韧和耐性的原因之一吧。可是,若不怀着对那“一日”的追寻,怎么度过往后的“三秋”呢?于是刘震云让《一日三秋》变成了一个打通了人神鬼怪的世界。倘若没有值得追寻的,人生都荒废在一地鸡毛的日常里,既度日如年般难熬,又度年如日般空虚。
“对立者可以共构,互殊者可以相通,那么在此类对立相、或殊相的核心,必然……存在着某种‘张力场’。”[1]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页。这种两极对立所形成的张力,成为刘震云叙事的结构动力,在叙事内层里支撑着表层的语言,使“喷空”式的简洁直白不流于庸常,调侃式的辛辣讽刺不至于偏激。
四、作为乡土哲学的“喷空”
刘震云将古典叙事里的连缀方法和两极互构的古典哲学融入到“喷空”式的写作中,形成一种富有隐喻性和开放性的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叙事结构。与此同时,刘震云对当代生活的深刻洞悉,使他的小说还呈现出一部分超越中国传统文化既有审美的底层生态美学,他那泥沙俱下的乡野“喷空”里渗透着独属于当代乡土的精神困惑。刘震云回过头向中国古代文学经典里去寻金,实则是想要借助历史的阶梯,洞透弥漫于今天的迷雾。
李丹梦评价刘震云的小说是“流民文化,宋朝文章”[1]李丹梦:《乡土与市场,“关系”与“说话”——刘震云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0期,第4页。。“宋朝文章”便是对刘震云将以《水浒传》为代表的古典文学融入到写作中所呈现出的古典味儿的肯定,“流民文化”则是指这古典味儿的语言所讲述的多是离开了土地的那群乡民的故事,是属于市场兴起的特殊时代的乡土困惑。正是由于将“民”特别是“流民”作为了自己的表现对象,市井民间的实用利己、生存至上原则在刘震云笔下常常一不小心就溜出气味来,让那些言辞显得油滑、痞气,让那些人物在道德上态度暧昧。
胡河清就在《王朔、刘震云:京城两利嘴》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达:“刘震云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功利性关系,看得可说入木三分。但他对人类的非功利性关系,如莫名其妙的恋爱心理、潜意识的黑暗秘景、生命本能的蠢动等等。知道得还很浅陋。”[2]胡河清:《王朔、刘震云:京城两利嘴》,《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2期,第48页。其实这种肤浅不难解释,刘震云的书中人代表的是离开了故土的流浪着的农民,围绕他们的是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里弥漫于中国乡间的落寞与茫然。杨百利们的孤独是乡土的孤独,他们也试图对这无边无际的孤独进行一种“绝望的反抗”,可是这种尝试不同于鲁迅那般带有知识分子的清醒与自觉,他们的各种行动都显得浑浑噩噩、没头没尾,却带着触目惊心的犟劲儿和韧劲儿,这是来自于土地的力量。
刘震云在新世纪以前花大力气描绘了这种孤独是如何在中原村庄的大地上降临的,故乡系列的冗长篇幅都是在严肃讨论宗族结构的社会中权力与欲望如何运作于民间——贫瘠的土地里,权力、欲望和为了生存的种种挣扎一起编织出错综复杂的“关系”大网,“关系”成为了乡土民间至上的生活法则,一代代乡民遵守着这些规约,渐渐对其中的悖谬习焉不察,在历史里描画宿命轮回的景象。
这种因袭的乡土苦痛在刘震云新世纪的小说里不再被浓墨重彩地描绘,而是浓缩成了故乡延津的忧伤底色。在他的新作《一日三秋》中,刘震云以寓言的形式将之凝成一个具有民间志怪风味的传说:花二娘跑到延津人梦里找笑话,没有笑话的人要被她化成大山压扁,在小说最后花二娘却说不是她自己要找笑话,她身上还附着一个三千年的鬼魂,是这个人要找笑话。这鬼魂是谁呢?恐怕是那乡土之上农民们代代相承、亘古循环的苦痛所化的幽灵,这个忧伤的幽灵亟需笑话的治疗。不得不说,这个精练的寓言要比拉拉杂杂的故乡系列具有更强的艺术想象力和更广阔的创作延展空间。
纵观刘震云整个文学创作历程,他一直关注着乡土还在蒙昧状态下的漫长时期里个体非自觉发起的抗争史。杨百顺们虽未觉醒,却仍然发起了一种本能的对抗,对历史的幽灵、生活的庸常的对抗。“喷空”,看似闲来无事地喷吐废话,却是为了寻到一句真心之言、找到一个精彩故事,是流民们用最直接的行动展开的对精神性生活的不懈追求。
乡土民间对于精神性生活的追求,正是刘震云在新世纪的小说创作中试图表现的。刘震云在创作完故乡系列后有一次答记者问,在其中他描述了生活中的一种精神游走现象,他举例乡间锄草的大哥一边锄草一边因乡间的八卦话题而走神、幻想,幻想看似无用,却是支撑着这位乡下大哥坚持劳动的动力,他说:“我们在生活中或是文学创作中,只是把我们的镜头和情绪对准了锄草,而其他这些锄草之外的辉煌创造认为不重要而把他忽略了。我们往往认为锄草是重要的,而这种精神的飞升和游走是不重要的……这种忽略和丢失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把他们重新寻找和打捞回来。”[1]参见周晓丽对刘震云的采访录音,转引自郭宝亮:《洞透人生与历史的迷雾:刘震云的小说世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18页。这种精神的飞升和游走在他的说话系列小说里被具象成了“一句话”,书中人为了这一句话寻寻觅觅、奔奔忙忙,实质上都是对自我灵魂的探索,虽然有些人物的探索并未成功,但他们在贫瘠环境里的不懈追求依然被作家视为生活里的悲情英雄而大书特书。
杨百顺只找到了一句发泄的话。他迟迟找不到那一句真言,颠沛流离之中无边无际的孤独让他感受到巨大的愤怒,这愤懑抓心挠肝、无处发泄,于是他在教堂图纸背面写下了“不杀人,我就放火”[2]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355页。。
牛爱国找到了一句慰藉的话。他有幸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言,但刘震云不曾呈现给读者,而是借他之口说出了一句质朴的安慰:“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3]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358页。这句话里包含着快刀斩乱麻的果决和勇往直前的坚韧,如果没有这样的民间智慧,那么承受生活重担的杨百顺、牛爱国怕是也只能靠宣泄活着。但是这句安慰在李雪莲看来不成立,梳理不好以前,她就不知道怎么过以后,倘若已发生的错乱不能各归各位,通向未来的路径也会随之杂乱无章。她二十年如一日的告状,其中也有数次想要放弃,回头去好好过自己的生活,然而总是横生枝节,而那枝节的根扎在过去的土壤里,所以她的前夫——唯一与她亲历过那个“过去”的证人一死,这个倔强坚韧的女性就崩塌了。
史为民、马忠诚找到了一句荒唐的话。史为民和李雪莲有同样的心境——“冤枉”,但他则是另一个做派了。他信奉的是别跟拧巴的生活较真,被生活嘲弄之后再嘲弄生活,苍蝇击不碎瓶子却可以嘲笑瓶子,总之就是“玩呢”,这是利己至上原则的真实写照。这一句话在马忠诚那里被总结成了“荒唐套荒唐”[4]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295页。:你捉弄了我,我就捉弄回去,生活戏耍了我,我也戏耍生活,大家都靠荒唐活着。结果因为这种“玩呢”的生活态度,荒唐反而化作了常态。
终于,陈明亮找到了一句哲学的话。相比史为民、马忠诚等人占了便宜一般的洋洋自得,陈明亮恳切地承认荒唐圈套里面的巨大耻辱,比如,老婆卖身是耻辱,用老婆卖身时的笑话逃过一劫更是耻辱;老婆卖身赚的钱是耻辱,用老婆的卖身钱做本生利亦是耻辱,他拥有作家其他的主人公身上少有的诚挚与自省。于是陈明亮算是有幸找到了反抗绝望的方法,他把“荒唐套荒唐”升级成了“负负为正”。他为了追忆童年里与奶奶的温馨时光买下一块假牌匾,并回答花二娘说,匾是假的,梦是假的,“负负为正,其中的情意不就是真的了吗”[1]刘震云:《一日三秋》,广州:花城出版社,2021年,第289页。。当两种荒唐的道理相撞,形成二律背反的时候,豁达的人依然不否认其中包裹着真情,就能从中品出“正”和“真”,哪怕这种真情有可能是回忆里的、梦幻里的,但只要感受过一日,就胜过庸庸碌碌的三秋,这是与生活的和解,是民间生存的哲学。
从“不杀人,我就放火”到“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从“荒唐套荒唐”再到“负负得正”,这是从市井流民的卑微之言里提炼出的哲学。将喷空闲侃上升到哲学,正是作家对儒家文学“贵民”传统在当代的回应,这种贵民重民的文学精神自先秦儒家起,至司马迁的史传文学,及至杜甫的仁民爱物,在中国文学的脉络中从未断绝,彰显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天悯人之情怀。刘震云文学里的“贵民”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超越,“悲悯”是古代士大夫用俯视的眼光审视底层才产生的情怀,而刘震云却是直接用流民的眼光看世界。
即便现在名声大噪,刘震云也经常素衣简行,大街上泯然众人,他的文学也坚持使用着乡土之音,尽可能还原流民在拧巴生活里的苦累、挣扎与义愤,还有他们在困厄中凝练出的生存哲学,这些带着乡音的荒诞哲学生长在市井闲侃里,流传于胡吣“喷空”中。
在刘震云的小说中,“喷空”可被视为一个桥梁。作为一个方言词汇,它的根系深埋于历史,连接着古老的文学传统、悠久的民族历史;但它又是一种活的话语,具有生产性,连接着正在向未来无限延展的当下,牵引着当代乡土间的喜怒哀乐。“喷空”作为一种具有本土特色的话语范式进入刘震云的创作,使刘震云的作品将中国古典的文学经验、西方后现代等手法与底层生存哲学的民间元素有机结合在一起,成为了具有刘氏特色的一种语言风格。
“喷空”也是一种对抗,“喷”出来的是“空”,是用看似虚空的精神生活对抗琐屑沉重的现实。在杨百利那里,这是用以抛弃琐碎日常的想象性对抗;在陈明亮奶奶那里,这是用以面对命运无常的诗意性对抗;作为一种文学叙事的“喷空”,某种程度上也展示着作家对人生的洞悟:人们被抛于大地之上,为生存所苦,为琐屑而累,却能暂时放下这些烦恼去“喷空”,市井闲侃也好,隔空对吹也罢,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在刘震云看来,精神性的存在即是存在,与实际的生活具有同等的分量,这是一个美丽的想象性世界,屹立于彼岸,慰藉着乡土间疲劳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