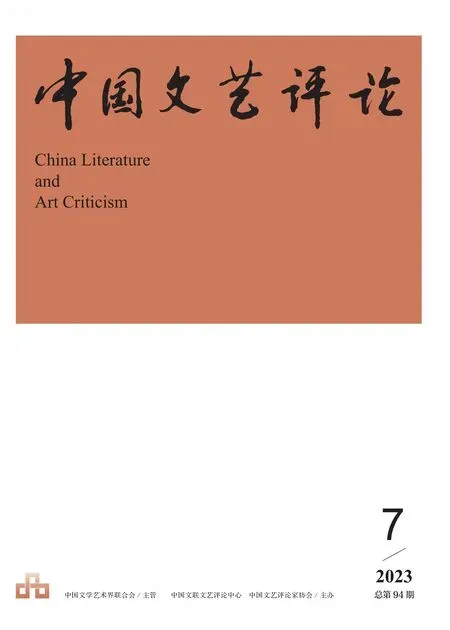世界文学视域下的民族文学研究及其海外传播
——王宁[1]教授访谈录
2023-10-23刘丽艳
■ 刘丽艳
中国文学包括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就漫长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而言,汉族文学虽是主体,但各少数民族文学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有着独特的存在价值。尤其是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学在中国民间文学中显得尤为突出——既有震惊世界的英雄史诗,也有雄浑有力的叙事诗,此外,还有绚丽多姿的神话传说。在作家文学创作领域,古代曾出现过元杂剧作家杨景贤(蒙古族)、诗词作家纳兰性德(满族)、小说家曹雪芹(满族),还有文学理论家李贽(回族)等。在现当代文学领域,也有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其中老一辈的文学大师有沈从文(土家族)、老舍(满族)、萧乾(蒙古族);当代作家有玛拉沁夫(蒙古族)、晓雪(白族)、张承志(回族)、乌热尔图(鄂温克族)、孙健忠(土家族)、阿来(藏族)、吉狄马加(彝族)、扎西达娃(藏族)、阿库乌雾(彝族)等。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族文学迎来了快速发展,对民族文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突破性的进展。在2010年之前,我国学者对民族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学史的梳理与民族文学的翻译工作。近十余年来,民族文学的研究角度逐步多样化,诸如现代性建构、民族认同、民族共同体、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生态批评等具有国际性意义的关键词也进入了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领域。然而,由于语言障碍,海外学者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关注得较少,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藏族及彝族文学。并且,我国许多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与研究成果由于译介传播等各种原因“不为西方文化所了解,造成部分海外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夸大民族对立,导致海外读者对我国民族地区发展状况和文化传统的误读”[1]黄立:《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海外出版的现状与思考》,《中国出版》2016年第21期,第66—67页。。因此,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如何讲好中国民族故事,如何让国内优秀的民族文学文化走向世界,与国外的文学研究者建立交流对话机制尤为重要。本文通过采访王宁教授,阐述他在新时代背景下对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途径以及民族文学海外传播等方面所作的相关思考。
一、民族文学的研究价值
刘丽艳(以下简称“刘”):王老师,您好!非常荣幸您能接受我的采访。您历来主张,中国的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在地缘环境上,不少民族地区地处“一带一路”的沿线。如何使民族文学可以与世界各民族的文学进行“对话”,是这次访谈的重中之重。
首先是关于民族文学界定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起,学界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界定就一直存有争议。比如部分民族作家的作品内容很少涉及本民族的文化生活,或者作家本人基本都在使用汉语进行创作,对此类民族作品的划分就存有争议。同时,民族作家的写作语言亦成为一些西方汉学家指摘的对象。比如,德国汉学家顾彬就曾批评过以阿来、扎西达娃为首的藏族作家“他们用汉语写作;他们不(再)能掌握藏文;他们也不(再)住在西藏”[2][德]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7页。。请问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应如何看待民族作家的创作内容及写作语言方面的问题?
王宁(以下简称“王”):关于民族文学的研究,我本人虽对之颇有兴趣,但由于语言的障碍,我涉及得不多,因此只能从理论上阐发我本人的观点。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一部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学史不应该只是汉语文学的发展史。正如你在前面所提及的那些蜚声文坛的文学大家,其中有许多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伟大作家都是来自少数民族,他们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为中国文学创作了不朽的杰作,这些优秀的作品自然是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它们已经或者必将载入中国文学史册。这一点倒是很像世界文学的发展历史:一些伟大的作家也是来自人口较少的民族或国家,尤其是一些近现代大作家,例如古希腊的那些悲剧作家和喜剧作家,还有丹麦的安徒生,挪威的易卜生,爱尔兰的萧伯纳、叶芝、乔伊斯,捷克的卡夫卡和昆德拉,等等。正是由于他们创作出了具有世界性影响和永恒价值的优秀作品,因而后来的文学史家在评论他们时往往不去追踪他们的国籍或出生地,而是笼而统之地将他们当作西方作家,或当作世界文学大家来讨论。同样,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家,如曹雪芹、老舍和沈从文等人,如果要问普通的文学爱好者,他们或许大多也不清楚这些作家是来自少数民族,这一方面说明了他们的作品所产生的普遍意义,早已超越了他们所出生和成长的民族。此外,由于他们自身被“汉化”,并自愿改用汉语从事创作,因此他们所讲述的故事并非是某个特定的民族所特有,而是全中国各民族、甚至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都可能发生的事件,因而就得到了汉语文学的同化与经典化了。再加之他们本人也十分认同汉族文化并用汉语创作,有的作家甚至已经不能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从事创作了,这种情形也同样发生在中国的海外移民那里:他们为了跻身所在国的主流文化,不惜放弃自己的母语,努力学习当地的语言,到后来竟然连自己的母语也讲不好了。但是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文学是一个大的概念,其中汉语文学固然是主体,但我们也应该充分尊重这个大家庭中的少数民族作家的艺术成就,因为正是56个民族在中华大地上共同组成了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此外,“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内部分就涉及了多个少数民族地区,要讲好这方面的故事就要深入发掘这些民族的文化和文学遗产。
刘:有学者曾批评中国文学学科“文本中心主义、大汉族主义、中原中心主义”[1]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8页。,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主流文坛对少数民族文学缺乏充分的价值评估,没有把其置于中国文学及世界文学的坐标上进行考查”[2]李鸿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书写的世界性因素和世界性意义》,《文艺报》2011年2月2日,第7版。。请问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您如何评价中国民族文学在当今世界中的地位及其研究的价值?
王:正如我在前面所强调的,在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史上,非汉族文学、甚至非汉语创作的少数民族文学也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而对于这一点,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们往往缺乏足够的重视。正如叶舒宪所批评的那样,他们确实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大汉族主义、中原中心主义”的情绪,就好比我们中国学者要想走向世界,跻身国际学界,经常也会受到国外汉学家的冷落。实际上,没有强大的中国和中国文化作为后盾,汉学在国外、尤其在西方的众多学科中,只能处于“边缘”地位。美国的宇文所安和苏源熙等汉学家主要是依靠他们在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方面的造诣和人脉才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的,而真正仅凭从事汉学研究步入主流学界的著名学者少之又少。因此就这一点而言,这些汉学家应该更为尊重中国学者。但是有时情况却恰恰相反,这些汉学家中的一些人对待中国学者就像对待小学生似的,认为他们英语不好,未受过严格的西学训练。而在国内,一些学者也就学着西方汉学家对待中国学者的态度,也这样轻视少数民族文学,这显然是不对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了诸如《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尔》史诗这样的出自各族人民群众手笔的优秀文学作品。但是由于长期缺少翻译的中介,中国的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在国际上缺少中国学者的介绍,光靠少数几个略懂一些民族语言的汉学家去推介,很难跻身世界文学之林。因此,毫不奇怪,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就其整体而言,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依然十分“边缘”,即使就个别杰出者而言,例如曹雪芹、沈从文、老舍等,也并未被当作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家来研究。不过现在随着族裔研究的兴起,这方面的研究肯定会多起来,中国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的地位也会逐步凸显出来。
二、民族文学研究与共同体理念
刘: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共同体理念的?在民族文学研究中我们应当如何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民族文学的世界文学性?
王: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国际马克思主义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在当代国际学界,关于共同体(community)的讨论近年来日益多了起来,这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体系不无关系。由于共同体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已经有之,因此这也应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当代形态。共同体这一术语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西方也一直有着不同的定义和众多说法。但就其基本的意思,不外乎这样几个:其一,人们在共同的条件下,例如经济的或利益上的,结成的某个集体或群体,也即早期被译成中文的“社群”;其二,由若干个国家根据各自的需要和共同的利益组成的集体组织,如早先的欧洲共同体或现在的欧洲联盟,这是一种政治共同体;其三,使用同一种语言或具有同一种宗教信仰的人往往出于沟通的方便容易结成一个群体,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共同体;其四,在爱情方面,指最具同心力的一个集体,也即双方具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基础,可以做到同荣誉、同命运、同生活。我们今天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讨论的共同体主要是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
诚然,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最早的共同体思想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来的,后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发展了这些早先的零散思想,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其升华为一种共产主义的(communist)社会和理想境界。由此可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仅有着历史的依据,同时也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来源,可以说是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造性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最新的发展形态,它打破了阶级、经济利益、政治观念、宗教信仰以及语言文化上的隔膜,认为地球上的人们都处于一种相互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中,因此基于这一点构建一种(代表)(全)人类(共同)命运(和利益的)共同体是完全可能的,同时也是十分必要的。
世界文学的理念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共同体的构想,根据歌德的构想,世界各民族文学的“文心”都是相通的,中国人的写作方式与欧洲人没有什么两样。正是由各民族/国别文学的相互交流与互鉴,最终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也是我们试图证明民族文学的世界性特征的一个依据。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在讨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时,不应该忘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出的贡献,只有弘扬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作用才是全面的、客观的、公允的。而中国的各民族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家庭中,就如同生活在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中一样,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共同体的角度来探讨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主流文学和合共生的历史和现状。
在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结合生态批评来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批评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面对全球化时代生态环境的破坏,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不得不对我们所生活的环境进行反思:我们的环境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什么会变得紧张起来?作为人文学者或文学批评家,我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因此,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之一的可持续发展观,我们便可考察当代民族作家在文学中对生态问题的描写、理解与探索。由于我们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生态资源丰富,有些地方甚至尚未被开发,现代化程度有所差异,但是那里的作家们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书写自己的作品。比如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开创了“中国草原文学”之先河的草原小说,蒙古族作家郭雪波创作的极具影响力的动物小说等。我认为中国大地上的生态文学作品也一定能够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家对自己所生活的环境及生态资源受到破坏是十分敏感的,他们希望通过文学作品来唤起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也是十分正当的。所以,民族文学研究者完全可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维度来挖掘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生态书写。
刘:从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概念到2014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正式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重心。而部分汉学家在其研究中有意或无意地去歪曲和“夸大民族对立,导致海外读者对我国民族地区发展状况和文化传统的误读”[1]黄立:《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海外出版的现状与思考》,《中国出版》2016年第21期,第67页。。您认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民族文学研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王:既然中华民族是一个大的共同体,那么每一个成员,也即每一个民族都应当是平等的,虽然汉语或汉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绝对的强势地位,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少数民族为之作出的卓越贡献,尤其是那些虽然也用汉语创作,但却出生于少数民族的作家,他们的贡献就更加值得珍视。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些少数民族的语言趋于消亡,或者长期未形成自己独立的文字体系,来自那些民族的作家便用汉语从事文学创作,但是他们所讲述的故事往往是自己民族的故事,这恰恰是他们的独特性。我们经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然而由于一些民族的语言并不流通,通晓者极少,因此越是民族的,反而越是难以走向世界的。也许这些作家意识到了这一点,便用汉语去进行创作,我们应该保护他们的创作积极性,并给予必要的扶持,使他们不仅在中国大地上用汉语讲述自己民族的故事,同时也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将自己民族的优秀作品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这样他们的故事就可以为全世界的读者所分享。任意夸大民族对立是一些对中国抱有敌视态度的海外汉学家的惯用手法,但是他们的这种歪曲和夸大并不占据主流,我们可以不去理会他们。
三、民族文学如何走向世界文学
刘:在中国当代文学界,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民族作家。一些作家在利用本土资源创作时成功地借鉴了西方文学的观点及技巧。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在创作上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创作出了《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小说,塑造了西藏独特的艺术文化及神秘的氛围,从而吸引了国外研究者的目光。而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用现代诗的方式书写神人支格阿鲁子孙独有的语言及其民族特有的文化色彩,使得自己的作品从传统走向了当代,“从中国走向了世界”[2]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上),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80页。。因此,有学者认为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下创作,是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主要路径。但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一些学者认为世界文学的视野亦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宇文所安与周蕾关于北岛诗歌之争就体现了某些作家在创作时寻求可译性的问题。[1]参见汪荣:《世界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69页。请问您是如何看待上述问题的?
王:确实如你所注意到的,在中国当代文学界,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民族作家,他们创造性地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写作技巧,将其用于讲述本民族的故事,特别是藏族和彝族这两个民族的故事尤其吸引本民族以外的读者和研究者,当然这些作家成功地走向了世界,特别是扎西达娃、张承志和阿来,他们的作品在国外的影响甚至高于国内。你所说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可译性问题并不是绝对的,优秀的汉学家如果与中国的民族文学专家合作必定能较为圆满地解决这种可译性问题。反之,一味追求可译性,在创作作品时就想着能否被译成外国语言,肯定是无法写出优秀的作品的。我们都知道,即使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灵夜》等被当作“天书”的文学作品,不是照样被中国学者译成了较为流畅和可读的中文了吗?土耳其小说家帕慕克虽然在哥伦比亚大学用英语教授比较文学,其英语程度不亚于当地的美国人,但他依然坚持用母语土耳其语写自己的文学作品,经过翻译的中介,他的作品照样畅销世界各国,他也照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的少数民族作家首先应该考虑如何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只要作品足够优秀,就一定有人能够将其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
刘:近几年来,有学者提出“区域世界文学”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一种路径。[2]参见谢江南、刘洪涛:《如何成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几种路径》,《光明日报》2015年5月25日,第13版。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王:所谓的“区域世界文学”指的是某个大的区域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背景的文学,例如东亚文学就是儒家文化和汉字文化的一种区域性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和朝韩文学的影响正说明中国文学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别的有着世界性影响的文学。美国的文学研究者也经常将加拿大文学和美国文学放在一起统称为北美文学,所以2008年美国学者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受我邀请出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并作主旨发言时,他提供的题目就是“作为世界文学的美国文学”(American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他试图强调美国文学的世界性特征、世界性影响以及对世界文学作出的贡献。受其启发,我在2015年应邀在美国人文中心发表演讲时,也以“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为演讲题目。在我看来,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即使我从事世界文学研究,我也有责任有义务在国际场合弘扬中国文学,扩大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影响,提升其地位。
刘:近年来,部分海外学者开始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比如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一直在译介西南少数民族的口传文学。在翻译的过程中,他开始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产生强烈的兴趣,继而将中国西南民族的诗歌与印度东北的多民族志诗歌进行比较,同时将彝族诗人作品与美国印第安诗人作品进行比较。由于本德尔的译介研究,彝族诗人阿库乌雾的诗歌被美国读者所知晓,并且作家本人也被邀请到美国与读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1]参见梁昭:《文学世界与族群书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89页。还有吉狄马加的诗歌也是由于美国汉学家梅丹理(Denis Mair)的译介研究,进入到了世界文学的流通网络,继而获得了国外读者的关注。[2]参见汪荣:《世界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74页。因此,想请教王老师,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下,海外学者的直接译介研究是不是更有利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
王:应当如此,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下,有时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一些在中国国内知名度并不算高、影响力并不是很大的作家通过翻译的中介以及国外汉学家的推介,反而在国外的知名度更高,其作品也更具国际影响力。在古代作家中就有寒山的诗,经过美国“垮掉派”诗人施耐德的翻译和推介,寒山的知名度在普通读者中曾一度超过李白和杜甫。当代的北岛、顾城、芒克、多多等人在海外的知名度也远远高于国内的一些小说家。所以,由于国外汉学家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考察和研究,进而在国外推介,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也许可以直接走向世界。但是,由于语言的局限,这种案例并不会很多。
四、民族文学的海外传播
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海外传播始于晚清,当时主要以西方译者的主动传播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对外译介的模式发生了变化,主要是以国家机构为主导的译介。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民族文学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就其传播效果而言,西方译者主动式的译介影响最大,以国内为主导的译介传播效果反而不佳。事实上,不仅仅是民族文学,中国文学外译普遍的焦虑都是被接受的问题。学界普遍认为“走出去”不等于“走进去”,尤其是国家机构支持下的文学外译。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被接受的焦虑”呢?
王:我认为这种“被接受的焦虑”是很正常的,因为任何一位从事中译外的译者都希望自己的译著能够为域外的读者所读懂进而被接受,特别是对他们花了很大功夫从少数民族语言译成外文的译著能否被域外读者接受更为关注。正如你所提及的,目前民族文学的海外接受和传播还存在着这样一个瓶颈:西方译者主动发起译介的作品往往比国内译者得到资助译出的作品更受欢迎和更有市场。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文学“走出去”以后能否“走进去”?也即首先能否走进著名大学的图书馆,其次能否走进图书市场,主要是各大学的书店,最后才是能否走进国外读者的书房或书架。如果我们和国外的汉学家合作,走进大学图书馆并不难。我在国外从事教学时,图书馆的管理员经常征求我的意见:哪些中文书籍需要订购,我一般都挑选著名作家或学者的著作。而走进后两者才是最难的,但是却意味着真正走进了国外读者中。
刘:在民族文学的具体翻译过程中,母语译者,比如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等,他们采取的翻译方式是直接以人类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民族志的方式来翻译,并不像20世纪的路易·艾黎(Rewi Alley)或戴乃迭(Gladys Yang)那样从汉语转译成英语,他们更希望能直接从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成外语。虽然母语译者本人并不精通少数民族语言,但他们通常会选择与少数民族的学者直接合作。当需要翻译当代作家的作品时,他们便直接与作家本人沟通,比如本德尔翻译阿库乌雾的彝语诗歌就是如此。然而,当前国内的民族翻译团队在进行对外译介时更多的是采取美国学者梅维恒(Victor H. Mair)所谓的“汉语过滤器”的路径,即从民族文学汉语译本转译,而这种转译方式受到了西方学者的指摘。请问在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时,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这种“汉语过滤器”或者说从汉语转译到英语等西方语言的翻译路径?
王:其实这种现象也不足为奇,因为毕竟国外的汉学家中真正懂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者少之又少。他们学好汉语就要花好几年的工夫,如果再让他们去学一门少数民族语言,他们肯定要思考一下学了这门语言有什么用,除非那些纯粹凭兴趣去学民族语言者或许不考虑是否有用。因此,一些民族文学作品被译成外语,大多是从汉语转译的,这其中也应该分析:有些作品是作家本人用汉语创作的,那肯定就无需经过“汉语过滤器”;有些则是少数民族作家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创作,然后作家自己或由别人将其译成了汉语,如果是自己译的,就无所谓“过滤”,如果是别人译的,我想误读的成分也不会太多,因为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都同时精通汉语和自己的民族语言,而真正的汉族人精通少数民族语言者并不多见。也许今后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的继续扶持和对其语言文化的保护,越来越多的民族文学作品将直接从自己的民族语言译成外语。
刘:近年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收录了大量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同时,许多传统的民族文学与艺术形式也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意味着我国民族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在当今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民族文学文化的对外传播也需要与时俱进。您的研究一直都具备前沿性、理论性、跨学科性及国际性等特点,近期又在研究“数字人文”。请问“数字人文”的诞生是否更有利于包括中国民族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呢?
王:确实,我们当前正处于一个数字化的时代,一切都可以通过数字来表达。作为人文学者,我们也提出了“数字人文”的概念。所谓“数字人文”,顾名思义,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且是大学的计算机学科与人文学科相交叉的一个项目。它从人文学科的电脑化、电脑的人性化以及数字人文实践发展而来,同时涉及多个研究课题。它融合了数字化和天然数字材料,以计算机和数字发表所提供的工具将由传统的人文学科衍生而来的各种方法加以结合。这样看来,我们便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数字人文的诞生,使我们得以使用当代计算机科学技术更新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使得人文学者从繁琐的资料搜集和检索工作中解放出来,不仅能在理论阐释和建构创新方面进行更多的思考,同时也可以使得人文学科各分支领域的研究成果“数字化”,从而为更多本学科领域之外的学者所共享。因此可以说,它给人文学者的研究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和效率,同时它也使得人文学科的研究更接近科学研究。同样,数字人文的诞生也有利于中国文学、包括中国的民族文学的海外翻译和传播。我们翻译成外文的图书也可以做成电子书,向海外发行电子版,这样传播的速度快、范围也广。
刘:除了以上方面,作为最早提倡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学者,您认为民族文学在海外传播过程中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王:我认为我们在向海外推介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时,不要去效仿西方的一些汉学家,他们试图强调民族文学不同于汉语文学的特殊性,而我们则要在承认其特殊性的同时也要将其纳入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也就是说,我们在向海外推介中国文学时,不能只是介绍汉语文学,同时也要介绍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和用其本民族语言创作的文学,这样才算得上客观和全面。正如我多次在国际场合中所强调指出的,一部没有中国文学或肆意贬低中国文学的世界文学发展史肯定是不全面的和有缺陷的。同样,一部缺乏民族文学或者民族文学的作用价值未得到客观估价的中国文学史至少也是不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