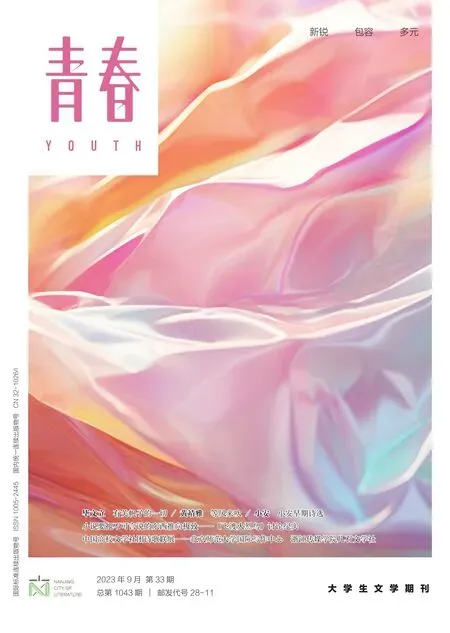短评二则
2023-10-23复旦大学宋炘悦
复旦大学 宋炘悦
生命书写的复杂向度——读《斯通纳》
“生命”是古今中外诸多作家关注的话题,展现人物的成长过程也是作家们常用的创作方式。在聚焦人物成长时,“截取特殊的时空面”最易表现冲突、塑造人物性格,但是,美国当代作家约翰 · 威廉斯的《斯通纳》却恰恰规避了这种写法,将叙事时间延长到主人公的一生,以密苏里州农家子弟斯通纳选修的一堂文学课作为叙事起点,拉开一条主人公成为大学老师、结婚生子、教学退休直至衰老死亡的漫长马拉松。回首以“知识分子”为书写对象的中国小说,我们会发现,从清代的《儒林外史》到20 世纪40 年代的《围城》,再到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应物兄》,这一系列作品最终都指向了对各种压抑个人天性的系统或体制的批判,因而在情节上频频采用带有强烈预设性的“展示”(representation)手法;《斯通纳》却以平淡的笔调着力于主人公蹚过生命河流这一过程本身,整部小说呈现出一种不疾不徐的“叙述”(narration)笔调。事实上,正是这种耐心细致地容纳一人一生时光的“叙述”,在经典的知识分子成长小说写法之外,辟出了别一种生命书写的复杂向度。
这部小说中,最动人心弦的便是斯通纳生活中“前行”与“顿挫”、“流动”与“凝定”的交错并置。在斯通纳的生命历程中,他每朝前一寸,身后就断裂一寸:在“求学”与“归家”之间抉择的犹豫、教书时磕磕绊绊的上下级关系与师生关系、在实践自我理念的道路上与几位朋友的“分道扬镳”,都是“前行”时无可避免的“顿挫”,也是在“流动”中为“凝定”之所赋形的动态过程。这番动静交错的游弋间,最令人动容处还是青年斯通纳做出留校学习决定时的频频回望——书中如此写道:“灰色引导着他的眼睛向外向上看到天空,他望去的天空似乎通向一种自己还无法名状的可能性”,但这种期待和渴望之后“他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仓促中选择的目标,感觉自己放弃的这个世界充满吸引力”,被农场解雇后斯通纳也感到“有种恐慌的刺痛感。好像自己与昔日生活之间最后的那条纽带被割断了”([美]约翰·威廉斯:《斯通纳》,杨向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在经典的成长小说或英雄复仇叙事中,“往昔”与“未来”很容易被粗暴地贴上“勇往直前”“为理想抛弃一切”等具有强烈断裂性的标签,作者也意图就此打造出一张新/旧天地两相隔的蓝图。但是,恰恰是新-旧地带的模糊之处最为沉静却也最激烈,暗藏着个体生命鲜活宝贵的经验。至此,斯通纳不再是被先验概念/理念定义的模板,而是一个以坚定会心的微笑与隐而不宣的挣扎“铸造”出自我生命活性的“人”。
实际上,人只要生活在世俗中,就不可能永远处于“革命”状态,以生活稳定为鹄的,就必然接受规范化、理性化、制度化,纯粹的卡理斯玛权威经过一段时间也必然会例行化(routinized),转变为传统型权威或理性的与法律的权威。(马克斯·韦伯将支配类型分为理性及法律的支配、传统式支配、卡理斯玛式支配。第一类支配的基础是确信法令、规章必须合于法律以及行使支配者在这些法律规定之下有发号施令之权利;第二类支配的基础是确信渊源悠久的传统之神圣性及根据传统行使支配者的合法性;第三种支配的基础是对个人及他所启示或制定的道德规范或社会秩序之超凡、神圣性、英雄气概或非凡特质的献身和效忠。希尔斯认为其他两种权威是卡理斯玛式权威的派生,传统的或理性的与法律的权威之所以具有效力常常是因为人们对这些权威所具有的卡理斯玛具有一定的信赖。)个体游动于生命长河,并没有“最理想”的选择,人最终要接受一种能够为之承担代价的选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作者传达的这种认知并不能与“虚无主义”画上等号。书中如此形容青年时期的斯通纳对“远景”的希冀:“他眼中的未来,不是事件、变化和潜在可能的涌流,而是犹如前方的一块领地,等着他去探索。他把未来看作那座宏大的大学图书馆,可能会从侧翼新起楼宇,还会增添新的图书,然后又清退掉旧书,但是其本质仍然基本不会改变。”([美]约翰·威廉斯:《斯通纳》,杨向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这种探索生命的方式,正像里尔克笔下“瓶”与“水”的关系:“瓶”固定住根基,为盈增莫测的生命元素——生死、高尚精神、伟大人格、孤独本质等等建起了纪念碑,而其中的生命元素变动不居,蕴藏着随时迸发新光景的巨大潜能。在小说的后半本,面临上级与学生的刁难,年近中年的斯通纳并非一直处于被动之位,他一步步稳住“心锚”,从将自身幸福、烦忧寄于“大环境”的泥沼中挣脱出来,最终走向了坦坦荡荡践行“心之所向”的道路。
这便是个体生命“绝望”与“希望”的辩证法:绝望之地的下方,亦有希望的潜流在暗中涌动。歌德在《浮士德》中借魔鬼之口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人类整体确实可谓“生生不息”,而斯通纳生活中“前行”与“顿挫”、“流动”与“凝定”的交错并置却昭示着:穿越生命长廊,个体脚步的且行且止才是常态。较于“成长小说”“反成长小说”梯度写法中对生命的暴力规划,约翰·威廉斯对斯通纳生命历程的这种“螺旋式”写法,正体现出对现实中个体生命复杂向度的体悟与关照。
从个体的生命理念出发,斯通纳对战争的回避态度也就能够得到理解。斯通纳的回避不仅仅是为“小历史”留下一方天地,更是源于其内在的生命经验。如果说,一开始斯通纳拒绝入伍还是出于听从其老师斯隆“牢记自己是什么人,选择成为什么人”的劝诫,当其好友待戴夫 · 马斯特思以“被派往法国,差不多在入伍一年后,跟第一批美国士兵一道去执行任务,已经战死在蒂耶里堡”的结局收场后,对于持有“生命完善”高于“生命毁灭”观念的斯通纳而言,侵略性的战争已然成为一种以“正义”为名、摧残个人生命的集体暴力,其对战争的冷然,即为一种对“常态化的权力”(power of regularization)将个人变为“赤裸生命”(bare life)的高度警惕与决绝反抗。因此,斯通纳的掉头离去并非由于“不在乎”,而恰恰因为“太在乎”——在乎“美”,在乎“生存”,在乎“生活”,在乎“生命”。
我想,我们并不能以“追求坚定的学者”或“逃避世事的懦夫”这样的词给斯通纳的生命下一个精确定义。文本是复杂的,个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命体验更不能依据几个词语或理论寥寥概括。《斯通纳》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在不同的镜头、视野中,个体生命都是具有相异色彩的动态图景,预设好特定摄像位置的“成长”与“反成长”,无法化约鲜活的肉身、灵魂以及它们经历过和正在体验的一切。投目光以“自我摄制”“被拍摄”“照片被漂洗”等诸种过程,便成了接近个体生命复杂向度的重要途径——在此,突出生命的“刺点”(punctum)固不可少,知晓生命的“全景”(panorama)亦是一种必要。
笔落饮食见真招——读《一把刀,千个字》
和哈尔滨的朋友聊起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时,朋友说,小说后半部的“东北主义”令她印象深刻,而对于从小生活在南京的我而言,感受颇深的则是王安忆对各色江淮菜品的描写了。小说开篇,一连串的淮扬菜在纸面翻滚一遭,便让人起了返乡的冲动。书中屡屡出现的饮食描写,在王安忆之前作品的“物质书写”基础上更进一步,王安忆本人亦对小说的名称进行了解释:“扬州三把刀,第一把是菜刀!”(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年版)——那么,王安忆落笔于此,究竟匠心何在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王安忆之前的饮食书写。在《长恨歌》中,当主人公王琦瑶走出爱丽丝公寓,走进平安里时,浓墨重彩的服饰描写逐渐淡化,味觉化的书写依次浮现:“鸡片,葱烧鲫鱼,芹菜豆腐干,蛏子炒蛋”“糕饼汤圆”“蛋饺肉丸”“糖年糕,炸春卷,核桃仁,松子糖”,再遇程先生时,小说展现的也是“王琦瑶家又吃肉了”的场景。在此,“吃”代表着王琦瑶历经人世繁华后的生命寄托,这种寄托虽然平凡琐屑,却又扎实可感。
《一把刀,千个字》中饮食书写的面貌更加丰富,地方风情、世故人情、文化裂隙、历史浮踪等多重面向无不寓于其中。上半部小说的主人公陈诚选择主打北美化的中国菜并取经于“私人订制”,这种食物层面的“易位”在世俗层面为居美华人赢得了生意的成功,却不可避免地带来身份认同与经济利益错位的两难处境,“上海青”的形同神不同、移民局抽访店家时前堂叫菜铃两响一停的应对策略同样指向这种困境;唐人街麻婆豆腐、咕咾肉、酸辣汤、扬州炒饭的菜码则是从文化夹缝中迸发出的默契——生意食材、日常饮食温和地托起了漂泊的旅人无处承载的乡情,色、香、味的集体记忆召唤出以国族/地方为单位的小群体。饮食早已超越了纯粹的物质范畴,以饱含烟火气的笔法书写异乡客的生存哲学与情感体验。从这一意义上而言,“饮食史”即“生命史”。
在第五章中,陈香梅菜式的烤麸、熏鱼、白斩鸡、糖醋小排、葱油软兜、腌笃鲜全家福,蕴含“记忆不在大脑,而是舌头”的生活之道,重庆的麻辣、山西老陈醋、山东大馒头、皖北的“啥汤”、武汉的热干面也成为维系“地方性”的纽带。后半部中,老杨一家一起做饭的场景更令人动容:妹妹专司蛋饺,大哥负责杀鸡,父亲划鳝丝,母亲备馅做大肉丸。“聚餐”这一日常活动似乎拥有特殊的魔力,在无形中扮演起伦理关系黏合剂的角色;写及20 世纪60 年代中期的俄式大餐“大盘的鸡块,大盘的灌肠,大盘的锅包肉,大列巴”,又是一处风风火火的光景。不承想时代易位,武斗爆发前的一家四口好不容易聚齐,却因吃饭时对政治议题的分歧,终致“事情真的谈不下去了”——在此,“小历史”与“大历史”的离合摩擦、兜兜转转,皆匿于食物类别的变化与餐桌话题的择取上;临近尾声处,东北的熏酒、酸菜暖锅、大棒骨、小鸡仔又回归了“地方”与“家庭”,人间的脉脉温情漂浮于厨房和餐桌上空,似乎在风雨飘摇的尘世中,唯有冒着腾腾热气的食物才能携来安慰人心的暖意。
如果说,《长恨歌》时期王安忆的饮食书写还根植于“赋比兴”的中国诗学传统,在无形中迎合了世纪之交读者对“私人生活”的期待视野,那么,《一把刀,千个字》中的对各色菜式和烹饪就餐的描写则多有“寻常之处见真章”的深意,此时的王安忆不再限于“写史”,更尝试以新的视野“写世”。《一把刀,千个字》中,当“历史的天使”在一场场名为“进步”的风暴中面对积满残骸的废墟被不可抗拒地吹向未来时,小说中的各种美食与聚餐活动却在过去、现在、未来的长廊中自由穿梭,呈现出缠杂的多重时间性,通过仿拟前工业社会的循环时间,逸出了线性时间的暴力规划,由“欲望-宣泄”“生育-性”“消耗-补给”组成的日常生活得以辟出一方自己的园地。当《一把刀,千个字》中的人物以当下为据点回溯往昔,“食物”便成了本雅明所言的“收藏品”:“收藏家”如革命者般梦萦一个悠远或消逝的世界,同时幻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食物不断与人沟通,钩织出个体和集体记忆的捕梦网,以温和而微妙的方式修复历史阵痛,使深陷现代遗址的个人回归“本真”,得到打捞与赎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由具有日常性的饮食书写代表的“稗史”与集成宏大话语的“官史”截然二分。放眼文学史,古代随笔中的美食往往采用一种分门别类的“专精”写法,独有士大夫情趣,如列出各种烹饪方法的《随园食单》、极其看重“饮食修养”的《闲情偶寄》的《饮馔部》、描绘出“茄鲞”复杂工序的《红楼梦》等,都是如此。这时的饮食书写或还在纯粹的私人范畴内,但到现代,情形却有所变。在新感觉派小说中,作家笔下的诸多物质只是毫无关联的、共时排列的意象。物件的去组合形式与1930 年代个人精神的摇摇欲坠形影相随,都市人纵使逃入“物”中,心底仍是荒凉一片,此时的衣食住行描写已然成为都市的理性规划法则与都市人孤立无援现代性症候的物化形式。到了当代,具有时代敏感力的作家写及美食——如陆文夫的《美食家》和汪曾祺的《黄油烙饼》等,更是颇有用心地通过“饮食史”展开大历史浪潮下个体生命的画卷。
再漫步至21 世纪,王安忆在《一把刀,千个字》中两次提及“草籽”与“纪念碑”的意象:“你以为历史是由纪念碑铸成的?更可能是石头缝里的草籽和泥土!”“她呢?她却是更高一筹,从本能上升到自觉,哥伦布竖鸡蛋的那一磕,鸡蛋碎了,却立起来了。而大多数的本能,却变形了,在纪念碑巨石的压力下,躯壳缓慢地迸裂开来,长出狗尾巴草。”(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年版)衣食住行便是“草籽”般的存在,因过于“日常”而为人忽略,却恰恰充盈着生活的实感,而对外界力量的侵蚀形成一定程度的防御和抵制,笔落此处,方见最真切的生命体悟。那么,“柴米油盐”在何种意义上成了“稗史”或“官书”?在何种情况下相互转换?我们又从中能体悟到怎样的个体/集体生命经验?时代大浪向前奔去,这又是留给每个“同时代人”的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