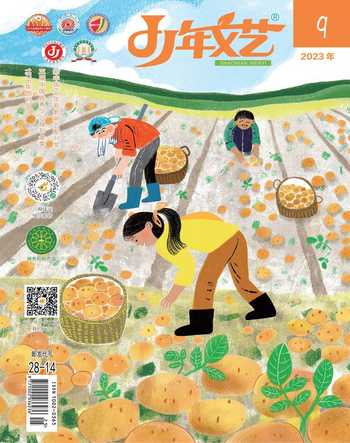天井里的无花果树
2023-10-14袁璐
袁璐
我三四岁的时候,母亲从姥姥家拿回来一棵小树苗,说是无花果树。她把这棵小树苗种在奶奶家天井的圆形花坛里。
小树苗需要两根细竹竿在一旁支撑着才能站直,像是生病了似的。它还没有大人的手指粗,个子也没比当时的我高出多少。不仔细看,与两根细竹竿没有区别,都光秃秃的。看着它瘦瘦小小的样子,年幼的我在心里想:它真能长成一棵树吗?
刚开始母亲给这棵小树苗浇过水,好像还埋过一些鸡骨头、鱼骨头,后来就没怎么管它了,它只能自己摸索着适应这里的阳光、土质、风霜、雨雪、病虫害……
两年的时间,原本弱不禁风的小树苗长得快有屋檐高了。它结实的枝干和片片如大手般的叶子层层叠叠汇聚在一起,撑开一把绿色的大伞。这伞真像市场上、马路边卖冰糕的小铺竖在外面的那种大伞。
初夏时节,一抬头,呵,无花果树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冒出不少碧绿碧绿的“豆子”。这让我们一家人在那个夏天有了不一样的期待。整整一个夏天,无花果树都在铆足了劲儿吸收阳光和雨露,果子们蓬蓬勃勃地成长,一天比一天大起来。
到了九月,太阳正是最晒人的时候,昼夜温差增大。对于无花果树来说,这大概是果子成熟前能量的最后一次大型积聚,乒乓球大小的果子已经换上了黄色新衣,它那红中透紫的小口张得越来越大,好像在呼喊:“别着急,我马上就要熟了!”
十月一日前后,无花果说到做到,鼓着发软的黄肚皮,在树枝上翘首等待我们发现的目光。
至今还记得这棵无花果树第一次结果时,全家人的那份喜悦,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大人、小孩齐上阵,踩着凳子,蹦着高,踮着脚,这个摘,那个接,无花果盛满了好几个菜篮。
拿起一个无花果,沉甸甸的。熟透的无花果的皮很薄,特别娇嫩,拿着的时候稍微用点力就会皱,顿时手就黏糊糊的。这该怎么吃?双手捏着一掰开,哈,原来无花果的花藏在它的肚子里!短短的嫩红花蕊朝着肚子中心窝在一起,密密麻麻的,一点缝隙都没有。这是藏了多少朵花啊!
咬上一大口——太甜了,甜得齁嗓子!无花果这么甜,藏在肚子里面的花大概出了不少力。怪不得它不把花开在外面呢。无花果吃起来软软糯糯的,润润的。它和苹果、梨、橘子、桃这些“水”果不是一个路数,反倒应该放在村里“多福林”糕点店里,和蜜三刀、桃酥等点心归为一类。
那一阵子,我一听到大门外有动静,就忙不迭地跑过去拉开大门,热情地迎接每一位到来的人。不管是亲戚朋友还是方边左右,只要是走进这个天井里的人,我都会不厌其烦地指着那大大的无花果树,对他们说:“看,无花果结了这么多,特别甜!你快吃一个尝尝!”
与无花果树长久地在一起,除了味蕾的甜蜜,还能探索出更多有意思的时刻。
无花果树是我跳皮筋时的好伙伴。它用健壮的身躯为我撑着皮筋,皮筋被跳跃的双腿拉着、踩着、扯着、缠着,无花果树也被拉扯得歪了身子,枝叶颤动着,发出一阵阵沙沙的响声。幸亏它的根扎得足够深,身躯长得足够健壮,所以能容忍我肆意玩耍。
无花果树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我很喜欢在下雨的时候坐在窗边,聆听雨水打在无花果树又大又厚实的叶子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有一种特别的灵动韵律,仿佛能在人的心上敲打出一朵朵晶莹的水花。真想到无花果树下面躲躲雨啊。
无花果树提供了一条飞翔的通道,将我与碧空和云朵联结起来。我喜欢飞身跃起,去触碰无花果树高处的叶子。这种幼稚的挑战每做一次,心中的翅膀就持续不断地扇动一阵,我与天空的距离仿佛也可以缩得更短。
有人说,无花果可以去瘊。有一年,母亲和妹妹的手上、脸上长了瘊。母亲不知从哪打听来的方子,说是无花果的汁可以治。掰断无花果的绿叶和不成熟的小绿果柄端,确实会流出牛奶一样的汁液,特别粘手,干了之后还蜇人。母亲和妹妹天天掰、天天抹,但没什么用。白白折腾许久,受了多少罪。有病还是得去医院。
无花果树其实也就是一棵普普通通的果树罢了。年幼的我却一厢情愿地把对世界不成熟的幻想强加在它的身上,企图在它身上发现不存在的神秘。
过了几年,父母的工作愈发忙碌,我也学业繁重,到奶奶家的频率减少到一个星期一次。母亲这最爱吃无花果的人,都没心思摘无花果了。无花果树的秋日盛装越来越华丽,但是人们已经对这个盛会失去兴趣。难道无花果树创立的这个属于秋天的节日就要消失了吗?
不会。动物们可不同意,过去它们少有机会品尝无花果,此时终于逮到机会可以大饱口福了。
麻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两只小爪牢牢地抓住树枝,埋头用尖锐的喙将一个又一個无花果鹐空心。它们仿佛是要在无花果树上住下不走了。平时聒噪的叫声,这个时候仿佛也沾上了无花果的丝丝甜蜜,变得悦耳起来。它们像是在呼唤更多的同伴:“真好吃啊,快来呀!”
蜜蜂、马蜂、苍蝇、蚂蚁嗡嗡地飞来飞去、爬来爬去。触角互相碰撞着,翅膀来回摩擦着,纤细的小手抱住无花果不肯放开,脚被无花果的糖分粘住,走不动道,那更合它们的心意。无花果简直化成了神仙的法物宝葫芦,口一开,风一起,不必喊其姓名,虫子们就争先恐后地要钻进这宝葫芦里,出都不肯出来了。
如果我当时是一只鸟,又或者是一只小虫,我想我也不会错过这个热闹的节日盛会。即使原本的我不爱吃无花果,也会受到同伴的传染,比平时多吃上几个,享受世间这份难得的香浓与甜蜜。
这份传播在动物们之间的无边无际的欢乐,对于奶奶来说,是一份要叹粗气的困扰。奶奶素来干净、利索,天井里鸟儿飞、虫子爬、果子落的样子,她是受不了的。
之前,奶奶总是让父亲在周日休息的时候砍一砍树枝,因为那伸长的树枝都沿着屋顶的瓦长上去了。父亲踩着凳子,拿着劈柴的小斧子,对着无花果树高处的树枝砍去。可是,无花果树的生命力过于汹涌,砍的速度往往追不上它生长的速度。父亲不是经常有空,奶奶会逮着机会让堂哥也上手砍。她站在屋檐下,紧皱眉头,手搭凉棚指挥道:“那边也砍了,不要了,别留着。”
一个周日,我照常去奶奶家,一进门,天井里有一棵光秃秃的树干直愣愣地立在那儿,顶上露出的黄白色尤其显眼。我站在门口都忘了进门,过了漫长的两三秒钟才想明白,无花果树的树冠被整个砍掉了。我一直以为它只会被砍掉多余的枝叶。
无花果树的树干与房屋的石头墙、天井的水泥地面灰成一体,灰得沉静。它成了被夺去头颅与臂膀的石雕像,只剩残损的身躯,其凝固的空寂讓人窒息。这个时刻是无花果树最痛苦的时刻吗?我无法知道。人类与一棵树的悲欢无法相通。
小的时候,从来不知道:变化是生活永恒的主题。
无花果树好像又成了它刚来天井时那副一无所有的样子。
很快,无花果树颇为光滑的树干被钉上钉子,挂上了篦子、笤帚。
麻雀的叫声变得遥远,蜜蜂、马蜂、苍蝇的踪影难以寻觅。倒是蚂蚁还在上面爬,有些火急火燎的样子,不过也不是成群结队、浩浩荡荡的,而是形单影只,伶伶仃仃。
秋日的阳光洒落,无花果树会不会下意识地伸出幻肢、摊开手掌,企图像从前一样去接住泼洒下来的阳光,颠来颠去,把光点溅得如水珠般四处散落呢?
北风吹来,白雪落下,无花果树已经不能再为它们提供休憩的角落。树干下端从被砍前就裂开一条的口子,露出了里面黄中泛红的韧皮部,这口子越来越大,看起来更加显眼。无花果树好像已经不再是印象里那么笔直挺拔,它向前倾斜着,腰有些弯,背有些驼,好像随时都会一头栽倒。
我默默地猜想:无花果树大概挨不过这一年的风雪与寒霜了。或许不久后,它就会被连根拔起,砍砍劈劈,扔进炉子里当柴火烧了。
不过,无花果树从来不按我猜想的道路去走。
第二年春天,无花果树被斧子砍过的部分竟然伸出直直的细枝,生出几片小花似的嫩叶。后来,树干底部也吐出小枝芽,像吐出一汪绿水。
无花果树正在制造一个新的春天。
它没有沉默,没有自暴自弃。它依然拥有十年前的冲劲,用生命的顽强呈现出不可忽视的绿意。这重新钻出来的细嫩枝叶,仿佛是佛像身上佩戴的璎珞与帔带,头颅与臂膀已无法修复,但仍能让人想象出它曾经繁丽与华美的神韵。
无花果树以这种清峻的姿态又生长了许多年。
上大二的时候,村里拆迁。那一年是不消停的一年。
天井里的很多东西扔的扔,卖的卖,租客们陆续搬出另寻他处。奶奶也被带离这住了几十年的平房,走出这个天井。最后空荡荡的,只剩下房子的墙体和天井本身。
拆迁的话,一切都要被推倒,当然包括无花果树。
那个时候我在外地上学,没有见证这历史一刻。我也不知道无花果树最后的样子如何,是先被砍倒,还是直接被推土机推平,又或是被倒下的房屋砖块砸倒?它会一下子倒下吗?如果不是的话,那它岂不是要受好多苦?
无论是哪种方式,我想它都会直着倒下。因为它是直着生的,所以它也会直着死去。
无花果树最后在拆迁款里还出了力。它折成了二百块钱。
去年搬新家,母亲又种下一棵无花果树苗。那纤弱的树苗让我不可避免地想起曾经的那棵无花果树。这株小苗从一开始就长歪了,再怎么拉扯也没有用。后来母亲索性不管了,任其自生自灭。
不知道这一次,又是一种怎样的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