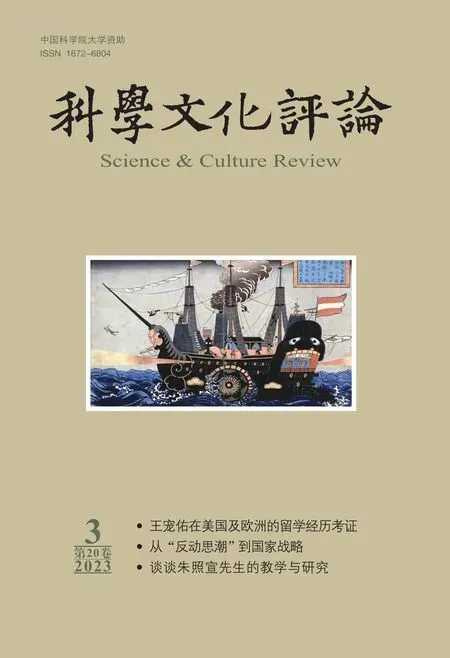博物学视野下的《本草纲目》评卡拉·纳皮《本草:李时珍与近代早期中国博物学的转向》
2023-10-13李建
李 建
国外汉学家对中国科学史与博物学史的传统的关注似有延绵不断的趋势,近年来,更是有不少被译为中文出版。2015年,吴秀杰、白岚玲译的《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出版后,在国内引起了江晓原、张学渝、龚俊文等学者的关注,并提供了一个国外学者研究晚明技术知识的新视角。明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刘黎琼译的《本草:李时珍与近代早期中国博物学的转向》(图1,以下简称《本草》)同样也以明代作为大的历史背景,两者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差异,都为揭示明代技术知识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图1. 《本草:李时珍与近代早期中国博物学的转向》书影
该书作者卡拉·纳皮是一位加拿大的学者,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中国史,现在匹兹堡大学人文联合中心任主任,曾学习古生物史和科学史,对近代早期的中文与满文文本有极大兴趣。该书题为TheMonkeyandtheInkpot:NaturalhistoryanditstransformationsinearlymodernChina,中文直译应为《猴子与墨汁:近代早期中国的博物学知识与转向》,原题用有趣的个例命名,从而吸引读者的关注,是西方专著命名的一个特点,这与中文专著中擅长于从整体内容的归纳上命名有很大的不同。而译者则根据全书内容,将标题转译为《本草:李时珍与近代早期中国博物学的转向》。转译后的题目更能体现全书的内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遵循了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更有利于阅读中译本的读者接受。另一个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作者在题目中使用的Modern China一词,即近代中国。与国内史学界公认的历史分期的有出入的,中国的近代史分期开始于1840年,明代属于中国的古代社会分期,而卡拉·纳皮将明代视为中国的“近代”,显然是不符合国人的思维习惯的。这就涉及到世界史观与中国史观指导下的历史分期的问题。在世界史分期中,近代史肇始于地理大发现,即大致从1500年开始,而书中所论述的时间正是16世纪之后,所以是符合世界史观中“近代”分期的。卡拉·纳皮将明代技术知识的发展置于全球发展的视阙,具有宏观的眼光,故被译者保留了下来。在对书名有一个好的理解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掌握该书各部分的内容。
一 卡拉·纳皮《本草》的主要内容
该书正文部分共有六章,附有前言和终论,在二、三章之间有“插曲”部分。前言以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小说《想象的动物》(TheBookofImaginaryBeings)中“嗜墨的猴子”为例子开篇,是一个想象式的情境,也引出了“好奇”驱动博物学发展的主题。终论部分讨论的是后世对于李时珍博物学思想的关注以及对《本草纲目》著作的传承和发展。“插曲”部分正好将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即李时珍的成长(一、二章),由李时珍的生平与《本草纲目》体例和内容的介绍(三至六章)。
第一章主要介绍作为一名博物学家的李时珍,对其完成《本草纲目》这样一部著作感到惊叹。对李时珍在事物秩序的构想到博物学方法的实践,再到本草学传统建立的过程进行了梳理,为对全文的理解提供了基调。
第二章主要分析李时珍的实践活动,即他探求博物学知识的方法论。首先是使用身体的认识,人是具有接受、感知、实践和反思能力的存在[1]。从“身体论”出发,也是西方人文主义视野下认识问题的重要方法。本章总结了李时珍观察自然时主要运用的“看”的方法以及对所“看”到的事物的真实性的反思。另一方面也梳理了李时珍对待前人文献的一个使用原则。
第三章是对《本草纲目》中,李时珍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学说——五行的分析,包括其构成形式与变化形态。说明了一些特例该如何对待。第四章讨论了“草部”中植物的命名、记录方法、效用与变化形态。介绍了“腹器部”是《本草纲目》在在本草学传统上的一个创新。第五章探讨了“虫部”,分析了李时珍怎样观察虫类以及他遇到的困难。在“虫”与变形一部分讨论中,昆虫形态的变化也体现了五行元素的背景。第六章则将视野转移到了兽与人的身上,“兽部”与“人部”布局在全书的后一部分,作者认为此部分中,李时珍对新的元素极为感兴趣,这也是作者的兴趣所在。将“人”置于自然界中理解,但又强调人与非人的界限,是明代知识文化发展中一个隐约出现的新转向。
该书的终论梳理了后世对于《本草纲目》的接受与研究,世界范围内的李约瑟研究;中国清代赵学敏的昆虫研究,现代“赤脚医生”广泛分布时期,对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的推崇。将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置于时代发展的潮流视野,肯定了其在医学知识探求方法与理论体系建立的进步性。
二 传统维度:李时珍与中国医药学发展
卡拉·纳皮无意于专门梳理李时珍的生平,更多关注其自然实践历程。作者既将李时珍视为一名医学家,也将他视为博物学家,体现了作者宏大的视野与对李时珍在探求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地位上的把握。
对于李时珍的研究,长期以来,学者关注较多的就是其医学成就,并将他与《本草纲目》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近来,虽然也有对其医学思想、生平活动的考察,但深入分析其探索传统医药学的实践活动及其驱动因素的却很少。
卡拉·纳皮从文化的传承中探析,李时珍的家族有着深厚的儒学与医学传统,李时珍成年后磨砺和拓展了他年幼时所接受的古典教育。他研究药物,是从观察他家乡的花鸟虫鱼开始的。蕲州城附近的自然环境是他研究药物学的天然大课堂[2]。李时珍对于辨识不寻常的动植物具有独特的眼光,并有自己的见解。如在植物分类时,他在按照从小到大分成五类的基础上,又根据植物的生长习性、栖息地或产地、气息香味等又细分为亚类别。
《本草纲目》引用文献卷帙浩繁,这部宏大的医学著作正是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然而,如何合理的使用前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开拓中医药的发展境地,亦是李时珍在撰写《本草纲目》的一大难题。与大多古代中医学家一样,李时珍认为,本草传统始于《神农本草经》,但其为人所知,是在陶弘景《本草经集注》问世后。直到明朝前期所涌现出的本草学专著,都是李时珍的涉猎范围。但他在参考前人的著作时,不是直接引用,更多是与其进行“对话”,李时珍与他们在自然万物及其在医学上的运用展开了长久的辩论,需要强调的是,他对诸多本草学专著的作者是十分尊重的。此外,李时珍并不满足于中国本土的自然物与医药学的记载,他大量涉猎文集、随笔、诗歌和典志甚至志怪故事来寻觅海外或境外自然物和药物的踪迹。
卡拉·纳皮在讨论《本草纲目》编撰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到了“权威文本”。西方历史学家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解释了何为历史学上的“权威”:别人接受那种陈述当做是真确的。那个相信的是历史学家,被相信的人就称之为他的权威[3]。李时珍相信了前文文献中某些资料,并将之运用在自己的著作中,如《本草纲目》的结构主要参照了宋朝的《证类本草》,它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证类本草》最初使用的引文形式。那么《证类本草》即是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过程中的权威文本之一。李时珍加入大量交叉引用,很可能依据了所做的阅读笔记,并在使用这些笔记内容时遵循了他本人的某种分类系统。
卡拉·纳皮虽然更愿意将《本草纲目》中所呈现的知识称为博物学知识,但并没有否定它在医药学上的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他充分肯定了《本草纲目》与李时珍撰写中的作用:《本草纲目》是一个组织严密的自然知识帝国,李时珍既是建造者又是管理者。
三 博物学转向:知识生成与变化
卡拉·纳皮将《本草纲目》中的知识看作是博物学的知识,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点。那么这种博物学知识与医药学知识的观点相冲突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认识。
首先,这两种不同的视点源于西方和中国不同的知识发展体系与学科话语权。古代西方没有科学,西方科技史学者习惯于将古代学者对自然的认识归纳为博物学传统。而在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中总是分门别类的指出古代农学传统、建筑学传统、医学传统,但其与现代意义上的农学、建筑学、医学又不存在于同一个体系,所以不免显得有些龃龉。近来,有学者从目的论出发,将古代这些知识归纳为“实学”系统[4],即实学知识,这也是对古代知识的较为客观的认识。
其次,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角度出发,也可以理解这种博物学与医药学的角度并不冲突。工具理性,医药学强调的是实际功用,即《本草纲目》对于治病救人、药剂药方生成的作用,实际上是实用价值的认识;在价值理性层面,博物学则更倾向于一种内在价值的导向,即《本草纲目》所蕴含的对自然的认识,如对动物、植物以及其他自然物的认识。这种认识就更加清晰明了。
卡拉·纳皮是一名加拿大人,对中国传统医药学知识了解并不深入。所以,在理解这一知识时,很自然地从博物学视角出发。近来,随着国际科学史界博物学史写作的兴起,博物学史俨然成为科学史里的显学[5]。《本草纲目》在卡拉·纳皮博物学知识视点中,可分为产生和变化两部分。
产生层面首先面对的是知识的分类。从无生命的世界到植物生命、昆虫生命,到人类。体现的是一种尊重自然的物质形态,又可为我所用的观点。这种划分体现了李时珍对自然的认识,也影响着“辨症施治”的医学观念。将李时珍这种分类方法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是十分必要的。如很自然地与老普林尼的《自然史》相联系,他提出的“这个世界是大自然的杰作,同时也是大自然本身的化身”[6]。这与李时珍的分类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一方面是在这种知识内部元素的变化。面对这种被视为医药学文献中剥离出来的自然知识,卡拉·纳皮也运用了中国传统的一套思想理论,即气、阴阳、与五行的基本概念及其变化来叙述。这一运用其实并不是卡拉·纳皮的创新,薛凤在《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一书中,就认为:宇宙规制的基本单位是气,气无所不在,并可以被探知。不可见的气由阴和阳两个阶段构成,二者彼此相合,结果便是和谐。人周边不同的“物”和“事”,实际上是水、火、土、金、木五气的成分与合成[7]。卡拉·纳皮认为,李时珍将水、木、火、土等物质视为“气”的具象化。“五行”是支撑《本草纲目》里“变”和“化”的基础,它们孕育了变化,也孕育了万物。“阳”与“阴”则因“火”的表现,自然的遵循了光明与阴翳的基本划界。气、阴阳与五行理论与学说,是指导传统社会人们生产、生活世界观,影响深远。
四 余论
可以看到,在整部作品中,虽然卡拉·纳皮用了不少西方视点来介入研究,但也可以窥见其用中国传统观念来尝试解释的努力。无论从传统中医学发展还是更大的博物学视角,《本草纲目》的价值都是巨大的。2009年,卡拉·纳皮这部著作的英文原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也引起了国外汉学家的关注。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亚史系巴瑞特(T.H.Barrett)教授称赞卡拉·纳皮的这本书是按照极高的学术要求来构思和撰写的。并且进一步认为长期以来,西方汉学界缺乏对李时珍的了解和研究,而这部书正填补了这一空白。卡拉·纳皮综合广阔的知识领域与巧妙的写作手法,其中也展示了她个人个人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8]。宾夕法尼亚大学学者纳坦·西文(Nathan Sivin)认为这本书是对当今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的经典之作的全新审视。它描述了它的内容和历史效用。更进一步说,描述了作者李时珍如何利用自己时代思维和世界观,在他的书中重构了周围自然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展示了如何利用这些知识来看待人体及其健康知识[9]。可以看出以上两位学者都认为卡拉·纳皮展现了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的另一面,带来的是全新的认识。普林斯顿大学费德里科·马尔康(Federico Marcon)认为卡拉·纳皮的著作是一本备受期待的专著,它填补了前现代东亚科学史学的空白。李时珍《本草纲目》对东亚文化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构成了东亚后来产生的所有药理学发展的基础,并激励了近代早期日本蓬勃发展的自然史领域。但同时他也认为卡拉·纳皮通过将《本草纲目》的“本土化”认识论运用到明代中国的语言、制度、实践、决策等的规则和真理主张中,成功地揭示了现代东亚早期知识交流的“推理风格”与其背后的逻辑[10]。是对此书在知识生产史方面的进一步挖掘。
由于近年来国外汉学研究成果日益丰硕以及中文版推出较晚等原因,此书在哈佛出版后,没有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关注,反而在同受《本草纲目》影响的韩国学界引起了讨论。延世大学人文社会医学专业学者薛英亨认为卡拉·纳皮关注到了过去《诗经》和《尔雅》的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发现了植物、动物以及其他许多事物的自然史与医学特征相结合,构建了自然世界中李时珍在此一方面所做的努力[11]。威斯敏斯特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东方医学研究中心的韩国籍学者徐素英认为:卡拉·纳皮笔下的李时珍不只是对自然界完整秩序的探索,或是以此为基础的世界观的构建。这也是对这种万物无限变化的形态持一种感兴趣的态度。徐素英得出结论,自然世界的本质不等于一元的、普遍的中国式知识框架[12]。韩国在古代社会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两位学者从文化产生的内在机理分析也就不足为奇。
卡拉·纳皮的《本草》突破了我们传统认识中《本草纲目》只是一部医药学著作的认知,将其定位为一本包罗自然万象的“百科全书”。正是这种涉猎广泛的博物学知识,推动着中国传统医药学的发展。卡拉·纳皮的《本草》为海外“中国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博物学”的视野。译者刘黎琼倾注了较多时间与心血,将这样一部视野独特、可读性强的国外专著展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无疑是为当前中国传统科技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正是像以上两位学者兢兢业业的治学态度,才能不断推动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取得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