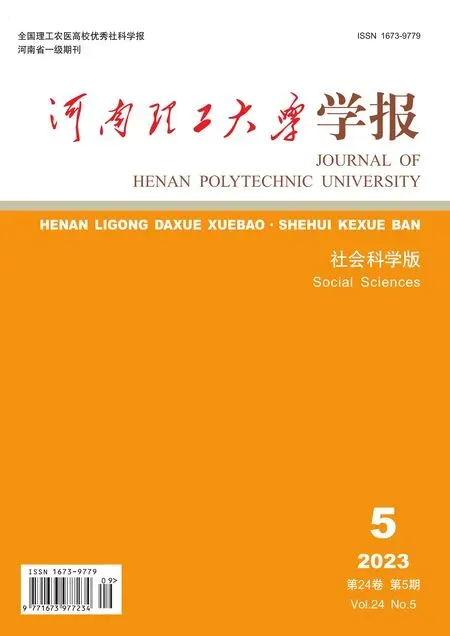明清南北官话用词差异管窥
——以《白姓官话》和《老乞大新释》特用方言词比较为例
2023-10-11张海媚
张海媚,李 俊
(河南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明清官话存在南北之分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清人已意识到南北官话语音上的差异,高敬亭《正音撮要》云:“既为官话,何以有南北之称?盖话虽通晓,其中音、声、韵仍有互异,同者十之五六,不同者十之三四。”时贤对其南北用词差异已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如张美兰利用域外汉语文献研究了清末汉语南北官话的词汇特点[1];陈明娥通过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考察了南北官话的用词差异[2]等,前述成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范式并奠定了基础。不过想要全面了解明清南北官话文献的用词差异需要更多的个案探讨,基于此,我们以成于18世纪中叶的南北代表性官话文献《白姓官话》和《老乞大新释》为例,通过比较二书特用方言词的使用情况来管窥清代南北官话用词差异。另外,明清北南官话之争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然而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致力于语音或文史方面,前者如陈辉(2015)[3],后者如姚小平(2020)[4],而从词汇视角关注者较少,因此我们在考察明清南北官话用词差异的同时尝试着探讨明清官话的南北之争。
《白姓官话》作为琉球人学习汉语的教科书,编写时间为乾隆十五年(1750年),关于其语言性质,虽有争议,但以南方官话者居多,如佐藤晴彦认为琉球官话的语言与下江官话(南京官话)的特征最为接近[5];濑户口律子考察了《学官话》《白姓官话》的语音特征,并将其与《汉语方言声调表 》进行了对照,发现它“和南京话相一致”[6];李丹丹、李炜认为琉球官话课本的“官话”是吴、闽、粤、客四大南方方言在“官话”层面上的投射,即南方官话[7];李炜等从语法角度证明琉球官话课本所反映的“官话”,是有别于北京官话的一种“南方官话”[8]。《老乞大》是朝鲜李朝时期学习汉语的教科书,通行的有四个版本,其中《老乞大新释》(不分卷)乃朝鲜边宪编,刊行于1761年,在现存的《老乞大》各本中,最贴近实际口语[9],大致反映了当时的北方官话[10]。综上,《白姓官话》和《老乞大新释》同为汉语教科书,口语性强,且同时异域,具有比较价值,不过限于篇幅,我们这里只考察二书特用方言词的使用差异。
《白姓官话》和《老乞大新释》都使用一批各自的特色词,其中有些应该属于方言词①
①历史文献方言词不易论定,我们借助大规模语料库尽可能全面考察一词在文献中的使用分布,大致界定其地域属性。,考察这些方言词的始末渊流,既有助于管窥二书方言背景的差异,又可以从南词北移和北词南移的时间节点管窥南北官话的竞争兴替。
一、《白姓官话》特用方言词例释
(一)[湾泊](船)停泊




综上,除《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外,明清时期“湾泊”多用于南方,将其视作南方方言词或无争议,《白姓官话》使用“湾泊”符合其南方官话的地域特点。公务文书《钦定平定台湾纪略》之所以使用或许和18世纪中后期南官话仍处于权威地位有关,故其词能入“官方文书”,且传继至普通话,《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收录“湾泊”一词可证,这为“普通话的词汇和语法实际上是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的混合体”[14]添一力证。
(二)[没干]没有用处


“三言二拍”编者冯梦龙和凌濛初为江浙(今江苏苏州和浙江湖州)人,带有一定的吴语色彩;《型世言》的语言性质为“白话通语+吴语+北方话”[15];《欢喜冤家》署名西湖渔隐著,作者的真实姓名及生平履历虽不可考,但书中所用方言,属于吴语系统,作者可能是浙江或江苏人[16];《比目鱼》作者李渔系浙江兰溪(今浙江金华)人。由检索到的用例来看,“没干”清一色地用于江浙籍作家笔下,属于南方方言词无疑,《白姓官话》使用“没干”符合其南方地域身份。《汉语方言大词典》“没干”条下注为“不好;不顶事”,显系“没有用处”的引申义,使用方言点为“吴语和闽语”。《现代汉语方言词典》未见收录。
(三)[夜饭]晚饭

考上述文献方言基础如下:《景德传灯录》和《朱子语类》均为南方官话方言文献[17];“三言二拍”和《型世言》都带有南方方言的成分,前文多述,此不赘;《都公谭纂》作者都穆系明代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其语自然带有吴方言色彩;《金瓶梅词话》主要反映的是山东一带的方言,但亦被学者证实带有一定的吴语色彩②
②见前述,此不赘。。《欢喜冤家》作者西湖渔隐主人真实姓名虽不可考,但因其故事多涉及江浙一带,且多用吴语词,故牛兰兰考证其作者应该是长期生活在江浙一带、相当熟悉吴语的人士[18]。显然,自宋迄明,“夜饭”多用于南方,当为南方方言词。清代仍以南方文献使用为主,不过北方文献亦见些许用例,详见表(一):
由上表可知,“夜饭”在南方使用的同时,亦开始向北扩散,《聊斋俚曲集》《情梦柝》《飞花艳想》《三侠五义》例皆可证,但总体仍以南方使用为主,这和其共时分布相映照,《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夜饭晚饭”条下,使用的方言点有“牟平、成都、柳州、绩溪、崇明、上海、苏州、杭州、金华、长沙、娄底、南昌、萍乡、黎川、南宁平话”,仅“牟平”系北方方言点,不过却说明了“夜饭”的北移;《汉语方言大词典》“夜饭晚饭”条下,使用的方言点有胶辽官话(山东荣成、牟平、烟台),中原官话(陕西汉中),兰银官话(新疆哈密),江淮官话(江苏东台、湖北红安、安徽天长等),西南官话(四川成都等、湖南宁远等、广西柳州等、贵州沿河),徽语(安徽绩溪等),吴语(上海、江苏苏州等、浙江金华岩下等),湘语(湖南吉首等),赣语(湖南浏阳、江西南昌、福建建宁、安徽怀宁等),客话(四川西昌),闽语(广东潮州),平话(广西南宁),土话(湖南临武),北方方言如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和兰银官话中“夜饭”的使用进一步证实了其北移的事实。
要之,“夜饭”当为南方官话方言词,《白姓官话》使用“夜饭”正和其南方官话的地域色彩相吻合,不过从其在明清北方文献及共时北方分布来看,“夜饭”北移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很可能在成于明嘉靖年间[19]的《金瓶梅词话》中已肇北移之端③
③《金瓶梅词话》中的“夜饭”有两种可能,一为南方方言词北移的产物,一为其带有一定吴语色彩的反映,但若一词(除《金瓶梅词话》例外)自始至终皆用于南方,可证《金瓶梅词话》用例或为其带有一定吴方言色彩的体现;若其后其他北方文献亦有使用,且共时亦南北皆用,那么,《金瓶梅词话》中的用例很有可能就是南方方言词北移的结果。。“夜饭”在宋代南方官话《景德传灯录》和《朱子语类》已见用例,为什么整个元代未见一例,直到明代才“大放异彩”,不仅南方用例猛增,而且开始向北扩散?这说明明代当以南系官话为主导,因为元代以大都为首府,南方方言词优势相对不易“发挥”,是以不用;明代建都南京,“强化了南官话的地缘基础”[4],故其方言词重振雄风并得以北移。
(四)[效脉]诊脉



表1 清代“夜饭”的使用分布
二、《老乞大新释》特用方言词例释
(一)[饽饽]面饼、饺子、馒头之类面食。也指用杂粮面制成的块状食物

综上,“饽饽”以北方使用为主,南方文献中的个别用例很可能是作者居北地时习染北词的结果,因为就“饽饽(波波)”的共时分布来看,仍以北方使用为主,《汉语方言大词典》“波波”条下,义项①为“(名)饽饽;馍馍;馒头”,使用的方言点有北京官话(如北京),冀鲁官话(如河北盐山、满城、南皮、新城、景县;山东济南、寿光),胶辽官话(山东即墨)。“饽饽”条下,义项①为“(名)圆形馒头”,使用的方言点有冀鲁官话(如山东寿光),胶辽官话(如山东青岛、平度、临朐、烟台、荣成、长岛、安丘、莱阳);义项②为“(名)馒头,卷子”,使用的方言点有东北官话(如黑龙江齐齐哈尔),冀鲁官话(如河北沧州),胶辽官话(如辽宁大连,山东牟平、蓬莱)。《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饽饽”条下,只有“牟平”使用。
综上,“饽饽”显为北方方言词,《老乞大新释》使用“饽饽”符合其北方官话地域特点。
(二)[歇凉]乘凉

①太原用“歇凉凉”。”。此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并收录了该词,俨然已成通语词。
综上,“歇凉”元代始见时或为北方方言词,元末明初向南扩散,发展至今已成通语词,《老乞大新释》用例显是沿自《原本老乞大》中的北方方言词用法。
(三)[嚼子]放在马口里的链形铁器,两端连在缰上,以便驾驭

①这里的“北”“南”是指“北南官话版本”。
《三侠五义》作者石玉昆系天津人,因为久在北京卖唱,多被误认为是北京人[31],不管天津还是北京,均属北方;《红楼梦》带有北京官话色彩毋庸赘述。就仅有的用例来看,《红楼梦》以前,“嚼子”毫无疑问多用在北方,不过19世纪晚叶开始南移,出版于1893年的南官话版本《官话指南》用例可证,由此可见,19世纪晚叶,北方官话应该已居于主导地位,其词向南扩散也便顺理成章。发展到今天,“嚼子”已成普通话词,《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即收“嚼子”一词;《汉语方言大词典》未见收录,《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嚼子”下,虽只有“徐州”使用,但我们调查了其他方言辞书中的收录情况,确证南北官话方言中均有使用,如凉州方言[32]、北京方言[33]、东北话[34]、安陆方言[35]、荔浦方言[36]、保山方言[37]等。
综上,“嚼子”在《红楼梦》以前主要用于北方,《老乞大新释》使用“嚼子”符合其地域特点。
(四)[多站]多早晚
检及文献,“多早晚”最初多用于元杂剧中,白朴《裴少俊墙头马上》2例、宫天挺《死生交范张鸡黍》1例、关汉卿《钱大尹智勘绯衣梦》1例、李寿卿《月明和尚度柳翠》1例,刘唐卿《降桑葚蔡顺奉母》1例,秦简夫《东堂老劝破家子弟》1例,石子章《秦修然竹坞听琴》1例,王实甫《四丞相高会丽春堂》1例,王晔《桃花女破法嫁周公》1例,武汉臣《散家财天赐老生儿》1例、《包待制智赚生金阁》2例,张寿卿《谢金莲诗酒红梨花》1例,郑光祖《梅香骗翰林风月》2例,周德清《越调·柳营曲·有所思》1例,无名氏《诸葛亮博望烧屯》2例,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1例,无名氏《包待制陈州粜米》2例,无名氏《都孔目风雨还牢末》1例,无名氏《冯玉兰夜月泣江舟》1例。
白朴,祖籍隩州(今山西河曲附近),生于汴京(今河南开封),后迁居真定(今河北正定);青壮年时期也曾游历过九江、岳阳、扬州、杭州等南方之地,但久居之地为山西忻州、河北真定;宫天挺,大名开州(今属濮阳)人;关汉卿,时贤多考证为“解州(今属山西)人”[40];李寿卿为太原人,《录鬼簿》载其曾做“将士郎,官县丞”,生平不可考;刘唐卿,《录鬼簿》称其“太原人,皮货所提举”,孙楷第考证“提举”当作“提领”[41],生平事迹不详;秦简夫为大都人,经常往来于杭州和大都之间,故《录鬼簿》记其为“见在都上擅名,近岁来杭回”;石子章、王实甫均系大都人;王晔,杭州人;武汉臣,济南府人;张寿卿虽为今山东东平人,但做过“浙江省掾”,《录鬼簿》载:“张寿卿,东平人,浙江省掾吏。”郑光祖,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人;周德清系高安(今属江西)人。由上述文献作者籍贯来看,除元末明初的王晔外,显然多为北方。而且明清时期,“多早晚”仍以北方为主,如带有山东方言色彩的《金瓶梅》(崇)1例,带有北京话色彩的《红楼梦》(120回)33例和《儿女英雄传》5例,南京官话版《官话指南》1例。综上,只有王晔《桃花女破法嫁周公》和《官话指南》(南京官话版)例用于南方,许是北词南移的结果,余皆用于北方。

写作“多昝、多喒、多偺”者,均始于清代,且用于北方,“多昝”,《醒世姻缘传》24例,《霓裳续谱》2例;“多喒”和“多偺”都只见于《官话指南》(北京官话版),前者13例,后者1例。
综上,从使用地域来看,“多早晚”“多咱(昝、喒、偺)”当为北方方言词,和“这咱晚”“那咱晚”使用地域一致,“‘这咱晚’‘那咱晚’等,是《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等某些明清文学作品中经常用到的一组指示时间的词语,带有浓重的北方方言色彩。”[43]《老乞大新释》使用“多站(多咱)”符合其文献地域特点。不过“多早晚”19世纪晚叶开始向南扩散使用,南方官话版《官话指南》例可证,这再次证明北官话在19世纪晚叶应当已占优势地位,故北官话词得以南移,成为共时南、北官话均用的口语词,如《汉语方言大词典》收录了“多咱”和“多早晚”,前者义项②为“什么时候;多早晚;多会儿”,使用的方言点有东北官话(如黑龙江哈尔滨等、辽宁沈阳等、吉林长春等),北京官话(如北京等),冀鲁官话(如天津,山东利津等,河北雄县等),胶辽官话(如辽宁大连等),中原官话(如河南南阳等、山东枣庄等、江苏徐州等),晋语(如山西文水、河北阳原),江淮官话(安徽嘉山,江苏镇江),西南官话(贵州赫章)。后者义项①为“什么时候”,使用的方言点有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如河南鄢陵)和江淮官话(如江苏南通、如东)。《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42个方言点中使用“多咱”的有“哈尔滨、济南和南京”。
三、结 语
明清南北官话的语言差异及竞争嬗变除了能从语音和语法角度进行考察外,从词汇视角也可窥之一斑,本个案通过南北代表性官话文献特用方言词的使用差异说明了这一点,详见下表。

表2 南北特用方言词现象
由上表可知:第一,明清南北官话用词差异显著,南用“湾泊、没干、夜饭、效脉”等南方方言词,北用“饽饽、歇凉、嚼子、多站(多咱)”等北方方言词,南北差异昭然若揭。第二,通过比较南北官话代表性文献用词差异可管窥南北官话的嬗变。“夜饭”始见于宋代南官话方言文献,元代未见,明代重新兴起并北移,说明有明一代可能以南系官话为主导,故其方言词得以向北扩散;而且直到18世纪中后期,南官话应该仍具有一定的威力,如“湾泊”于此期可入“官方文书”便可证之。另外,北词南移或发生在元末明初,或发生在19世纪晚叶,这说明元代以大都为首府,其基础方言处于权威地位,藉此,方言词得以南移;不晚于20世纪,北方官话在与南方官话的竞争中再次占优成为权威官话,故其词得以南移,这和张卫东从语音角度[44]、姚小平从文史角度[4]证实19世纪中叶以来北官话已然胜出的论断有可资互证之处。第三:普通话词汇是明清南北官话词汇的聚合体。南北均有传承至普通话的方言词语,如南官话词“湾泊”和北官话词“歇凉”“嚼子”,这为“现代汉语普通话词汇系统的基础部分,是南系官话和北系官话的融合”[45]论断提供了例证支持,证实了普通话和明清官话的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