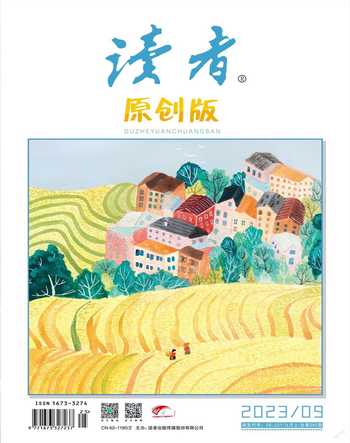我妈的重启人生
2023-10-11蛮像个小孩
蛮像个小孩

初夏的早晨,打电话给我妈,问她在做什么,她冷哼一声,话里有话:“打扫卫生!”她前天晚上抵达老家,到家后就睡了,起床后才发现家里乱成狗窝一般,这会儿正在气头上。
“嚯,你不晓得有多乱!”我妈的嘴架起“机枪”,“成堆的衣服摞在椅子上……窗户大开,到处都是灰……厨房的灶台可以拿小刀刮出一层油……我气得胸口痛!”
我妈去年10月初到成都过冬,整整8个月未回家,这期间我爸喜提单身汉生活,天天在外潇洒,对家务不闻不问。按理说,我妈回去之前他应该紧急收拾一番,只是这次我妈决定回去时他正好出差,后果可想而知。
我妈并不是主动选择8个月不回家的。2022年年初她做了一场手术,1/3的肺被切去,出院后,平日多走点儿路都喘得不行,更别提应付冬春寒冷的空气了。
手术导致的身体变化只是其一,事实上,2022年是我妈的“大考之年”,她先后经历了手术、退休、被骗3件大事,其间又穿插了数件不可忽视的小事,变化涉及的范围之广、发生的频次之密,让她几乎无法喘口气。
在这一年的应对中,她展现出坚强,展现出倔强—这是我能预料的部分;然而在这一年里,她也变得开阔,变得舒展—这是我不曾期待过的意外之喜。
不夸张地说,她的人生好像重启了。
一切都得从那场猝不及防的手术说起。在单位组织的例行体检中,我妈查出一个不太妙的结节。元旦后入院手术,从体内取出一颗不小的瘤,万幸还是早期,切除约等于治愈。之后是长达半年的康复期。
我妈在患病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坚韧让我震惊:住院期间她没有当着我的面掉过一滴泪;能自己做的事绝不麻烦我,伤口再疼也生忍着;术后隔壁床用了好几支止痛针,她一支都没用。
至今我还常想起两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发生于我妈术后第二天的中午,我们拿到了术中病理报告,“癌”字犹如当头一棒敲了下来,我们仨将床帘拉起,进行了一场艰难的家庭会议。
“嗐,没事。”我爸说。那段时间他好像只会说这句话。
“手术前你就说没事,现在傻了吧?”我妈语调平稳,竟还有心情嘲讽我爸。
“你不要多想。”爸爸说。
“我没了就没了,”我妈瞥了我一眼,“就是担心老母亲和我女儿……”
“还说没多想!”我心里难受,大声呵斥她,“尽说丧气话!”
我妈笑了,一脸不在意:“坦然面对,接受命运。”
另一个场景是某天傍晚,我俩在病房的楼道里散步,我举着输液杆,她提着引流管,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我以为你会哭。”我没忍住说。
“哭能解决问题吗?”她轻蔑地笑了。
“不能,”我认真看着她的眼睛,“可是能缓解不好的情绪。”
她没说话,径直走回病房。
我妈唯一的一次崩溃发生在康复期。某天半夜,她被伤口疼醒,把我递过去的止痛药一掌打翻在地,哭喊着:“你们非说没事,就骗我吧!骗得你们自己都信了!”我捡起药,呆站在角落,看着她因为疼痛蜷成一团,我却什么也做不了。我像是被抽去了全部力气,滑坐在地上。
我们没有骗她,只是她需要时间接受现实并消化它,接受这源于体内但蔓延至生活方方面面的变化。这个过程没人能帮她,她得自己蹚过汹涌的变化之河。
随着疼痛的减轻和体力的恢复,以及对相关医疗知识的学习,我妈开始相信“坏东西”是真的离开了她的身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一劳永逸”,相反,我妈变得无比惜命。
生病前,我妈不喜欢医院,甚至可以说害怕医院,有了什么病痛最多去诊所或中医院开点儿药调理。现在她也不喜欢医院,但能硬逼自己去,今年甚至主动做了CT,又做了全身检查,吃该吃的药,忌该忌的口,渐渐地,人胖了起来,气色也好了。
从前我费心费力没能让她做到的事,一场手术令她做到了。这或许就是福祸相依。
现在她甚至可以用这件事开玩笑:“依我对这几家医院的熟悉程度,完全可以去当陪诊师嘛,专门陪我们这种从小地方来成都看病的人挂号、问诊、取药、复查,一条龙服务。”
我妈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大概是因为她退休了。原本还可以再干两年,因为生病,她接受了单位分配的提前退休名额。令人意外的是,我妈居然没有退休综合征—从维持了几十年的状态里剥离出来而产生的迷茫和无助—她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做健康美食,看电视剧、热门综艺,独自或是和朋友一起四处游玩,疯狂拍照并制作视频—她的视频做得比我好。
她和朋友分享自己的感受:“我觉得退休了好舒服哦,再也不用操心工作上的事,每天睡到自然醒,散散步养养花,太安逸了!”
但也有一些不安逸的事,比如我妈被骗去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财。具体怎么发生的,我就不详述了,毕竟我妈评价自己在这件事上的表现是“好丢脸,好瓜(方言:傻)”。我得维护她的面子。
但我想讲讲事后她的反應,她又一次震惊了我。确认事情发生后,我第一时间给我爸打了电话,我们的对话主要集中在对我妈的担忧上,那时候她身体刚刚恢复,我们生怕她遭到太大的打击。
结果人家淡定得很,处理完事情已经是晚上8点,回家给自己煮了碗面,说:“要不然呢,气得吃不下饭,把身体也搞垮?”
“那你气吗?”我问。
“还是气啊,晚上都没睡着,”她说,“眼睛一闭就是那些东西。”
“我们很担心你。”我说。
“怕我想不开啊?”她张口就是一个“地狱笑话”,“跳到梭磨河里头?放心嘛,不会。”
我哈哈大笑,认认真真地放心了。
生病、退休、被骗钱,我妈闯过一关又一关,或许是因为密集地接受了生活的考验,她对很多事不再计较了,脾气好了很多。最重要的是,她终于把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了自己身上。
我妈生性内向且敏感,朋友不多,又常住在我们那座人口刚过万的小城,交际圈子极小,没什么新鲜事儿,因此我和我爸理所当然地成了她注意力的承接者、情绪的发泄口、存在感的构筑器。
有时候,我觉得我妈像一面镜子,通过我和我爸在镜面中的反射“看见”自己。有一回她和我们闹别扭,我一周没去哄她,后来她拉下脸跑来跟我道歉。她说,以为我们都不管她了,她很难过。她几乎是哭着问:“谁看到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谁看到我了?”
我听了这话非常难过,我不愿让她做一面只能反射别人的镜子,或者说,我不希望我和我爸是她这面“镜子”中唯一的对象—“唯一”这个词太可怕了,一旦失去,崩塌的就是全部。
但是—很开心这里能用上“但是”这个连接词—2022年,我妈不靠我和我爸,也能看见自己了。她正在靠近我一直鼓励她、希望她达到的状态—“妈妈,我希望你以后的人生能为自己而活”。
她买了无人机,夏季的每个月她都有旅游计划,按部就班地调理身体,和外婆和谐地相处了两个月(从前她们在一起待两周必吵架)……但最让我快乐的,是她不再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了。
刚辞职那年,我告诉她和我爸,自己打算靠摄影和写作过活。她和我冷战了两个月,才勉强接受这件事,但在之后还是触发了多次争执。我妈拼了命要将我拉回到“正道”上,我却像头蛮牛,根本拉不回来。
原本我以为这种痛苦的较量会持续很长时间,但在她“重启人生”后,她一日比一日开明,先是转发我的文章到她的微信朋友圈(虽然转发的评论中充满无奈和不满);后又平和地接受了我从家里搬出去的决定;慢慢地,我可以和她倾诉工作中遇到的趣事和困难,她则从她的角度给出建议;再后来,她频繁地转发我的作品,几乎是每发必转;现在已直接“进化”到为我吆喝、打广告,请求朋友们转发……
她正在放手。
因为她的放手,我可以更勇敢、更投入地做自己喜欢的事。她放开的那双手,好像撑在了我的背后,推着我心无旁骛地往前走;从前那条束缚我的“脐带”,如今成了让我依靠的“安全绳”。
我和我妈好像在一条小溪的两岸,她在那岸,我在这岸,我们走在各自的路上,但又能随时看到对方;若是想念了就来到岸边,乘上共有的小船,度过一程轻盈饱满的时光……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
行文至此,我真心感激让我妈重启人生的2022年,虽然她可能不想感激,因为受了太多苦。
我又想到我妈出院那天,我在醫院外的街上暴走,等待我爸传来我妈最后的大病理报告。上午9点半,我爸发来信息:“完全没问题了。”
我在马路上号啕大哭。
我对我爸说:“命运给我们提醒了,以后要谨慎,要平和,要从头开始。好的坏的,我们一起经历。”
他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