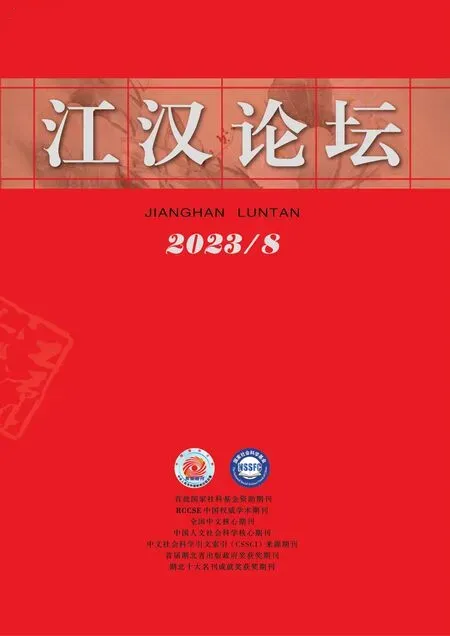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文化根脉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多维透视
2023-10-08黄雄义
黄雄义
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必须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自主知识体系,应彰显鲜明的传统文化底蕴,坚持历史与现实相贯通、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得益于中华法系数千年的绵延发展,我国自古便积淀了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其中蕴含的法律概念、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法律理念和法律价值,构成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直接文化渊源。作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多有传承与发展。这为我们准确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提供了多重维度,也为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如何融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指明了路径方法。
一、本体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内涵
任何一项事物,都涉及一个本原问题,即“是什么”的问题。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首先要面对的亦即这一根本问题。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对复杂,它既是一个颇为时髦的政治概念,带有特殊的时代意蕴;又是一个复合型的法学概念,由“中华”、“优秀”、“法律文化”等多个基础词汇共组。只有彻底释除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什么、主要由哪些内容构成或体现为何种形式等疑惑,准确知悉所要传承的对象,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发展、运行和传承。
习近平法治思想着重强调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可从内容和效力两个方面来解读。在内容上,主要是指法律思想、理念和价值。“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1)。这清晰表明,优秀的法律思想和理念,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主体构成。至于《唐律疏议》等古代的代表性法典,并不是将其排除在法律文化之外,而是因为“法典背后有强大的思想运动”(2),本质上仍属于法律思想、理念和价值的制度表达和外在体现。在效力上,具备文化的指引性功能,潜在影响着国人的法律思维和法律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3)。这实质上强调的是文化的功能和效力,它必须具备现实影响力和客观约束力。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所涉及的“法律文化”,主要是指具有文化指引性功能的法律思想、理念和价值。
在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律文化”所指后,还需注意附加在前的三个限定性条件。这些限定性条件,从主体、品质、时间等多个层面划定了清晰的界限,将不应纳入本体范畴的各种法律文化阻隔在外,深刻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益求精。
其一,主体限定,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而非其他民族的法律文化。“中华”代表中华民族,包括汉族以及所有少数民族在内,是“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4)。汉族法律文化之厚重自不必言,少数民族也为中华法律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回顾数千年历史,鲜卑族、契丹族、党项族、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均曾建立起政权。他们大多选择将立足本族惯习与仿照汉族成法相结合,不断为中华法律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元素,清律“详绎明律,参以国制”即是典型样例。其他少数民族亦创造了多彩独特的法律文化,如瑶族的“石牌制”、壮族的“土司制”等制度中蕴含的优秀法律思想、法律观念和法律价值。那些认为“汉家独大”、少数民族在法律方面乏善可陈的观点,无疑是片面和错误的。正如学者指出的,“在中华法系和中华法律文化共同话语体系的创造过程中,不仅有汉族同胞创造的诸多果实,各少数民族勇于引进、善于发展、积极传播汉族成果的贡献同样功不可没。”(5)其二,品质限定,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优秀的而非低劣的法律文化。事物有正反两面之分,法律文化也有优劣之别。新时代要传承弘扬的,不是传统法律文化的全部,而是限于优秀的、积极的、有益的精华部分,像封建专制那种文化糟粕自当犹弃敝屣。何谓优秀?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6)。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其实暗含着一套全面且严格的筛选标准。“跨越时空”突显的是稳定性,要求其经得起时空变化的检验;“超越国界”突显的是普遍性,要求其不管在哪个国家都将获得认同;“富有永恒魅力”突显的是持久性,要求其魅力不会伴随时间推进而弱化或变质;“具有当代价值”突显的是功能性,要求其对当代法治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四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三,时间限定,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传统的而非当代的法律文化。一个民族的发展,总是会经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每一个阶段,其在社会经济结构、国体、政体、制度等方面都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对应孕育和发展的法律文化也归属于不同类型。毕竟,“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7)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发展繁衍,积淀的法律文化也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这其中,既包括在传统社会积淀而成的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也包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年代创造的红色法律文化,还包括在建设、改革过程中创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属于传统的维度,时间坐标位于“我国古代”。这并不是奉行文化保守主义来以古非今,而是文化新创主义的“不忘本来”。相较于传统法律文化的“过去式”而言,当代法律文化是“进行时”,目前仍处在一种不断建设和持续积淀的开放状态。
综合对“法律文化”概念的理解以及对三个限定性条件的解读,可对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作一个基本界定,即中华民族在传统社会中积淀形成的,厚植国人内心的,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法律思想、法律理念和法律价值。若具体到其中的代表性内容,可谓相当丰富,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等内容,皆属其列。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融入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积淀的优秀法律文化,首要即在于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内涵,将其核心内容抽象和总结出来,使其在法学概念、思想、理念、制度等多方面发挥出辐射效应。
二、发展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淀形成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能有今日所见之深厚,非一朝一夕之功,其形成、发展、淬炼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它依托于中华法系,伴随中华法系的数千年演进而不断孕育、积淀和完善,属于中华法系的文化投影。历史上的王朝迭代虽赋予了中华法系一个相对清晰的历史发展图轴,然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淀之路更为繁复。二者的关系就如同果树和果子的关系,中华法系是一棵参天的果树,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则是果树上所结出的一颗颗绚丽果实。果实虽萌生于果树,但具有明显的独特性,每颗果实的发育位置、生长周期、体积大小乃至甜度高低也互不相同。概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非某一项法律制度,也非某一种法律思想,既不是某一个法律机构,也不是某一部法律典籍,而是一个包含着传统中国社会历朝历代优秀法律思想、法律理念和法律价值的大型“文化门类”。这些法律思想、理念和价值之间,可能存在着或显或隐的联系,但又是相对独立的。对于这样一种融汇多种元素的集合体,注定很难从整体上对其积淀形成的过程予以全面呈现,只能另辟蹊径,择取其中的典型代表,走“局部映射整体”和“微观印证宏观”的道路,应是科学选择之一。可通过“解剖麻雀”,耙梳某种相对具象的法律思想的发展历程,以之佐证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淀之路,从而达到“窥一斑而知豹,落一叶而知秋”之效果。
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为例。民本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梁启超曾将民本主义列为我国政治思想的三大特色之一,(8)足见民本理念的文化根源之深和历史地位之高。早在先秦时期,民本理念就已备受推崇。《尚书·五子之歌》有载:“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9)这不仅强调了统治者对民应持的基本态度,还点明了民在邦国之中的根本性地位及其与邦国安宁之间的密切联系。周公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保民”和“惠民”思想。其中,“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要求君王小心谨慎、勤于朝政;“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要求深入了解民之疾苦,施加恩惠;“以万民惟正之供”,要求君王为万民的事尽心尽力。(10)《周礼》中以“国危”、“国迁”、“立君”三事询万民,即是一种制度践履。之后,孟子从多个方面丰富了民本理念:一是作出了关于民、君、社稷先后次序的著名论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1);二是界定了天下、国、家、身四者之间的核心关联,“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2);三是借助夏桀、商纣的事例将天下得失的原因归结于民心得失,“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13)。及至秦汉,贾谊论述了民本的横向宽度与纵向深度,强调民既是国本、又是君本、还是吏本,而且应当守之以恒。“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夫民者,万世之本,不可欺。”(14)伴随历史车轮往前推移,民本理念未停下前进脚步,其内涵不断得以充实。唐太宗提出“存百姓”的思想,认为损害百姓的利益无异于自食其肉的自杀性行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15)宋代朱熹释解了先哲们的论点,认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16),并围绕这一思想提出了“使民有常产”、“爱民如子”、“爱民必先于节用”、“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等一系列实践要求和治国举措。正是传统社会数千年来对民本理念的一以贯之与持续完善,才使得它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里的一颗璀璨明珠。
通过梳理个别法律理念和法律原则的发展进程即可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不断的法制理论探索和实践锤炼中日积月累而逐渐形成的。其包含有诸多内容,各项内容之间彼此虽有联系,但基本意蕴、发展阶段、主要人物、制度体现、适用领域互不相同。很多法律思想、价值和理念在先秦时期就已萌芽和形成,此后又在历朝历代不断得以充实和完善。“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17)这其中,有赖于理论层面的论证、创新和突破,也离不开实践层面的落实、检验和变革。历史发展周期之长、参与推动主体之多、运用完善方式之繁,共同筑就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之深厚。这也为建构当代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指明了前行路径。其一,要充分认识到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是一个非一蹴而就的长期工程,需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发展规律,伴随时代的进步不断丰富其构成内容。其二,要擅于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归结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要素,这些法律思想、价值、理念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而在不同朝代有着不同的形式与内容体现,择其精华者而承之、择其糟粕者而去之方是科学的选择。其三,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应当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理论指引中升华规律性表达,在实践操作中发现问题并加以完善。
三、价值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发展,必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它见证了中华民族在法制领域的成长历程,能从法律层面充分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它又映射了中华民族在长期法制实践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积聚的治国理政经验具有突出现实价值。
(一)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决不照搬别国法治模式和做法的重要底气
“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19)近代以后,中华法系的影响日渐衰微,不少人希冀通过照搬西方法治模式来实现救亡图存。理想虽很丰满,结局却令人唏嘘。清末“钦定宪法”、民国“贿选宪法”等所谓的“法制故事”,即是强揉两种文化所导致的异变产物。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法律不应是千篇一律的机械重复或者舍我其谁的单项选择,而应呈现为千姿百态的葳蕤春景。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有一点要明确,我们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决不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走西方所谓‘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20)
中华民族的这种自信、底气和定力缘何而来?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拥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传统给予我们的正是开拓新的法律生活世界的强大信念,它召唤我们以自己时代的精神气质和价值选择去衡量、评估历史。”(21)历史深刻表明,中华法制文明是久远的,中华民族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通过制度来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最终建构起在世界法系之林中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中华法制文明又是独特的,中华民族对很多法治问题有着契合本土实际的独立思考,并在长期的法制实践中将这些思考转化为丰富经验和突出优势。相较于西方模式,民族自我孕育的中国式方式通常更为吻合,只不过受限于外部的话语权压制和内部的自我误解,无奈蒙尘而不为人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既能“强心”,让国人全面了解民族优势和特色所在,树立起我们完全有经验也有能力建设法治中国的坚定自信;又能“纠偏”,让存在偏见的国人自觉撇弃错误观点,认识到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治模式,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
(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滋养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开创了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伴随这项工程的持续推进,其中遇到的很多法治建设问题都可在历史图轴中找到相似的痕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自然就成了一把量身定制的“密钥”,能为现实法治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参考。两千三百多年前,秦孝公曾向商鞅表达了一个困惑:“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22)商君当年给出的答案里,很多智思妙想对于当今普法仍具有时代价值,“行法令,明白易知”即是其一。《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 年)》要求的“同步进行解读”、“生动直观的形式宣讲法律”,便与商君之意相契合。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以解决现实法治问题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考量,若结合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来看,客观上也蕴含着传承传统的题中之义。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就必然要在法治建设中赓续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是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法治体系”(23),要“不断完善法律规范、法治实施、法治监督、法治保障和党内法规体系,汲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24)。“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5)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民族养分成长起来的法治体系,才能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耳熟能详的内容、约定俗成的规则与法治的专业性融贯起来。否则,只能黯然沦入“亦步亦趋”的尴尬境遇,徒具其形而承载文化撕裂断层之重,断然不可称之为“中国特色”。
(三)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支撑
“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26)时处当今云谲波诡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占得先机的必由之径。于我国而言,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需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具体到法治领域,即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又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渊源。
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存在,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这将有力增强人民群众对传统法律文化的认同,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修炼好文化“内功”。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播,是向世界讲好中华传统法治故事、阐释中国法治特色的过程,这将让世界看到其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域外影响力,打磨好文化“外功”。2019 年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中国人历来讲求‘一诺千金’。我们高度重视履行同各国达成的多边和双边经贸协议,加强法治政府、诚信政府建设”(27)。这向世界表明中国自古就对诚实守信视若拱璧,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魅力,又为中国与其他国家法律文化的交流互鉴指明了重要方向,阐发了一个共同对话的基本向度。伴随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走向世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从“中国方案”里寻求破壁灵感。总之,“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8)如果丢弃了民族法律文化,在这一领域的自信心、凝聚力和向心力将深受影响,文化软实力亦将为之受挫。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多重价值,进一步证成了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过程中必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必要性。通过对本民族法律文化的传承,既能强化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又能充分诠释“自主”的内在含蕴,彰显法学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
四、运行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实践应用
“我们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规律,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世界法治文明有益成果,形成了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举措。”(29)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不能停留在闻之、见之、知之的层面,要将其切实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价值,也将其广泛应用至法治建设的实践场域,为新时代新征程如何应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塑造了现实范例。
(一)宏观应用:治国方式与法治道路的选择
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总是能妥善处理好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做到根本指引与具体举措良好结合。习近平法治思想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应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首先体现于宏观层面,主要含括对治国方式和法治道路的指引。这一类应用关乎法治事业之根基,为法治建设中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如何抉择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调,有力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使中国法治彰显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选择什么样的治国方式,是一个政党、一个政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法治,毫无疑问是当今世界最为主流的治国方式。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法治建设,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法治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法治、厉行法治,把依法治国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党和国家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这般对法治的执着和坚持,既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大势,也是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转化发展。我国古代不乏依法治国的思想积淀,诸如“万邦之君,有典有则”、“法者,天下之至道也”、“法者,治之端也”、“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等载述,无不彰显着古人对法制的推崇。思想指引下的治国理政效果,也以实践经验证成了法治的正确性。“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从我国古代看,凡属盛世都是法制相对健全的时期。”(30)除法治这一治国方式之外,中国共产党也注重将德治与之相配,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近年来,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入法入规、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等等,即是推行德法合治的重要表现。这种复合型的治国方式,既“科学地概括了道德和法的关系,体现了经典作家的一贯思想”(31),又源自于我国古代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和礼法并重、德法合治的治国思想。
既然将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那就需要思考走一条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对待这一根本性问题,“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32)。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再次发挥了镜鉴作用,启示我们找到了唯一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古语有云:“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3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即是由我国国情实际决定的,是在“观民族时俗”和“察时代国本”基础上作出的科学选择。而要真正走好、走稳这条法治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需要保持正确方向和坚强的政治保证。世界上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34)我国法治保持正确政治方向的核心密钥就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之魂。这在中国古代也能找到对应的法律思想支撑,是为“以道统法”。“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35)“道”虽不是“法”,却对于法的建设及其实施具有不可替代性,是“法”必须坚持的根本性原则。党的领导,正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
(二)微观应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全方位引领
“良法善治”,首要在于立法,确保治国之法质量优良。中华民族历来有着浓厚的尚典传统和丰富的法典实践。从先秦时期的《法经》,到之后的《九章律》《开皇律》《唐律疏议》,再到《宋刑统》《元典章》《大明律》《大清律例》,皆是成就四海之治的“一代之典”。法典事业的发达,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立法思想尤盈,这对当代科学立法的推进裨益颇多。比如,古人重视立法质量,主张“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36)。这启示我们坚持立法先行、追求良法善法,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立起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古人推崇“法与时移”,认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37)。这启示我们“法律体系必须与时俱进加以完善”(38),要结合社会时势即经济基础的变化来不断修改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有效调适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天然矛盾。现行法律中的很多具体条文,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近颁布的民法典,即是典型的“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 多年优秀法律文化”(39)的立法成果。
单单聚焦立法而忽视执法,再完备的法律亦是一纸空文,无法发挥出真正的规范效用。古人对法律执行视若至要,在执法方面积淀了诸多宝贵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诸如“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纵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等等,无不体现着法律执行之要。这些优秀执法文化对执法地位、执法作用、执法主体等普遍性要素的揭示,决定其之于新时代法治建设仍有借鉴价值。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也多次旁征博引古代的经典著述来阐释。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说明时,他就援引了“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和“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两句古文,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40)。当前执法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事实上也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牵引作用,颇有“日用而不觉”之韵味。比如,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时忠于法律,将个人情感的感性让位于法律规范的理性,这是对古代执法如山思想的传承;对于一些情有可原的特殊情况,在保证执法力度的同时融入执法的温度,这是对古代情理法思想的传承发展。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实践应用的重要场域。在司法理念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强调要坚持公正司法、司法为民,提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41)。其中蕴含的朴素正义观,在我国古代不乏对应的思想主张。两千多年前,管子有论:“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听治不公则治不尽理,事不尽应。治不尽理,则疏远微贱者无所告;事不尽应,则功利不尽举。功利不尽举则国贫,疏远微贱者无所告则下饶。”(42)言语之间指明司法不公的后果极其严重,将会触发国家治理失效、社会贫困、百姓含冤、秩序混乱等一系列连串反应,故而必须追求司法公正。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很多做法,其实都创造性地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以反腐倡廉为例,党的十八大以来,领导干部只要触犯了法律无论其职级高低,或经审判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或按党内法规予以纪律处分,有力说明“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在当代法治中得以赓续,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法律原则相辉映。
除立法、执法、司法之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推广应用到守法、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法治宣传教育等多个方面,为相关法治问题的解决指明了前行路径。比如,古人讲求以身作则,“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这启示我们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做守法的模范,带头遵纪守法、捍卫法治”(43)。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已经以多样的方式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方方面面,构成其重要的精神内核。
得益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也应基于其具体内容的不同向度,以合适的方式融入到法学知识体系的方方面面。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过程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绝非是简单的“复制”或“照搬”,必须是将其在当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场域中的再运用,使之与当代法学知识体系实现“形”与“实”的双重融合,在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中,“创造性转化”是第一步,要求结合时代背景从内涵和表达形式两个层面进行改造,实现“形”与“实”的双重转化,让原本已陷入沉睡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重新“活起来”。“创新性发展”是第二步,建立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要求结合法治建设的时代发展为其不断注入新的内涵,让已经“活起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动起来”,持续完善以扩大实际影响力。
五、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法治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必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把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同其相结合。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蕴涵,清晰指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淀之路,深刻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现实意义,科学回答了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切实应用于新时代的法治实践、如何在新的发展阶段进一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导向、强烈的历史担当和坚定的信心态度。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这场国家治理的深刻变革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不断挖掘、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将其转化发展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有机构成,深度渲染中国法治的中国特色。
注释:
(1)(20) 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求是》2021 年第5 期。
(2)[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李琼英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241 页。
(3)(17)(2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 卷,外文出版社2018 年版,第170、170—171、164 页。
(4)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4 期。
(5) 何勤华、张顺:《民族智慧的叠加:唐代中华法律文化的辉煌》,《法学论坛》2022 年第2 期。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 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0 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 页。
(8)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年版,序论。
(9)(10) 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369、254—258 页。
(11)(12)(13) 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24、150、154 页。
(14)[唐]魏征等撰:《群书治要》,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545 页。
(15) 骈宇骞译注:《贞观政要》,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1 页。
(16)[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7 页。
(18)《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3 页。
(19)(24)(30)(32)(40)(41)(43)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年版,第110、273、225—226、3、96—97、22、139 页。
(21) 赵明:《中华法系的百年历史叙事》,《法学研究》2022 年第1 期。
(22)(33) 石磊译注:《商君书》,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174、64 页。
(23)(29) 习近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求是》2022 年第4 期。
(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 卷,外文出版社2022 年版,第315 页。
(26)《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第87 页。
(27) 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10 页。
(31) 刘瑞复:《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读书笔记》第1 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120 页。
(34)《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年版,第34 页。
(35) 顾迁译注:《淮南子》,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286 页。
(36)[宋]王安石撰:《临川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78 页。
(37) 高华平等译注:《韩非子》,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759 页。
(38) 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22 年第5 期。
(39) 习近平:《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 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求是》2020 年第12 期。
(42) 黎翔凤撰:《管子校注》(下),中华书局2004 年版,第1196 页。